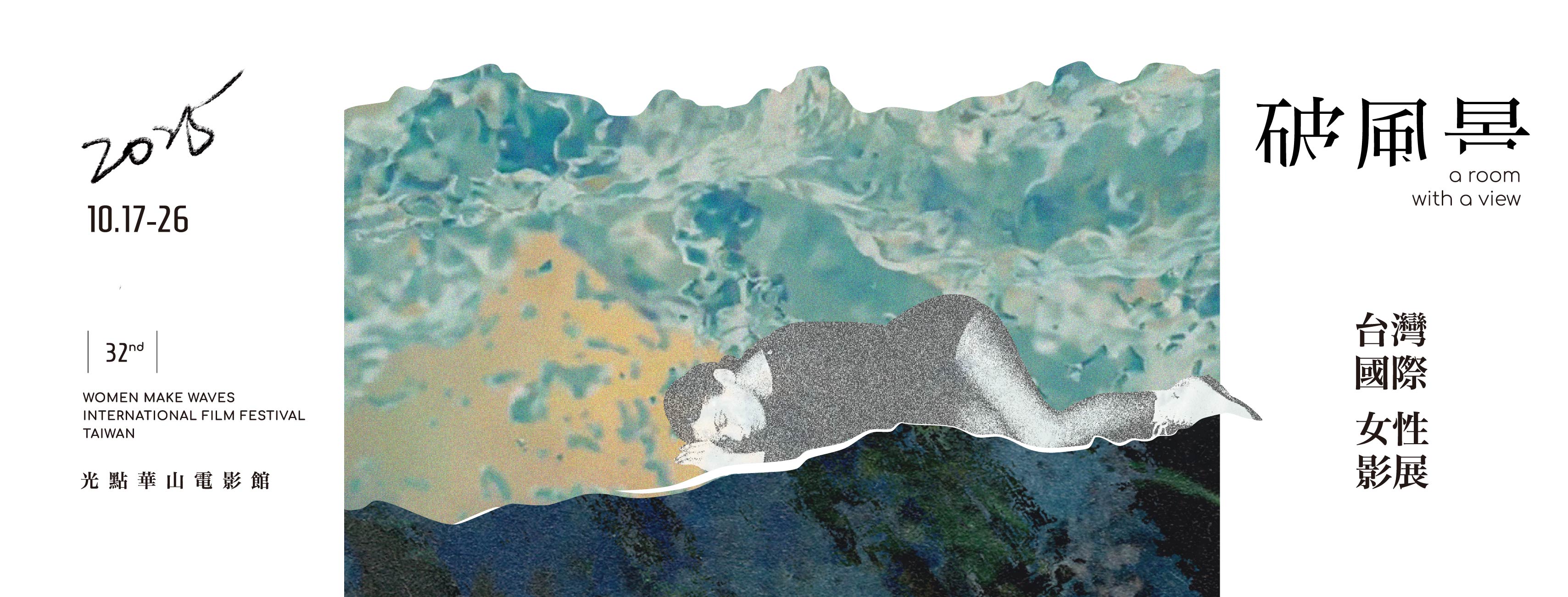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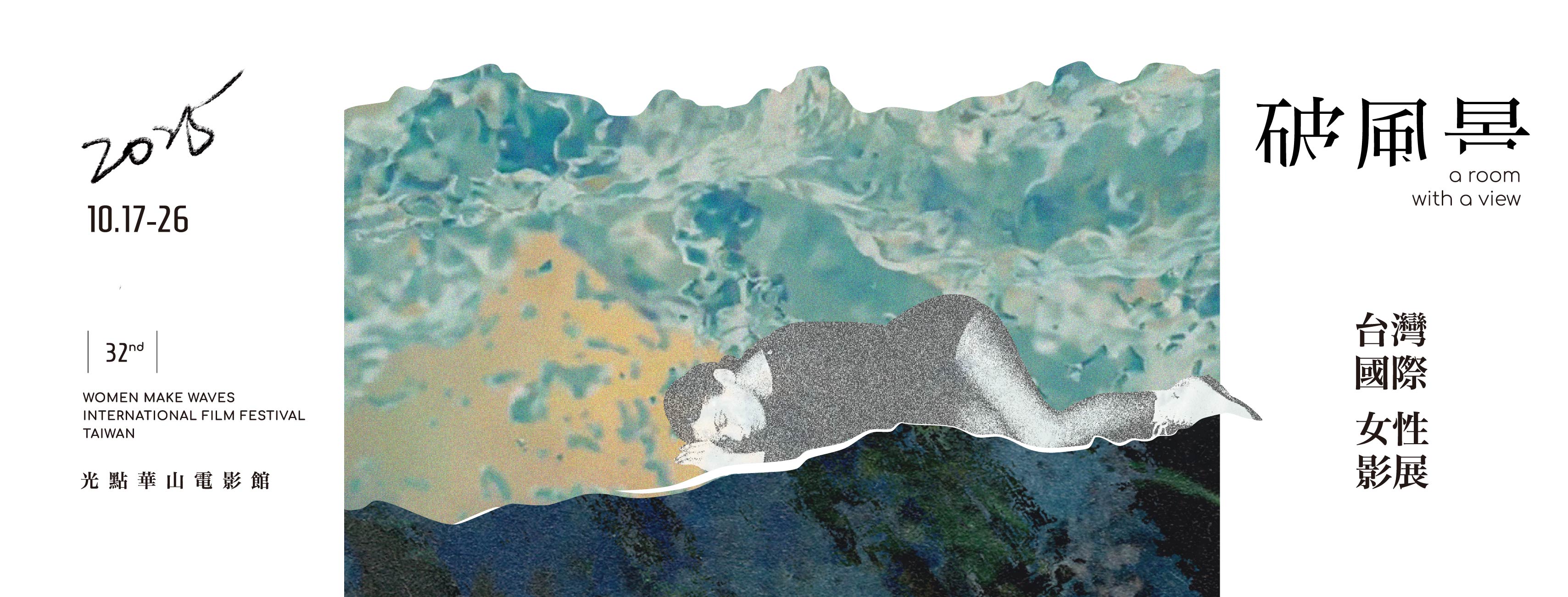
片名:《行動代號:躺》 場次:10/26(五)12:40 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謝以萱 與談人:導演 寶拉.杜里諾瓦 Paula ĎURINOVÁ 口譯:林若瑄 文字紀錄:周妙芊 主持人: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這部片的導演Paula ĎURINOVÁ來到現場,與我們進行映後座談。我自己非常喜歡這部影片,也看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有滿不一樣的收穫和發現。這部片子對我來講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雖然在講一個我們現代人都面臨到的「過勞」或「焦慮」狀態,但在電影語言裡,它留下了非常多的模糊或空隙,讓我們可以在裡面,不論發呆也好,或從裡面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與意義。 請 Paula 跟我們聊一下,她決定要拍這部片的契機,以及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她想要開始做這部作品? 杜里諾瓦:謝謝主持人的提問。這個拍攝計畫其實我已經進行了很多年了。最初是從我自身的過勞與倦怠經驗出發。後來我發現,我好像需要把自身經驗放進更大的脈絡裡,於是就開始讀一些關於人們過勞經驗的文章,特別是從政治層面出發去思考過勞這件事的文本。 在構思影片的過程中,我也有在柏林參與一些互助團體或意識覺醒(意識提升)團體。我們分享彼此的個人經驗,也特別從反思資本主義社會的角度出發。我那時候覺得,自己好像一直被制約,一直在怪罪自己沒有辦法跟上資本主義社會的步調,因此產生很多焦慮。我想把這樣的焦慮轉化到影片中,去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為什麼無法命名這種狀態?我想創造一個空間,讓我能找到命名這個狀態的語言。 我發現自己在製作這部影片的過程中,總是會回到最初影響我的那段文字。那個文本對我而言像是定錨一樣,縱然歷經多年的拍攝與不同經驗,我好像一直仍圍繞著那段文字。 主持人:可以追問一下是哪一段文字嗎? 杜里諾瓦:其實有三段文字,也都出現在影片當中。第一段是從敘事者的敘述中講出的,是從一本書摘錄的。 這本書是《Depression: A Public Feeling》,討論的是憂鬱症的一種公共性,或者說是一種共有的感覺。它想要講的概念是,似乎透過抒發自己的感覺,就能達到一種政治目的。簡單來說,是一本探討憂鬱症的政治性與社會性的書。書中也包含許多個人回憶與自述,也有分析性的文章。它深深影響了我製作這部片的出發點。當時,我對其中一句話特別有感:「我們好像都過於焦慮了。」書裡提到,焦慮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社會體制希望維持每個人都焦慮的狀態,而這種個人焦慮會讓我們覺得自己失敗。但當我們意識到這點之後,就能開始覺察自身狀況,並開始抵抗。 主持人:電影中有趣的地方在於,它呈現出一種非常個人的狀態,但同時又是集體的。導演在片裡做了一個有趣的對照處理,一段是人物集體談話的過程,另一段是街頭抗爭畫面的組合。我想請導演分享這兩種既私人又集體、同時帶有強烈行動主義與政治意味的片段,是怎麼處理的? 杜里諾瓦:我覺得結合私人與公共影像的想法,來自於我在柏林居住的經驗。這部片主要在柏林拍攝。我想呈現柏林這座城市如何被移民與酷兒群體逐漸改變。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以巴衝突、巴勒斯坦問題,在柏林街頭抗議的群體多是移民與酷兒。德國政府對抗議仍有些壓抑,因此這些人更想走上街頭,因為他們可能是失去最多的一群人。我想透過他們如何改變城市氛圍的過程,呈現城市中新記憶的形成。 在影片中,我也想探索記憶與經驗不斷被生成的感覺。在拍攝過程中,我注意到城市裡有些重複的事物正在改變與被記錄。我在這幾年也開始產生一些憤怒情緒,在互助團體中我們也討論了很久。一開始我想呈現憤怒、警察暴力的畫面,但後來覺得更需要拍攝人們如何集體思考抵抗的策略,以及(透過)更廣大的社會運動影像,呈現人們聚在一起思考如何改變社會與權力結構(這件事)。 Q1: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想問導演當初是怎麼找到片中四位角色的? 杜里諾瓦:第一個我接觸到的是Eliana,她是我好友。有一天她跟我分享過勞與倦怠的感覺,那天我也拍了下來。我們因而產生很深的連結,即使剛認識不久,卻很有熟悉感。後來我透過朋友認識另外兩位被攝者,他們都很喜歡這個影片的概念,也想透過分享個人經驗找到更大的命題。 這算是互助團體吧,我一開始邀請七個人,是一個比較大的團體,一起來互相討論這個題目,但後來發現這個比較大的團體氛圍沒有那麼好,運作得沒有那麼順利,因此後來是這七個人中留下四個人,形成一個比較小的團體。之後運作得比較順暢,我後來也加入了一些文本,讓大家一起討論、也有讓大家一起做一些練習。這些人之前是不認識的,是透過這個團體才認識彼此的。 拍攝互助團體的概念,也源於我在柏林參加一些團體的經驗。但是我那時候沒有想要直接拍攝我正在參與的這些團體,因為我覺得那好像是一個很入侵的事。主要是我不想要去破壞一個已經在進行的團體的氛圍,因此我才重新邀請一群人組成團體。好像從片中還滿明顯的可以看出來,我就是想要組成一個新的團體,然後在這個團體中,想要探討如何幫助彼此抒發、探討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拍攝,讓我們想要探討的主題更被呈現出來。 Q2:請問導演怎麼處理聲音?焦慮的感覺好像透過聲音特別明顯。第二個問題是,導演之前有說過剛拍完這部片時,好像沒辦法抽離去看它,但過了一段時間後,現在您再看有沒有不同感覺? 杜里諾瓦:我一開始看素材時,好像還滿直接的,就突然想到了一個音樂作曲家Lenka的音樂,便很想要把他音樂中的這種聲響放進去。我一開始也是想要玩一個概念,也就是讓有些聲音元素,像在這個片中經歷了一些成長跟改變。一開始有一些聲音,我想讓它們感覺是有點敵意的,甚至好像有點破壞性的。但漸漸的,我想讓這些聲音變成是它們能夠陪伴被攝者的。我想要玩這些聲音的層次(的過程),有點像是在創作,或可以說是再一次的改變,像是這些聲音漸漸能夠陪伴被攝者的感覺。 我在做聲音設計時,也想建構城市聲音。我上一部作品是關於大自然,那時候我已經建立好一個大自然的聲響,但這部片是城市,所以這次我想建立城市聲響。我後來就覺得,我想要從比較主觀、個人經歷城市的這個方式出發,片中聽到的聲音,可能是這一位被攝者他感受到、他聽到的聲音,不見得是客觀城市環境中會出現的聲音。有些也可能是他記憶中場景的聲音,在某一些時刻那些聲音又跑回來。 我在今年上半年密集剪輯這部片,同時製造出新的影像跟新的聲音,這個過程是非常有流動性的。但是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快速的過程,那時我和剪輯師Deniz一起合作。我們合作的方式很好,但那時真的是時間很緊迫,我好像無法好好的沉澱下來,思考這些影像跟聲音,要做什麼更深度的的串接。 那我覺得這部片可能有十種以上的、不同的路徑跟可能性,但我在剪輯的當下,因為時間緊迫,沒辦法去探索那麼多的可能性。很多決定都已經定好了,好像也只能這樣下去。現在回頭看,當然比較冷靜下來了,我也覺得當初的決定好像其實是對的,對於那時的工作過程,也覺得滿開心的。對於我如何找到自己的電影美學,在這個過程也教會了我很多。 Q3:請問導演在創作過程中,對於男性與女性兩者在憂鬱的這個集體性,或政治性上,有沒有發現一些特別的觀察跟差別?為什麼在片中,我們可能看到的是女性的觀點居多? 杜里諾瓦:對於男性跟女性如何去經歷,或是感受憂鬱的狀態有沒有什麼不同,我好像很難下註解。對我來說很難去辨識,但在影片中,正如您所說的,我的確好像採取了比較多女性跟酷兒族群的觀點。 對我來說,這個過程是滿自然而然發生的,因為我當初就是想要一些能夠傾聽他人、能去深刻自省的一群人合作。尤其是,對於我們「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如何被影響」,已經有一些省思的人。好像很自然的就找到了女性跟酷兒,或許是個我沒有意識的決定吧。 我那時還覺得,我必須要去探討大家共同感受到,「正在失去一種主控權」的感覺。而我認為這種失去主控權的感覺,當然也可以發生在各種性別的身體,也可以是男性的身體。片裡團體中的Sam是一位男性,他會加入是因為他有很深刻的、更多關於憂鬱症的經歷。對我來說,好像很難去回應,男女經歷這件事情有什麼差別,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希望加入這個片子的人,都是有能力去反思以及傾聽彼此的人。 最後我想要謝謝各位觀眾來,也想要謝謝女影邀請我。我覺得剛才跟大家一起看這個影片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好像跟大家也產生了一些連結,謝謝。
片名:《然而餘音未葬》、《犬靈之詩》 場次:10/26(日)14:3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方念萱 與談人:《然而餘音未葬》導演 尤莉亞.諾瓦切克 Julia NOVACEK、《犬靈之詩》導演 彭.邦塞姆維查 Pom BUNSERMVICHA 口譯:林若瑄 文字紀錄:鄭羽妡 主持人:在座各位大家好,午安,我是方念萱,是這一屆女影學會的理事。很高興兩位影片導演在這邊。在開始之前,先請兩片的導演來跟大家打聲招呼。 彭、諾瓦切克:謝謝大家今天來看片,很高興能夠回應各位觀眾的問題,也很高興看到很多人留下來聽映後。 Q1:請問Julia導演,為什麼想到要把鋼管舞和《然而餘音未葬》所表現的主題結合起來呢? 諾瓦切克:我剛開始規劃這部片時,就一直都對「表演性」很感興趣──就是我們如何在社會中表演跟展現自己。像大家看到在片中有用身體去展現哀悼、用身體去抗議,我覺得這個概念它其實一直在演變。 在我的創作過程中,後來加入了鋼管舞,對我來說它對於跳舞的女性,也是種自我賦能的方式。片中的這個鋼管舞舞者,她也是黑衣女性(Women in Black)組織中的一份子,但鋼管舞對她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自我展現的方式,也是她讓自己感受到有力量的方式,不管是身體上的,還是心靈上的力量。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要加入鋼管舞片段,是後來認識了這個(鋼管舞)舞者後,才決定來發展這個概念的。而我也一直都覺得,思考如何運用自己的身體表達以及抗議,是非常重要的事。 Q2(主持人):請教一下導演Pom,我很好奇在《犬靈之詩》完成之後,您的家人有沒有機會看到這部作品?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在影片介紹裡提到,導演這部自傳性的影片,起因部分是來自於妳與你的父親在家中不交談。 彭:我全家人都有看過這部片,爸爸也看過了這部片。對我來說,當我爸看到這部片的時候,我覺得這部片已經是完成度很高了。 我創作這部片的過程蠻長的,大概有三年的時間,從編劇開始,接著跟演員工作,後來剪輯、又再次剪輯。我覺得這部片在這整個過程中,經歷了很多的演變,那我的父親好像也在這過程中,消化了一些事情。當他第一次看到這部片的時候,他也需要一個消化的空間跟過程。 我爸看過片後,我從來沒有跟他談過這部片,他也從來沒有想要跟我談。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一開始我想要拍這部片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辦法跟我爸溝通,但是我爸看完片之後,我們也還是沒有溝通。但我總感覺好像在(製作)這部片的過程中,我們的關係有一些改變了,我認為是一個蠻正向的改變。 Q3:想問Julia導演,哭喪女參與Women in Black(黑衣女性)活動,她們是想要主張什麼東西呢?我對這個國家(巴爾幹地區)的歷史和正式情況沒有很了解。 諾瓦切克:像在《然而餘音未葬》中看到的抗議場景,它其實是雪布尼查大屠殺的紀念日抗議,這個大屠殺是九零年代在巴爾幹地區一個很大的戰爭犯罪事件。她們主要是在抗議,賽爾維亞這個國家或賽爾維亞的媒體至今沒有正式、甚至不談論這個大屠殺。也因此,很多國人根本不知道這個大屠殺曾經發生。 在片中也有看到,她們在抗議的時候,現場有些人對她們有語言與肢體的攻擊,因為很多人其實根本不承認這件事情(雪布尼查大屠殺)有發生,但這件事是確確實實發生的。當初有一些參與這個大屠殺的軍人,他們甚至在國際法庭上有受審,也被定罪的。 我覺得這一群女性她們主要抗爭的是,希望這些罪行被正視、希望大家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事。她們其實也有跟整個巴爾幹地區的其他女性主義組織合作,希望一起去記憶以及療傷。 主持人:補充一下,在臺灣的媒體部分,風傳媒曾經有幾篇報導特別是有關於雪布尼查大屠殺。在這場大屠殺當中,大家記憶的是8000名成年男性被屠殺,但是其中大概有約30000以上的父母其實是被驅趕,性侵的犯罪更是多。這個是臺灣我們可以看到國內中文的一些相關報導,如果觀眾朋友有興趣可以去查閱。 Q4:想針對剛才Women in Black(黑衣女性)的問題,稍微追問。我的理解是,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網絡,最早的時候2000年初期,在以色列就有以色列的女性Israeli Women for Palestinian(以色列女性為巴勒斯坦人)的這一個行動。Women in Black(黑衣女性)在國際上,有個意義是peace(和平)、no violence(非暴力)、 against the wolrd(對抗世界),它不只是一個國內議題,還有一個跨國維度。 我覺得跨國的維度放在南斯拉夫的政治裡,顯得很微妙,因為這麼複雜的族群背景,而且南斯拉夫今天已經是六個不同的國家。所以我不太知道Julia導演當時要處理這個議題時,有沒有考慮過處理這個層面? 諾瓦切克:你剛剛講的完全正確,Women in Black是國際性的組織沒錯。 對於貝爾格勒地區來說,這個組織是大概在八零年代末期、九零年代初期成型的,很多你看到的片中女性,她們是一開始就參與,並持續參與了三十多年。這一群女性都是很好的朋友,她們每週都會有抗議的活動,還曾經被提名領諾貝爾和平獎。 但我覺得我想要講的,好像也不是這個地區的政治複雜性,因為對我來說,我沒有巴爾幹半島的血緣,我是奧地利人,我好像沒有立場去好好的訴說這段歷史。我覺得我的焦點會是在這一群女性上,(去看)她們有多勇敢去爭取她們的權益。 我也很想要去找尋哀悼跟政治行動之間的連結。我跟我的剪輯師密切的合作,我們想要試圖在片中去突顯這個連結,也想要看到,是否家庭的關係也可以在這個連結中被展現。比如說鋼管舞的舞者,她的祖母曾經是哭喪女,然後祖母的女兒,也就是她的母親,後來也成為黑衣女性。好像這樣世世代代下來的連結,其實是可以延續的。我主要是對於這樣子的政治行動、哀悼以及自我展現的形式,怎麼樣世代的傳承下去很感興趣。 Q5(主持人):兩位導演的作品當中都提到元素「黑」,《然而餘音未葬》的黑衣女性是一個;在Pom的《犬靈之詩》中,影片後面大家瞪視著岩縫,那一段時間很長,頓入一個黑暗當中。想請問一下,導演在最後那個部份的處理,當時在設計的時候有沒有哪一些考量? 彭:我可能要先解釋一下那時候創作的背景。 我那個時刻好像不太能夠跟我爸溝通,感覺到非常多的痛苦。當時我想嘗試去尋找一個我跟我爸如何能夠產生連結的方式,因為我跟我爸非常不同,但我還是很想要跟他產生連結。 在寫《犬靈之詩》劇本之前,我其實已經寫好了這一場洞穴的戲,這場戲我想要探討的就是迷失、走失的感覺。同時,也想要探討兩種不一樣的空間,是不是能夠呈現兩種不同連結的可能性。像片中看到的旅館場景,它就是一個非常人工的空間,每個人在這樣的空間,好像都會展現自己應該要展現的樣子,但是我們來到了另外一個空間的時候,可能層層社會化的自己就會被脫去。 我當時很想要建立(關係),不管是我個人跟我父親的關係,還是片中女兒跟父親的關係,我希望他們兩個可以找到方式去跟彼此產生連結。剛才提到的黑暗,在黑暗中呈現角色的方式也不是我一開始設計好的,是當初我們在拍攝的當下,我們架好了燈,然後我的燈光師就跟我一起在現場找到了呈現角色的方式。我的剪輯也在後製時,幫我在這個場景(洞穴)中,找到一個我想表達這個概念的方式。 另外還可以提的是,除了旅館的空間外,我也想要找一些另類的空間,像是廟宇、洞穴。我認為這些空間好像比較超乎日常,也許可以在這些空間中,讓父女找到跟彼此連結的可能性。 Q6(主持人):如果用空間來說,我想請教Julia在《然而餘音未葬》當中有一段,是哭喪女到她先生的墓前用吟唱表達哀傷。在影片前段,我們也看到按照習俗,哭喪女她是可以去哭兄弟、去哭不認識的人,但是獨獨不能夠為自己的伴侶而哭。想知道在習俗跟傳統之下,拍下哭喪女為伴侶而哭會有任何困難嗎?導演的處理有沒有特別的用意? 諾瓦切克:在片末看到的哭喪女,她去自己的先生墓前哭泣,那個女性是從蒙特內哥羅搬到了賽爾維亞北邊。她原本居住的山區比較傳統一點,但她六零年代就已經移民,也就是已經移民蠻久了。她在表演公共的哭喪前一年,她的先生過世了。那這個地區的傳統是在先生過世的一年間,不能公開的哀悼他,但是一年之就比較ok了。 我們拍攝的時候,其實並不知道這位女性會直接在墓前哭喪。 在那之前,我們認識她已經有五年之久,常常去探訪她,同時也認識了她的先生。她後來告訴我們她先生已經過世了,我就提議我們一起去墓前拍攝,而拍攝當下她突然哭喪起來了。那我們當然就覺得,「哇!我們一定要拍」。拍完之後她也認為這一段畫面應該要送給我們,像是一個禮物吧!因為她的先生生前也非常喜歡我們。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堅強的女性,她也沒有那麼在乎一些傳統的限制。 對於哭喪的文字,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這些幾乎都是即興發揮的。也就是這些哭喪文它從來不是被寫好的文字,是當下哭喪的女性她們自己油然而生的文字。 Q7:想問Julia導演,《然而餘音未葬》裡面有一段是,鋼管舞舞者說:「當你的動作比較慢一點的時候,可以讓人感覺到你的故事和你的情感。」因為這部片跟女性主義有些關係,很好奇導演是怎麼看待藝術和倡議之間的關係? 諾瓦切克:這是一個蠻大的提問。對我來說,我在片中特別想要探討的,就是這個群體能夠在一起展現的事情。我認為在一個變動的、動盪的政治跟社會中,我們就更需要彼此的支持、需要其他人加入我們的行動──這個行動可以是藝術性的、也可以是政治性的,或是兩者兼容的行動。我覺得這兩者好像沒有到那麼的分開,總是可以相輔相成。
片名:《萬歲家庭》 場次:10/25(六)19:2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羅珮嘉 與談人:導演 吳念樺、 製作人 蔡崇隆、剪輯師 黃懿齡 文字紀錄:楊昀鑫 主持人:謝謝大家在這十天的影展期間選擇來看《萬歲家庭》這部片。不管是從個人的經驗,或是透過攝影機、紀錄片的方式來探索自己的心路歷程,這都是一部有很多層次可以討論的片子。裡面的親子關係,或是導演個人的創傷經驗也好,都或多或少喚起、勾起我們每個人對自己家庭的共鳴。 今天很難得,我們也請到念樺導演,歡迎妳!現場也有幾位參與這部片的劇組人員,我們也邀請他們一起上台──製作人蔡崇隆導演和剪接師黃懿齡。大家對崇隆導演應該不陌生,他是《九槍》的導演,而在這部片中擔任製作人。等一下也可以請他聊聊這次的參與。我會先提兩個問題,再開放給大家提問。 從片中可以看出,拍攝的動機似乎和父親有關,是因為五年前爸爸的出現,才開始這段拍攝的旅程嗎?先請導演聊聊這個契機。這過程橫跨八年,從開始梳理到妳願意去碰撞、面對自己,應該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氣,也會伴隨不安和焦慮,而且還要用鏡頭來抓住。請先跟大家分享,當初是怎麼鼓起勇氣、下定決心開始拍攝的? 念樺:當然我生父多年前再度聯絡,也是一部分的原因。但我覺得真正想拍攝的契機,應該是有一年年初和媽媽有一場比較重要的談話。她跟我分享她的故事之後,我才發現自己有很多其實還不夠了解她的地方,因此才正式決定在那個時候開始拍這部片。 主持人:一開始拍攝時,媽媽對這件事的反應是什麼?妳剛提到那場談話某種程度上很親密,但親密中又可能帶著衝突。加上現場還有攝影機的存在,妳又是如何和媽媽溝通(要拍她的)這個部分? 念樺:好像比較不是一個「說服」的過程。有次媽媽來找我時,我就順勢拿起攝影機,說想記錄下我們相處的畫面。所以大家在片中也會看到,我其實一直都有出現在鏡頭裡面。那也是我真實的想法──一方面想留下家庭的影像,後來慢慢也越來越清楚,自己想講的故事是什麼,就開始和媽媽討論。 我會問她:「如果我想拍這個、講這段妳覺得怎麼樣?」一開始她其實不太習慣,會覺得:「幹嘛拍這個?這要幹嘛?」但後來也蠻有趣的,我媽有時候反而會主動說:「這時候應該要拍啊,怎麼不拍?」(觀眾笑) 主持人:在整個拍攝過程裡,媽媽跟妳一樣,也都在面對、融入這個過程。令人好奇的是,在影像或溝通上,有沒有真的得到某種療癒?或是因此讓家庭關係更親近、更圓滿?妳們現在的狀態又是如何? 念樺:我覺得這個拍攝的過程,或者說這個故事,其實是我內心想講的一個秘密。但我覺得真正有幫助的,應該是我、姊姊、還有媽媽之間的關係。在拍攝過程中,有一部分是因為我想多拍一些東西,所以回家的頻率變得更高,但同時也是真的想知道,自己這七、八年不在家的時候,家裡發生了什麼事。經過大概兩年多的時間,我覺得和姊姊的關係變得比較親密,跟媽媽之間也更能互相理解。 主持人:接著請問崇隆導演。你這次的身分是製作人,算是念樺的老師嗎?因為她在片中既是導演、又是被攝者,你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提供一些協助,比如拍攝的距離、角色的拿捏上如何處理的建議? 崇隆:我跟她的關係其實有點複雜啦(笑),因為我們很早以前,念樺還是記者的時候我就認識她了。老實說,我也不太確定為什麼她會找我當製作人,這可能要問她。 我想等下還是讓導演多分享一些,觀眾也可以提問,我就先簡單講一下,從製作人的角度來看這部片。我覺得像這樣的家庭紀錄片,其實比我拍《九槍》還難。因為最親近的人,往往是最難理解的,更何況你還要去拍她,讓她成為影像。 我也曾經想過要拍我媽媽。她生前我拍過一些畫面,但一直到她過世那麼久了,我還是沒有勇氣去碰那些影像。所以我覺得「家庭紀錄片」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題材,它屬於一種私領域的創作。 我記得念樺找我聊這部片時,講到她跟媽媽的故事。我那時候就想到,像很多人應該也看過的《日常對話》、《神人之家》這類作品,要達到那樣的層次其實不容易,因為家庭的議題很難。我們在面對社會議題時,可能還能對外發出控訴,但在家庭裡,你很難「指責」誰,就像有句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不論是婚姻還是親子關係,都是這樣的複雜。 當時我給念樺的建議,是希望這個故事能找到一些更普世的人性價值,不要只停留在個人的創傷或經驗裡。而這部片有趣的地方是,它一開始像是在尋找造成童年創傷的「兇手」,但看下去你會發現,其實不是在找某個人。 片中外甥講了一句話,我覺得特別動人──他說要「找心上的大野狼」。那個「大野狼」到底是誰?也許是人,也許是心裡的一個象徵。但我們都能感受到,導演和媽媽之間有非常強烈的愛,只是這份愛是透過一種帶刺、帶掙扎的母女關係呈現出來的。很多家庭關係其實也是如此,親密中帶著傷。我自己看這部片很多次了,雖然早就知道這個故事,但在大銀幕上看還是覺得很動人。我相信很多人也會從中得到共鳴或某種啟發。 最後我想說,我真的很想給念樺和她媽媽一個鼓勵。如果沒有她們兩個的勇氣,這部片是沒辦法完成的。她們願意把自己這麼真實的一面呈現在觀眾面前,那需要非常強大的心臟。我希望大家在看完這部片,也能把正能量回送給她們。 主持人:謝謝他們兩位(念樺及媽媽),真的很需要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因為像這樣所謂的「私電影」能夠呈現在大眾面前,其實非常不容易。某種程度上,要打開自己最赤裸的一面。也謝謝崇隆的分享。 想延伸一個問題。因為這部片其實談的是「撕裂的關係」,我看到有專訪提到,念樺原本是想自己剪這部片,但後來在老師建議下,決定找懿齡來剪。某種程度上,這也讓作品多了一個旁觀的角度。能不能請妳聊聊這個決定? 念樺:在很前期的時候,我原本真的想自己拍、自己剪。因為那時候根本沒有任何經費,也不覺得能找人一起做。但後來遇到蔡導幫忙後,他就非常強烈地建議我一定要找剪接師。 崇隆:根據我自己過去的經驗,包括我自己的片子在內,都發現導演在拍攝跟剪接時很容易有盲點。一個好的剪接師能帶來第三人、新鮮的視野與觀點,通常也都會讓作品更完整。因此,我才會強烈建議念樺,不管有沒有預算,都一定要找剪接師。而懿齡又剛好是對這類題材很有經驗、也很細膩的剪接,我們對這點也都很有共識。 念樺:對。後來就很榮幸可以邀請懿齡。 懿齡:一開始是蔡導先找我,說他有個朋友在拍紀錄片。我問了一下背景,結果發現我們都是屏東人,而且她還是我屏東女中的學妹,雖然差了好幾屆(笑),但覺得挺有緣的。她剛開始拍片的時候剛好是過年,我們人都在屏東,就約出來聊一聊,聊得滿投緣的。後來我就說:「OK啊,我可以幫妳剪!」 Q1:導演好。謝謝你帶來這麼精彩的家庭紀錄片。我有三個問題想請教,這三個問題都比較私密,如果有不方便回答的部分沒關係,這只是我看完後心裡的疑問。 導演在影片前半段提到「家暴的記憶會讓你有一種扭曲的感覺」,但後面似乎沒有再多談這個「扭曲」。請問這個扭曲是指記憶的扭曲,還是在人際或親密關係上的扭曲? 念樺:我指的「扭曲」是我自己性格上的扭曲,或者是我理解童年記憶的方式,有時會覺得矛盾,又懷念、又不想回顧。 Q2:關於「姓氏」在父權社會中的位置,導演以「吳念樺」這個名字,用的是父親的姓氏來呈現作品。有人也會認為,即使從母姓,母親的姓也是外公的姓。我很好奇,在這樣的家庭經驗中,導演如何看待用這個父親姓氏來呈現這部私人紀錄片? 念樺:我其實有問過媽媽要不要改成她的姓。她小時候也有考慮過要幫我和姊姊改姓,但後來沒有。後來我就覺得,這就是我的名字,所以作品名也就直接用本名。 Q3:導演在與父親重逢時,已經是以大人的身分面對童年缺席的父親,而非以孩子的角度。想請問導演對這樣的相遇,有沒有更多的想法或感受可以分享? 念樺:關於和生父見面。那時候(看到他)就覺得:「喔,原來真的有一點像。」也發現見面這件事其實沒那麼困難。小時候的我總覺得那是一個永遠不會見到的人,但當我真的去做了,就發現也沒有想像中那麼難,對這件事也就沒那麼有懸念了。 Q4:片中有拍到妳和父親互動的過程,我很好奇父親是怎麼看待妳想記錄這些過去的回憶?在拍攝時有沒有感覺爸爸說話時有「表演」的成分?他在某些話題上會不會刻意迴避,或在他感興趣的話題中會願意多講一些? 念樺:我覺得只要有鏡頭在現場,無論是我還是被拍的人,多少都會有不同的展現。就像你和朋友吃飯時,如果突然擺上一台攝影機(大家可以自己試看看),一定也會有人開始「表演」。所以我想那種狀態多少還是會出現。 Q5:導演和姊姊對童年創傷的記憶似乎有些不同,請問妳怎麼看待這樣的差異? 念樺:我和姊姊的部分,這其實也是我在片中想表達的感受。我很愛我姊姊,也能理解她,但同時又不太能理解為什麼她的記憶跟我不一樣。不過我也相信她真的「忘記了」。這也是我拍這部片的原因之一,想讓自己學會接受,她的記憶和我的不一樣。 Q6:導演好,首先真的非常開心,也恭喜你完成自己的作品。我在看到第一顆鏡頭的時候就泛淚了,因為整段故事與回憶和我自己的經驗其實蠻重疊的。再次恭喜你。請問在剪片過程中,因為妳需要處理大量素材,也得面對自己過去的回憶。想知道妳是怎麼處理這些情緒或感受的? 念樺:剪接的過程是跟懿齡一起完成的,所以等一下懿齡也可以分享。我先講我自己怎麼處理這些情緒好了。常常是懿齡剪出一個新版本,我看了之後就在家大哭(笑)。明明是我自己拍的東西,但當它被轉化成故事的時候,那種感覺完全不一樣。片中我一直想回顧一些記憶,想抓著我媽和我姊說:「我明明就是這樣啊,為什麼你們都不記得?」可是當我越問,越接近那些我原本不知道的部分時,又會很想去做像是催眠,或找什麼能消除記憶的診所,把某些不想再記得的片段抹去。那應該就是我情緒最衝突的時候,但好像也沒有什麼更好的化解方法。 懿齡:目前還沒有特別想到要怎麼說。對我來說,我本身不是那種會去追根究底家庭關係的人,我的想法比較是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我覺得念樺真的很勇敢,那些事情一直在她心裡,她覺得自己必須把它處理好。至少在我看來,當她和媽媽、姊姊三個人一起面對這些事時,她才有辦法往人生的下一個階段走。這部分跟我不太一樣,也因此我特別佩服她的勇氣。 在剪接過程中,因為我看素材的角度跟念樺不同──她背後有二十幾年的情感累積,而我不一定能完全理解那種感覺。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沒有被拍到的部分」,目的是希望觀眾不會誤解我們呈現的內容,同時也想保留「記憶本身的曖昧性」。因為我覺得,即使是面對你最愛的人,記憶也不一定是可靠的。愛可能是真的,但記憶未必如此。這就是我們在這部片中不斷來回思考的主題。 最後我們有給雷姐(雷震卿)看過,她有點像是幫我們「定錨」的角色,確認我們應該往這個方向走。最終成品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完成的。 主持人:可不可以多描述一點「沒有看到的那些部分」是什麼? 懿齡:因為念樺是拍攝的人,所以她的感受非常明確。可是像她的媽媽、姊姊,甚至生父的情緒,我就會一直問她,確認那些部分。我要確保我從素材裡看到的東西,和她在現場感受到的,或者她之後跟家人談話時的感覺(一致)。雖然不可能完全一樣,但至少要確定方向上不會背離。 Q7:想請教導演父母看完這部片後的反應是什麼?另外,片中呈現了每個人記憶矛盾的地方,我覺得這部分處理得很成功。那你自己又是怎麼消化或看待這些記憶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部分呢? 念樺:我的生父應該還沒看過片子,因為他人在澎湖,但我有傳一些他的片段給他看,他就覺得OK。我媽媽之前看過,但她可能不太記得全片,所以今天又再看一次。她的感受,就看她想不想分享,或我回家再問她,她不一定想在這裡分享。 至於記憶不一樣這件事,我不是拍攝的時候才知道。以前我和姊姊就常因印象不同而產生不理解,所以早就知道我們的記憶會有差異。剛開始,我會對她有點生氣,希望她的記憶和我一樣,也會覺得我們是姊妹,又同時在現場,所以(記憶不同讓我)感覺自己被誤解。 隨著成長,我的想法慢慢改變。拍攝過程中,有了團隊夥伴加入,我也聽到不同的觀點,這對我理解和看待這些記憶非常有幫助。 崇隆:這部分我也特別想補充。我剛剛有提到我之前是記者,也許每個人的經驗不同,但就我過去的觀察,我們常常以為只有政治或司法領域才會出現「羅生門」式的狀況、才會有人說謊。可是在看這部片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家庭裡其實也充滿羅生門,而且這其實是很正常的事。不能以為那只是政治或社會事件才會發生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人的記憶真的很有限。像我自己就常常會忘記一些讓我不舒服的事情;但也有人恰好相反,會永遠記得。這不是誰故意或不故意的問題,只是每個人的特質不同。這部片對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我會開始回想自己的家庭經驗。很多時候,我們和親人爭吵,可能就是因為記憶不同。雙方都以為對方在說謊、或故意扭曲事情,但其實只是記憶差異。 念樺在片中很細緻地訪問每一個家人,我覺得這讓人重新思考「誰說的是對的」這件事。或許根本沒有誰在說謊,只是記憶本身就不一致。這也讓我覺得,家人之間如果能理解並接受這一點,彼此的寬容度也許會更高。我們常對最親近的人期望最多,覺得「你應該最了解我啊,為什麼還會說錯?」但有時候,真的只是因為記憶不同而已。這是我從這部片中得到很深的啟發。謝謝。 主持人:是啊,正如剛剛老師提到的,其實記憶不同,也沒關係。 念樺:在處理片中不同觀點時,我一開始其實很猶豫。像有些片段,我和姊姊的說法非常兩極,就一直在想,那些要不要放進去?我擔心觀眾會覺得我瘋了,或者反過來覺得我姊姊也瘋了。那種「別人會怎麼看我們」的焦慮其實很強烈。 後來剛好有一個版本完成,我們給雷姐(雷震卿)看。她鼓勵我們保留那些片段,也讓我感受到她有理解了我對「記憶不確定性」的那種不安。她說,那種「明明記得卻被大家說沒有」的感受,是最難被接受的,而這份矛盾正是作品的核心。那一刻我覺得,好像有被理解的可能。於是我跟懿齡討論後,決定還是把那些片段留下來,呈現那個記憶模糊卻真實的狀態。 懿齡:對。我記得我們剪的時候,我有提醒念樺,這部片未來上映之後,可能會有很多人看不懂妳想講什麼。可是她那時候回我一句話,讓我很感動——她說:「沒關係,其他人不理解也沒關係,只要媽媽和姐姐能懂就好了。」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也代表這部片的價值所在。 Q8:看了妳們家庭的故事,發現父母的感情真的會影響子女,我也能感受到你心裡的那份創傷。經過這樣的拍攝與了解之後,妳覺得自己能釋懷了嗎?對未來的生活,會有什麼改變嗎?覺得自己會更開心快樂嗎? 念樺:謝謝提問。我覺得雖然片中呈現了許多關於童年傷痛的記憶,但同時我也從這些經驗裡獲得了很多成長的養分。我的快樂其實也同樣來自這個家庭——媽媽和姊姊也是形塑我今天這個比較正面、開朗性格的重要部分。 我想,我在這個家庭裡曾受過傷,也確實留下了一些創傷;但同時,現在的我能夠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並在成年後以比較健康的心態生活,我覺得那份力量也同樣是從這個家庭來的。 主持人:對啊,說得很好。其實在女影這個平台上,我們並不要求每個人都一定要「正面快樂」。更重要的是,願意不斷透過作品與自己對話。 天非常謝謝大家,也再次謝謝製作團隊。
片名:《酷兒解放曲》 場次:10/25(四)12:2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謝以萱 與談人:導演 曾憶雯 口譯: 林若瑄 文字紀錄:周妙芊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女性影展選片人以萱。今天非常開心,可以在這個週末跟大家一起在這觀賞《酷兒解放曲》。也非常榮幸,我們邀請到這部片的導演曾憶雯來到現場。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她。 首先請導演跟我們分享,她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開始接觸這個題材,並認識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的這些主角?因為憶雯本身比較是記者的背景,也很好奇,她如何從比較偏新聞傳播的專業,轉移到紀錄片的拍攝。 憶雯:大家好,我是導演曾憶雯,我來自馬來西亞。我的背景其實是紀錄片製作,後來才成為一個新聞記者。我認識這個團體是在 2017 年,我有一個同事的妹妹曾經參加這個樂團,我就透過他認識了。 主持人:認識樂團後,是在什麼情況下覺得要開始拿起攝影機拍攝他們?其實紀錄片拍攝了很長一段時間,至少從畫面看起來是從 2018 年一路記錄到現在。是在什麼時間點你開始覺得想把它變成一部紀錄片? 憶雯:我開始想要拍攝這個樂團,大概是在 2017 年的時候。那時,我其實只是想要拍一個很好玩的音樂紀錄片。當時我正在柬埔寨金邊參加一個紀錄片的工作坊,也在工作坊上認識了我的共同製片。那時我看了一部紀錄片,它拍攝了一個柬埔寨樂團「柬埔寨太空計畫」(The Cambodian Space Project)。我覺得那部紀錄片非常酷、非常好玩,我也想拍一個很酷、很好玩的紀錄片。 主持人:所以妳就開始帶著攝影機,跟著我們在電影裡看到的幾位主角,進入他們的生活?因為片中有不同的人物,很好奇妳怎麼做選擇。樂團身邊也有一些(酷兒)社群的朋友,你是怎麼挑選這些主角的? 憶雯:其實一開始拍攝的三位主角是同時間展開,我花的時間差不多,都是同等的時間拍他們。而且一開始我拍Faris拍得比較少,大概到第二年的時候,才漸漸覺得他好像是主角,於是開始拍他的畫面更多。到剪輯階段,我慢慢剪、慢慢認為Faris應該是這部片的主角。 Q1:我想請教一下這個樂團現在的狀況如何?還有,因為主角是公開出櫃的,會不會在這樣的政治或法律環境裡面,遇到比較多的國家暴力? 憶雯:第一個問題,樂團現在如何?Yoyo ,那個貝斯手成員離開之後,還有另外一位加入,所以他們還有繼續在營業。第二題是問說Faris是公開出櫃的跨性別男性,會不會面臨政治上的風險?其實是有的,一直都會有風險。 Q2:謝謝導演的電影。我有一個問題關於成員,他們似乎有不同的性取向,有跨性別、也有 lesbian,也有些看起來是異性戀。片頭兩位異性戀成員表示,他不反對 LGBT rights,但覺得像婚姻這類訴求可能「要得太多」,其中也有宗教壓力與公民權等問題。我想問的是,如果成員的政治觀點與性取向都比較多元,那他們在日常生活或表演時,是如何處理彼此之間的分歧? 憶雯:如果想知道個別成員對議題的意見,可能還是要問個別成員比較好。我唯一可以說的是,整個團體的認同是,他們是「酷兒團體」。 Q3:在片尾有看到一位剪輯師的名字Takeshi Hata(秦岳志),很好奇導演是怎麼認識他,並邀請他合作的? 憶雯:我在 2023 年參加「Docs by the Sea」印尼紀錄片剪輯工作坊,於是認識了Takeshi Hata。後來我們在剪輯過程討論是否需要顧問,製片 Mandy 提議問問看Takeshi願不願意,他很高興地答應了。 Q4(主持人):接續剪接的問題。可以看到,片子跟馬來西亞的政治現況有很緊密的關聯,樂團唱的音樂也非常具有政治性。導演是如何思考人物的情感描述的比重?以及跟可能政治的一個氛圍之間,妳怎麼去拿捏?尤其是當這個剪接的素材有這麼大量時,又如何跟剪接師做討論? 憶雯:我拍完這個團體去歐洲巡演之後,本來以為片子已經拍完,以為這部紀錄片就是關於他們巡演的生活。但後來在 2018 年,遇上馬來西亞 61 年來首次政黨輪替,那一年又發生了很大的事件,有一對女同志回到法庭接受鞭刑,接著又遇到全球疫情。馬來西亞在這幾年間經歷非常多的政治動盪,我慢慢覺得這部片會漸漸長成,一個樂團回應政治改變的過程。後來,我也覺得把政治背景加入很重要,因為政治環境會影響我們每個人。 Q5:想請教這部片是否能夠在馬來西亞放映?如果不可以,那馬來西亞的觀眾要如何看到這部影片? 憶雯:這部片沒有辦法在馬來西亞放映。除了對被攝者是很危險的事,對整個拍攝團隊、整個酷兒社群都很危險。甚至對於片中出現的場館,對那些場館經營者也有風險,因為我知道馬來西亞的警察已經開始注意這些場館。當然,也知道這部片還是會在一些文化單位,甚至像大使館這種地方放映。不過,馬來西亞的朋友還是可以去新加坡看,確實有蠻多馬來西亞朋友會到新加坡看電影的。 Q6:我很少看到馬來西亞電影,在這部片中,看到很多感覺不是馬來西亞當地人的臉孔。請問,是因為曾被殖民的背景,他們還留在馬來西亞,或是用其他方式移民去那的?是這些因素讓當地文化如此多元,還是他們對 LGBT 特別有興趣,所以會參加這樣的活動? 憶雯:你看到的外國人,通常是樂團成員的伴侶,雖然觀眾裡面也有。另外可能是去英國演出時,或之後他們去歐洲巡迴時的畫面,所以會看到觀眾裡有一些白人女同志。不過你看到的其他非馬來西亞人,通常是樂團成員的伴侶,這些伴侶在馬來西亞也有工作。 Q7(主持人):我們確實在電影裡看到非常多語言,英文、馬來語,以及部分中文。也很好奇,樂團的團名有什麼特殊意思嗎? 憶雯:「Diam」,在馬來文中是「住口」的意思。 Q8:請問新加坡看起來比馬來西亞開放嗎?因為我們印象中新加坡對多元性別也不算友善。就算在新加坡放映,對片中人物會不會有影響?國家暴力這個風險永遠在沒錯,但是我想要問的是,他們有沒有直接真的遭受到什麼樣的、警察盤問之類的? 憶雯:關於新加坡的自由程度,我不便多談。不過這部片昨天剛宣布入選新加坡國際電影節。至於片中主角們有沒有直接受到政府迫害,對主角Faris來說,他算滿幸運的。最嚴重被警察盤查、詢問,可能就是影片中那場在車上的「重演戲」。那是真實發生過的,有一次他被警察臨檢,警察問他為什麼有鬍子、為什麼腿毛這麼長等等。可能有些人覺得那個場景比較詼諧,但如果你是因性別而被警察攔下來,那一點都不好笑。 Q9:因為不能在馬來西亞放映,有沒有試過用何種管道宣傳?它帶有很多 queer 的元素,如果沒辦法在馬來西亞讓大家注意到這個議題,那這部電影對馬來西亞的意義、提升關注的重要性,會不會被消掉? 憶雯:在馬來西亞有管理「新媒體/多媒體」的法律,通常也會管到網路使用與言論。這個法律訂得非常模糊、範圍也很大,所以你在網路上的任何活動都有可能被視為犯罪行為。因為對我們來說仍有風險,我們有印尼的共同製片,他的策略比較像是讓別人主動找到我們,而不是我們自己發很多宣傳文。或許以「有機式」的方式放映,可能還會還會行得通吧。 Q10:好奇電影中的音樂。然都是樂團的創作,但他們的歌曲應該不少,妳怎麼決定要放哪些曲目? 憶雯:關於音樂選擇,我一開始就確定想選哪些歌,有些則是後來慢慢加進去。像〈Lonely Lesbian〉非常受歡迎,就一定會放。開頭那首歌也放了,因為那是少數我有Faris脫掉上衣畫面的演出。 我也覺得結尾需要是一個音樂表演,要有一首歌。這個結尾是我唯一比較有跟(樂團)他們稍微策劃過的,也就是有先選好要放哪一首。因為那是Faris做完平胸手術後的演出,特別具意義,我覺得作為結尾很不錯。中間的部分則是有回應時事以及當時的情境,比方加入了疫情期間寫的作品。 Q11:導演好,想先致上敬意。妳可以一個人幾乎獨力完成這部影片,我非常佩服。想詢問,記錄了這麼多年,怎麼決定「這部片該完成了」?就像妳剛才提到有跟樂團一起策劃一個 ending scene,妳如何決定是在那個時間點可以結束拍攝的? 另外也想跟觀眾分享,既然憶雯這麼努力、獨立地完成這部影片,而在馬來西亞很難看到,甚至要到新加坡才看得到。希望觀眾願意多多支持、曝光,讓更多影展選片,才能繼續對亞洲的影像有所支持。 憶雯:謝謝你。 關於這部片什麼時候決定停止拍攝、也就是拍完了。幾個主角的狀況不一樣,像Yon生了小孩,是很大的轉變;而Yoyo 後來結婚。我其實等了滿長時間,等待一些事件發生,有天Faris告訴我,他決定做平胸手術。那時也差不多接近馬來西亞下一屆的首相大選。馬來西亞的首相任期是五年,對我們國家來說,五年就是一個週期,而我也在這五年間看到三位主角生命中的變化。我覺得五年到了,差不多可以結束了。 Q12:謝謝導演,我非常喜歡妳的作品,我現在是妳的大粉絲!我的問題很簡單,我們能買得到他們樂團的音樂嗎?可以順便支持樂團。 憶雯:謝謝。我知道他們有 Spotify是免費的,也有平台可以直接捐錢。 Q13:謝謝導演,我非常喜歡,欣賞片中主角們能以愉悅又自在的觀點看他們所在的當下。想請問,片中曾出現樂團穿綠色連身衣拍攝的影片後續? 憶雯:那是一支還在剪的 MV,有段時間他們很想拍很多 MV。 主持人:最後留一點時間給導演,她帶了非常特別的東西到現場。 憶雯:今天正逢同志大遊行,如果你還沒有準備好裝扮,可以跟我選購影片周邊的內褲,上面有片名、有各種顏色。現在只剩少數幾件,已快要賣完!
片名:《雪水消融的季節》 場次:10/24(五)11:0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林珏竹 與談人:製片 陳詠雙 文字紀錄:魏安琪 主持人:《雪水消融的季節》入選本次臺灣競賽單元,從 2024 年首映至今已經參加過許多影展。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製片陳詠雙,來和大家分享這部片在製作過程中,或是在長達七年以上的拍攝期間,有沒有遇到什麼特別的事情。先請詠雙跟大家說幾句話。 詠雙:大家好,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場放映與映後座談。苡珊因為正在山上拍攝,今天無法前來。我自己是在 2022 年加入《雪水消融的季節》的製作。當時苡珊剛從尼泊爾結束三個禮拜的拍攝回到臺灣,正要開始進入後製階段,她希望能找到夥伴一起討論剪接,並與剪接師共同合作,所以我就在那個階段加入了這部片。 因為尼泊爾的影像中有許多外語內容,我們最初是從整理這些素材開始。後來隔年,也就是 2023 年初,我們一起參加了日本山形的道場工作坊,與多位導師討論這部影片的結構。接著到下半年,我們也嘗試參加一些提案會,希望能爭取更多資金。從韓國到臺灣,最後一路走到去年初在國際影展首映,開始與觀眾見面。 去年下半年,我們很幸運地與希望行銷合作,讓這部片有機會進入院線發行。因此這次在女性影展的放映,算是這部片比較後段的旅程。其實在 OTT 平台上也已經可以看到了,但我仍然很高興大家願意來戲院觀賞,這部片的視覺與聲音在大銀幕中能被更清楚、更深刻地感受到。 主持人:片裡有非常多私人的部分,也有許多像是靈魂拷問般的鏡頭與場景。導演在這個過程中,因為他本身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當事人,對他來說,拍這部片應該也是一種療癒或救贖的過程。就你旁觀或對他的了解而言,從他決定開拍到現在,整個心境的轉變大概是什麼樣子? 詠雙:從山難事件發生以來,整個過程經歷了非常多的轉折,其中也包含片中另一位很重要的角色——聖岳。因為我是在後期才加入製作的,但在參與的過程中,我不斷地向苡珊詢問她與聖岳的關係,也觀察他在面對這個故事、要對外訴說時的狀態。 舉例來說,在影片初期,他嘗試參加提案會,希望了解身為一位非科班出身的導演,拍電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那時候的他,幾乎無法控制情緒,只要一上台就會情緒潰堤。那時他還沒有真的走到尼泊爾山上的洞穴。直到多年之後,中間又經歷了 Covid,他終於完成了那趟最初、最堅定的目標「走到尼泊爾山上的洞穴」,去理解宸君當時到底在想什麼。 經歷了這趟漫長的旅程後,他在剪接的過程中,也慢慢學會如何面對外界的目光。從一開始只有內部的討論,像是我、苡珊、剪接師之間,到後來參加工作坊,在那樣一個相對安全的內部空間中,她一步步整理自己的心情,也逐漸能以比較有距離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當時為什麼要拿起攝影機?」以及「為什麼執著於回到那個洞穴?」。 這確實是一段非常不容易的旅程。必須說,當年發生山難時,宸君才 19 歲,而聖岳與苡珊也才 20 歲,當時的他們仍在學習、摸索和消化這一切。 Q1:在剪接與後製的過程中,有沒有想過要加上一些字卡或說明?因為片中有許多不同時期的影像——像是過去拍的、尼泊爾拍的,還有後面有點像 Docu-drama(紀錄劇情片) 的段落。是否曾考慮標註「這段影像是誰拍的」或「這是哪一年、哪個時間點」,讓觀眾在觀影時能更清楚掌握時間軸?因為影像很多、時間軸也很複雜,我想知道當時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詠雙:應該是說,觀眾在觀看的時候,確實會出現一些疑問,例如「這是誰在說話?」或「這段到底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我可以分享的是,苡珊從尼泊爾回來後,影片的故事結構其實和現在版本非常不同。從最初版本到現在,中間經歷了不少轉換。 一開始苡珊的構想是,希望透過在尼泊爾拍攝的素材,去回應 2017 年宸君和聖岳登山時的經歷,試圖重建那趟旅程,從出發、到每個地點,直到他們在洞穴中失聯。在最初的設定裡,最後才揭露出苡珊其實是當時「缺席的人」,而最終他們在洞穴裡重逢。那是一個相對抽象、也有更大創作野心的版本。但當我們在工作坊放映給導師與夥伴觀看時,大家都發現:「這個敘事完全行不通。」因為後來在 2022 年拍攝的素材,很難和 2017 年的事件連接起來。當我們試圖面對 2017 年那場山難時,手上能用的素材其實非常有限,只有搜救隊當時帶著 DV 進洞穴拍下的片段。經過工作坊的討論,我們意識到有些素材根本無法被改動,也無法支撐原本的創作企圖。於是後來的版本變得比較線性。就像現在大家看到的──一開始是有人失蹤,接著有人接到語音訊息,於是開始搜救,然後一路發展到聖岳回來的事件。這其實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轉換。 隨著時間推進,素材拍攝的方式也不斷變化。苡珊的拍法在中間過程中一直在摸索、嘗試。面對聖岳的改變,原本他們之間是比較親密的狀態,DV 就跟著他拍,「你到底說什麼?」錄音品質其實不太好,聲音設計也有些留不住,因為那支小 DV 的指向麥克風只對著前方,苡珊說話的聲音常常聽不太清楚。後來 Covid -19(疫情)發生,她一度去不了尼泊爾,那段期間她開始接一些委託案、做不同的拍攝練習,風格也因此出現轉變。直到最後真的重返尼泊爾時,這次有一位攝影師同行,她對畫面的掌握度也更高,所以後期出現了更多漂亮的畫面,也有不少 POV(主觀視角)鏡頭。 你剛提到的那一場,我猜是指re-enactment(重演、再現)的段落,那一場剪接,可惜婉玉(剪接師)不在這,我想想可以怎麼回答。有一個人穿著曉明女中的服裝趴在樹上,那場其實是苡珊透過宸君的信,回溯他們剛認識時的狀態。我們思考了很久該用什麼樣的視覺最能貼近那種情感,最後在遍尋素材的過程中完成了這樣的設計,那是我們當時能做到的最好樣子。我們也確實不計劃在片子裡放入過多的字卡去解釋,這是創作團隊的選擇。 主持人:剛剛提到的婉玉,就是林婉玉,她是《日常對話》的剪接師,也是一位導演。這部片的素材我相信非常多,如果大家在大銀幕上看,其實可以分辨出來哪些是早期拍攝的、哪些是後來新增的畫面,像畫質也能看出差異。我覺得在剪接與導演的討論中,這部分一定經過了很多拿捏與選擇。這部片非常私密,但同時又要讓導演能夠真實表達自己,也讓觀眾理解,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平衡。 其他觀眾:我想表達一個不同的意見。我覺得影片來源與時間軸的交錯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問題。有些重演或回溯的橋段,我也覺得無可厚非,反而更能感受到當下的情境。 詠雙:謝謝。確實,每次在整理素材時,我們都要面對兩顆硬碟。一顆是從 2017 年到去尼泊爾前陸續拍下的畫面,已經非常多了;另一顆則是尼泊爾三週集中拍攝的素材。只要把時間軸拉開,就會發現苡珊與宸君在曉明女中時期的素材幾乎沒有,頂多只有一些照片,甚至連合照都很少。因為他們並不是喜歡拍照的人,比較偏向文青,他們會寫信但很少拍照。那場戲其實就是創作者在面對「沒有素材」時的一種嘗試,她想用畫面貼近那段自己未曾紀錄,卻想紀念的時光。 主持人:我自己觀察,也覺得那段雖然有點像表演或重演,但其實很能帶我們進入那個狀態。他們兩個來自同一所高中,穿著相同的制服,過著相似的生活。我覺得片中最動人、也最沉重的一句話,是信裡那句「苡珊,這一輩子都感謝你。」那句話就像他們之間感情,是他們友誼與人生最後的交代。他想把這份情感傳遞出去。我相信導演在選擇最後那個畫面時,一定有他特別深的情感。我整個人都起雞皮疙瘩,太感動了。 Q2:我蠻喜歡這部片的節奏感、時間軸的堆疊,以及剪接的節奏,能讓情緒慢慢累積,也讓觀眾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聲音與剪接我都很喜歡。不過我注意到,在拍攝時聖岳好像有在假裝堅強,不太想被拍,感覺他是整個事件裡最悲傷、但在壓抑情緒的人。這有點像在創傷後不斷觸碰傷口。想請問,在這個過程中是怎麼和他協調的?因為他好像擔心苡珊在拍攝時會有危險,也答應未來再一起去,但後來他又消失了。很擔心這段創傷他是怎麼面對與撫平的? 詠雙:關於聖岳…..片中有一場很關鍵的戲,是他們在房間裡終於收到搜救素材的時候。那時苡珊問:「要不要看?」聖岳回答:「當然可以看啊,反正我是局外人,我才不care……」這類的話,但當他們真的打開畫面、開始瀏覽當時的影像時,聖岳卻突然把電腦關上,說:「你不要再看了,你在旁觀他人之痛苦。」那一場戲對我們來說非常關鍵,呈現出聖岳複雜的情緒。 事件發生後,聖岳的情緒起伏很大。一開始有很多媒體湧到醫院外報導他,稱他是「倖存的男孩」,想了解他的故事。他一方面被外界包圍,一方面也陷入「我真的活下來了嗎?」的亢奮與混亂中──這段情緒真的很複雜──隨著亢奮的情緒消淡,那時候還是他跟苡珊提議:「我們應該幫宸君出一本書。」也就是後來有一本叫《我所知道的關於山的一切》的書,那是苡珊跟聖岳一起合作,將宸君的文字進行出版的一個作品。 之後,正如片中所呈現的,聖岳開始拒絕再被拍,甚至對苡珊說:「你別再拍我了,我不想再談這件事。」苡珊當時也很錯愕,因為他們其實非常親近。外界並不了解聖岳與宸君的關係,媒體又常將他神化,甚至有網友攻擊他:「你帶女朋友上山出事了。」這讓他承受了極大壓力與情緒層面的折磨。 隨著他在片中拒絕拍攝,故事也轉向成為苡珊自己一個人的旅程。我們在電影對外發表前後,都會定期與聖岳聯絡、向他報告影片進度,他通常不太回應。他目前已在環境倡議團體,長期從事研究與登山相關的工作。像最近花蓮堰塞湖事件發生,他們在那也有些工作。我想,那也是他最擅長、也最能讓自己得到平靜與快樂的方式。 主持人:聖岳有參加臺灣的放映嗎? 詠雙:從來沒有。 Q3:想問關於在尼泊爾的採訪。因為導演是在事發一段時間後才回去,那當地搜救隊或旅館老闆的反應如何?你們在拍攝時會引導他們回想當時的情景,還是他們真的還記得那些事? 詠雙:因為我沒有親自去尼泊爾現場,所以只能轉述苡珊與攝影師回來後的分享。他們說,即使事隔五年,那些當地人一提起這件事,仍然記得很清楚。有人說:「我知道這件事,是這樣、那樣的情況。」甚至有搜救隊成員還留著當時兩位登山者的鞋子,其中一位還繼續穿著。對他們來說,那是實用的東西,不會因為是逝者留下就不用。這讓苡珊感受到,那段記憶在當地人心中依然鮮明。我覺得這趟旅程對苡珊來說,是一次很大的療癒,她原本想知道當地人是否還記得他們,而得到的回應是溫暖且正向的。 主持人:今天的映後座談就到這裡。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上網搜尋相關資料,或等一下有機會再和製片詠雙聊聊。再次謝謝大家今天的參加。
片名:《婚.紗.罩》 場次:10/24(五)16:5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康庭瑜 與談人:導演 陳昱伶 文字紀錄:王湘筠|文字整理:彭湘 主持人:實不相瞞,我其實在兩、三年前有榮幸偷偷看過導演的作品計畫。今天終於看到很多條線,非常幸福的融合在一起,帶給我們笑中帶淚的電影。非常的感謝導演! 昱伶:我想先感謝大家,謝謝女性影展給我這個機會,如果不是這個機會,這件作品無法在大銀幕播放。感謝女性影展,品味很好(觀眾笑)。我要謝謝影展的(工作人員)博尹、彭湘跟沅君幫了我很多的忙,之後還要繼續麻煩他們。 再來,我一定要介紹我的受訪者!他們通通都有來,真的很棒。因為是女性影展,我先介紹女性──謝謝中視新娘世界的廖嘉今,真的謝謝她。你們看到的所有年代很久的那些(明星),方芳芳、秦祥林呀都是他們拍過的,他們當時就是可以請到這麼厲害的人來拍廣告。再來要謝謝我們的麥燦文,他的篇幅雖然沒有很多,我非常的抱歉,但他提供了非常多幫忙,很多對的新人都是他介紹的。再來,要謝謝聲哥林聲──叛逆的老頑童,他是古時候的文青,現在還是。再來要介紹茶壺,我們的婚紗界的一本書,就在那!他現在不拍婚紗照了,我想找他拍也沒辦法,他不要拍了。他現在拍家庭照,還是非常的厲害。最後一位,我們歡迎最年輕的英奇,也沒有真的很年輕了。謝謝這些受訪者,把你們的故事跟我講,讓它變成一個這樣的片子。 主持人:因為我看過作品的企畫,我認為結尾非常美,將很多條線收束在一起。妳一直在表達,希望透過攝影、靜態的影像,表達自己曾經存在過。妳拍了這麼棒的一部的紀錄片,紀錄片也是一種影像,而它留下了非常深沉的妳。紀錄片的影像跟婚紗照比起來,這兩種影像對妳來說的意義是什麼?不一樣或者一樣的是什麼? 昱伶:兩者對我來說真的不太一樣。膚淺的我當然會希望漂亮,我還是沒有機會穿上片中那一件婚紗,因為是綁帶的,沒有人可以幫我穿。衣服本身很漂亮,我還是很喜歡,但我覺得在拍這部片的過程中,認識了大家(指被攝者),那個過程的確是療癒了我。我現在可以用比較愉悅的心情去看婚紗照,喜歡看也知道膚淺(笑),但我還是覺得這件事情就女性而言,在那個時間點留下婚紗照是一個很珍貴的紀念。我認為這部片的確療癒了一部分的我自己,我現在長大了。 主持人:是療癒的作用。 昱伶:對。我很希望這部片透過最通俗的商品,也就是「婚紗照」,來談女性內在的某些層面。我自己覺得,女性的確有一個深層的、必須不斷的失去跟填補不滿的洞。那個洞是,妳總會覺得「我好像少了一點」,尤其因為這個社會、世界的各種眼光以及壓力。我其實本來覺得我喜歡婚紗照這件事情很背離(笑),那個背離是,我作為一個讀書人,作為一個文青,怎麼可以喜歡,對不對!但我現在已經跳脫了,喜歡還是喜歡,我是可以喜歡的。但我理解那個深層的東西是什麼,其實就是那個「缺」,我覺得自己沒有被填滿,而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Q1:我非常喜歡這部片。我好奇的是,片子是從一個女性婚紗的觀點,但片中有個很動人的部分是它紀錄到四個男性攝影師,而且是四個攝影師不同的故事。對我來說很特別、也很動容,是一種很大的對比。同時,它也是個關於婚姻的兩種不同的聯想。開始拍這個計畫時,導演如何決定或挑選這四名被攝者?第二個好奇是,好像少了一個男人,也就是導演的丈夫冠宇,但片中還是有出現丈夫的原生家庭。您又是如何選擇這部分的? 昱伶:我不是沒有選過女性,可是女性攝影師後來沒有跟我聯絡了。我覺得很可惜,因為她非常的厲害,我也很喜歡她。至於為什麼是男生?真的只是剛好是男性。我在跟他們聊天的過程,發現他們某種程度上,好像想跟我講一些事情。於是,我後來的拍攝,其實完全跟他們拍婚紗照這件事沒什麼關係,我沒有在講技法、攝影機,也沒有在講相機的品牌。我的重點都掉進了他們的故事、他們自己的人生。當然,我也很謝謝他們把這些故事告訴我。 那麼,他們的人生故事多多少少影響了,比方我跟我先生之間的關係。例如說,我一直覺得英奇跟我先生很像,可是我當時說不上來,我只是覺得「真的好像喔」,想說拍拍看好了。拍聲哥的原因則是,剛開始那種文青形象的婚紗照我覺得好像也不錯。茶壺完全是因為他就是一本書,是個婚紗界bible,我當時就很想認識他。他是個超級自律的人,永遠都比你早到半小時。總之,我就在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有或沒有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一直覺得男性、女性不太可能分開來看,兩者一定是一起生活在這個世界裡面的。我昨天看了今年女影的一部片《敬!莎莉》,她(片中主角莎莉)希望可以跟男生分開,男性最好只剩下10%,是比較極端一點的女性主義者。但對我來說,我嘗試看到男性比較辛苦、比較脆弱的那部分。而我思考的是,藉此是否可能調和我自己心裡,那個比較容易對另一半生氣的部分。 其實他(先生)有出現啊!他大部分都是在攝影機後面(拍攝)。我的指導教授盧非易老師,就非常厲害的幫我點出了──雖然這像是個男性凝視的東西,攝影師在凝視新人、我在看這些攝影師,還有一層是鏡頭背後,我先生在看我在搞什麼鬼。他其實在(攝影機)後面,我也沒有特別想要把他點出來,特別點出來就不夠美了、不夠有感覺。我會放入在先生老家那場,是剛好我公公那時候講出有點哲學的話。因為我除夕在那邊燒金紙,他說「初二才可以回去」之類的,我覺得很微妙。 Q2(主持人):身為女性創作者,可能前幾部作品時常是將自身的創傷、人生的慾望和體驗揭露給觀眾,當我們在挖掘那個痛苦時,有的時候便會不小心暴露了周邊的人。比方說我想寫我的先生,但我又不知道寫到哪裡是倫理,把他寫得太壞會不會有傷害,把他寫得太好,好像又在說謊(觀眾笑)。我想問的是作為母親的傷痛──我自己也有一個兒子──比方可能也會擔憂,孩子長大以後看了會不會覺得自己害了媽媽。導演覺得在倫理方面,以及因為有愛不想要傷害的心,要如何拿捏呢? 我剛生了兒子時,其實有段時間是感到比較辛苦的,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沒有明天了。那時候天氣很差,我記得好像是十二月,只要天一暗我就很想哭,想著「天啊,什麼時候才會天亮?」,因為天亮了,我的月嫂才會來。沒有月嫂之後,我就覺得自己是個廢人。印象中,我好像隔了三個月之後才騎摩托車出門。我就覺得這件事情真的很恐怖,可是很多女性,其實在生產完之後都有一段這樣的經歷。只是因為小孩大了,他們生理上可能不需要妳了,就覺得病好了。但我認為,其實沒有。 我也有想過(作品內容)會不會對不起小孩。在上課的時候,我也會看到一些片,思考到這樣(拍)對這個小孩會不會太殘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看,片中最後一段。那段其實是有一天睡覺時,我聽到我兒子講話,覺得很好笑,就把它錄了下來──那其實是錄的,我沒有拍──他說他在外太空飄漂流。我聽到的時候有點內疚,我在想他是不是感覺到我沒有那麼喜歡他、我是不是不要他了。的確從那次之後,我很認真的想,是不是因為我的工作或唸書這些壓力全部集中在一起,導致我對這個小孩就有一點──「你為什麼這時候要大便?」、「為什麼這時候不睡覺?」、「為什麼不吃飯?」……好像是我沒把自己調整好。 當下,我可能只是希望這個人不要再煩我而已,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的確是從兒子說到那個漂流後,我就有點內疚。我不知道他長大之後(看到片子)會不會討厭,以後再說好了,不好意思(對兒子)。 主持人:謝謝導演非常深度的分享。 Q3:冠宇(導演的丈夫)是攝影師,後來又是剪接師,也是隱形的主角之一。在這個創作的過程中,你們如何去溝通和處理? 昱伶:就是不斷的溝通啊,不斷的吵架。 我們開車經過桃園的時候,他就會跟我說 「欸,你為什麼要拍桃園那個攝影師啊?」,他指的是英奇。我那時候還說不上來,就回了我先生:「我就是覺得這個人很特別」。然後他就覺得,這個不像啊、那個不像啊,就開始一直碎念了。所以有一段時間我非常討厭跟任何人講到這個事。 我喜歡婚紗照已經太久了,就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神經病,所以又拍到一段時間覺得很卡,我到底要講什麼?然後我又一直被先生挑戰,因為他自己也是導演,比我成熟很多,他就會覺得「妳搞什麼鬼?」、「妳趕快畢業可不可以?」。但我就一直覺得,我還在等,所以中間有段時間,我是不想給任何人看我的初剪的。 我有初剪一個蠻難看的東西,是直到後來才請我先生看。他剪得比我快很多,也比較好看,因此就變成請他剪。但我之前會有一種,好像被干涉了的感覺,會覺得「憑什麼干涉我的作品、這是我拍的。」後來我嘗試和他溝通,因為他其實可以讓我的作品變得更好,但我也還是想將我想傳達的東西放進去。 另一方面,聽說在剪的過程中,他終於了解我為什麼困惑於婚紗了。他好像終於了解,「喔,原來女生有這個想法啊。原來你拍這個攝影師是為了這個、為了那個。」我們好像有在製作的過程裡面,得到某種程度相互理解,但我不確定有沒有全部。 (觀眾:冠宇在場,是不是本人可以回應?) 冠宇:其實我在剪的時候,我是用直覺來剪的,看那個畫面有什麼,我就自己剪。我也不知道到底剪成什麼樣,只是覺得要讓它變好看。但是在剪的過程裡,我依稀感受到好像要講什麼東西,而且是很女性的部分。那個感覺我是說不出來的,我就隱隱約約有感受到,好像包子(導演)要講什麼東西。 當然最後剪完給她看,那她看完她就覺得好像有這樣子的東西出來。這個變成是互相地,我往前推一步,然後她再稍微修一步,我們就這樣來來回回、來來回回後,我最後才知道她到底在做什麼。 應該也不是說我幫她剪的很完整,我只是想讓作品變好看而已(笑)。最後很多的觀點都是她自己理出來的,像字幕的那個部分,還有心裡的感受,通通是她自己做出來的,我只是操作員而已。 昱伶:謝謝他。 主持人:可以說是文青夫妻通過作品進行一個相互理解的過程。 昱伶:某種程度上是。 Q4:為什麼會選擇拍自己娘家人的婚紗照的部分,但是沒有選擇拍先生那邊老家婚紗照的內容? 昱伶:我問過我公公很多次,但他就是沒有拿出來啊!我覺得他現在一定後悔了。我之前是想要拍他們的(指公婆),我覺得他們一定有拍,畢竟我公公也是那個年代一個潮男的。但他一直沒有拿出來,我每次都下去問他「欸,我可以跟你借嗎?」,然後每次都沒有。真的不是我刻意只拍娘家,是因為我公公沒有拿出來給我們看。 觀眾分享:我是導演的妯娌。她(昱伶)在家族裡面真的是好媽媽、好媳婦,也是好太太,但我覺得她對自己很要求。因為她結了婚後變得四分五裂,她原本是個女兒,但結婚後就變成媳婦、變成太太、變成媽媽了。我的同事也滿多都覺得生小孩CP值很低,因為生了小孩又再被分裂了。包子就是再找回自己,從我認識她開始她就喜歡婚紗照,那是一個公主的夢,但當公主夢碎裂時,她得一塊、一塊地撿回來。我覺得她最後要追求的是得到先生完整的愛,我期待她先生有一天會把她的婚紗吊起來打spotlight。 Q5:很恭喜包子!我很喜歡這部片,它非常幽默、很好入口,也就像導演說的它非常通俗。我也很喜歡這部片的節奏感,以及一個讓我感到很可貴的地方是,導演非常誠實。我尤其可以理解身為文青,喜歡婚紗好像是一件很丟臉的事,但從來都沒有人去定義這兩件事不能畫成等號。從我認識包子以來她就是很勇敢、很執著,她只要看到相關的婚紗就一定會分享,一定會發表她的心得感言,我覺得超讚!我想問的是,妳還有要再續拍第三組婚紗照嗎? 昱伶:應該暫時不會。有的時候再告訴大家好了我覺很棒啊,我現在就是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現在喜歡婚紗變成一個很開心的心情,這件事我覺得很好。 Q6:導演沒有拍下組婚紗的計畫,那有拍下一部作品的打算嗎? 昱伶:其實我上一部片是大學的畢業製作,是20年前的事。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做創作的人,我應該還是會繼續在傳播這一塊,但我不知道有沒有下一部。如果有下一部的話,就做「追星」好了⋯⋯(笑)。 主持人:那我們就期待導演的下一部。我們今天也知道了,拍片是可以促進婚姻的溝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