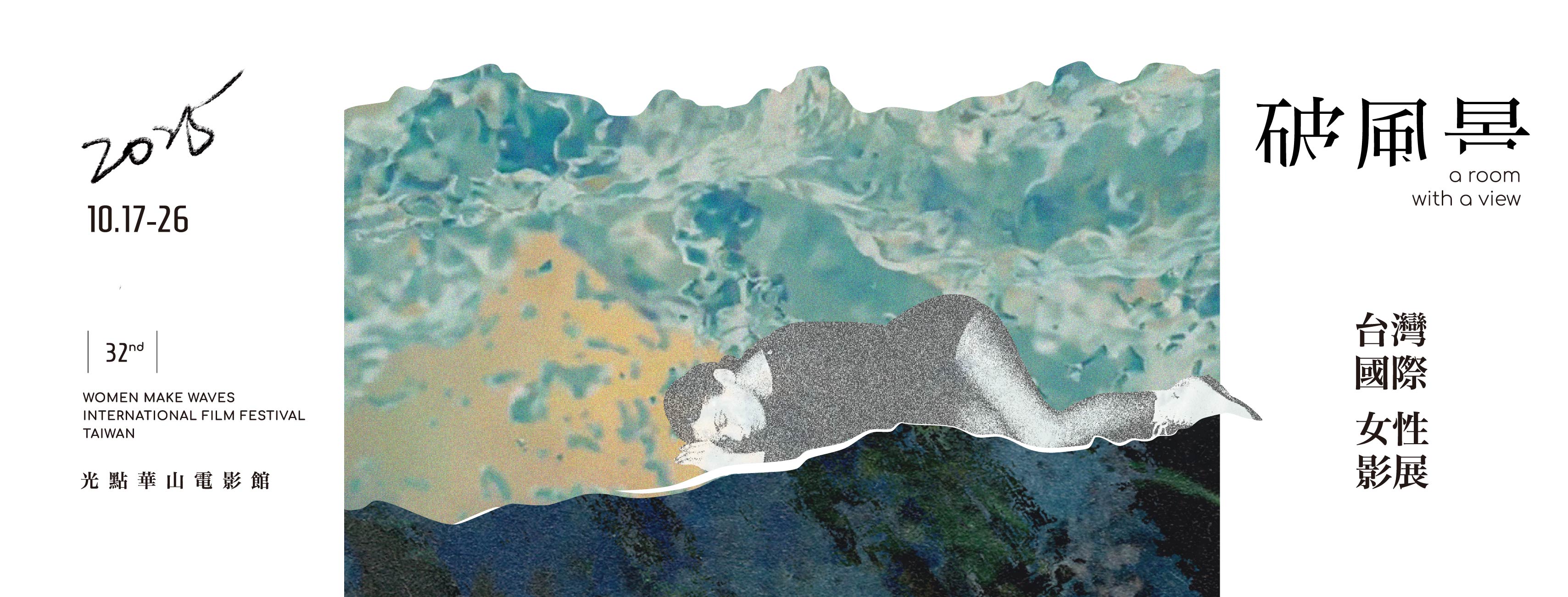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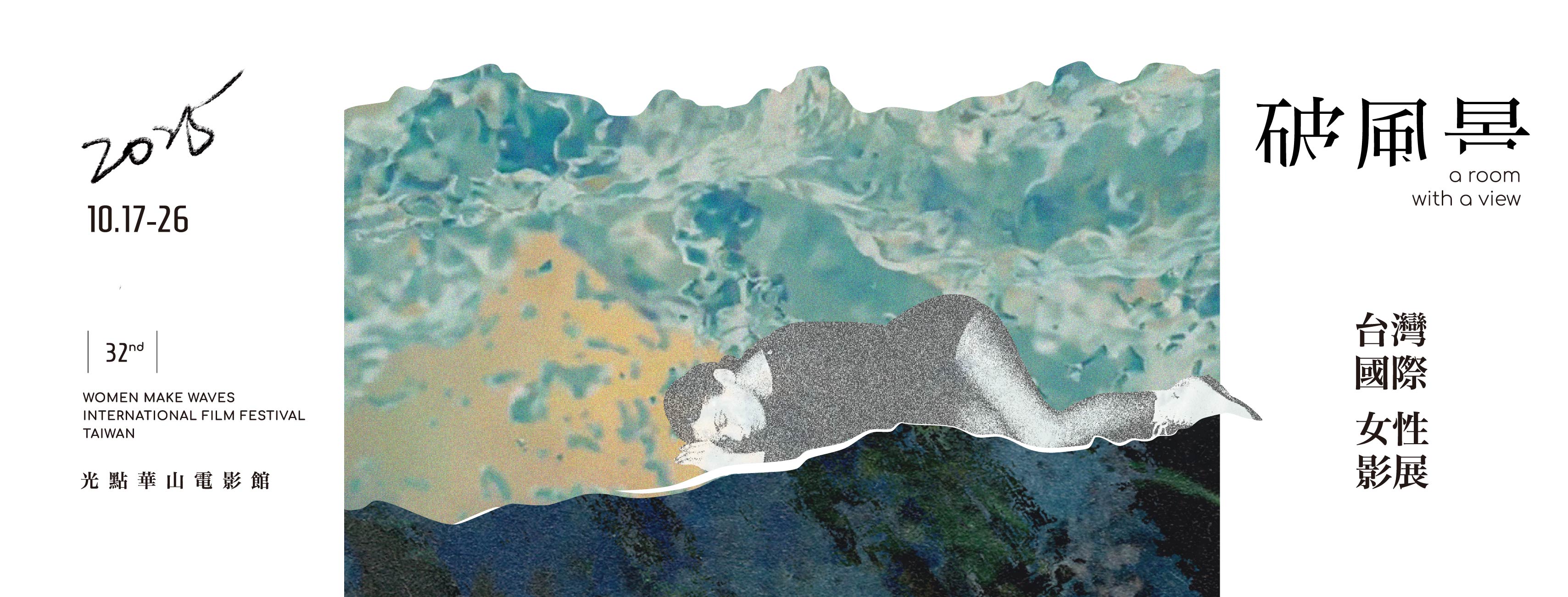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時間:2025年10月25日(《拍電影的女性們》映後) 地點: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第六、七屆理事長 范情 與談人:導演 熊谷博子 KUMAGAI Hiroko 文字記錄:魏安琪 范情:大家午安,我是范情,台灣女性影像學會2014年到2018的理事長。今天非常榮幸有機會為大家主持這一場映後,《拍電影的女性們》是非常難得的紀錄片,我們也很難得的邀請紀錄片的導演熊谷博子女士來到現場。先歡迎熊谷博子女士。 熊谷博子:大家好,我是熊谷博子,很開心大家特別過來看這部電影,也很開心能夠遇到大家,謝謝。 《拍電影的女性們》拍攝動機與構思 范情:我看了這部電影三次,我第一次看的時候,心想:「哇!怎麼會有這樣一部電影,讓我這麼喜歡」。第二次是前天在戲院看的,我非常感動;而今天再看一次,我則是非常激動。這部電影不只談到了過去日本女性導演的經歷,也連結到了女性影展。 談到爬梳早期女性導演的歷史,這幾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其實也做了不少努力。比如,曾放映過世界第一位女導演──愛麗絲·吉·布蘭奇(Alice Guy-Blaché)的作品;針對台灣導演的部分,我們也爬梳了早期女性導演如李美彌(代表作如《未婚媽媽》、《女子學校》)、楊家雲(代表作如《瘋狂女煞星》)的作品。也很棒的是,2022年,台灣女影放映了日本導演田中絹代的作品,同一年還放了韓國較早期嶄露的女性導演,申秀媛的作品《女影人生》。 《拍電影的女性們》這部2004年拍成的電影,能在2025年的今天因緣際會於女性影展放映,真的非常難得。就我所知,這部電影在2004年放映後,去年又於東京影展的研討會上重映。我們暫且不談其中的原因,想先請導演和我們分享,當時為什麼會拍這樣一部電影?是什麼樣的機緣?而這些導演又是在什麼情況下進入到這部影片中的? 熊谷博子:《拍電影的女性們》是為紀念第15屆東京國際女性影展拍攝的,可以說是一部紀念性的作品。其實在影展的第一屆,日本的女性電影導演只有一位(參展),就是羽田澄子。到第15屆時,曾參展的導演人數已經越來越多了。像我自己,是在第三屆時參加東京國際女性影展。基於這個機緣,策展人高野悅子小姐便問我:「我們要不要為這個影展拍一部紀念性的電影呢?」對我來說,我拍這部電影並不只是想記錄「有一群女性在拍電影」,而是想呈現──女性拍電影,其實同時是在與時代、社會,甚至與自我進行一場戰鬥。對我而言,這部電影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奮鬥紀錄。 范情:我在看這部電影時,有很深的感觸。這些導演在片中談到的議題,讓人感受到拍電影這件事並不像寫作、寫詩那樣單純的創作,而是牽涉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政治、經濟、個人所要突破與堅持的種種。政治上更涉及「性別政治」,而文化中女性的形象與角色所面臨的限制,也使拍電影變得更加艱難──這樣的困難真的不是一般創作能相比的。 接下來請問導演,正如您剛剛提到,這部片不只是拍女導演而已,那在構思時,您是否有先思考過,希望呈現她們的哪些面向?有哪些部分是您特別在意的?有沒有在訪問過程中發現一些原本沒想到、但特別讓您印象深刻的地方? 熊谷博子:是的,在這部電影裡,我訪問的對象其實都是在這15年間曾帶著自己的作品去參加東京國際女性影展的人。無論是製作人還是導演,我問她們的問題其實都相同,但每個人的回答卻因為所處的時代與環境而非常不同。這種差異與獨特性讓我相當驚訝,也非常興奮。每次訪問不同的對象時,我都抱著興奮與期待的心情進行訪談。 范情:我很好奇,妳問她們的問題有哪些? 熊谷博子:譬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訪問了一位製作人飯野久,就是《黑雨》(今村昌平,1989)的製作人。讓我非常驚訝的是,她竟然要在兩天之內籌到2400萬的資金。這對導演來說其實很難想像,像她這樣的製作人角色,在背後做了多少工作。因此,當我聽到這個故事時,真的非常震驚。還有一位澀谷昶子導演,她在片中提到,當她在片場喊「要開始囉!開拍!」時,竟然被其他工作人員說:「蛤?我們的導演居然是女生?」接著就把燈光全部關掉。即使在這樣嚴峻的狀況下,她仍然堅持繼續拍電影,我從她的精神裡得到了很大的啟發。 至於我實際上問的問題,其實都一樣,我會問:「妳在進入電影產業時遇到了什麼困難?」、「你怎麼處理?又是怎麼跨過這些困難的?」大家給我的答案都不太一樣。還有一位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植平多鶴子小姐。她一開始是做場記的,當時隱瞞了自己已婚、有小孩,並且生病的狀況。後來,她發現自己必須要找一個能自由調整時間的工作,於是決定要當導演。但當她決定當導演時,必須去說服身邊所有男性工作人員,曾經花了三到六個小時,去逐一說服每個人。我聽她講這個故事時,心裡便想:「如果是我,能做到嗎?」這次訪談讓我非常驚訝。 熊谷博子的個人經驗與電影創作之路 范情:導演直接切入了女性在電影產業中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這些狀況在片中也都能看到。而在電影裡,大家有注意到嗎?熊谷博子女士本人也有出現,她的作品《阿富汗之春》(1989)曾在第三屆女性影展中放映。這邊我也補充介紹一下,熊谷博子導演的名片上寫的是「Documentary Journalist」,也就是紀錄片導演兼新聞記者。她在1970年代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後,進入電視公司工作,參與了許多邊緣議題的拍攝,如戰爭與社會紀實。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作品,是她要求政府將原爆時期的影像歸還給日本人民。因為當時這些影像被美國政府壟斷,而這樣的舉動,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直接且具有正義性的行動。1985年之後,她成為自由工作者,陸續拍攝了關於礦區女性等議題的紀錄片。 在《拍電影的女性》中,有一點讓我特別感動──熊谷博子導演提到,她過去拍了許多一般女性不會選擇的題材,她必須勇敢地進入戰區、礦區去拍攝。包括她2024年拍攝漢生病紀錄片在內,她逐漸發現自己對普通人的生活並不熟悉。因為這樣的體悟,她開始回過頭來關注身邊的世界。她說,早年曾覺得拍小孩、拍生活瑣事、拍女人做的事不是自己想做的題材,但如今她重新回到了這個領域。 我想請問,就妳個人或從女性影像創作的角度來看,妳覺得這其中的意義是什麼? 熊谷博子:首先,非常感謝您這麼詳細地調查了我的資料。回到自己的個人經驗,因為我的祖父是軍人,其實我父親是在台北長大的,我的伯父、伯母,也就是父親的弟弟、妹妹,也都出生在台北。也因此,這次我來到台灣,心情其實是很複雜的。 我小時候常聽到祖父和父親談話,他們聊的內容大多與戰爭有關,但他們並不會反省日本在戰爭中做過的錯事。反而還帶著一種懷念的語氣說:「戰時的什麼、什麼很好啊……」他們也常提到喜歡台灣、喜歡台北。這讓我從小就產生疑問:「為什麼我的家人會覺得戰爭是件好事?」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影響,我後來想成為一名記者。 當我去阿富汗時,正值蘇聯撤軍之後,我每天都看到有人死去。久而久之,我對死亡變得麻木,只覺得「人死就是戰爭的一部分」。回到日本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竟然對「死亡」這件事失去了感覺。後來我結婚、生子,才慢慢開始關注身邊的事物,理解照顧家庭、養育孩子的重要性。以前我認為那只是女人或小孩的事,與我無關,但當自己親身經歷後,我體會到那份辛苦,也明白人際關係與社區連結的價值。於是,在思考與追蹤議題時,我的觀點也因此逐漸改變。 范情:對,導演在片中提到,她在拍《阿富汗之春》時,從伊斯蘭《可蘭經》中得到啟發,提出「右手拿著攝影機,左手抱著小孩」的口號。我也想到,在台灣1970年代,有一位早期婦女運動者呂秀蓮女士,她在《新女性主義》中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她的口號是「左手拿鍋鏟,右手拿筆桿」。我覺得這兩者有點異曲同工之妙。這當然是個巧合,但也能感受到,正如導演所說,這樣的口號看似有力量,但實際上要做到卻非常不容易。 我也很好奇,導演曾提過您拍過一部與生育有關的作品,好像也曾進入東京女性影展。相較於您拍攝許多戰爭或邊緣題材,這部作品是否可以被視為「一手拿攝影機、一手抱小孩」這個理想的具體實踐?因為當我們談到女性導演拍電影,以及進入產業的困境時,常聽到有人說:「等我把小孩照顧好、孩子長大後再拍電影。」但現實往往不會等人。那導演當時是怎麼面對「照顧」這個角色與課題的呢? 熊谷博子:第三屆東京國際女性影展,我帶了《阿富汗之春》參加。當時的記者會上,聚集了各國的女性導演。有個記者問了個問題:「妳們既然是女性,要怎麼一邊顧家、一邊拍電影?這兩件事有辦法兼顧嗎?」 那時,一位攝影師回答,如果是編劇的話,可以在家裡寫作,兩邊都能兼顧;但如果是攝影,就必須到外面工作,根本不可能做到。另一位外國導演則說:「對我來說,工作人員就像家人,所以我不需要再結婚。」 輪到我回答時,我想到伊斯蘭世界的一句話:「右手拿著《可蘭經》,左手拿著劍。」於是我脫口而出:「我右手拿攝影機,左手抱小孩。」但我後來發現,這句話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非常困難。 我個人認為,不管事情多小,重要的是要持續去做。幸好隨著科技進步,攝影機越來越小,女性也能自己拿著拍。而後來的電視產業,也出現一些規模較小的公司。如果要和他人合作,就得配合時間,但當時我要照顧孩子。因此我後來盡量自己拍、自己編、自己剪,在小電視公司製作節目,並且不斷持續下去。 至於為什麼會拍到「生產」這個畫面,是因為那時遇到一個企劃,內容是關於東京的一條老街「巷島」與德國一條古老街區的交流。主題是「不要因為老舊就拆毀,而要珍惜與保存」。在那個企劃中,我遇到了很棒的人,便很想拍下這個過程。 回到拍攝生產的畫面,那次真的非常困難。攝影師是資深前輩,我們合作多年,但整個團隊全是男性,像錄音師是四十歲單身男子,助理則是二十歲單身男子。我原本預測這位媽媽會提早生產,結果卻晚了,他們因此責怪我,甚至說我是騙子。 好不容易拍完進入剪輯階段,剪接師又是五十歲單身男性,他說:「為什麼要拍這種東西?我完全看不懂這鏡頭的意義。」他覺得這段應該兩秒鐘就該結束。我努力說服他,但最後他甚至不高興地離開團隊。幸好,後來加入一位有育兒經驗的男性,他能理解這個畫面的意義,協助我們順利完成。正如電影裡所說,每一部電影背後都有許多故事。 【Q&A】 Q1:謝謝導演帶來這麼多啟發。片中訪問了許多閃亮的女性,想請問有沒有哪一位受訪者在約訪時特別困難?是否有在女性電影發展中有重要地位,但婉拒了採訪的? 熊谷博子:我在拍這部電影時,受訪的對象多半是對電影產業抱有非常多想法的人。能夠把她們一直想說、卻說不出口的心聲記錄並呈現出來,讓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大家也都很開心、很支持我完成這部作品。 至於有沒有覺得可惜、但沒放進電影裡的畫面?有一位剛也提到導演澀谷昶子,她的作品《挑戰》(1964),曾在坎城獲得短片金棕櫚獎。不過她在剪輯過程中一直不滿意,在截止日期前仍堅持地說:「我還要再來一次。」她不斷重新剪接,最後完成的版本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那一部。不過這段過程我沒有拍進電影裡,覺得有點可惜。 Q2:導演您好,我是台灣女性影展以前的策展人之一。今天看了您的片子,我想表達我的敬意。過去三十多年來,台灣女性影展放映過許多日本女性導演的作品,例如濱野佐知,以及剛剛提到的田中絹代導演。我自己在策展亞洲女性影展的經驗中,也曾遇過東京女性影展的大洋竹子小姐,台灣與日本之間其實有很多交流。 這部影片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以前認識的日本女性導演作品多半是劇情片或長片,但今天發現日本也有像您這樣拍攝新聞性、紀錄性題材的女性創作者,這非常重要。看完這部片,我覺得像是上了一堂很豐富的課,真的非常感謝您。不過容我問一個稍微尖銳的問題,請您多包涵。 我覺得您的影片切入角度很好,能夠同時看到日本社會、文化以及導演自身的挑戰。不過我也注意到,儘管片中的女導演們表達了對結構與環境的不滿,或提及所受的壓迫,但影片中幾乎沒有直接使用「父權社會」或「父權壓迫」這樣的概念或字眼。這點讓我覺得很有趣。 今年台灣女性影展的策展很棒,把您的片與另一部挪威導演的作品《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放在同一單元。那部片的角度很明確也很單一,對父權體制有強烈的批判,從電視台到媒體文化都在反思。而您的影片則比較多元、更女性化,也帶出豐富的訊息。兩部作品各有千秋,但我很好奇,為什麼您的片子在製作時,沒有更強烈地批判父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但這是我的觀察與感受,謝謝。 熊谷博子:您剛剛提到的《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我今天早上也來看了。那部電影的素材是1973年拍攝的,當時女性主義才剛開始發展,與我的拍攝年代不進相同。我在拍這部電影時,更想聚焦於每一位電影人的內在──她們怎麼思考、怎麼奮鬥。如果我們今天再回頭看,就會發現,不僅是電影產業,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女性所面臨的處境與片中所談的仍舊相似,這是個至今仍具共通性的課題。 女性影展的意義 范情:正如導演所提到的,其實我們之間有文化與時代上的差異。我自己也很想知道,日本的婦女運動發展,與日本女性導演、以及東京女性影展之間的關係。 東京國際女性影展從1985年開始,幾乎與東京國際影展同步,但在2012年結束。1985年時,台灣還在戒嚴,過去的日本女性影展曾是我們學習的對象,但它卻再2012年戛然而止。這當中的原因我也很好奇,只是今天沒有時間深入。不過有趣的是,去年東京影展又重新放映了這部電影,並舉辦了一場跨世代導演對談的研討會,我覺得這可能也是一種新的跡象。 今天我們不僅與過去的女性導演產生了縱向的連結,也與日本電影史中的女性導演產生了橫向的交流。現在就先在這裡畫下句點,請大家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熊谷博子導演,以及她帶來的這部作品。 熊谷博子:謝謝大家這幾天的參與,我也從各位身上得到了許多感動與勇氣。應該是我才要感謝大家,真的非常謝謝。 范情:很多事情往往是結束、消失之後,才會讓人明白它的意義。我們現在其實還蠻幸運的,台灣女性影展已經來到第32屆。最後,我想請問熊谷博子導演,從您的經驗來看,女性影展的意義是什麼?可以給我們一些指教嗎? 熊谷博子:因為很少有機會,能讓一群女性工作者、電影工作者聚在一起。在這樣的場域裡,大家能夠有共同的空間分享彼此的資訊與感受。雖然外界有時會說:「這群人聚在一起就是在講壞話、發牢騷。」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這些人其實對現實狀況都有非常具體的意見。我覺得有這樣的場域,讓大家可以交換意見,進而得到啟發,思考我們下一步要怎麼走,然後再往前移動,這是非常重要的。 范情:謝謝導演。導演今天也帶來了第25屆東京國際女性影展的場刊給大家看。為什麼要有女性影展?因為它能讓我們看到女性的視角,看到女性真實的樣貌。而要讓這一切被看見,也需要觀眾的支持。請大家多多支持,謝謝大家。
時間:2025 年 10 月 19 日 地點:財團法人三創育成基金會(共想咖啡吧!) 主持人:女性影展策展人 陳慧穎 主講:克萊爾.阿瑟頓 文字紀錄:楊昀鑫 慧穎:謝謝大家今天來到大師講堂。克萊爾.阿瑟頓從 1980 年代就已經開始從事剪輯,從IMDb 上的數字可以看到她剪輯過 50 部以上的作品,但我相信一定更多。我剛剛初步問了阿瑟頓,知不知道她自己參與了多少部影片?她其實也有點不太清楚。 與艾克曼合作外,阿瑟頓也跟無數資深導演、新銳導演合作。參與作品類型橫跨劇情、紀錄、實驗。除了電影外,她也有參與一些錄像裝置創作。錄像裝置的合作,則是從跟香妲艾克曼合作時就已經開始。 2019 年時,阿瑟頓在盧卡諾影展獲頒一個專門給幕後影視從業人員的獎項——Vision Award Ticinomoda。這是非常重要的肯定,她更是首位獲得此獎項的女性。 今天實在很開心能夠邀請她進行大師講座。這個講座是搭配今年的【焦點影人:香妲艾克曼】。我想那我們先從阿瑟頓跟香妲之間的合作開始聊。 初識艾克曼 慧穎:在《故鄉在彼方》(Là-bas) 的映後座談, 阿瑟頓有簡單提到,最一開始跟香妲合作是《Letters Home》(1986),她們認識的機緣跟她在西蒙波娃影視中心工作有關。 先請阿瑟頓從她最一開始跟香妲的相遇開始。請問妳第一次接觸香妲時,對她的第一印象是什麼?以及是怎麼樣的契機,開始發現自己好像可以試試看剪輯這件事? 阿瑟頓:謝謝大家來今晚的講座,也謝謝慧穎的介紹。我跟香妲是在 1984 年認識的,當時我們一起做一部舞台劇的拍攝。那時候我是被派去擔任攝影技術層面的協助。請我去的是黛芬・賽麗格(Delphine Seyrig),一位相當有名的女演員(有參演艾克曼的《珍妮德爾曼》,本身也是導演)。 我過去後,就在現場架腳架。攝影器材都架好了,本來應該是香妲自己要來拍,我幫她對焦。但在拍了兩分鐘後,她就覺得今天感覺不對,於是就請我拍,改由她來負責對焦。 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我當然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機會發生,我也非常驚訝。而且當時我很年輕,才21歲,真的沒有料到會如此榮幸。但我當下沒有想太多,就專心在我的拍攝工作上。 非常有趣的是,每次我的鏡頭可能想要往左轉、往右轉,或想要 zoom in 特寫某個地方時,香妲都正好要給我下一樣的指令。很快地我們就發現——我在這邊引用她當初說的——我們在同一個時間都會感受到一樣的東西、想到一樣的想法。在拍攝結束後,她跑去跟黛芬・賽麗格說:「今天這個小朋友是誰?我覺得她很棒,我想要繼續跟她合作。」這就是我跟香妲相遇的故事。 我自己也蠻喜歡我們相遇的這段故事。第一,當然是因為這對我來說很有意義、很動人;第二是,我想,透過這個故事,大家也可以稍微一窺香妲的為人,以及她的工作方式。因為香妲當時完全沒有先過問我的學歷或工作經驗,她就是全然地相信,那個相遇的當下帶給她的直覺和感受。而我也很喜歡她沒有過問我的背景或學歷,她就是很相信,覺得很喜歡我這個人、很欣賞,想要跟我合作。我想,從這一點大家就可以看出香妲這個人的為人與個性。 當然,在相遇後,我們開始一起合作了非常多不同的作品。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直都保持像剛才說的,非常單純、純粹的合作關係。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每次的意見都是百分之百一樣的,而是「我們想要把電影帶到什麼地方」這方面的想法,是一直都很一致的。 香妲她很喜歡用兩個小故事談我跟她的合作關係。第一個故事是,我們會一起看拍攝下來的各種素材,在看的時候,我們需要決定這顆鏡頭要留多長、什麼時候要喊卡。有趣的是,我們之間有個小遊戲,如果我們覺得時間到了、可以剪了就要拍一下桌子,如果我們手拍下去那個時刻是一樣的,代表我們的想法是非常同步的。 至於第二個小故事,因為我們通常是在早上一起看素材,有的時候針對片段的長度,我會覺得太長,而她覺得太短。即便我們兩個的意見不一樣,香妲認為這代表我們還是有一定的共識——也就是我們兩個都覺得這個片段的長度是不對的。 在今天《奧邁耶的癡夢》(La Folie Almayer) 的映後座談,我有回答關於剪接和電影節奏韻律的問題,這邊就先稍微再提一下。關於感覺對、還是不對,我認為真的要做了才會知道。而過程中要全然的相信自己的感受,自問:「這個感覺對嗎?」如果不對的話,是太長還是太短?並且要不斷的去嘗試,也適時的遺忘,並重新發現。 慧穎:香妲的作品當中確實充滿了韻律與節奏,聽阿瑟頓分享工作過程中有這樣的——可以說小遊戲也好,或是這樣的默契,真的很不可思議。 與艾克曼的工作模式 慧穎:阿瑟頓跟艾克曼相遇在 1980 年代,也就是艾克曼已經拍出《珍妮德爾曼》 (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 了,簡單來說,他們相識是在艾克曼已經成名之後。下午《奧邁耶的癡夢》映後時,阿瑟頓也有簡單提到,他們合作的《巴黎情人,紐約沙發》(A Couch in New York) 已經算是一個蠻大的劇情片製作,香妲需要去說服各方,請阿瑟頓來擔任剪輯師是個正確的選擇。從這些小小的點滴,都可以感受到剛剛阿瑟頓所講的「信任」。 除了剛剛先談到的一點與艾克曼的合作過程,想進一步詢問,因您跟香妲合作多年來累積了非常深厚的默契,是否可以簡單的分享妳們的工作模式?除了早上看毛片或素材之外,請再多分享妳們又是如何在剪輯室當中梳理,並找到一個切入點的呢?以及根據我曾看到的訪談,很有趣的是,香妲從來不會說「我有一個想法」,而是會說「我有一個什麼樣的感覺......」。您跟香妲之間的溝通方式令人好奇。妳們是如何談論眼前所看到的素材? 阿瑟頓:我想分享我們合作《巴黎情人,紐約沙發》的故事,不曉得在座各位知不知道?我其實是半個美國人。這件事情不是非常重要,但跟我即將說的故事有關。 《巴黎情人,紐約沙發》一開始的設定是個「浪漫喜劇」,片子剪出來後,製片都非常喜歡。可是到了發行商這一關,才遇到了一些麻煩,他們覺得這不是浪漫喜劇,因為它開場的地方看起來更像部「驚悚懸疑片」。這也是我喜歡香妲的地方,她在《奧邁耶的癡夢》開場也帶給人這種令人摸不著頭緒的感覺。總之,發行商就回頭跟香妲說:「請妳跟一個美國的剪輯師合作。」他們可能覺得剪輯風格的差異來自國籍或是文化問題。然後,香妲就回答他們:「但我的剪輯師就是美國人啊!」我很喜歡她這樣回答。 在剪輯工作上,她的工作方式其實不是每次都一模一樣。有些電影會讓她比較緊張,但有些她就會比較放鬆。不過,她一向都是個非常直率、也非常單純的人。她如果那一天特別不耐煩,或者很累、想慢慢來,其實我都感覺得出來。她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很順利地表達出自己的感受,但她會用各種方式讓我知道她的狀態。 比如說,有些片她可能會覺得,在剪輯這部片的過程中,我們每天都要出去吃午餐。她是一個很容易餓的人,大概十一點半肚子就會開始餓、想吃午餐,通常我們就會去吃義大利麵。有時候,她甚至一天會吃兩頓早餐。如果那天沒有那麼餓,第二頓可能就只吃一半。有些日子,她也會特別想早點休息、早點睡。 我們一起看素材的時候,通常是在她家。她家有兩層樓,因為家裡的東西常常搬來搬去,有時候素材是在樓上看,有時候是在樓下,她如果想要休息就會去另一層樓。她在剪輯某部片時,也曾決定每天都要自己煮飯。於是,她就會忙進忙出,去買東西、煮菜。 她真的是一個非常單純,也非常慷慨、樂於分享的人。像我們兩個都會抽菸,但我個人通常是下午才會抽。如果我早上看見她在抽菸,她還會特地跑到窗邊去搧風,說:「妳看,我有把空氣弄好比較好喔!」還有,我剪接時如果一直待在黑暗裡,我的眼睛會不太舒服,有時候會需要一點光線。但她家的燈泡總是會有些狀況,她就會說:「欸,我剛好要去買燈泡,要來修一下燈。」她其實是一個滿好玩、也滿好笑的人。但一旦開始工作,她就會非常專注。 而一旦進入工作模式,可以感覺到她是用整個身體在經歷、在體驗這些畫面。有時情感會非常強烈,有時則比較平靜。有時會看到她離畫面很近,有時她又會刻意拉開一點距離。像《奧邁耶的癡夢》當中,有場戲是女主角妮娜在船上說,她不知道怎麼學會乖巧聽話。香妲當時在看著這段毛片,就對我說:「我發現我是為了這場戲才拍這部片的。」她在看素材的過程中,常常會重新發現一些她之前沒有注意到,或者沒有意識到的東西。她總是保持非常開放的心態,也非常樂於接收這些未知的東西,所帶來的驚喜。 她也從來不會對我說「妳應該要這樣做」。她在意的,是我們兩個對影像的感受是不是一致的。只要我們都覺得「對了」,那就是對了;但如果我們的感受出現落差,那也代表這邊還有需要調整或修正的地方。 在看素材時,我們幾乎一直都待在同一個空間,一起經歷這個過程。但實際進入剪輯階段,有時我會需要一點自己的時間,自己先處理剪輯再給她看。但她一定會跟我一起看,而「陪我一起看」這件事,對我來說也非常重要。她在這個過程中講出的話,不只對我來說很重要,常常也會給我很大的幫助。很難明確說她做了什麼,但光是她觀看的方式,就能給我很清楚的方向和指引。 談到我和香妲合作的故事,真的多到講不完。每次一聊,又想到一些新的事情。但我覺得有一點非常重要,很想跟大家分享——也就是香妲從來不會愛上她的影像,她也不會對特定影像有任何執著。即便她有喜歡這場戲,就算是一場再重要的戲或畫面,她也總是保持開放的態度,隨時抱著可能會把它剪掉的心態,不會在心中過度去美化它們,也不會過度崇拜它們,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在剪接的過程中,曾多次嘗試把很重要的戲拿掉,然後去感受、去觀察,這樣處理是否會帶來更強烈的情感?還是反而沒有。有時候我們也不確定,有時會放回去,有時會先拿掉,也許放個兩個禮拜後再放回去,有時在那時你才會真正明白它的重要性和意義性,以及為何要特別為這場戲保留空間。像在剪剛才提到的《巴黎情人,紐約沙發》(A Couch in New York) 時,我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我覺得這點真的很關鍵,香妲從來不會執著於任何特定的戲或影像。對她來說,這部電影最終完成的全貌永遠是最重要的,電影的全貌勝過任何一個單一畫面。 合作作品中最挑戰與困難的經驗:《巴黎情人,紐約沙發》、《東方》 慧穎:您和香妲從很早期就開始一起創作,也陸續合作了許多重要的作品,除了剛剛提到的劇情片,其中還有像是《東方》(D’Est)、《國界彼方》(From the Other Side)、《故鄉在彼方》(Là-bas)等紀錄片,也橫跨了不同的形式。想請阿瑟頓分享,在這些合作經驗裡,有沒有哪一部作品對妳來說特別具有挑戰性?或在剪輯過程中遇到很辛苦的經驗呢? 阿瑟頓:如果說到比較有挑戰或覺得比較困難的,要回到《巴黎情人紐約沙發》(A Couch in New York) 這部作品。這是一部預算非常大的劇情片,因為女主角非常有名,片酬也很高。相對地,也讓香妲感到很緊張、承受了很多壓力。 那時候製片跟她說:「妳是個天才,一定可以創造出在商業上非常成功的電影。」她聽了很開心,香妲自己也很希望能拍出一部商業上成功的片子。但對她來說,對商業成功的渴望,並沒有超過、也沒有強過她自己和電影之間的關係。她和電影的關係,還是最重要的。 在剪輯的過程中,我們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當時製片還特別要求我們換配樂,用不同的音樂試試看。因為那時不像現在可以直接傳檔案,他們給了我們一大堆錄音帶。我拿了那些錄音帶給香妲,結果她不想聽。我就說:「等製片問起來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說『我們聽過了,覺得不適合』。」她當時答應我說好,結果等製片真的來了,一進門,香妲就頭抬高高的對他說:「我告訴你,我們根本就沒聽你們給的音樂!」我在旁邊覺得又緊張又好笑。 從這個故事,大家也可以看出她的個性。我覺得這很重要,你如果沒有自信、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是沒有辦法拍出好電影的。很多時候,沒有強大的自信,就沒有辦法去回答來自外界的質疑。他們會問你:「你確定這樣是對的嗎?」、「你確定這樣做是最好的嗎?」如果你陷入自我懷疑,你可能連你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 因此,有這樣一個很強大、很篤定的心智在工作過程中,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有時可能會覺得很舉步維艱、很難進行下去;有時可能會覺得需要放慢腳步、需要多點時間。總是會碰到很多質疑,不管來自外界或是自己的。 我還記得在創作裝置藝術作品《東方,在虛構的邊界》(D'Est, au bord de la fiction,1995)時,這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我盡量簡單說明。《東方》本來是香妲在東歐拍的一部電影,電影裡是完全沒有台詞的。當初我們一起做這個裝置藝術,就是把電影轉換成空間裡的影像裝置。這對我來說,就是全新的挑戰。 我們把電影分成 24 個小部分,在不同的螢幕上面播——我現在說的是簡單版,實際上更複雜,只是讓大家快速理解——由於我們以往都是「在時間上做剪輯」,但這次,我們等於是在「在空間上做剪輯」。很快地,我們就發現好像缺少了什麼東西。因為在電影這個表現形式中,時間是線性的,會有開場、中間、結尾,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時間順序,慢慢建構出一些張力。但在這個處理空間的裝置裡,它比較像是以四分鐘重複播放的影像,因此這個張力是在於「空間的穿越」(voyage of the space)。 回到剛剛說的,我們覺得它少了些什麼,於是發現,它缺少的正是「另一個空間」——畢竟我們是在「空間上做剪輯」,我們感覺它需要用文字、用語言來表達。但到這個階段才有這樣的發現,就讓執行非常得困難,因為電影的版本本來是沒有文字的。而且,香妲之前也從來沒有用文字去描述過,她想在《東方》這部電影,或這些影像裡,帶給大家什麼樣的情感。這也是另一個,可以讓大家知道我們是怎麼合作的例子。 剪輯之外的策展經驗 慧穎:很高興阿瑟頓提到參與錄像裝置的合作經驗。其實香妲的作品,算是蠻早進入美術館的。而《東方》這件作品,剛好今年在北美館的〈開放式結局〉也有播放,也許在座有些觀眾剛好有看到。 阿瑟頓在將艾克曼時間性的作品,形塑成錄像版本這件事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近期,阿瑟頓有策劃一個關於香妲的展覽,叫做《Face the Image》。很巧合的是,其中一個展出剛好是這週閉展。雖然是很小的巧合,但也可以看出阿瑟頓非常活躍地參與這些工作——從電影,再到思考它在另一個場域當中如何呈現。 也想請阿瑟頓稍微聊聊這個部分,您在思考不同媒介時,又是如何展開的? 阿瑟頓:當初有個美術館請香妲做一個可以在藝廊或藝術空間展出的作品,她也欣然接受了。因為她一直都很喜歡接受新的挑戰,但她跟美術館說,為了做這個作品,她要先拍個電影。當年找資金並沒有像現在這麼困難,所以找到資金後,她就在兩年後完成了《東方》 這部電影。 電影拍完後,美術館跟她說:「我們現在有錢來做這個裝置藝術了。」但其實,香妲早就完全忘記,直到人家回頭來找她才想起來。就像我剛才提到,她是個很好笑、很好玩的人。很多時候我們在聊她時,都只講比較嚴肅的話題,比如政治與歷史,常常會忘記她這一面。我也希望讓大家知道,她這個人的個性其實是很好玩的。 在拍《東方》之前,她有十年的時間一直很想去東歐,所以也是個機緣。這部片就是穿越東歐一路到莫斯科的旅程。但也因為我們都很喜歡這部片,因此當我們要將它做成裝置藝術時,過程變得更加困難、有點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一開始,我們先拷貝了一份影帶,然後再從這份影帶又拷貝一份。我就將手上兩份拷貝放在不同的螢幕上,併置去觀看。我想看看同一部片在同時間出現不同的影像會有什麼效果,有時左右螢幕上會出現一樣的影像,有時一邊比另一邊還要延遲;有時一邊是靜止的,另一邊則是移動的動態畫面。 後來我們發現,還需要第三個元素。只有兩個(螢幕)的話,不是重複、一樣,就是對比,我們需要第三個去增加層次。最後呈現出來,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樣子(實際總共24個+1個螢幕,分成8排,每3個螢幕併置)。這在技術上也非常困難,因為要同時呈現不同的螢幕播放不同的內容,需要做很多拷貝。 但香妲很喜歡,也很享受這個創作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為此發展了一些新的技術,而她也從中感受到自由和自信。對她來說,每次做這種裝置藝術委託,她都非常開心,因為這也讓她重新去發現,也像是回到當年拍《珍妮德爾曼》時,那種年輕、無畏、充滿自信的感覺,甚至還不太明白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情,那同等對事情的重新發現感。香妲很喜歡裝置藝術帶給她的自由,很重要的一點是,她可以在不受拘束的情況下,去表達對這個世界很多的看法和想法。而當我們把影像剪成更短的片段時,它散發出來的訊息其實更強烈。 我剛才提到,覺得好像少了什麼,後來結論是,我們需要另一個空間。這部作品已經有兩個空間:第一個是16釐米的影帶(即電影版),第二個是同時播放的24個螢幕。那麼第三個空間,我們當時覺得需要加入文字。(加入阿瑟頓所說的第三個空間,最終《東方,在虛構的邊界》這件作品,是一個25頻道錄像裝置) 這也是香妲第一次,她想用文字表達這些影像激起了她什麼樣的情感、讓她想到了哪些事情。其實影像本身很單純,比如很多人在等公車的畫面,但她在觀看時,可能會想到其他人、其他事,或是些與歷史有關的情況。 因此,她寫下了在我看來最美的東西之一,《The Twenty-fifth Image》(Le vingt-cinquième écran)。它叫做第25個畫面,因為是第25個螢幕上,配合抽象感的影像播放。 我也簡短提一下我的策展經驗。四年前,我受邀在西班牙巴塞隆納策劃一個跟香妲有關的展覽,現在剛好正在巴斯克地區展出,但只到明天。這麼多年來,其他關於香妲的展覽我都有參與,因為我知道要怎麼呈現她的作品。但當我自己當策展人時,感受完全不同,對我來說,好像又是一種「剪輯」(edit)的工作,因為我必須去思考不同元素在空間中的呈現方式,去感受它們。 我非常喜歡這個過程,會一再回到空間裡去感受並嘗試新的方式,去想像、去調整。在這次的展覽叫做《Face the Image》。雖然展覽只到明天,但這個網站會持續存在,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站查看,上頭有英文、西班牙語和巴斯克語版本。 這是展覽的小冊子,裡面有很多內容(現場展示冊子)。主辦方做了我的專訪,我在這之中非常鉅細彌遺地講述、說明,當初這個展覽是怎麼策劃跟執行的,內容都收入其中。在這邊,我還想跟大家分享小冊子裡的一幅水墨畫。當時編輯問我最喜歡哪一幅水墨畫,我選了這一幅(展示該頁圖片),於是編輯就把它編進了小冊子裡。畫裡面雖然沒有太多額外的訊息,但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感受它帶來的情感跟情緒。 【Q&A】 Q1:我想請教的是,法國著名演員黛芬·賽麗格,她不但演出過亞倫·雷奈的作品《去年在馬倫巴》(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1961)以及《穆里愛》(Muriel ou le Temps d'un retour,1963),她自己也導演過一些紀錄片,這些紀錄片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於關懷女性,尤其是女性主義和女同志議題。請問,當初香妲邀請這位女演員主演,是因為欣賞她作為傑出、偉大的演員,還是因為認同她對女性主義和女同志議題的關懷與貢獻? 阿瑟頓:關於選角的問題,當初香妲希望由黛芬・賽麗格來演出,正是因為黛芬・賽麗格作為一位女演員的狀態。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她是知名或一線女星,而是黛芬・賽麗格更是一位Diva級的女演員,因此她希望要這樣氣質的演員,來演出片中角色,從事洗碗或做家事等等,她認為這會帶來很強烈的感受。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黛芬・賽麗格的一舉手一投足都非常優雅。選擇她來演出這些女性角色,也在某種程度上也呼應她們的角色特質。 Q2:《奧邁耶的癡夢》映後座談中,阿瑟頓提到對「紀錄片」這個詞,某些部分還有所保留、想再多思考。也提到,拍攝過程中仍有很多創造性的空間。想請問,能否就這一點,分享得更深入或更廣一些,談談她對創作過程的思考與觀察? 阿瑟頓:謝謝您的提問。我下午有提到,其實我不是很喜歡「紀錄片」這個詞。尤其在法文裡,對不熟悉電影圈的人來說,這個詞可能會讓人覺得這是一部只講特定資訊或主題的電影,有時候我不太喜歡這樣的定義。 我自己其實不太喜歡把電影硬性區分為紀錄片、劇情片。對我來說,電影是一個活的、當下的體驗,它能帶給觀眾很多自由。當然,也有另一種電影,它比較含蓄、規矩,比較沒有那麼自由,那對我來說相對就沒有那麼有趣了。 我認為電影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參與。我們創造一個空間,讓觀眾在裡面去思考,陳述自己對這件事的想法與觀點。而製作電影、讓它被觀看,其實也是一種參與政治的行為。 Q3:因為阿瑟頓剛剛有提到,香妲其實是一個非常天真、幽默的人,我想延伸問一下,您過去有沒有合作過性格和香妲非常不同的創作者?如果有的話,在那樣不同的相處模式下,會不會影響到妳觀看素材、或是在剪輯時思考影像的方式?還是說這樣的差異也會反映在最後完成的作品裡? 阿瑟頓:當然,每次和不同導演合作的模式都不一樣。我這個人的好奇心比較重,所以我一直想去發掘、觀察新的事物,不管是人、空間,甚至是說話的語氣等等。每一次和不同導演合作不同作品,其實都是段不一樣的旅程。 比如說,香妲離開之後一年,我就認識了Éric Baudelaire,他的個性和香妲非常不同,但我們也建立了很深厚、緊密的合作關係。和他工作的時候,他給我的訊息可能就只有他說出來或畫出來的那些部分,但我必須用更多的力氣去想像他沒有明說的東西,然後透過這種方式去理解他、理解作品。 我覺得,不管和哪一位導演合作,最重要的還是我們一起做剪輯、一起看片、一起創造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整個創作最核心、最珍貴的部分。 最後,我想再回應一下。剛才有提到王兵導演的作品,其實對我來說,他和香妲的電影都在處理生死這類的議題。雖然他的個性和香妲很不一樣,但我從他身上感受到的生命力和投入的程度,其實同樣非常強烈。
片名:《不存在的從前從前》 場次:10/19(日)10:10 光點華山 二廳 主持人:影展主席 史惟筑 與談人: 青少年選片人 劉柏廷、林子筠、張郁萱、王翊甯、呂秉鴻、林巧婕、宋朋澤、陳璿仁 文字記錄:王湘筠 主持人:這部片也代表了我們今年影展的主題「破風景」,面對世界上有這麼多衝突、戰爭和緊張局勢,我們可以看到《不存在的從前從前》片中,四位女性如何去面對這整個世界的變化。大家等一下可以跟我們的選片人團隊一起分享。 我自己很喜歡裡面一句話,在戰爭時其中一位女主角在鋪她的床,她說:「每天維持日常的那種清潔,還是很重要。」不管世界發生什麼事,我們如何能夠持續日常的運作狀態、我們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都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會有這樣的場次,是因為女性影展從去年開始跟富邦文教基金會合辦了青少年人的選片活動。我們是在暑假的時候有一系列的課程,這次有二十二位同學一起參與,在三天時間大家一起看了七部片,其中有長片也有短片。這過程也包含了電影解析課程,邀請了策展人跟學生分享,女性影展的編制與組織、如何辦一個影展。 過程裡這些同學非常努力的集思廣益,也在這七部片裡,他選出一部長片跟一部短片。我相信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有很多的討論,我不知道有沒有到很激烈,但大家一定都很熱切地分享自己的想法。我們現在來就歡迎我們青少年選片團隊的代表來跟我們分享,他們為什麼在這七部片中,選了這部《不存在的從前從前》。先歡迎兩位同學,也請兩位先自我介紹。 子筠:大家好,我是子筠。我們會選《不存在的從前從前》是因為它跳脫了男性凝視的視角,由女性切入戰爭的主題,帶領我們去觀看這個故事。這個故事跟我們之間之所以有很大的共鳴,是因為台灣這個地方也有點處在這樣的狀態。比較特別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片中好像有出現導演的身影?這點也是我們覺得很特別的。像我自己也有在創作,拍紀錄片時,都會去考慮導演介入的成分。導演是旁觀者,還是她要出現在這個影片中多少,去呈現她的故事?她疑似有出現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等下也可以討論看看。 柏廷:我也是這次的選片人代表,我是柏廷,但都差不多快被子筠講完了(笑)。 我這邊再分享一些剛才講的部分,關於「導演在一部紀錄片裡介入的成分到底要有多少?」我在看的時候,也覺得非常不一樣。導演在裡面好像不只是一個拍攝者、不只是一個負責把這件事記錄下來的人,她好像也是這部片的第五個主角。 另外一個部分,畢竟是女性影展選出來的片子,就會發現——我自己覺得蠻不錯的點——像剛才講的比較少男性(凝視)的視角。如果從一般的戰爭紀錄片來看,好像會有一大部分在講到底多殘忍,或是到底戰爭剝奪了什麼東西,但這部片其實講了蠻多一般紀錄片不會去講的部分。 還有一點,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不存在的從前從前》的視角以及鏡頭真的非常漂亮。我們第一次觀影的時候,會覺得「欸,它真的是一部紀錄片嗎?還是它其實是一部set好的片子?」。關於這部分,到底紀錄片該不該set,或怎樣的鏡頭才是紀錄片該存在的?我們在選片的時候也做了蠻多討論。 最後是關於我們選這部片的討論。《不存在的從前從前》是我們幾乎所有人都非常認同,認為很適合推薦給大家看的一部片。其他部就有比較多的小爭論,有大家立場不太一樣的地方,或是大家感受有些不同。而《不存在的從前從前》是我們青少年選片人五星推薦(的)一部片!我覺得還是有蠻多東西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很值得回味以及找一些共鳴。 主持人:柏廷剛才有提到,這是女性影展選出來的一部片。因為大家來到的是女性影展,不知道在場同學,除了策展團隊外,有沒有其他人看過女性影展? 你們都是第一次進到女性影展的電影院裡嗎?真的太好了。那邊(有人舉手),你們來幾年了?第2年了,太好了。 昨天我在女影看完電影已經是11點半,我就跟幾個朋友,也是女影的工作人員,邊走邊聊電影。走著,走著,旁邊就有一個女生,她上了捷運的時候跟我們說,「我可以參與妳們的討論嗎?」她說她2023年第一次看女影,因為真的很喜歡,後來就每年都來看女影。她告訴我們,那一年她高二,所以我覺得辦這樣的活動,其實就是希望讓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可以有這樣的平台接觸到多元類型的電影。 現在大部分商業電影院能看的電影類型很有限,大家在女性影展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尤其是女性觀點的電影。我認為青少年是很棒的一個階段,那是你們在正在尋找認同、建立自我價值,很重要的一個階段。當女性影展可以在高中時期就進入到你們的生活,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珍貴的事。 接下來將重點回到青少年選片人之間的交流。不知道現場的大家看完這部片,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在場的兩位代表,或是其他的選片人代表?比方他們為什麼選這部片,或者看完這部片有什麼想法,都歡迎大家利用這個機會交流。又或者,大家剛才聽他們講的觀點之後,覺得「紀錄片本來就可以這樣啊,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也可以來挑戰他們。 希望在電影院這個場合,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思辯,分享看完的想法,或你最喜歡哪個角色,對哪一個場景印象最深刻?像《不存在的從前從前》的故事,它分為戰爭前跟戰爭後,大家不覺得整個世界的變化都是這樣子的嗎?就像我們現在生活在經歷Covid-19後,未來還會有什麼挑戰,我們也不知道。這些人在戰爭前跟戰爭後,有什麼樣的改變,或者沒有什麼改變,就持續維持他們的日常生活面對挑戰。 青少年選片邏輯與方式分享 子筠:我來多講一點關於我們的選片。大家可能會好奇我們怎麼進行這個選片,為什麼今天是播這部。那時候,我們有上了還蠻密集的課,在一段時間像評審一樣瘋狂的看了長、短片,最後要選出一部長片在這邊播放。 選片的時候,我們要先去了解女性影展是什麼。台灣其實有很多影展,不只女影,可能有金馬、金穗等很多影展。女影是做什麼的?在這之中,我們就先去了解,原來女影可能是在講述女性的故事,透過女性的視角,告訴這個世界一些什麼。因此,我們在選片的時候就要緊扣這個主題,也剛好我們覺得這一部片是最符合女影的。 最近不是才在頒金鐘獎嗎?有時候我會看到一些人會質疑,評審討論的過程是不是不太公平。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選片的邏輯,我們就坐在一個圓桌,然後每個人都有好幾次投票跟發表的機會。每一次投票跟發表,大家就要分享自己選的是什麼片、為什麼選這部片⋯⋯這就是有互相激烈交鋒的時刻。 絕對會有私心的喜好,或自己在看片的觀點,但因為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見解,加上每個人的背景不盡相同,會用不同的視角去解讀一部片。也因此,會有很不一樣的交流跟碰撞,然後在最後會得出一個算是客觀,也最符合這個主題(女性影展)的一個片子。 柏廷:就是像剛剛說的,我們選片的時候,真的有蠻多激烈的碰撞。畢竟大家都來自不同的地方,有高中生、有大學生,大家的興趣、職業也都不一樣,會聽到跟自己不太一樣的觀點,甚至可能會有些不見得認同的部分。 主持人:以《不存在的從前從前》來講,有什麼觀點不一樣的地方? 柏廷:這部算是我們少數大家都互相認同的一部片。只要每次開始講,就會看到旁邊的人瘋狂點頭,會突然覺得好像有被認同的感覺。 主持人:可以多談一下,讓大家瘋狂點頭的最贊同的一點是什麼? 柏廷:一剛開始當然是從由淺入深的去討論,最淺的是我們都覺得,畫面怎麼可以這麼美?它真的是紀錄片嗎? 子筠:在這個紀錄片裡它保留了詩意去呈現。它雖然講戰爭,戰爭的畫面我們可能會想像比較是血肉淋漓之類的,但是它的畫面卻很美。 主持人:可能你們想像會有很多晃動啊,可是它卻每一個畫面都非常的沈靜。 子筠:它用很詩意的方式講了一個蠻沉重的故事,這點讓我們覺得很厲害。再來,就是它很符合女影的主題。 主持人:對你來說,女影到底是什麼?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柏廷:我們討論的時候,我有談到女影到底為什麼要存在、它的目的是什麼。其實會發現,我們選片團隊裡,好像男生特別的少。可能也蠻能理解的,因為是女性影展。 在選片的環節開始前,有關於女影存在的(課程)介紹,那時候有講到一個我蠻認同的。女影的存在,不一定只是單獨為女性開啟一個空間,而是因為在歷史脈絡上,關於電影或是選片上,女性得獎的機率比較小(應是指比例比較少),因此才會開設這樣一個平台給女性。這是我個人的理解,但我也不確定。 回到《不存在的從前從前》,它很扣合女影的是它的主角是以四個女性出發,加上導演算是五個,裡面就蠻少看到男性的聲音或是視角出現。 Q1:我們是去年的青少年選片人,去年選的是《烽火下的愛與隔閡》,也一樣是戰爭與女性的議題。蠻好奇你們怎麼會選出這樣的題材的? 柏廷:我記得大家有一個出發點是,如果以初次來觀影的觀眾來說,這會是比較好懂、比較好理解的片。像我們看的其中一部短片《石頭狂想曲》,它是一部動畫片,稍微比較抽象一點,可能會有比較多不一樣的理解空間。我們那時候是覺得,《不存在的從前從前》會比較好理解、比較吃得消。 子筠:我們確實在選片時有去思考,剛進入這個議題性作品的觀眾,會吃不吃得消?這次片單中有一部長片《兩個海倫》,這是我必生看過最難的片!大家看完之後就互相問,你看得懂嗎、你看得懂嗎?沒什麼人看得懂。那怎麼辦?沒有這麼深入接觸特定議題作品的觀眾會想看這麼難的片嗎?於是,我們就取了一個中間值,大家最能理解,也最符合女性的就是這一部片。 Q2:你們覺得這部片對台灣的觀眾來說,最希望我們大家可以反思的事是什麼? 子筠:我覺得電影要改變世界是很困難的事,但是它有力量可以讓我們反思或是帶來一些影響。對台灣的觀眾來講,我相信看完可能會有一種更大的感觸,是更想去珍惜,或是守護我們這塊土地。因為它也有可能在明天、後天或是下一秒,就不屬於我們自己了,我們的回憶也有可能在下一秒就遺失。我覺得這部電影教會我們的,就是珍惜所有,然後珍惜我們的土地。 Q3(其中一位青少年選片人):我今天有帶朋友來看,她有點看不懂《不存在的從前從前》的時間線。對於初次看電影或這種議題性電影的人,會不會選《維多利亞的鳥日子》更好? 因為我在選片時是《維多利亞的鳥日子》的支持者,雖然內心可能還是有點想要支持那部,但還是很謝謝你們有把我們選片人的心聲講出來。 柏廷:如果大家對《維多利亞的鳥日子》有興趣的話,等一下還會有其他介紹。之後影展也還有放映場次,可以去支持一下,幫她翻轉一下她支持的片子。 主持人:接下來我們請選片團隊來一一上台,跟我們用一句話,介紹你們這一次看到的七部影片。 《然而餘音未葬》 翊甯:我們共同認同的是,它用陰性力量的方式去對抗陽性的戰爭。它還有再加上年齡層,老、中、青三代對於戰爭的看法,以及不同人群支持戰爭跟反對戰爭的人的看法。 《石頭狂想曲》 郁萱:這部動畫是在說一顆石頭,它的心理狀態以及情緒流動。它用了一些元素,比如說馬、黑影、玫瑰等,去映照出在青少年階段可能會經歷的身份認同掙扎或是矛盾。選片之中,大家也都蠻認同的,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不同的生命歷程中,帶入自己的經驗。當時大家對動畫中的每個物品,像是玫瑰的象徵是什麼?都有不同的反思。在看完影片之後也可以討論,因為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 《喵的通話中》 朋澤:它在談的是關於多元性別的主題,但我覺得它更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跟大家平常的觀影經驗可能會不太一樣。不管在畫幅的選擇,還是各種元素、節奏的編排上,都會跟大家看過的影像──不管是電影或是短片──有很大的差別。我覺得它是個很適合看完後好好思考,每個元素為什麼會出現?每個節奏的安排,為什麼要讓他快或者慢?很值得思考的一部片。 《犬靈之詩》 璿仁:這部片講述了一個家庭旅遊,其中展現了這個家庭之間的裂縫。裡面用到了很多長鏡頭,我覺得那些長鏡頭表現了整部片後段空間的寧靜,也讓觀眾可以投入體驗那個空間,還有氛圍。故事中的家庭也可以反映到我們自身的經驗,去轉換思考自己對家庭的理解。 《兩個海倫》 秉鴻:先問一下,大家有沒有follow到代孕這個議題?如果有的話,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的爭議點是放在生殖上還是母職上。《兩個海倫》這部片用兩個名為海倫的人去詮釋了,關於生殖跟母職這兩件事的衝突。它真的很難,但在這個很難的前提之下,大家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解讀這部片。歡迎大家多去看,然後可以討論自己對於影片當中各種意象的展現。 《維多利亞的鳥日子》 巧婕:這部片聚焦在一個印度女性的視角,這個女性就是維多利亞——我們主角本人。故事講述她在美容院上班的一天中所發生的事,有一些忙碌的日常跟對話。可以透過這些日常對話中,看見女性在印度種姓制度下,以及一些父權壓迫的影響。
時間:2025年10月09日 地點:玲瓏Sue藝空間 主持人:女性影展策展人 陳慧穎 主講:藍貝芝│C-LAB CREATORS沃時文化「擴延檔案的維度——台灣同志史的有機串連與數位策展」計畫成員、陳佩甄│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文字紀錄:魏安琪、彭湘 慧穎:今天非常開心,在這個微微飄雨的夜晚、又是連假前夕,仍有這麼多朋友來到現場。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兩位優秀的講師,陳佩甄老師與貝芝老師。佩甄老師是政大台文所的副教授,近年研究主要聚焦於臺韓女性主義的冷戰系譜與酷兒文化史;而貝芝老師則是資深的劇場工作者,長期從事各類製作與策展,並擁有豐富的戲劇教學經驗,同時也是臺灣女性影像學會的理事之一。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兩位嘉賓。主要會談到今年的一個單元——【唱,或者不唱】。女性影展每一年都會設有一個常態性單元「酷兒單元」,而名稱會隨著每年的影片策劃而有所不同。今年的主題正是「唱,或者不唱」。除了這個單元之外,今年還特別加贈了一個小小的 bonus,也就是與 XPOSED 柏林酷兒影展合作的交換單元。這個交換單元也一併收錄在【唱,或者不唱】的酷兒單元之中。 此外,今年的短片單元(短短)中也收錄了許多與酷兒議題相關的短片,等下兩位老師也會提到這部分。我就不多說,把時間交給兩位,謝謝。 佩甄:很高興大家在連假前,外面還飄著雨來到這。我今年第一次幫女性影展和酷兒單元寫介紹專文,接著答應了這場座談。我認為這是個非常困難的座談,畢竟我在學院裡,大多時候只需要針對一個主題深入講解 ,但這次我們必須看將近20部電影,想辦法在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讓大家能掌握全貌、心生想買票的欲望,責任很重大。 在幫忙寫專文的時候 ,開頭的地方我先點出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今年 2025年,也是1995年全球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 30週年。因此,今年影展與各種議題,對我而言都有一種歷史性的意義。今天我會從我們如何透過女性影展的作品、酷兒專題,乃至於單元裡新進的這些作品,去觀察這三十年來全球性別議題的脈動與變化。 談【唱,或者不唱】單元選片 我們先從長片單元【唱,或者不唱】開始。本來這個單元共有六部片,如果有讀過我的專文,應該會注意到其中一部 1985年的作品(《愛的甘露》)很可惜未能播映,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在臺灣的影展再次看到! 今天要談的另外五部作品則較偏向紀錄片,而剛剛提到那部較早期的作品,其實是一部劇情片。這五部紀錄片正好呼應今年「性別主流化30週年」的豐碩成果,同時也揭示了整個性別運動在這三十年間所面臨的某種疲態,以及新議題被迫浮現的現象。因此,我希望特別談幾部對臺灣讀者與觀眾而言相對熟悉的議題。 《成家進行式》 佩甄:第一部《成家進行式》,我非常喜歡它的英文片名,它叫《Love Alone Can't Make a Child》。我們在談同婚的時候,不是會說「愛最大」、「愛可以戰勝仇恨」、或是「有愛就可以結婚」嗎?結婚之後你就會發現,「愛」沒有辦法幫我生小孩。這是一個德國的紀錄片,拍攝長達將近十幾年,記錄一對女同志想要透過人工生殖懷孕的過程。至於最後有沒有成功,歡迎大家去戲院欣賞。 因為我沒有想要生小孩,這部片一開始不會特別引起我興趣,但是看了之後發現整部片的情感濃度非常、非常深。說震撼倒不是,但就是會讓我很痛苦地回想以往的一些親密關係。在「後同婚時代」、性別主流化30年後的這個當下——尤其,台灣在2019年通過同婚後,我們在這一、兩年一直在掙扎跟辯論的就是生育問題。不管要透過什麼方式生,當然會牽扯到經濟,以及社會文化對於女性、男性——無論男同志或女同志——對於擁有小孩會有完全不同的認知或期待。這些都是台灣最近討論非常激烈的議題。 關於紀錄片的主角,這兩位在德國的女同志也蠻像我們身邊許多認識的朋友,可能是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之類的。她們的故事也牽涉到一個現實問題,生小孩這件事情,並不是真的只有「愛」就能成立。你需要金錢,也需要有人進入整個醫療系統,甚至要與醫療系統對抗。 而醫療的議題,其實正是我們在整個公民權運動之後延伸出來的重要面向。公民權運動銜接著80年代末期、以臺灣來說大概是90年代的「identity politics」(認同政治),也就是 gay 就是 gay,lesbian 就是 lesbian。到了90年代之後多了 Q,2000年後又加上 A、I,到了2010年後就出現了「plus」。「L、G、B、T、Q、A、I、+」是現在要在正式的場合表示「性少數」都要寫到的英文字母。 最近有些嘈雜的聲音,無論是女性主義運動內部,還是同志運動內部,這幾個英文字母所代表的群體,在2010年之後的運動中,比如後同婚時代的論述裡,開始產生張力。其中有個英文字母,在最近經常被target(針對),或引起一些反對聲音。大家知道是哪一個英文字母嗎?沒錯,是「T」(Transgender,跨性別)。 T有另外一個層面,就是T也是女同志裡比較陽剛的那個角色,英文會稱為Butch。其實在女同志的化內部,我很傷心的是,大家也出現了不那麼喜歡T這個標籤的文化。也就是,她們會認為兩個比較feminine(女性化)的女生在一起才是真的女同志啊。但在比較可見的範圍裡,不管是電影或戲劇中,女同志的配對還是多半呈現陽剛與陰柔的組合。這個文化,或說這種組合的方式,現在也有反對的聲音。 另外一個是Transgender的T。然後,現在也出現講「LGB就好了」的聲音——(對貝芝說)B(Bisexual,雙性戀者)還在喔!你說是無用標籤,但它現在還在喔——從 JK 羅琳對我們奧運選手的評論,到英國、蘇格蘭對生理女性定義的明確界定,這些都在這一年多來發生。跨性別的論述與張力,彷彿形成了一個全球共享的現象。而這一次【唱,或者不唱】單元裡的許多作品,以及接下來會提到的Xposed或【短短】單元中的多部作品,正正展現了女性影展作為社會溝通與議題開展平台的重要功能。今年收錄了非常多與跨性別相關的作品。 《虹色回擊》 佩甄:《虹色回擊》英文片名為《Hightened Scrutiny》,中文直譯是「高度審查」。整部片講的是美國的醫療系統,以及最高法院如何透過行政訴訟禁止青少年,也就是未成年者,進入醫療系統獲得醫療保險與資源,幫助他們在未成年階段選擇自己的性別。 這部片可以跟主角 Chase 一起感受到那種不安,他非常緊張——畢竟他是個即將被寫入歷史的人,他除了是第一個跨性別律師之外,他也很怕自己一個人會毀掉所有跨性別青少年的權益,整個重擔都在他身上。整部片可以看到他一直在murmur,不斷練習著他要上戰場去辯論的內容。 他們在 2023 年的三月提出抗告,高等法院在今年 6 月 18 號結果出來了。他們最後堅持讓各州可以自行決定,並認為禁止青少年或未成年使用性別轉換等各類醫療服務是合憲的,也就是說這樣的禁令並不違憲。所以,算是失敗吧。 影展是七、八月開始籌備的,而我是在知道結果之後才看這部片。我其實更加感激這部作品,因為它並不是以「我要戰勝什麼」為目的,而是非常細緻地呈現一個很official statement(官方聲明)。片中拍出了他準備上法庭辯論的過程,同時,我們能直接看到那些在未成年時期就非常明確知道自己想要轉換性別的當事人,也參與了這整部紀錄片的拍攝。 《酷兒解放曲》 佩甄:帶到一部比較輕鬆的作品,也就是《Queer as Punk》。這部我們兩個也都很喜歡。它呈現的是在臺灣或一般當代酷兒影像中比較少見的場景——東南亞,具體來說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穆斯林群體非常龐大,在整個東南亞的許多國家中,因為特定的宗教屬性,性別角色都受到深刻影響。我們在短短單元裡也會再提到其它相關作品。這部片讓人感受到的是,她們並不覺得自己不屬於那個文化,而是持續在與文化進行negotiate(協商),而她們所使用的方式,便是透過音樂。這部片的導演曾憶雯,展期也將會來到台灣。 主角非常可愛,我們其實也在這部片中跟他一起經歷了性別轉換。這部片透過龐克音樂、透過一起玩有趣的事情,在這些過程中讓我們去補足、或參與了一些溢出私人生活之外的事物。 這部片讓我感受到,後同婚時代的運動其實是來自於生命經驗的需求,而這樣的需求需要共同一起去達成,而非單靠個人就能完成。主角在一開始看似是個lesbian,也就是位女同志..... 貝芝:他是跨男。 佩甄:對,他後來開始注射賀爾蒙,變成一位很帥氣的主唱。 這部片有個小細節讓我覺得很有趣,馬來西亞其實一直和臺灣很親近,不論是文學研究或飲食文化等領域。唯一能夠注意到它與臺灣比較大的差別在於,它隱性地呈現出社會內部因宗教組成而更難達成的某種社會溝通或連結。簡單來說,你會看到這個樂團的表演場景,以及這位主角的親密關係很大程度上都與白人有連結。也就是說,他仍需透過西方的群體來協助、並參與他們的公共事務或抗爭運動。這點相當微妙,同時對臺灣來說又是蠻珍貴的參照。 這個單元還有兩部作品也可以回應到剛剛講的議題 ,我們請貝芝說明一下。 貝芝:我跟佩甄的專長完全不同,沒辦法像她那樣有那麼多論述,但她剛剛講的那幾部片,會讓我回想到很多身邊朋友的生命經驗,但就是比較感性的部分。還記得以前同家會(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剛成立的時候,我二十幾歲,也有一種被生理時鐘推著想要生小孩的感覺。那時我有一陣子很熱衷參加同家會的聚會,而當時才剛開始有女同志到國外生小孩,大家都很想知道那個步驟到底是什麼──去北美生小孩有什麼不同?和在亞洲生小孩的花費又差在哪裡?但後來我發現自己其實沒有那麼想生小孩。 但我覺得,從那個時候起,看著很多朋友從「想生小孩但不能結婚」,到後來同婚通過之後,又被問「你們要結婚嗎?」、「同婚都已經過了,那你要結了吧?」。反而又得再抵抗這種被逼婚的壓力。一直到這幾年,有人真的成功生了小孩,而且還是混血兒。有許多相關的育兒日記、Vlog、小孩的粉專和IG,到現在更進一步地在談生小孩這件,好像已經沒那麼困難了。有錢、知道去哪裡,這些都能解決。 現在反而更在乎的是「親權的歸屬」,更回到日常生活本身。那個 aftermath(事件後的後續挑戰),我們還有下一步要去跟體制對抗的事,也就是又進入下一個階段,就覺得「哇,真的很辛苦」。我這幾年都住在南部和東部,我真的覺得有城鄉差距。佩甄剛剛提到現代的女同志都沒有T、婆之分——沒有沒有!我們南部還是有分,角色依然存在。但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這次的幾部片裡,也能看到一些類似(城鄉差距)的影子。 《沙漠孤心》 貝芝:尤其在《沙漠孤心》裡,講的是哥倫比亞一位高齡跨性別女性的故事。她以前叫Jorge(喬治),但她想改成Georgina(喬吉娜)。整部片圍繞著她想去更換身份證,光這件事她花了45 年的時間。 佩甄:因為她不會西班牙文,只會講自己部落的語言。在公部門也完全沒有資料,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 貝芝:我覺得很有趣,它不只是有跨性別,也有城鄉差距,甚至有原住民的議題。因為我現在住在臺東,這就讓我想到部落裡那些很勇敢的阿嘟姐妹們。她們的處境和這部片裡的情況相比,真的非常有趣。 註:阿嘟(Adju):原是排灣族女性之間稱呼「姐妹、閨蜜」之意,現演變出稱呼具陰柔氣質的男性,特別是男同志及部分跨性別族群,同時延伸出多元性別之涵義。此詞語之意仍持續演進中,亦可無關乎性別地泛指對親密好友的暱稱。 佩甄:這部片真的要去看大銀幕!它的沙漠景觀,以及Georgina老化之後臉上的皺紋,都非常有美感。它的視覺美學非常強,不只是事件導向,而是透過沙漠映照出整個人生的軌跡與紋路,這部片絕對要進電影院看。 貝芝:的確,即便只是在電腦或iPad上看,也能感受到它拍得非常美,質感細緻。尤其如果你喜歡公路電影、沙漠或拉丁美洲的風情,其實都很值得一看,雖然節奏稍微慢了一點。 佩甄:它有一種詩意,非常接近藝術片。但很好看,因為裡面流淌著非常獨特的生命經驗。 貝芝:而且視覺的滿足感非常強。即便大概能預測故事會發生什麼,仍會很享受那個畫面與敘事。最後,Georgina在2021年終於拿到身份證,但身份證上的地址不是她的居住地,因為她住在哥倫比亞西北部,也就是原住民的原鄉。她反而要到1000公里外的首都才能拿到身份證。 我就特別查了哥倫比亞同志的法律,其實 2016 年哥倫比亞就通過同婚,而且 Google 上的 AI 還告訴我,他們跨性別身份轉換是 easy 的,AI用「easy」這個形容詞!我非常驚訝,也因此更能想像城鄉差距有多嚴重。雖然她在首都最終拿到了身份證,但在原住民部落那樣資源極度缺乏的地方,她甚至面臨生命威脅。作品裡提到,她的兩個兄弟曾去她家想殺她,後來是鄰居出面保護。但仍發生了兄弟們把主角的東西和房子燒了的情節。她一無所有,但她活下來了。 《暴力蜜桃回來了》 佩甄:我覺得視覺很重要,這點也可以延伸到另一部片——《暴力蜜桃回來了》。 貝芝: 《暴力蜜桃回來了》很可愛。 佩甄: 是視覺非常豐富的紀錄片。 貝芝:我們會用「視覺系藝人」來形容Peaches,它在加拿大是女性主義酷兒龐克樂團的先驅。從80、90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這部紀錄片歷經十多年的拍攝。 我想提一個很有趣的觀察,《暴力蜜桃回來了》跟剛剛的《酷兒解放曲》可以放在一起看。尤其,你如果是喜歡聽團的人,非常推薦一起看!前者有馬來西亞那種可愛的龐克樂團,後者則是北美那種硬核的風格。相較之下,一開始看《暴力蜜桃回來了》可能會有點無法融入,因為它實在太重口味了。她們在舞台上的表演、服裝與道具,都彷彿是一種行為藝術的展演。 她們的表演中有很多觀眾互動,比如用超大的塑膠袋吹成巨型陽具,觀眾可以一起玩,還邀請觀眾上台,整個氛圍非常瘋狂。但與馬來西亞的《酷兒解放曲》相比,又形成一種有趣的對比。總之,喜歡看團的人,很值得把這兩部一起看。 佩甄:這個單元叫【唱,或者不唱】,也有種莎士比亞式的提問:「To be or not to be」——這則是「To sing or not to sing」自己決定。大家從預告片就可以看到《暴力蜜桃回來了》視覺真的非常強烈,幾乎是酷兒藝術裡少見的肉體呈現。 貝芝:我就在想,為什麼我們臺灣都沒有? 佩甄:不只臺灣沒有這類樂團,北美現在也很少。 貝芝:真的嗎?想問問大家有沒有其他想法?畢竟我現在比較少去聽地下樂團。我那個年代最接近龐克的女子團,大概就是「白目樂隊」了吧。 佩甄:你不要講一些沒有人知道的樂團。 貝芝:說到「肉體派」就可以接著下一個單元。 談【XPOSED:慾望狂想】短片輯作品 《血肉機情》、《肉體莊園》、《坐愛》、《電梯的慾感》 佩甄:接下是跟柏林酷兒影展交換的【XPOSED:慾望狂想】。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這個子單元。 第一部片《血肉機情》,它比較像是這幾年在主流電影圈經常看到的影片類型——「肉體恐怖」。去年就有部蠻受到注目電影《懼裂》,是我們這個年代的女神黛咪摩爾主演的。再早一點,還有部我非常喜歡的作品,2021年的《鈦》。之所以提這兩部,是因為它們都在臺灣上映過,也有非常多影評。看《血肉機情》前如果想稍微了解一下這樣的美學形式,到底有什麼樣的激進性或批判性,可以先把這兩部片以及相關的評論找來看。 《懼裂》以及《鈦》在臺灣的接收,都把它們指向某種「酷異」以及女性主義對於身體的重新演繹,而《血肉機情》又更加的復雜。這幾年,在各大展覽、各種各樣的時事議題裡,舉凡氣候變化、數位時代,會去導向某種比較非人類、賽博格的討論,《血肉機情》即使片長短短的,但它蠻全包式的把當代美學藝術裡指向的各種激進議題都納入了。 這部片導向的身體,有點反向的去挑戰女性身體被物化,或性被物化的問題。中文片名「機情」取的非常好,女主角就是讀機械科的理工女。她有點像是在機房當中實習,在裡頭會看到不是我們一般使用的引擎,而是透過一些人造肉去維護的。 我非常喜歡這部片的結尾,我也不爆雷。結尾讓我留下很深印象,我做夢都還夢到,但它是很美的,並不是恐怖的結尾。對我來說,肉體恐怖的酷兒性在整個XPOSED的單元中,還有其中一部叫《肉體莊園》,它很直接指向了指向Judith Butler所謂的「性別操演」的論述。從《血肉機情》到《肉體莊園》還有《坐愛》,其實都透過非常局部的身體,比如體液的流淌啊......。 其實我在看這些片時候,一開始是想到有些貓奴會特別買透明的碗,讓貓睡在碗裡面,就可以看到牠的肉球(笑)。那個畫面就很像《坐愛》這部片,它讓一個屁股像坐在玻璃的平面上。我們看著的就是屁股坐在玻璃上的畫面,這裡用的是坐著的「坐」在講愛,玩了原本Making love(做愛)這個詞,這個中文片名真的也很會!這批作品的中文片名都取得非常好。 比方,還有另外一部叫《電梯的慾感》。大家都應該懂,搭電梯時怕它突然故障的恐懼,很多電影也都會演這樣的橋段。當危機出現時,電梯裡就會發生很多事情。 貝芝:不能暴雷(片中)電梯裡發生什麼事。但我真的非常喜歡這部,它就是兩個阿桑(笑)在電梯裡,中間發生的那個情欲爆炸可愛。 我想再回去講《血肉機情》。可能我們之前談得比較多的是賽博格的概念——在人類身上植入各種科技;但這次的方向有些相反,是把「肉放進機器裡」。這正是我覺得特別有趣的地方。 另外《坐愛》我也很喜歡,如果你是喜歡實驗影像,應該也很喜歡這部片,我把稱作是「Poetic erotica」——是很有詩意的情色。它用了像萬花筒或鏡像反射,但有某些意象,會讓你覺得像肛門、陰道,或很像大腿等肉體,但它又變成很幾何的形狀,很有趣、看起來非常的繽紛。 佩甄:《坐愛》跟《肉體莊園》整個是嫁接在 Judith Butler 談的 gender performativity(性別操演),或者就是performativity(述行性),兩部片可以並置觀看。 在《肉體莊園》中,會看到幾具有男有女的肉體,直接有性活動的畫面出現。看似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但它就是介於情色跟色情之間,介於雜交或者某種集體意識的交換,那種更精神層面的呈現。導演或說這部片的拍攝者,他其實是很有意識的透過某種酷兒理論的操作去拍攝。裡面會有些學院派忍不住想分析——在坐有研究生的話也可以試著去看看——你是否買單它透過某一種理論框架去設計,甚至去操作跟實驗,然後再次衍伸出對性或身體的一種重新的想象。我看這部片,也有一種自己在思想上練習。 那像《電梯的慾感》這樣的短短作品裡 ,也可以稍微去思考,一個我們看似日常但也充滿危機的一個狹小空間當中的兩個女性——兩位看起來不會發生什麼事的人,因為那個危機、緊張,其中一位恐慌症就要發作了。為了互相拯救彼此、讓彼此在那個環境中不至於恐慌到會發生什麼,她們進行了一個活動。但那個活動是什麼?我現在不能講! 《電梯的慾感》是慾望的「慾」,看的時後我就覺得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我其實看了三遍,想看透到底是哪一刻,讓她們會進入到那個活動(笑)。我可以共感的是很緊張的那位女士。裡面有一位是比較man的想辦法要按對講機、找解決方案,另外一個則是整個呆住了,各位去看電影時也可以找到自己可以對號入的角色。 貝芝:這反而讓我聯想到某種辦公室偷情,可能我自己會編出其他小劇場。 佩甄:以美學來說,還有另外幾部比較不是以肉體出發的。就「酷兒性」來看的話,我們比較能想像的是性跟肉體重新被翻轉、重新被定義邊界,以及重新定義它的功能,也就是剛剛講的這幾部。但這個系列還有兩部片,可以請貝芝談談看,它們有一點超乎我的想像。 《惡女誌》、《拉拉金星X拳拳歌劇》 貝芝:剩下來兩部:《惡女誌》跟《拉拉金星X拳拳歌劇》我想放在一起談。 《惡女誌》是在介紹一個80年代在澳洲的原住民女性主義的Zine(小誌),大家有在看小誌、有喜歡小誌的人嗎?總之,它其實講到這種小誌刊物,大部分是次文化的社群很流行的,以手工製作——以前很手工到手繪、手寫,再用影印機去Copy,接著自己用釘書機把它釘起來,再去發給就是喜歡看這個同樣內容的好朋友們。Zine在很多的次文化裡,就像是當時的某一種媒體。 佩甄:這要特別講一下,現在的Zine有點太精美了,但Zine文化其實也是從地下龐克文化來的,它在追求的就是rough(粗糙),解析度超低、釘書針也絕對不會對齊(笑)。真的是用很薄的那種粉紅色、藍色的紙,在影印機上隨便印。但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傳達媒介,因為那時沒有任何主流媒體會願意去幫助次文化做各種各樣的記錄或宣傳。 貝芝:就像是以前的平面自媒體。 佩甄:對,我跟貝芝現在也正在進行一個計劃。有點像把臺灣90年代也曾有過這樣一段時間,留下一些紙本物件做數位化建檔的工作,在年底預計會有個呈現,希望有機會可以再跟各位多談。 所以《惡女誌》的「誌」也翻譯的很好。小誌或同志文化對次文化社群以及同志社群來說,曾經是一個承載各種各樣文化記憶非常重要的媒體。 貝芝:片中特別提到,它用Zine這樣的方式去呼應酷兒精神——如何忠實的呈現自己的美學,以及剛提到的那種很rough的東西。 接著《拉拉金星X拳拳歌劇》則是女同志+異次元外星生物+生心靈的類別,也是非常B級、史詩級的情色片(笑)。以及它談到了「拳交」,英文fisting比較直接,至於是甚麼意思,大家如果不清楚可以自己回去搜尋。 我認為它的某種很「粗」的美學,跟上一部有一曲同工之妙。片中某種很B級的東西也會讓我聯想到,以前女巫店菜單裡就會有「大奶麵」,海尼根就會叫「含你根」這種B級的諧音梗。類似這樣的感受,很有趣的出現在片中。 佩甄:它的視覺呈現,就妳觀察也蠻多重的對不對?它有動畫以及類似舊影像的應用。 貝芝:對,有。就是我說的很B級、很像家庭錄影帶的感覺。 佩甄:我覺得這類型的作品是我們現在比較少見的,即使在臺灣獨立創作的領域,好像也比較少看到以這樣的方式呈現視覺。我覺得它還蠻懷舊的誒! 貝芝:一種很90的感覺嗎? 佩甄:對。在今天提到的三個單元中,我認為XPOSED這個單元的娛樂性最強。除了剛剛提到完全溢出我們日常身體經驗的肉體恐怖外,還有《拉拉金星X拳拳歌劇》這個部分——現在比較少那種手作,尤其數位化、電子化之後,手作感的部分也溢出我們現當代的日常生活經驗非常多。XPOSED的短片娛樂性很高之外,也有點讓我們的感觀重新去建立,性別這個大主題以下各種各樣實踐面向的可能性。 貝芝:進入下個單元前我想要補充。XPOSED這個單元短片,是特別跟柏林酷兒影展合作,據說單元的策展人會來臺灣,大家屆時也許能跟她有些對話,應該會很精彩! 談【短短#1】 佩甄:剛剛說XPOSED是非常娛樂性,高度身體性、感官性的,那麼【短短】雖然短短 ,但它是在我的觀影經驗裡,可能是最貼近現當下「後同婚時代生活」的。尤其各種同志或作為女性來說,共享的某些生活困境或經驗,也是這系列的幾部片子非常明確指向的。 另外,短短#1的五部片中,其中《石頭狂想曲》這部動畫作品比較無法界定外,其他全部是亞洲。它是一個「亞裔」,包含有印尼、越南 ,以及一個白人跟非裔美國人的故事。這些短片都有很完整的敘事,不像可能以前看某些短片時,會有種議題好像還沒有到位,就很像是掠過一個人的生活一樣 。 《半路貢到愛》、《喵的通話中》、《夜色溫柔時》 這次選擇的幾部片,我覺得都有蠻完整的敘事。特別是我非常喜歡《半路貢到愛》,片名的「貢」,是取自西貢這個在越南的城市。 這幾部片也都各自有蠻重要的元素, 比如《喵的通話中》,來自印尼的作品 ,它整部片就透過手機螢幕呈現,從中看到家庭跟親密關係的張力。它的故事非常簡單,有一對女同志遠距離透過視訊在線上玩遊戲,聊她們接下來想要結婚。此時,就有其中一位的媽媽電話一直打進來。後來,女兒不得已接了,於是畫面就轉到她跟母親的視訊畫面。也就進入大家應該很能夠想像的,母親對於女同志女兒各種各樣的不適應。 貝芝:她又是穆斯林媽媽。 佩甄:最後是怎麼結束的,就請大家進電影院。總之,整部片都是用手機介面的方式,呈現了一個非常真實,我們日常生活都經驗過的感受。在那個過程中,儘管是一個小小畫面 ,就呈現了複雜的情緒、情感跟張力,是很精彩的呈現。 至於《半路貢到愛》,則是溫柔的呈現大城市裡的愛情。裡面有個非常長的畫面是兩個人在機車上穿越了西貢,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她們的相遇非常偶然 也非常短暫,整個故事結束在一個非常棒的畫面,我個人非常喜歡這部短片。 這幾年我們在所謂的酷兒文學或是同志文學作品,已經有點稍微離開某種高度悲劇性或憂鬱的情節展現。這部片其實就是兩個人偶遇後,非常短暫的共騎機車,在城市穿梭的過程中,透過某種對話去交流的一種情感。它的結局拍的很好...... 貝芝:它沒有很明顯,是有一點開放的結局。 佩甄:它有個溢出我們期待以外的呈現,也讓一個大都市中起了小小連漪的一段情感以非常詩意也很真實的視覺去包覆。 這又可以談到另外一部《夜色溫柔時》,一個白人Butch(形象較陽剛的女同志)跟一個非裔,偶遇後兩人有個短暫的約會,後來在城市裡騎單車。 這三部我都很喜歡的女同志短片都很生活化,相信也是對臺灣觀眾來說蠻能夠投射的三種介面——手機、機車跟腳踏車。這種移動通訊作為一種親密關係的基礎建設,也是這幾年在酷兒研究領域經常觸及的。所謂基礎建設就是通信、交通,只是以往在討論酷兒或親密關係時,我們比較不會去討論它,因為我們還在上一層次——性別意識形態、LGBTQ這種身份標籤的討論。而這三部短片不管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對我來說都是往前推進了整個酷兒論述的一種呈現。透過通訊、交通工具這樣的基礎建設,再次反向的印證跟操演,親密關係不需要用所謂的性的認同或是家族的形式去做界定。貝芝怎麼看? 貝芝:這三部好像有個共同點就是「展演性」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 《喵的通話中》她們用虛擬的線上遊戲在互動,一開始會覺得「這是一個紀錄片吧?」。但後來又覺得好像是docudrama(劇情紀錄片)嗎 ?它到底是什麼?我就覺得很有趣(註:此片為劇情片)。裡面展演性還蠻強的,尤其線上遊戲的部分真的有被驚艷到。 越南的這部《半路貢到愛》除了整個畫面很美之外,其中一個女生有個排練,另外一個人就協助她抵達那個地方。這就讓我感覺到,原來現在越南年輕世代的身體語言,不只是情慾方面 ,也包含在身體展現上,會看到很有趣的狀態。 佩甄:裡面有一幕我很有感 ,因為我們以前在臺中念書都是騎機車。其中一個人的機車壞掉,她要幫助她前進,就是用腳「嘟」著她的機車。因為有過這樣的經驗,也是有點懷舊。 貝芝:然後第三部《夜色溫柔時》的展演,因為一開始有練習摔腳的畫面,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在這些片子會看到這些酷兒社群很肉身化的一種日常。片中另一個主角,她白天在肉店上班...... 佩甄:這個梗也是蠻直白的,butch as a butcher(女同志是肉販)。非裔的女士則是拳擊教練,就都跟肉有關。 貝芝:以上大概是這三部片都有的一些展演性,也讓我感到很有趣的部分。 《石頭狂想曲》、《TTT》 貝芝:另外兩部,其中《石頭狂想曲》是動畫短片。這部動畫有入圍柏林金影展,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擬人化的石頭是它的主人翁這樣子。 這個石頭,我很有感覺耶!最一開始我想說,「天哪,這要怎麼導讀?」於是,我就去查了導演的資料,她來自捷克的導演還很年輕,目前在布拉格的的藝術學校念碩士班。這部作品是從她的學校作業開始發展的,在做成動畫前,她畫了這個石頭的漫畫/繪本。她先畫的三部曲繪本,還有得到漫畫獎項,然後才把它拍成動畫。可以看得到它醞釀了很久,導演也有講到,她自己是在比較鄉村的地方成長,來到首都布拉格念書,就覺得有點格格不入。那顆石頭有點像是她的另外一個自我,她在都市裡面求學跟生活的經驗,很多時候就跟這個石頭是一樣。 佩甄:最後一部的片名叫做《TTT》。 貝芝:這部應該是最實驗的吧,它非常短,影片風格非常實驗性。從頭到尾會聽到這個主人翁在說話,像是個很長的獨白。他就一直在很大聲的做自白,不管是抱怨、抵抗或者是陳述 。 這是個很Trans的實驗片,這個裡面的主角就講到自己的轉變過程。他特別提到自己是FTM(Female-to-Male,女性到男性),但是他不只是 FTM,他是「DTF」——dyke to fag,從一個陽剛女同志變成男同志。很有趣的將酷兒性又推到另外一個層次。 他在片子當中也說到,因為他是亞洲人,所以他身上沒有毛。當他變成一個男同志時 ,因為他肉肉的,他便問說「我可以當一隻熊嗎?」然後又被他的男同志朋友笑說,「你當然不行!因為你都沒有練,然後你又沒有毛。你就只是胖,不是熊。」 我們會看到很多重的,不只是性別上的一種審美,它又有一個種族上,很亞洲的、跟毛髮相關的討論。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也是我們看到這種Trans經驗的記錄裡一種新的身體經驗。 佩甄:關於種族部分,這部片名叫《TTT》,原文「Tㅌト」其實是三個國家的字母。ㅌ是韓文(發音類似ㄊㄛ),ト是日文(發音to)。剛剛講種族的部分除了毛髮、身體性外,它也非常實驗性的用了語言,穿插日、韓文。「Trans」在日韓文當中是拼音文字 ,因為日本、韓國在翻譯很多外來語都是直接用英聞的翻譯,不像我們有翻譯為「跨性別」,他們就是說Trans。它也在玩的是,雖然是用韓語或日語來發Trans這個音,但它終究不是英文的身體性。所以大家看的時候,千萬不要忽略它在影片裡穿插的東亞文字訊息。 貝芝:難怪!它中間跑文字上去,我還特別截圖請我的日文朋友幫我翻譯,結果他居然看不懂,原來這裡面還有韓文。 除了可以看到他在玩文字符號 ,影像上還可以看到他拿著一個針筒在注射。他一直重覆這個動作,像在種田一般。好像他的身體是一個土地、一片田,是很有意思的意象。 佩甄:因為他正在進行性別轉換,變性過程其實要注射各種東西。最近在臺灣也翻譯了一本西班牙蠻激進的酷兒研究者Paul B. Preciado的知名著作,有點類自傳的學術專書(《睪固酮藥癮:當避孕藥、威而鋼、性與高潮成為治理技術的一環,一位睪固酮成癮者的性實踐與生命政治》)。這位作者就故意去注射這些東西,不要讓藥品凌駕它,而是他去控制......也是提供另外一個reference給大家,如果要去貼近這部作品,其實是有一整本書可以幫助大家貼近,即使它是一個非常短的實驗影片。 我覺得女性影展選擇的這一批作品,在非常多的層次上,如果真的深入去「感覺」——甚至不要思考,而是用感覺的方式——其實會更新當下非常多的性別議題。在檯面上不管是公民運動,或是私底下的情欲的實踐,這兩者之間的斷裂,正可以通過這批作品幫助我們去做思想跟感覺上的連結。 分享「擴延檔案的維度——台灣同志史的有機串連與數位策展」計畫 貝芝:最後跟大家聊一下我們現在的計劃。 佩甄:主要是我跟貝芝是同個世代,活過了所謂的——像剛提到小誌,在手機、網路、自媒體全面入侵我們生活前,女同志作為性少數,我們是如何交流的?總在那個時代,90年代末到2000年初,有一些東西留在我們身上非常深刻。但會發現,在2010年代後,臺灣同志運動的論述是沒有辦法連結那部分的,因為同婚的論述太強了。 那個強,不是說我們很成功的那種強,而是他是第一次有同志的議題因為公投進入了家家戶戶,雖然這不算是一個正面的結果。但它進入到家家戶戶,大家得去辯論跟討論同志的生活或同志的未來。因為它的影響太大、層面太廣,像我自己在大學遇到,現在都是2000年後出生的的學生,我都叫他們「客戶」。我每年都要重新跟這些客戶分享我們不同的感覺結構,對於性認同、性身份的經驗。 我有一批很好的學生,他們是很少數現在願意在性別社團運作的學生。政大有個1995年成立的同志社團「路人甲社」,今年也是30週年。過去所謂的學生社團非常重要 ,因為當時年輕一輩,沒辦法從他的生命經驗或者上下世代尋得,作為一個同志他要怎麼樣活過青少年時期、怎麼去想象他的未來?因此,校園的空間變得非常重要。 我會舉這個例子倒也不是要講90年代的這個狀況,而是現在在性別社團的這一批我一起合作的客戶們、學生們,他們很特別。我會用我老派的方式跟他們混在一起,就曾問說:「哎,你們這裡為什麼很少好像很女同志?」因為社團中都是生理男性,而他們也不會說自己是gay,社長就跟我說:「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女同志。」 也就是說,他們會討論性別議題,可是他們不聊彼此的認同。甚至,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命名自己、也沒有那麼喜歡這些標籤的了。我就覺得很衝擊,我們剛剛其實會很快的去把這些術語拉出來,不是因為我信仰它,而是它其實是需要被填充、需要被爭論,它是需要去記錄的一個語言符號,或說學術名詞作為符號的存在。沒有這個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去記錄不同時期的討論?這是我現在感到很困惑的。 回到我們的計畫,我們活過那個90年代,我們20出頭歲的當下其實也還不知道那個重要性。經歷過整個數位化,一夕之間有個資訊完全消失的危機跟恐懼,以及建檔的不適用性。而現在討論各種各樣的議題,到底要去哪個機構?可能在threads上得到一點、在Facebook上得到一點、在Dcard上得到一點......,可是你沒有一個完整的平臺去記錄這些不同的聲音。但我們那時候是至少有——吵架在特定的地方吵,會有人很認真把他記錄下來,放在一個女同志雜誌上。 我跟貝芝現在做的這個計劃,是在C-Lab空總這個這個單位,我們已經從 2019年進行到現在,第一波的成果是在2020年左右完成,是跟文化部底下的國家文化記憶庫合作。通過計劃,我們建立了200筆90年代所謂的「臺灣同志酷兒文化史」。大家也許都不知道這些學生社團曾經存在,也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女同志、男同志雜誌,或是網絡的平臺,在90年代到2000年初承接了一個世代的的男女同志或校園女同志們。這些平臺上到底發生過什麼事?那個時代的人在討論同婚的時候在討論什麼?我們透過200筆的記錄,把它建立下來。 跟貝芝合作是因為她有非常強的跨領域藝術展演經驗,我們不想要它流於一個平面的數位的資料庫,所以會借助她的策展的能量,讓這一批資料有一個敘事,將會做成一個線上策展。 這個計劃也有自己的粉絲專業,叫做「臺灣同志數位博物館」。我們本來用「酷兒」,但現在還是用「同志」,因為同志對臺灣來說有一個蠻特殊的歷史意義,跟文化意義。我們會跟中研院的開放博物館合作,它會是永續的,希望這些線索、碎片,能夠在數位空間裡發散出去,也許會停在某一個人的生命經驗。透過這些小小的粉塵或是星點 ,再往外去推敲你們自己的經驗做連結,通過如同星系宇宙的概念,讓處在臺灣各個世代、各個鄉鎮的同志們,都能夠對臺灣自己的歷史有一點點連結。 貝芝:佩甄是檔案組,我是創作組,我就是負責就把這些硬邦邦的檔案 變得有趣,讓大家在線上看的時候會有些互動感 。我們還在努力當中 ,請大家多多支持! 佩甄:最後想補充,前年是女性影展30週年,那年做的專刊就很點符合我們在思考這個計劃的意義———也就是用一個非常快速的方式做階段性的整理,讓來不及參與前面各個時期的影展觀眾,能夠很快去掌握影展自身的歷史,還有臺灣女性影像的歷史。我們想做的就是這樣的事,都是在做記錄跟詮釋的工作,而女性影展一直以來也把女性的議題隨著影像做了非常好、非常重要呈現。我想,去做到社會議題的溝通,這也是影展之所以存在一個很必要的意義。
時間:2025年10月05日 地點:誠品南西5F FORUM 主持人:女性影展策展人 陳慧穎 主講:羅珮嘉│女性影像學會顧問、謝淳清│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 文字紀錄:徐瑋璐 文字整理:彭湘 慧穎:非常高興看到大家參加這個講座,也很開心邀請到女性影像學會顧問羅珮嘉及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謝淳清。今天講座會聚焦今年女性影展非常經典、十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片單。 其中有個重頭戲就是【焦點影人:香妲.艾克曼】單元,熟悉女性影展的觀眾應該知道,這是我們第二次做香坦・艾克曼的專題。2016年,曾做過【數位修復:再見香妲艾克曼】,是因應艾克曼於2015年過世,我們在隔年便做了這個比較紀念性的單元。那年,除了她的遺作《非家庭電影》外,我們也放映了她非常經典作品,比如《珍妮德爾曼》等。今年稍微不一樣是,目前香坦・艾克曼的電影已大致完成數位化與修復,也因此我們能選入許多曾想放,但礙於尚未修復完成而未能選映的電影。而再度去面對艾克曼五十多部作品,我們該如何挑選?這次,我們便從大家比較不認識的艾克曼的其他面向,包含文學改編作品,或者可能是電視作品,但它們其實非常經典。希望讓大家通過這些作品,讓是這位當代非常重要的女性導演。 除了香坦・艾克曼外,這次有一個很特別的單元【特別放映:致先鋒女性!】,希望去回應女性影展本身的歷史。我們會放映的是一個由挪威導演拍攝的作品《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之中可以看到在柏林發生的早期女性影展雛形。而除了回顧歐洲的脈絡外,也期盼提醒大家不要忘記女性影展在亞洲的位置。因此,我們選了另一部來自日本的《拍電影的女性們》,會聚焦在日本相關的討論。我就簡單介紹到這邊,接下來的時間交給淳清老師以及珮嘉。 談【焦點影人:香妲.艾克曼】單元選片 淳清:就像慧穎剛剛提及,女影是第二次做香妲艾克曼的專題,而大家比較熟悉的艾克曼作品可能已經被介紹一輪。當我第一次接到這個專題規劃的時候非常開心,因為它延續了過去專題的脈絡,再進一步補足大家對於艾克曼的認識。一個導演可以拍五十多部電影是非常厲害的成就,也正因為如此,只做一屆回顧其實是非常不足的。接下來,我會從我自己比較主觀的閱讀帶入,一部部介紹今年的選片。 《安娜的旅程》 事實上,安娜的旅程除了旅程外,還有她的幾場會面。包含她的情人、老鄉。在這些會面裡,延續了導演之前作品中「關係連結的失敗」這件事。這部片有一部分自傳性,但艾克曼在談論到這件事時,其實是否定的,她認為這樣會太侷限安娜這個角色。那為何說是自傳呢?因為這部電就是一位女導演帶著她自己的電影在歐洲旅行、宣傳。這部片推出的時間在1978年,那大家可以想像1975年,艾克曼就是帶著《珍妮德爾曼》參加各個影展,也開始奠定了她做為一個重要女性導演的地位。可以說,她就是將整個過程放入了這部片,而且香妲的中間名就是Anne,她也曾說曾祖母會叫她安娜。而這部片有其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會面,就是她與母親的會面。她拍得非常的寂寞,但這份寂寞,一方面她回到母親的懷抱,與母親的連結彷彿有個既親密,又化不開的隔閡在那,可以把它當作艾克曼電影很大的核心,或者說她的基調。 除了自傳性,艾克曼的作品也常帶有實驗風格,我們可以在她的每一部電影裡都看見這樣的基調。我會推薦這部片做為看今年影展的起點,因為它不但可以連結到艾克曼1975年的名作《珍妮德爾曼》,也能見到她在美學上很節制的,處理一個渴望關係再築起,一再的努力但又一再失敗,以及「囚禁」等主題。而這個囚禁也會在稍後會介紹的兩部文學改編作品裡看到。以上是關於《安娜的旅程》的簡短介紹。 《故鄉在彼方》 這部2006的作品,也可以回應剛剛提到的囚禁。這部片的背景是艾克曼接受了去以色列拍攝紀錄片的提議,當時外面是有危險及暴動的,整部片就透過房間去拍攝外面的世界,可以說她就一直將自己囚禁在公寓裏頭。片中,艾克曼自己也有在電影裡獻聲,她像是把自己當成一個有疑心病的女生,過著平凡瑣碎的生活。 這部片的片名之所以為Là-bas,艾克曼特別解釋過,在法文裡,當她認識的猶太人朋友、親戚說要去以色列時,他們不會說自己要去自己要去以色列,而是會說「我要去彼方(Là-bas)」。 這部片,可以將它看成是紀錄片,而其中也有可以做政治性解讀的空間。片中看見她像是被囚禁在房間裡,這個囚禁又連結了艾克曼的童年回憶。她提過,母親不喜歡她在外面玩,希望她待在房間裡,她兒時便長期透過窗戶看著外面的小朋友玩。因此,這也成為了一種她觀察以及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 文學改編作品:《奧邁耶的癡夢》、《愛的俘虜》 接著介紹兩部小說改編的作品,它們都帶著囚禁、限制,把人限縮在一個空間或是縮限在一個無法自由活動的空間裡,帶有空間感的拘束,以及受到外頭的凝視。這兩部電影分別是《奧邁耶的癡夢》、《愛的俘虜》。如果帶著閱讀文學的眼睛去看,會發現艾克曼她改編的幅度其實滿大的。有點像是重新去發現小說,比方說剛提到的無論是囚禁也好,還是建立關係卻始終失敗的母題,她通過小說的情節,去跟它這些母題做連結。 我們先聊聊《奧邁耶的癡夢》她原文片名中的「La Folie」可以用「癡夢」去理解,也可以解釋為「瘋狂」,放在這部片主要指稱人內在瘋狂的狀態。相較於艾克曼其他電影的風格,這部片在美學上也帶有很多野心,它大部分在夜間拍攝,也使用了很多古典音樂。這部電影的開頭非常有意思,大家看片時千萬不要遲到!非常好看。 尤其,片中使用許多自然元素,人物則帶有神秘感。這也與《愛的俘虜》有相似之處,片中人物有種神秘性、不可穿透性,我們用文字形容其實很有限。而剛剛提到的內在的瘋狂,片中很多畫面在深夜,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它通過這個方式,帶給觀眾一種密閉感,甚至窒息感。 《奧邁耶的癡夢》(2011)與《愛的俘虜》(2000)還有一個共通點是,艾克曼用了同一位男演員擔任主角,角色有非常類似的精神狀態表現。大家可以去看這位男演員相隔十多年,如何呈現這樣極盡瘋狂的角色。 再介紹一下《愛的俘虜》,它是自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當中的〈女囚〉這部小說改編。講的是一個男子把一個女子囚禁在家中,觀察她的生活。但他最想介入的其實是這個女人的「渴望」,可是這個女性是無法穿透的,非常神祕。片中男子問女子:「妳在想什麼?為什麼不說?」她回答:「我要是知道我在想什麼,就會告訴你。」所以事實上,男子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女子在想什麼。他想跟她建立關係、想要連結,可是這個連結始終落空。 男子囚禁了女子,但其實最後會看到這是個「自我囚禁」的男性角色。在這部片中,可以看到艾克曼作為「作者導演」的特質——她總是能夠把不同的故事,轉化成她自己的東西。 有一部分也與文字到影像的轉化有關,我們可以看到,她如何去轉譯文字。片中有一幕,男子通過影片看女子在講甚麼話,文學作品中可能是用很濃郁的文字在描述這段不斷重複、不斷觀察的情節,艾克曼便用了影像的方式去轉譯這一塊。另外還有個部分是,她放入了希區考克《迷魂記》的風格。《迷魂記》是一個男子對一個女子的跟蹤的故事,透過這個引用,你可以說,艾克曼在重新閱讀普魯斯特,也同時在重新閱讀希區考克。 《我餓,我冷》、《1960年代末一名布魯塞爾少女的肖像》 《我餓,我冷》是來自一個以巴黎為中心的短片合輯《巴黎 20 年後》,在1984年播出。《1960年代末一名布魯塞爾少女的肖像》則是是來自一個電視選集,當時電視台給了幾個規範:必須使用搖滾音樂、反映當時的政治背景,並且包含一場舞會場景。當年他們便把這些規定交給幾位導演,除了艾克曼外,還有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泰希內(André Téchiné)等等,挑的都時當時一時之選的導演。 艾克曼選擇回到布魯塞爾,拍她的六八歲月。裡面其實也有很高的自傳性,可以看到一個女孩子,跟一個年輕的逃兵一起在城市裡遊走、聊天。有點像《午夜巴黎》那樣,一整天兩個人不斷聊天。當然結尾有點悲傷,也回到了她一直呈現母題——想要連結,但又失落。 《長夜漫漫》 前述的「流動性」也在另一部非常特別的作品裡出現,叫《長夜漫漫》。這部片沒有台詞,像是一支舞。艾克曼在同一年有一部拍攝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紀錄片,就我的理解,艾克曼也有關注表演藝術。而《長夜漫漫》這部片的作法是,可以看到人物的行為、運動,它的連貫性以及情感。正如它的片名,它的主角就是黑夜,也有別於她的其他作品,這部的實驗性很高,有一點情節,但沒有故事性。 《在那天.....》 最後是《在那天.....》,是藉此向高達致敬的一部短片。艾克曼用了到過去另一部作品《房間》曾用過的手法,她讓鏡頭在床上不斷地繞著這個空間。它的繞法是很有節奏的,她不斷的說話,好比說著她不能再抽菸、有個作家因為抽菸死掉等等。整部短片用一種重複性的方式呈現,是一個很簡短、很個人化的艾克曼式電影。 《暴風雨中的無名風景(致香妲・艾克曼的兩封信)》 最後是一部向艾克曼致敬的紀錄片,這部作品除了是致敬,也帶有對艾克曼的一點批判。雖然並非直接表達,但從創作者的選擇一個艾克曼忽略的場景——作為作者有意識的選擇——可以看出,在致敬之於,他們也提出了不至於到反對那麼尖銳的一些質疑,也是這部片相當聰明的地方。 再次回顧,如何超越十年前的感動? 珮嘉:2016年我們第一次做香妲艾克曼的回顧是因為她剛好離世。隔了九年,將滿十年要再做時,我一開始就想:「會能超越十年前嗎?」大家知道《珍妮德爾曼》的偉大,以及帶給觀眾的衝擊,那我們真的能夠超越當年的感動嗎?但我必須說,這次的焦點影人專題比十年前更厚實。還不認識她、沒看過她作品的人,從這次下手是對的。 上一次的《珍妮德爾曼》被《視與聽》雜誌選為影史第一名,確實很難超越。但我可以掛保證,《安娜的旅程》不會輸《珍妮德爾曼》。完成《珍妮德爾曼》三年後,艾克曼拍了《安娜的旅程》。前者以一位主婦兼性工作者每天一成不變的生活,可以看到一成不變又冗長的生活裡,每天的樣貌、生活的環境是會在細節中改變的。三年後的《安娜的旅程》做得更加、更加精采,片中看起來像是有邊界的各種距離,不管是鏡像的距離還是人物角色感官的位置,與它的心理狀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有著非常清楚的算法。觀看時,你的身體與眼睛會跟著她移動:向右、向左走。如果要抓到香妲艾克曼的特色,這部片真的非常可圈可點,不輸《珍妮德爾曼》。沒看過的觀眾,就從這部下手就對了。 我也簡單分享幾部我自己特別愛的作品。從年份看,70年代的她像一隻兇猛野獸,拍出女性主義的激烈與難忘;《安娜的旅程》拍出女性導演生命裡的冷靜批判。到了80年代,她轉換情緒:不論實驗片或紀錄片,討論家國離散、社會議題、母女與各種人際關係,風格類型不斷變化,並藉影像的變化形塑她自身的生命樣貌。 80年代後拍的《長夜漫漫》、《我餓,我冷》,呈現更加地隨性、更多地身體展現。比方,在拍攝《長夜漫漫》時,她要求演員用身體拍戲、用身體想像,而非仰賴旁白,片中有很多舞蹈與以及兩個人的對戲,都是用身體去展現。 看她的電影時,不只是打開眼睛去觀看,也包含你的身體如何跟著她的鏡頭擺動。可以看到80年代後,她作品中的節奏、音樂、呼吸都有嶄新的樣貌。這也歸功於她在這個時期與一位很棒的剪輯師合作,是她後來的長期夥伴克萊爾阿瑟頓。 我們今年也在展期邀請到克萊爾做「大師講堂」。如果想多認識艾克曼在風格、形式上的思考,一定要去參加,可以藉此更理解她們如何讓作品產生新生命。克萊爾提過,她不管在剪輯上,還是和艾克曼討論敘事上的思考,其實都帶有道家思想,比方她會說不是為了「cut」,而是為了「再製/edit」這件事。 談先鋒女性與經典片單 《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 珮嘉:剛提到,70年代是艾克曼發跡的時候,那麼以女性主義運動來說,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大概是從6、70年代的西方女性影像開始,也接續了六八政治與大家較熟悉的5、60年代的法國新浪潮。雖然當時已有女導演如安妮.華達、瑪格麗特.馮.卓塔,但真正是到了1970年代,大家才開始意識到,我們要討論的好像不只是影像本身,還包含著產業鏈中,是否有些對於女性創作者不友善的狀態。在當時有幾個時至今日仍很重要的關鍵女性人物,就在德國的「兵工廠電影院」,辦了一個研討會。 現在要分享的「致先鋒女性!」這個單元的第一部片《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片中的這個研討會辦在1973年,可以說是接續了我剛剛提及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思潮。當時的契機是,這部片的導演維貝克・勒克伯格(Vibeke LØKKEBERG),《墮胎》這部作品在一系列的女性放映會放映。於是,她就記錄了當時一起去參加這些像是研討會、交流會的每一個女性創作者,她們對於產業的觀點。片中,她就拍到了包含德國、西歐的創作者,其中像義大利最有名的女性主義創作者也在內。 這部片出品年標「2025年」,但導演1973年就拍了這個部片。這是因為,它因為種種原因,也沒投資人就佚失了。一直到將近50年之後,2019年由挪威國家圖書館尋獲,當時拍的音像、影像素材,並讓這些16mm影片得以進行修復。而這一位挪威導演——今年台北電影節也放了一部她的作品《空房間裡的妻子》——便以這些素材重新創作,完成了2025年的這個新的版本。 紀錄片中也討論到了,產業內的女性比例真的很少。比如70年代的西方世界裡,不管是持攝影機的人、製片、導也好,幾乎都是男性,女性從來不被鼓勵做這類工作。而我們可以看到,經過四、五十年時代的變化後,這部片的導演仍舊掌鏡拍片,算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她也是挪威影史上很重要、產量非常大的女性主義導演。 今天的我們,看這部片絕對有它的意義。它並非有什麼特殊形式的紀錄片,就是中規中矩的採訪,我會建議大家看之前可以先做些功課。不過,沒時間做的話,我也已經幫大家整理好了。 這部片中採訪很多很重要的人,其中就包含德國的赫克.桑德爾(Helke Sander),她是德國女性主義電影運動核心的人物,也是柏林女性電影節的創始人。 而這個研討會很重要的地方又在於,正是在這之後,西歐各地的女性影展如雨後春筍的展開。片中會看到柏林女性影展的創始人,還有德國女性紀錄片運動先驅克勞迪亞.馮.阿萊曼(Claudia von Alemann),她的作品《Blind Spot》講年輕女性歷史學家追尋19世紀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Flora Tristan的故事,這部片是歐洲女性電影的經典。 這些人都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在當時這麼辛苦的環境之下,她們建立起自己的電影之路,非常值得去了解。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美國的代表Ariel Dougherty,她是美國 Women Make Movies 這個組織的創辦人之一。這很重要的原因又來自於,全世界各類的影展組織,可能都沒有像這樣女性與女性間的串連,但因為我們(女性)有相同的情節、相同的意識,才會一直這樣延展下去。 而台灣的女性影展的創立也有很大成分受到美國 Women Make Movies這個組織的影響。還有如法國後來很重要的克雷泰伊女性影展(Créteil International Women's Film Festival)、西蒙波娃影音中心(The Simone de Beauvoir Audiovisual Center)等,各種不同類型的影像組織都因此紛紛建立。 稍微延伸等下會談的第二部片(《拍電影的女性們》),這個關於東京女性影展的片子,裡面也去探訪了剛提到的法國克雷泰伊女性影展,日本就決定把70年代西方女性這樣的結盟意識帶進東方,做一個亞洲的——不只是都是白人——所謂的亞洲女性導演群像的重要記錄。 裡面還會介紹到一個叫做努里特・阿維夫(Nurith Aviv)的導演,她曾擔任安妮華達導演的攝影師。片中就講到,她在那個時代身為女性攝影師,經常找不到工作。大家會覺得生理女性根本做不起這類勞動,怎麼可以當攝影師?而像這樣的事,在2000年初的臺灣影視產業,其實都還持續發生。 我記得2000年底,公視還報導過有第一位女性攝影師出來了的新聞。由此可知,我們的路程也走得相當慢,這是個需要披荊斬棘的歷程,才有辦法建立。另外,還包含同工不同酬的問題,都在這部片子裡被討論到。 值得一提的還有義大利的安娜貝拉・米斯丘里奧(Annabella Miscuglio),是我認為在這部片中南歐女導演裡面也很重要的一位。 以上是我的建議,大家如果要看這部片,可以做一點關於70年代女性主義的功課,也可以把香妲艾克曼想成是這個時期出來的創作者。 《夜班時分》 順著下來,想先談另一個單元的一部經典片《夜班時分》。在我們剛剛談的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女性主義電影之外,英國一直是最少被提到、最被忽略的。而提到英國女導演,大家可能會想到莎莉・波特(Sally Potter),但不太有其他選項。我自己是學電影史的,我們常談到歐洲新浪潮,但最少接觸的就是英國新浪潮,這其實相當可惜。 英國電影雖然沒有其他地區那麼強烈的實驗性,但它的音樂性的歷史是非常強的,包含搖滾的歷史、各種時尚產業的歷史。《夜班時分》很有趣,就像是歐洲新浪潮鋪天蓋地之下被忽略的「遺珠」,但又是最能代表英國地下次文化、女性先鋒、前衛的作品。它和剛才介紹到挪威導演拍攝國際女性電影研討會的紀錄片相仿的是,這部片的導演是在四、五十年後自己參與作品的修復。而這位導演在完成修復後,就在今年過世了。就我自己對電影修復的研究,導演有親自參與修復自己作品的比例極低,她算是很幸運的。 如果對英國次文化有興趣,這部片非常推薦。這之中包含音樂的創作、演員——演員喬登(Jordan,本名Pamela Rooke)是當時龐克場景中滿重要的人物外,也是Vivienne Westwood 的店員——以及找了一位美國攝影師掌鏡。導演跟製片那時候在旅館打工,他們就用了五天完成拍攝。他們沒有甚麼厲害的攝影器材,就以非常低的成本,靠著一群有興趣創造另類又有前衛風格作品的工作人員,拍出了這部很特別的片子。 如同我剛提到《安娜的旅程》一樣,你可以用你的身體去隨著演員進入,跟著角色在旅館裡的各種空間移動。大家也可以看它怎麼選擇在這個空間做各式各樣的視覺呈現,看這部電影就像在看畫,它的場面調度,包含空間的設置、光影的線條,都有宛如繪畫般的呈現。而且是蠻巴洛克的呈現,比方我們看一個光影的變化,人的思維與情緒,都可從片中影像呈現的情境去感受出來。 這部片也是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下,重要的女性導演作品,導演羅賓娜.羅絲(Robina ROSE)今年剛過世,放映此片也作為對她的深刻致敬。總而言之,大家可以把前述提到的這一整群人,視為同一批,她們就在在西歐同一個思想脈絡下創作。 《拍電影的女性們》 東京女性影展可以說是把前述西方女性主義的思想、女性的結盟、影像的放映,同一時間將各國的國際交流帶進東方的代表。 《拍電影的女性們》這部片的導演熊谷博子影展期間也會來到台灣。片中有很多大家應該知道的日本導演在其中,比如河瀨直美、女影也做過焦點影人的田中絹代、日本第一位女性導演坂根田鶴子。接下來我提到的名字,建議大家也可以先做些功課。 坂根田鶴子與田中絹代不同的是,田中絹代是女演員出身,轉導演時已有名氣,資源相對好,而坂根作為第一個女導演則常被排擠、被忽略,作品也常失傳,每位導演的路徑不太同。 還有像浜野佐知,她是拍類似情色電影出身的,她從70年代就開始創作,但大家不太知道要將她的位置放在哪裡——她拍情色片,但不是以男性凝視的角度去拍——在東京女性影展出現之前,很多人甚至不把她放在「正典女導演」裡,這部片也訪問了她。另外還有高野悅子,東京女性影展創辦人,以及大家比較熟悉的河瀨直美。 比較可惜的是,東京女性影展在2012年因籌辦者年事漸高而停止舉辦。雖然其他縣市仍有女性影展(如大阪、愛知)試圖延續,但我們仍很期待東京女性影展可以再重新開始。也許影展期間可以來問問熊谷博子。 淳清老師也曾去過東京女性影展,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淳清:我在東京念書時去了兩屆的東京女性影展,印象很深的是他們的影廳很大、很正式,不像我們可能小一點,比較有次文化的感受。創辦人高野悅子也有出來演講,談談影展的意義。可能我作為外國人比較難進入核心參與,但整體來說,他們的放映與邀請都是很典禮式的活動,官方正式性很強烈。 至於後來為何消失,我其實並不清楚。我個人的想法是,東京對於產業制度更為傳統、嚴謹,或許在這樣的限制較下,便較難突破,它不像台灣有像游擊隊的方式可以處理。 珮嘉:就剛剛這三部片,淳清老師還有沒有想補充的地方? 淳清:今年剛好有好幾部都以「夜間」為主題,不管是艾克曼的《長夜漫漫》、《奧邁耶的癡夢》或剛提到的《夜班時分》,也許可以把「夜間」當作一種選片主題來看。尤其,《夜班時分》跟艾克曼的《長夜漫漫》剛好可以做一個對照——《夜班時分》主角是在旅館的看房人,它比較靜態,幾乎沒有語言,可以去看它如何在靜態空間講一個「流動的夜晚」。《長夜漫漫》則是在整個城市的每個角落裡,有正在發生的情感故事。這兩部或許會是滿有意思的對照,兩者音樂的使用、演員的表演也都很值得一看。 另外,《夜班時分》的女主角也非常特別,她也帶有點行為藝術性的成分。尤其在片尾她神秘地卸下妝容,接著白天來了、清晨到了,她走出來,新的旅客或舊住客又開始接續生活。這個轉換,又有點像是回到《安娜的旅程》中關於旅程的邊界,一切未知又有什麼即將展開。如果把這幾部片串在一起,好像也會有一個主題性。 必看女影的理由 珮嘉:這次不管哪個單元,有很多很強的女導演、作者導演。觀眾也許會想問:「為什麼需要知道這麼多女導演?」《拍電影的女性們》這部片有一段令我很感動,片中有人問:「女人為什麼要拍電影?」,她的回答是:「我們拍電影不是職業,是生存。」 大家可以細細品味、思考,我們為什麼看女性拍的電影、為什麼看女性影展?其實我們都是為了生存,那是一種思想的推進,也是美學的豐富。 可能有人覺得很多片太過實驗性,但我必須說,艾克曼有些短片真的很實驗,有一部一直在空間裡轉圈圈(《在那天......》),會讓人疑惑為什麼要這樣轉。但我們就是需要看與日常觀影模式非常不同的作品,才能感受到它的美學價值。我很希望大家來挑戰這兩個單元。聽說《安娜的旅程》賣得很快,大家要趕快搶一下了! 慧穎:我也稍微補充一下。剛珮嘉有說可以先做一些功課,但我覺得也許不用,以《拍電影的女性們》這部片來說——我先聊聊為什麼會選這部片,如果大家有注意,會發現這是 2004 年的作品。那為什麼要放 2004 年的片?我們會發現這部片有個重要的契機,近年東京的日本國立電影資料館(National Film Archive of Japan ),它連續三年做了非常完整、針對女性創作者的爬梳。從 1930年代一直到近年,把所有從早期包含剪輯師、編劇等各崗位的女性創作者都找出來。並以年代區分,做了非常紮實的爬梳。 若對日本女導演稍有了解,就會發現她們女導演數量非常少,這與影像產業的性別樣態、社會氛圍都有關。而在這樣的前提下,這部片的重要性就浮了出來,這也是東京電影中心在研究過程中少數被納入的紀錄片作品。 這部片之所以如此重要,在於它用一整部片的篇幅,非常完整地介紹了大家應該要認識的日本女導演們。這些導演在很早期就開始拍片,熊谷博子也很有意識地在建構他所認知的日本女性電影史。當然,每一種建構都有主觀性,但當影片以坂根田鶴子開始說起時,也能感受這其實是野心滿大的一部片。 我們選片團隊看到它時,都覺得這就是一部「必看」的片,大家看這部片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重要的女導演,但我們過去不一定認識,它真的非常難得。 而與這部片對應的,就是剛剛提到的西方或歐洲脈絡下、女性影展的雛型之一(《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推薦大家可以透過這兩部片的呈現,一邊是亞洲脈絡,一邊是歐洲脈絡,去感受兩者之間的對照。
時間:2025年9月28日 地點:松菸誠品 主持人:女性影展總監 江孟軒 主講:2025女性影展台灣競賽獎遴選評審 史惟筑、洪健倫 文字紀錄:楊昀鑫 主持人孟軒開場:首先感謝誠品生活松菸對場地的大力支持!這場講座有點像選片指南的下半場,延續去年的方式,我們特別把台灣競賽這個單元獨立出來成為專屬的講座,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認識今年的入圍作品。 女性影展從 2014 年開始舉辦台灣競賽獎,今年已經是第 12 年了,創立宗旨是希望能持續推廣台灣女性導演的影像創作。今年徵件作品總共 141 件,經過激烈的評選會議,入圍了 18 部作品。這些作品都會在今年女性影展期間進行決選並公布得獎名單。請大家拭目以待!當然,大家也能在影展觀賞到這些入圍作品。 回到評選過程,我們今天請到兩位講者,就是我們今年台灣競賽的其中兩位初選評審。他們在評選過程當中,也有對自己欣賞的作品展開非常精彩的對話。很榮幸今天可以邀請他們到現場來,跟我們一起親自分享這些精彩的作品。歡迎兩位—— 與談人(史惟筑、洪健倫)介紹 健倫:大家好,我是健倫,我是今年女性影展台灣競賽初選評審。目前我是全職在家當爸爸,身兼影展打工仔的工作者。之前在台北電影節擔任過三年選片人,感謝女性影展今年的邀請,讓我可以跟惟筑、友容一起擔任初選評審。 其實我蠻ㄘㄨㄚˋ的(笑),畢竟我是個生理異性戀男性,想說我真的要來擔任女影競賽的初選評審嗎?真的可以嗎?但我想說,或許可能我過去從大學念外文系,到後來接觸的大多工作環境,都是以女性占絕大多數的環境,多多少少還是有從中慢慢去理解一些女性的觀點。 當然我必須說,我自己跟女性的觀點還是有非常大的距離。不過我自己在有了兩個女兒後,慢慢可以理解到一些身為女性對於未來人生的恐懼跟壓力,所以我有盡可能在看片的過程中去貼近女性的觀點。 惟筑:大家好,也很高興這次可以跟健倫一起擔任台灣競賽初選的評審。我們這次很認真希望可以在影展呈現不同的類型、不同的影片長度、還有不同的形式風格,讓大家看到台灣的女性創作者。 我們現在雖然都是講「女性」創作者,但其實今年的賽制有改。今年賽制是,只要性別認同為女性或是多元性別,就有報名資格。所以我們今年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影片,題材主題各式各樣,我跟健倫其實兩個人的意見常常有很精彩的對峙,等一下可以再來跟大家分享。 健倫:我們在初選的過程之中有帶入了一點選片上的思維,也就是說不是完全依誰拍得最好就能夠入選競賽。我們會去思考,在我們今年的 18 部影片之中,例如劇情片、紀錄片、實驗片之間的比例是否有一定的呈現?或者是在性別的主題上是不是有獲得一定的關照?因為如此,我們會把其中覺得在某一個主題上有代表性的影片拉上來,讓它成為最後入選的作品。最後總共入選了 7 部劇情片、 7 部紀錄片,以及 4 部動畫跟實驗電影。 很榮幸在今年入選片單裡面有 3 部世界首映的長片,其他 13 部作品,多多少少在各個影展放映過,從去年的金馬影展或高雄電影節,到今年金穗獎到台北電影節等等。那有什麼理由再說服跟大家來女性影展看呢?我覺得,當時我們討論的時候也有提到,當台灣整個影視產業,在創作端男性還是在一個相對多數的環境之下..... 惟筑:這邊我想先補充一下。我為了今天講座特地先去查了一下,「金馬獎過去 61 年來有幾位女性導演獲獎?」(指最佳導演獎)我沒有計算入圍,但獲獎的女性其實只有五位。那五位裡面只有一位是台灣導演,就是《哈勇家》的陳潔瑤。另外,許鞍華導演自己就得了三次,非常厲害。但就這個比例來說大概就只有 12% 左右,真的不是很多。所以我們希望藉由女性影展的平台,可以讓大家更了解在台灣還有很多的女性電影創作者,在這個領域裡面很努力,並跟大家分享她們用電影語言所呈現出來的價值與實力。 【長片】 阿婆非死不可・Granny Must Die ——陳怡蓉 Yi-Jung CHEN 健倫:那首先我們介紹的第一部是劇情長片,它叫《阿婆非死不可》,是陳怡蓉導演的作品。它其實是一部電視電影規格拍攝的作品,也是我們這一屆在初選過程之中唯一的劇情長片代表,但這並不代表它是唯一所以就當然獲選。我們會希望讓《阿婆非死不可》這部長片入選,主要是因為它在創意端、執行端上都有滿好的表現。 這部片用喜劇手法來談失智這個議題。除了這在台灣是相對新鮮的一種切入角度之外,還有對我而言,我很喜歡導演在這個影片中,呈現出這個家庭裡面「女強男弱」,爸爸永遠躲在背景環境裡的一個狀態。 它的美術設計色彩非常鮮豔。這些風格好像非常強烈、刻意,但它的刻意是必須的,它跟喜劇的調性其實相輔相成。而且在笑點上,拿捏的也非常剛好,收放自如。有的時候是很誇張的神經喜劇式笑點,可是有的時候又有點黑色幽默,有經歷過的話就會會心一笑。作為創作者,導演的這些掌握程度都非常不錯。 惟筑:還值得一提的是,它除了是喜劇類型外,也是以客語發音的一部作品。台灣既然通過了國家語言發展法,這到底能不能落實在很多的文化產業裡面,還是很值得我們關注。 婚・紗・罩・My Last Wedding Photo ——陳昱伶 CHEN Yu-Ling 健倫:這是導演陳昱伶的第一部紀錄長片,也是她的畢業作品,非常榮幸是在女性影展進行世界首映。我蠻喜歡這部作品的,在評選時我就想說:「會不會只有我喜歡?」(笑) 片子在講的是,導演自己對婚紗照的憧憬,她想要拍一個美美的、夢幻的婚紗照來代表能夠擁有一個幸福的人生,後來發現事情好像不是這樣子的。也因為這樣,她踏上了一個尋找婚紗照這個產業在台灣到底是怎麼樣發展的過程。 惟筑:這部片我們在評審過程當中幾乎沒有討論,因為我們三個人都是給最高分的,基本上就直接入選,也是第一部入選到 18 部片單裡的片子。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就我個人來說,在女性影展討論婚紗這個議題,我們大概通常都會想到婚紗跟婚姻,然後直接就會帶上女性主義批判的眼光來審視。可是相反的,這位導演是非常、非常誠實地告訴大家說:「我好想穿上婚紗呀!」這件事情就很吸引人想要了解,到底為什麼? 她透過梳理婚紗產業及訪問婚紗攝影師,以及片中受訪的婚紗攝影師也分別去闡述他們目前的婚姻、感情以及家庭狀態。這有點像是一個媒介,去呼應導演自己對於婚姻,或她自身狀態的一種拷問。當她問出「我很想要穿婚紗,可是到底為什麼?」這件事情,並透過這一部長片來回應這個問題,真的蠻有趣的。而且導演本人在片中有出現,她非常可愛。 健倫:導演非常用心去挖了整個台灣婚紗產業史的發展過程,跟自我背景養成各異的婚紗攝影師。其實她也從他們身上去尋找,到底什麼叫做幸福?你拍到這張照片就是幸福嗎?那你自己幸福嗎?我覺得這部片其實聽起來題目很大,但是她用一種非常幽默、時而自嘲的方式來講述對她而言帶一點心酸血淚的過程,是一部調性蠻輕鬆的作品。 萬歲家庭・A Long Way Home ——吳念樺 WU Nien-Hua 健倫:這部片也是在女性影展世界首映的長片,同時也是導演吳念樺的第一部紀錄長片。這部片講的是導演自己帶著攝影機回到老家,跟母親對質過去媽媽對她所做的肢體和語言暴力,還有她父親在成長過程中缺席的原因。在這個質問的過程中,她慢慢找到了一個從小反覆出現在夢境中的惡夢,找到那個惡夢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惟筑:其實片名就是導演家小時候住的社區名稱——萬歲家庭,所以導演就直接把片名取作《萬歲家庭》。這個導演很有勇氣,她用攝影機去面對家庭問題。相信大家在看的時候一定會心有戚戚焉,當父母親關係不那麼和諧時,孩子通常會被抓來當作情感的籌碼。也因此,孩子對於父親或母親的記憶,會因為被某一方拉走而產生偏頗,對另一方產生不是源自自己與親人真實關係的理解。我覺得導演在這個過程中,跳出了父母親之間的衝突,試著跟父親和母親分別建立屬於她自己跟對方的關係,看了頗微感動。 健倫:在成長過程中,男性跟母親之間的相處跟女性還是有點不一樣。譬如,從我身邊觀察可以發現,有些女生在成長過程中,媽媽會把女兒抓得很緊,像是「妳跟我是一國的,妳爸就是怎樣怎樣」,這種情況在這部片裡多多少少會出現,一開始看可能會想:「我要看這個幹嘛?」但在跟其他兩位評審討論的過程中,我覺得這部片有趣的地方是,我看到一個家庭成員面臨某種危機時所產生的保護機制,以及這個機制如何影響到女兒——對她人生的認識、對家庭的認識,甚至對她自己性格發展和對整個世界認識。這部片的結局其實也滿令人震驚的,它的回馬槍很強,會讓你從頭去思考剛剛看到、聽到的這一切。 雪水消融的季節・After the Snowmelt ——羅苡珊 Yi-Shan LO 健倫:我相信大家應該對這部片還蠻熟悉的。這是羅苡珊導演的第一部紀錄長片,去年入圍了金馬獎、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長片,也已經上過院線了。 這部片講的是導演的兩位摯友——他們是一對情侶,和導演計畫結伴去爬喜馬拉雅山,但導演因為一些原因無法成行,最後只有這對情侶兩人前往。後來發生了山難,只有男朋友生還。導演懷著一種想盡可能貼近他朋友生命最後一刻的心情,去完成這部紀錄片。 導演不斷詢問倖存的朋友:「那個時候你們在想什麼?你們的心情是什麼?」 惟筑:但後來這位朋友決定不再接受採訪,於是導演決定親自走上那段旅程。 關於這部片,其實沒有太多言語可以分享。非常誠摯地邀請大家去電影院觀賞,很難相信這是導演的第一部作品。後來查了一些資料才知道,她在剪接過程中,日本導演河瀨直美給了非常多的意見,協助她重新梳理原本的敘事線,才有了現在我們看到的版本。這是一部非常貼近導演內心的作品,同時將環境、自然還有性別議題都很隱微地融入在他回溯朋友旅程、重現山難發生過程的敘事當中。看完之後不知道該怎麼形容,覺得很感動。 健倫:請大家一定要去看這部片。導演對冒險精神的嚮往,以及她在朋友身上投射的那種浪漫情懷,有點像是《阿拉斯加之死》(Into the Wild) 裡面年輕人的狀態。她也是抱持著這樣的精神去拍攝這部紀錄片,這有點像是只有二十多歲、還不到三十歲的這個年紀,才拍得出來的作品。 惟筑:它談論青春、死亡、友情、感情、冒險,真的是只有那個年紀才會擁有的想法和感受,有些東西一旦過了那個階段就不會再有了。很推薦大家,雖然它已經上映過了,但如果還沒看過這部作品,真的值得去看看,不要再錯過大銀幕的機會! 大風之島・Island of the Winds ——許雅婷 Yating HSU 健倫:接下來這部則是之後即將上院線的作品,這是導演許雅婷耗時二十年紀錄樂生療養院的抗爭,去記錄這些長者、院民,他們如何在這麼長的時間裡爭取自己應有的尊嚴。不只是權益——我覺得權益是一回事,但爭取政府對於他們應該要有的尊重,才是最打動人的地方。 惟筑:對我來說,其實現在看紀錄片,已經很少——我是說在台灣來講,不能說很少,可能是我看得不夠多——一部片願意在一個地方蹲點二十年,持續記錄樂生療養院的抗爭,非常、非常不容易。如果大家比較喜歡電影的話,可能會知道日本的小川紳介,他也經常以長期蹲點的方式拍攝。 可是在台灣,我想起我一個中央大學的同事說過:「我們現在都不會再等待了。」現在有手機,就算去咖啡廳或去看病,我們已經不想等待,永遠都會用手機各式各樣的訊息填滿我們自己。可是這個抗爭,其實是需要很長時間的等待,而等待最終可能不見得會讓正義獲得伸張。但在那個時間過程當中,我們可以藉由這部影片看到很多東西——不管是拍攝者、抗爭的樂生青年,以及特別是療養院裡面院民的整個過程。從原本開始抗爭時還覺得可能有希望,一直到裡面的人慢慢凋零、慢慢凋零,到最後結束。 健倫:最令人感慨的是那個凋零,就是那個年紀的逝去。因為樂生的抗爭運動,其實是很多社運界或者藝文領域的參與者,對於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起點——應該說是在我們這個年紀的政治人物。但我自己是沒有經歷過的,所以我是用一個比較有距離的方式去看這部片。而導演在這部片中,並未刻意去喚起當時的種種情緒或情懷,片中會看見政府一些官僚體系的拖延、敷衍,可是這些院民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去爭取他們應該有的、身為一個人的尊嚴。可能到最後等不到了,這個過程是最讓人感慨的地方。 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Welcome to Taipei Main Station Hall ——曾文珍 TSENG Wen-Chen 健倫:這是曾文珍導演創作的最新作品,也是在女性影展世界首映的作品。台北車站大廳在多年前取消了大廳長椅的政策,但大家還是有在那邊聚會的需求,所以這部片就是從北車大客廳裡面聚集、聚會的這些印尼移工出發,尤其是聚焦在家庭移工、女性移工身上。 這部片分成四個段落拍攝四個不同的主角。特別的是,過去我們在看到、想到關於移工有關的作品時,切入點總是在控訴台灣對於這些移工的壓迫、剝削等,但這部片帶出的觀點並不全然是這樣。裡面還是有移工可能在台灣遭遇到一些不好的經歷,但導演也帶出,其實有些移工在台灣很幸運地獲得了一些不錯的工作環境。這讓她們在行有餘力之時,可以去照顧在北車的其他同鄉,甚至到漁港去照顧印尼的漁工,照顧他們心理上、精神上、閱讀上的需求等等。同時也有因為在台灣遭遇到一些挫折,因此透過藝術創作作為一種治療以及表達的工具,最後走上藝術創作之路的人。另外,也有移工是來到台灣開始追星(笑)。 惟筑:對,裡面有一位移工非常喜歡蘇打綠,因為蘇打綠的關係,她開始認真學中文,中文非常好!她也會用中文寫日記跟心情,後來更回到印尼從事翻譯工作。 可以從這部片裡面看到,每一個移工都有自己的樣貌。當然壓迫的情況在此時此刻的台灣可能依舊沒有獲得很大的改善,但我們至少在這部片可以看到,這些人在台灣生活時,她們如何長出自己的能動性、主動性,去透過其他的媒介,成立支持團體。她們其實在這裡也會關心印尼的大選,會舉辦集會,互相幫助、鼓勵,這都滿令人感動的。 健倫:對,很重要的是,它讓我們看到這些女性個體,她們在台灣為自己、為家庭去賺取收入的時候,展現出一種很堅強的生命韌性。 【短片】 這之中包括劇情短片、紀錄短片和實驗短片。其實台灣競賽是一個不分種類的競賽,這也是我們當初討論時最大的難題之一——長片要怎麼跟短片比?劇情長片又怎麼和實驗短片比?因此,我們也花了不少時間思考,到底哪些作品值得被提名。 討論過程中,三位評審最在意的是:創作者在面對題材時,是否真的理解自己的題材,並選擇了最合適的媒介、長度與形式。以短片為例,它的長度是否恰到好處?有沒有無病呻吟而硬是拖成長片?又或者,在短片形式下,是否有意識到必須在有限時間內抓住觀眾的注意力,同時把議題闡述得足以激發更多想像?這些都是我們評判短片時的重要依據。 最後,今年的短片被整理成三個節目,主要依照作品之間在主題上的交集來分類。但在每一個短片節目中,也會看到不同類型的作品並存。 【短片輯 #1】:聚焦非典型關係 第一個短片節目,比較像是聚焦在非典型關係,所以會在裡面看到各種不同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親情的關係等等。 愛情★星星・LOVE★STAR ——李姿婷 LEE Tzu-Ting 健倫:第一部短片是我的愛片,她的畫風非常幽默。預告片中只能看到它的 A 面,它還有另外一個 B 面。 A 面畫風非常漂亮,插畫手法很細膩,細膩到我直接寫在評論寫:「出繪本我會想買!」 而且導演不只是做了一個插畫風格很強烈的作品,創作者還知道「要怎麼去打破畫面中的框」,對應劇情去翻玩媒材上的限制,是對媒材很有意識的創作者。 故事在講的是,一顆星星有一天突然愛上了大海,它想盡千方百計向大海示愛,卻始終得不到回應。其實是在講愛情,在講一個非典型、跨不同種類的愛情。 惟筑:它的B 面就要進到電影院裡面去看,B 面是非常有趣的。 健倫:對,很像《銀魂》,突然性格大變。可是很妙的是,導演在這兩種不同的、幾乎是精神分裂般的兩種極端人格之間切換,但切換得很順。 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可以現在先提,因為在專文裡面有提到——其實今年入選的有三部動畫短片,它們分別是在三個不同背景養成之下形成的作品。像《愛情★星星》的創作者是在東京藝術大學所受的動畫訓練,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一個嚴謹而細膩的風格,它的 B 面很東京、也很日本。還有一部短片是在歐洲受的動畫教育,另外一部是在美國受教育,然後在台灣也經過一些產業上的工作經驗。等一下會看到她們的風格是非常不一樣的。 風流少女殺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 for the Lady Avengers ——洪瑋婷 Birdy Wei-Ting HUNG 健倫:如果大家有在關注台灣影展,你可能已經聽過,因為她已經拿獎拿到手軟了。這部片是在仿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以及結合一部分《瘋狂女煞星》裡面的影像風格以及劇情元素,來做成一個少女——算是遐想嗎?,少女的非典型遐想。 惟筑:因為它就叫做《風流少女殺人事件》,然後看到女主角的穿著,你馬上就會想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可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面的女生是被殺死的,我們先不要管它是怎麼改編真實事件或什麼的,它裡面的女性其實是沒有能動性的,她就是一個客體,被愛、被殺掉。 這部片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賦權——不是那個父權,是 Empowerment。賦予那個被消聲的女性的聲音,一些力量,重新活靈活現地出現在實驗的形式裡面。她會讓你看到「我的性、我的慾望」。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少女是被慾望的對象,可是在這裡面她會一直不斷告訴你:「我在展露我的慾望,甚至我的身體也是我為了要展露給你看的那個慾望。」我自己很喜歡這部片。導演跟台灣電影史的一些經典影片致敬,雖然說《瘋狂女煞星》也是她致敬的對象,可是看到西瓜就一直讓人想到蔡明亮。 健倫:沒錯,主角在片中的眼神讓也會讓我想到楊德昌的《指望》。 惟筑:看了會知道她一直在跟這兩位男性導演對話。在這兩位男性的作品裡面,女性經常缺席,導演就是透過這部片談:「現在換我們來講話了。」非常推薦這部影片。 健倫:說到她該講話,但這部片裡面完全沒有對白。它是實驗片,可是並不難懂,導演厲害的是,靠剪接跟構圖,以及影像在各種特寫跟遠景、中景之間的切換,去帶出故事的節奏跟氛圍。真的是很厲害。 惟筑:難怪拿獎拿到手軟! 健倫:其實今年我們看到幾個年輕的女性創作者的短片都在做類似的事情,也就是把少女在過去影視作品中的形象進行反轉,展現出惟筑剛剛講的「能動性」,讓女性變得更主動一點。不管是國內外的電影,少女的形象經常是清純、被動,然後是別人情感的投射對象,她永遠是被愛的那一個,或者是「被」怎樣的那一個,現在的作品中則可以看到,這些少女要自己出來做一些事。 草莓蛋糕・Strawberry Shortcake ——莊岱雯 Deborah Devyn CHUANG 健倫:這是莊岱雯導演的最新短片。導演留學美國,受到邪典電影很深的影響。她很喜歡邪典作品,裡面有很多可以玩的、可以討論的東西。 惟筑:在評審會議的時候,我其實有一度覺得被挑釁到了。看完這支影片時,覺得非常不舒服。真的要選它嗎?我一開始是很保留的。可是我又想起,我常常在教電影或在分享電影時提到,我們就是需要電影來挑動、挑釁我們,去把我們原本既有的常規,或把我們原本的一些想像翻轉掉。另外一個評審友容,就是我們在美國的評審——她講了一句話,她說:「可能它是一個淫夢,也有可能真的有母女關係是這樣。」我就重新再了看一次,用其他的觀點去看,它真的是個非常挑釁人道德邊界的一部片。 健倫:我們在講到所謂的女性剝削電影,它永遠是在道德觀上極盡所能地去把觀眾挑動到最徹底。所以其實莊岱雯導演也在這裡用類似的方式,很露骨地談論慾望這件事。然後她不只是冒犯女性,其實身為男性觀眾,你在裡面也會像被打了一巴掌一樣。它有些畫面是,你不會在一般的電影看到的男性影射。無論身為男性、身為女性,在觀看時都會有些坐立難安。導演其實很隱晦地在講一段母女間的關係,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釋。我也有自己的解釋,主角可能在做一件對母親的復仇之類的,但為什麼?觀眾可以自己解讀看看。 莊岱雯導演也用了一些過場的鏡頭,是很實驗性的手法,有非常強烈的影像風格,去讓你去探討這種觀看跟慾望之間的關係... 惟筑:還有對於母女的想像。 健倫:對,還有「戀物癖」也在這部片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她滿敢拍也敢去挑戰觀眾的,尤其,敢挑戰觀眾這件事情,是身為創作者一個很值得、很需要具備的要素。 金魚缸小姐・The Fishbowl Girl ——巫虹儀 Hung-Yi WU 健倫:這是巫虹儀導演的第三部短片,也入選了許多影展,像是國外的克萊蒙費宏國際短片展、去年金馬影展的最佳短片以及今年的台北電影獎,各個重要的競賽都有入圍。我喜歡它的前半部,然後惟筑喜歡它的後半部。 我喜歡前半部是因為,它用一種不直接點名的方式,告訴你這個主角跟她的曖昧對象之間的關係,以及當主角看到曖昧對象跟別人好的時候,自己心裡的感受。這個東西回過頭去,其實是反映出導演本人以及編劇,對於角色的認識程度有多少。 惟筑:喜歡後半部的原因——是因為有床戲(笑),是這樣嗎?不是! 後半部女主角跟男性朋友們去洗了泰國浴,導演在處理泰國浴的場面調度,我非常喜歡。泰國浴是裡面的女子提供性服務,關於性服務這件事情,導演通過場面調度,先處理了「服務」,再處理了「性」這件事情。她在處理性場景的這個部分,把「奇觀」的部分降低了,把提供性服務的人「客體化」的成分也降低了。總之,導演處理兩個女生在泰國浴的這部分是我非常欣賞的。雖然這是很小的細節,但歡迎大家去看的時候,想想到底我在講的那個「服務」是什麼?為什麼是先處理服務再處理性? 健倫:這個故事是在講一群大學生,一起相約到泰國畢業旅行。裡面男性們忍不住說:「嘿,都來泰國了,泰國浴很有名,是不是晚上大家幾個人約一約,一起去鬆一下?」片中的女主角是一個 T,大家也都把她當作兄弟一樣看待,所以自然就約她,這個故事就是這樣發生的。 後半部的床戲,對我來講好像有點功能性,想展現出一種不同性別之間對於性消費這件事情的態度。因為一般從事性消費的男性,女性就是一個他的慾望對象,或說是他釋放慾望的對象,因此可能什麼事都不太需要多處理、多講。 惟筑:這部片在女生跟女生的性場景就有很多的溝通。導演也有帶這部片到中央大學來,然後我記得就有學生就問:「是不是女同志話都很多?所以就是連性消費的時候話都要一直講、一直講,然後才能進入到那個部分?」 健倫:看得出不同性別之間對於性這件事情的看法不同。 【短片輯 #2】:處理家的羈絆 接著的四部短片主要圍繞「家」的議題,探討家人之間的羈絆。 近視・Myopia ——張善淳 Siān-Sûn TIUNN 健倫:這部短片,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 惟筑:我個人是最喜歡的,於是就要來說服其他人。 健倫:先分享我當時看完的觀點。今年其實收到了不少兒少相關作品,如果要講跟小孩有關的故事,目標觀眾又包含小孩,說故事的方法就必須調整。因為小孩注意力比較短,理解方式也和大人不同,若用太成人的方式,小孩不一定能看懂;但如果完全切到小孩的頻道上,又會讓作品放在影展競賽裡顯得有點尷尬。我覺得《近視》在「兒少」和「成人觀眾」之間,抓到了一個非常好的平衡。 故事講的是一對母女,女兒大概五、六歲,來自單親家庭,媽媽是個年輕的直播主。女兒近視,醫生交代要固定點眼藥水。媽媽覺得既然近視已經很嚴重,那直接戴眼鏡就好,但小女孩卻一直拒絕戴眼鏡,堅持靠點藥水就能治好眼睛,她其實只是想要媽媽多注意她,希望媽媽每天親手幫她點眼藥水。而媽媽的處境也很真實:白天要工作,晚上想跟朋友出去玩,因此常把女兒獨自留在家中。導致女兒很渴望媽媽的陪伴,卻常常落空。 惟筑:這部片只有十五分鐘,細膩捕捉了母女的生活張力。其實很多女性創作者都會拍家庭、親情,尤其是母女關係,但這部片讓我驚喜的是,它也同時讓小孩當主角,而且處理得很自然。 我很開心看到這類片增多,一直以來台灣兒少題材相對少,孩子們多半看的是國外的影視內容。如果有更多創作者投入,說出屬於我們本地兒童的故事,會是一件很棒的事,今年有趨勢看見越來越多創作者投入這個類別。而且導演們都知道和小孩合作拍戲是非常困難的,但這位小演員的表現非常自然,和飾演媽媽的互動也很真誠。 更值得注意的是導演的鏡頭語言,用了很多特寫與失焦,讓觀眾感受到小女孩的內心狀態。有人可能會覺得這樣的表達方式過於直接,反而被視為缺點,但對我來說,這是個優點。 健倫:沒錯。因為整部短片幾乎都在主角住的套房裡拍攝,這是相對吃力的地方,也是我們其他兩位評審一開始覺得沒那麼討喜的部分。它使得場景畫面相對單純、單調方,相對有一些侷限。 但最後,我被說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導演對角色的認識,真的非常深。她很清楚年輕單親媽媽在生活中對「自由」和「責任」的拉扯,也讓我們看到小女孩強烈的依賴。這些訊息完全透過角色互動展現,而不是台詞直接告訴觀眾,這是我期待在短片裡看到的東西。 惟筑:這位導演在公視學生劇展又拍過一部短片作品《髮圈》,同樣處理母女之間的渴望,而且用的還是同一位小演員。導演似乎持續透過作品,處理自己對母女關係的反思。 跳房子・Little Mirage ——劉人鳳 LIU Ren-Feng 健倫:下一部是紀錄短片《跳房子》,我們兩位都非常喜歡。它很棒的地方是,導演在前一部紀錄短片《乙方及其後》討論了租房子產生的一些問題後,開始對「家」這件事情有更多思考。在《跳房子》裡,她找微縮模型師把老家的客廳重新用模型還原,帶著這個模型去找她分別住在不同地方的爸爸、媽媽還有弟弟,問他們:「你看這個模型跟以前像不像?」他們就會提出:「有像,可是有什麼地方有點怪怪的,以前不是那樣子。」 很有趣的是,每個人指出的點都不一樣。可以從指出的點看到,這個人在家庭裡的角色會讓他一直去注意某些面向。比如說媽媽注意到書櫃,弟弟的關注則是電視。能夠看到透過一個小小的模型作為影片的引子,帶出每一個被攝者不同的觀點,以及他們對於家的切入點跟印象。透過這樣小小的一個物件,引發出很大的、無限的想像,包括被攝者,也包含我們這些看影片的人。 惟筑:這個「跳房子」就有點像跳格子。導演是用一種視覺化的方式,就像剛才健倫講的,連她的爸媽現在都住在不同的城市,而弟弟跟他太太住,導演自己也住在不同的地方。導演就用不同的媒材,比如用 Google Map 顯示「現在要去哪裡?要去到媽媽的家,距離幾公里...」。應用Google Map、照片或是模型——每位家人看到模型的時候會想:「我們家以前真的是這樣嗎?這裡真的有這個東西嗎?」用地理上的距離跟記憶上的距離去重建這個家,以及以前屬於「一家人的家」到底是什麼樣子,蠻可愛的。 其實很多電影都在講家庭,幾乎所有題材都被創作者講過了,但導演們還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什麼樣的觀點去談這個議題方?《跳房子》的確找到了一個新的測量「家」的距離的方法,是我很喜歡這部影片的地方。 健倫:我相信很多觀眾可以從這部片找到一些共鳴,大家大多是是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的觀眾。我們在這個成長階段,家的模樣跟家人之間的關係和距離也一直在經歷很多不同的變化。有時候也會想:「為什麼我跟我爸媽之間的關係現在是這個樣子?」或者「我們家為什麼現在的相處模式跟以前不太一樣了呢?」在這部作品裡,都可以找到這種思考的共鳴。 貓與雞・After the Cat ——朱凱濙 CHU Hoi-Ying 健倫:這是香港導演朱凱濙導演的最新短片作品。導演的前一部短片《紅棗薏米花生》,我也非常喜歡,她一直都是一個很擅長寫實風格的創作者。《紅棗薏米花生》關注的是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媽媽對小孩子的照顧、成年子女對媽媽的回應。這部片則是導演在台灣拍攝,處理的話題往外擴大,是人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故事其實很簡單——一位女士,她的貓過世了,她要把牠埋葬。她用一種很類似趙德胤《冰毒》那時的寫實、對環境的關注拍攝這部短片。趙德胤是將鏡頭擺在那,一直拍大家走過去、走過去、走過去,每個畫面之間切換都有一種犀利的感覺。而朱凱濙導演在這部片中,拍攝這些現實的東西時,做了一種溫柔的處理,不論從影像的色調上、風格上都有這種感覺。還有一點很令人喜歡的是,即使這是個劇情片,她在裡面凸顯出一種對於整個真實環境的尊重,因此便讓「真實」深入到這個劇情片的裡面。 惟筑:作品裡面的時間性很特別,除了裡面的人在面對死亡的時間感受外,比如拍空景時,有時雞會跳到她們家料理台上,導演就把攝影機放在那邊;或者貓躺在那邊,可能已經死亡了,她就慢慢地放一個很長的鏡頭,放很長的一段時間。所以當你在面對死亡,或面對這個關係時,那個時間性也會投射到我們自己身上。它讓我們啟動對於時間的感觸,是非常細膩的一部片。 大家也可以在這部片看到楊麗音這位非常優秀的資深演員,截然不同的表現。在另外一部《阿婆非死不可》裡,是比較誇張、戲劇性的喜劇表演,這裡就完全是另外一個面向,是個非常厲害的演員。 健倫:沒錯,而且朱凱濙導演她很願意花大量的時間去等待事情的發生。她用了一個很近的特寫鏡頭在貓咪的前面,然後你就會看到牠的呼吸越來越淺、越來越淺、越來越淺,最後牠就沒有動了。她捕捉這個時刻,那個力道對我而言蠻強烈的。 山裡走走・Prey and Prayers ——全懿儒 Langui Madiklaan 健倫:這是部劇情短片,是全懿儒導演的作品。導演自己是布農族人,但她過去的經歷比較是在產業裡面從事跟類型、商業片相關的製作(擔任副導)。這部《山裡走走》,我認為是類型風格比較明確的作品。 惟筑:你覺得這是一部類型風格比較明確的作品?跟我想的不太一樣,這就是我們評選時有趣的地方。 健倫:影片講的是一對布農族父子,他們晚上想去山上打獵,打獵時,一直遇到森林裡有些跡象,跟老人家說的禁忌有關。爸爸便一直提醒兒子:「要小心,等一下可能會有事。」但兒子仍想,他難得來打獵,終於打中了一隻獵物,但牠又跑掉,他很想去把牠找回來。而爸爸只是說:「不行,這個是禁忌。」後來就真的發生了一些不祥的事。片中,比如在山裡打獵時,有東西掉下來,我認為是導演想去營造的懸疑氛圍,其實是很類型片的,包括她的攝影方式、配樂的運用與聲音等等。 惟筑:它整部片都是在夜裡的山中拍攝的,氣氛營造非常好。 在山林裡面等待獵物,展現性格完全截然不同的父親跟兒子的關係。兒子就是「我已經打到獵物了,但為什麼我沒有看到牠?」其次,是環境、聲音跟夜裡的黑暗所營造出的神秘感,也許可以回應導演想要表達的——在原住民的信仰裡面,我們到底要如何跟這個環境相處?如果你把自己的「我」放在太前面,像是片中的兒子就是對照組,那他可能會怎麼樣?我很喜歡它光線運用的方式,但我可能不太會聯想到類型片的方向,也許可以帶著健倫的觀點再看一次。 健倫:順帶一提,《山裡走走》也是今年入選影片裡面跟原住民議題相關的代表,但其實我們也不只收到一部跟原住民有關的片子。我們希望除了形式外,在題材上也可以多元一點,讓不同的題材都可以被看到。 【短片輯 #3】:聚焦個人生命經歷、心理思考狀態 今年台灣競賽的最後一個短片節目也有四部短片。這個節目比較聚焦在我們個人生命中的一些經歷、痕跡,可能是關於我們心理思想的狀態,或是關於我們的生活,甚至觸及更大的生命經驗。 褪皮 以及露出來的・The Peel ——林南彤 Nan-Tung LIN 健倫:第一部是一部動畫短片《褪皮 以及露出來的》,是留歐導演林南彤的作品。她在歐洲學動畫,所以整個畫風跟氛圍——如果之前有關注台中動畫影展,看過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的動畫作品——就會發現它的風格非常歐洲。 歐洲動畫常常會觸及比較內心、更深沉甚至偏陰暗的面向,這部片也是如此。它像是作者跟自己內心的「內在小孩」對話——那個可能曾受過創傷的內在小孩——是一個和解的過程。 這部動畫很厲害的地方在於,跟剛剛提到的《愛情★星星》一樣,在動畫技法、繪畫技法上非常出色。導演能掌握不同的材料,像是粉蠟筆、色鉛筆,運用不同材質的特性來創造效果。精彩的是,她很懂得用這些繪畫效果去觸動觀眾的心理感受。 而且她很敢在畫面上呈現一些具有「觸覺感」的東西,讓你產生身體上的體感反應。這些畫面會勾出觀眾心裡正面或負面的情緒,是這部作品最精彩的地方。 蒸發書簡・Jouhatsu Letters ——張若涵 Johan CHANG/工藤雅 Masa KUDO 健倫:下一部短片《蒸發書簡》,是由台灣導演張若涵和日本動畫導演工藤雅合作完成,這是一部非常本格派的實驗短片。兩位導演是在日本認識的,後來因疫情分隔兩地,便用「影像書信」的形式互相交流。 惟筑:她們各自記錄自己的生活,再把影像寄給對方,對方可能再從這些影像進行再製或回應,整部片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對話。你會看到雙螢幕、疊印等形式,她們討論的是:當我們看到影像時,還能看到什麼?又有哪些東西是看不到的?因為有兩位創作者,這些交流的方式變得特別精彩。 健倫:她們不只是用膠卷拍攝,更多時候是用很手工的方式製作。有些畫面是靜止影像的逐格翻拍,必須自己在暗房裡用翻拍機一格一格完成。 惟筑:以沖片為例,她們也不是用傳統方式,而是隨手取材,像是用維他命 C、咖啡來沖片,因此影像的質感與色調都很獨特。 健倫:我特別喜歡這樣回到本格實驗電影的創作態度,對媒材與製作方法的關注,在數位當道的時代已經很少見了。尤其導演若涵才二、三十歲...... 惟筑:對,她出生於數位時代,但因為在學校參加過一個實驗電影導演的工作坊,對膠卷產生興趣,後來幾乎都以膠卷創作為主。 健倫:這部片很安靜,需要大家花一點心力去看。 惟筑:它的聲音非常細微,對白也不是直接聽到,而是用字幕呈現。 健倫:裡面還包含了工藤雅導演的動畫,畫面也相當可愛。 惟筑:對,兩位導演都很注重材質,但用的媒材完全不同,她們之間的影像對話非常值得一看。 健倫:同時,我覺得這部片也讓我們回顧疫情期間人與人被迫拉遠距離的生活狀態。當無法接觸時,創作者如何從身邊的物件與環境中觀察獲得靈感。 風的前奏・Rocked by the Wind ——黃小珊 HUANG Hsiao-Shan 健倫:第三部是動畫短片《風的前奏》,由導演黃小珊創作。她是留美背景,也參與過台灣一些產業型動畫製作,這樣的經歷反映在作品的節奏與風格上,和前兩位導演完全不同。 惟筑:她今年也以這部片獲得金穗獎大獎。 健倫:故事很簡單,一場颱風即將來襲,台中草屯的一家人如何準備這個夜晚。影片充滿青春氣息,也帶點懷舊風格。 惟筑:動畫最大的魅力就是能表現出攝影鏡頭無法拍到的東西,而這部片就充分展現了這點。我特別喜歡它的轉場設計,既細膩又流暢。像是男主角在車站聽 iPod 的場景,先用全景呈現,再透過前景裡他操作 iPod 的手帶你轉場。畫面中結合了速寫筆繪、寫實的照片與小模型,與動畫角色混合得非常自然。故事雖短,但非常感人。颱風天裡,媽媽和妹妹卻遲遲沒回家,那份焦慮與擔心被描繪得非常細膩。 健倫:裡面角色的氣口也很鮮活,彷彿就是我們身邊的家人或鄰居。 惟筑:片中有提到,爸爸以前是製作薩克斯風的。但產業沒落後媽媽去做辦桌,讓日常故事多了一層在地意義,默默讓我們看到台中已經沒落的夕陽產業。 健倫:技法上,創作者結合了多種繪畫方式,還加入照片與 3D 模型,和導演之前的作品《大冒險鐵路》有點相似。這也呼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三部動畫短片,它們都展現了「動畫能做到電影拍不到的事情」,並透過不同技法、材質或 3D 與 2D 拍攝方式的結合,展現出高度的創意。 吹得到海風的地方・Where the Sea Breeze Blows ——陳韶君 CHEN Shao-Chun 健倫:最後一部是紀錄短片《吹得到海風的地方》,由陳韶君導演執導。她也曾拍過劇情短片,這部作品的背景之一是導演外公自殺後,對她和母親帶來極大的打擊。片中捕捉了最後一班開往澎湖的台華輪,船上既有澎湖居民往返,也有專程搭最後一班船的旅客。這些人與景,成為導演尋找外公痕跡的背景,她也試圖藉此貼近外公生命最後的心境。 惟筑:我非常喜歡這部片,在家看時就想在到大銀幕看感受一定更強烈。它讓我想到今年女性影展的焦點影人——香妲·艾克曼。艾克曼的作品常用定焦鏡頭長時間凝視,把看似客觀寫實的影像轉化為主觀的情感投射,而《吹得到海風的地方》也掌握了這種力量。導演一開始拍攝海景,並說:「我身為澎湖人,但我非常討厭海。」隨著影片展開,看到家裡的廚房、吹動的電風扇、走過的貓、船上的乘客。這些安靜而細膩的鏡頭,加上極低頻的聲音,就在這樣的氛圍裡,導演把對外公的傷痛,以及她與母親的情感,寄託在澎湖的地景與船上的空景之中。畫面與情感互相加成,形成一部沉靜卻極具力量的作品。 健倫:攝影也非常出色,捕捉了澎湖不同港口、地景與船上人潮,讓我們從中感受到島民對家、海、島嶼的複雜心境——抗拒、無奈或其他情緒。寄情於景最後留下的,是一部安靜卻深深打動人心的影像,非常動人。 以上就是今年入選台灣競賽的十八部作品。即便有的作品可能相對有一點挑戰性,但都非常值得大家去看。 Q&A時間 Q1 :我剛剛Google 了一下,有些影片就像評審說的,不是每天都在重複日常,而是會刺激我們去思考,讓我們在影像或互動中重新檢視自己的行為。我想問一下,這次看電影是一部片一張票嗎?是否建議看完之後休息一下,先消化再看下一部? 孟軒:如果是長片,就是一個場次一張票。短片比較特別,因為片長短,我們把四部短片集結成一個放映節目。買一張票,就能一次看到四部短片。 惟筑:看片的步調完全要看觀眾自己的狀態。有時候我也會一口氣看很多,但有時候看完一場就覺得需要時間沉澱,也會選擇放掉下一場。這其實也是一種跟影像的緣分,端看你想怎麼安排跟這些作品的對話。 Q2:想問個比較敏感的問題。近十年來大家常談到性別光譜。既然是女性影展,那在評審的時候,你們會不會因為性別光譜的議題,在思考上有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尤其是現在有陰柔的男性、粗獷的女性,你們怎麼看這些差異?是不是有些東西就是「女性才會有」? 惟筑:謝謝你的問題,其實一點都不敏感。這確實是我們今年有討論到的,才會有更開放的報名資格(認同為女性或非二元性別)。過去我們寫「女性導演」,但因為有些創作者雖然生理上是女性,可是她不一定認同這個詞,我們今年就把報名的光譜打開了,讓酷兒、同志、跨性別創作者也能報名。在評選時,我自己還是會希望作品能和女性或性別議題有所連結,但我們的想法就是尊重導演的自我認同,然後看她/他如何把議題表現出來。 健倫:補充一下比較實務的面向。我們在報名資料裡會看到導演的自我認同,例如有人寫女性,有人填非二元。我在看片時,會先留意這作品和性別或女性議題的連結。但看完 141 部作品後,最重要的還是「有沒有把事情說好」。最後還是得回到品質——題材有沒有掌握清楚?形式上有沒有做到最好?這才是我們最終評斷的依據。 Q3:我想問形式上的問題。影展裡有劇情片、紀錄片、實驗片,還有長片短片。你們在比較的時候,是怎麼判斷不同形式的優劣?是看如何回應主題嗎? 健倫:我自己會先把它區分成「敘事」跟「非敘事」。重點還是導演自己對題材夠不夠清楚。像有些作品知道題材需要非敘事或拼貼,就會選擇那種方式。關鍵是導演清楚知道「為什麼要用這種形式」。例如《跳房子》就用了紀錄和拼貼媒材,像 Google Map 的影像,讓題材變得更有趣。對我來說,這就是導演知道自己想要說什麼,並且找到了最合適的工具。 惟筑:對,我也覺得導演的選擇能不能被執行好,是我們最看重的。我們評審討論之前其實就有共識,希望能展現不同形式的多樣性,所以我們會刻意平衡,比如要有實驗、紀錄、動畫、劇情。但最後比較的時候,還是得看導演在這種形式裡能不能做到最好的效果。像《雪水消融的季節》故事的確需要長片的時間來鋪陳,但《吹到海風的日子》只用 30 分鐘就創造了沉浸感,兩個都很厲害。所以評判的主要標準是導演選擇了這個媒材後,有沒有做到把故事說好這件事。 健倫:補充一點關於實驗片。很多人會標榜「實驗」,但對我來說,實驗片應該在影像形式或素材運用上,真的有一些突破,讓觀眾開始思考「這算電影嗎?」出現這樣的對話才是實驗片帶來的挑戰。因此,最後還是要看導演是否清楚知道自己為什麼用這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