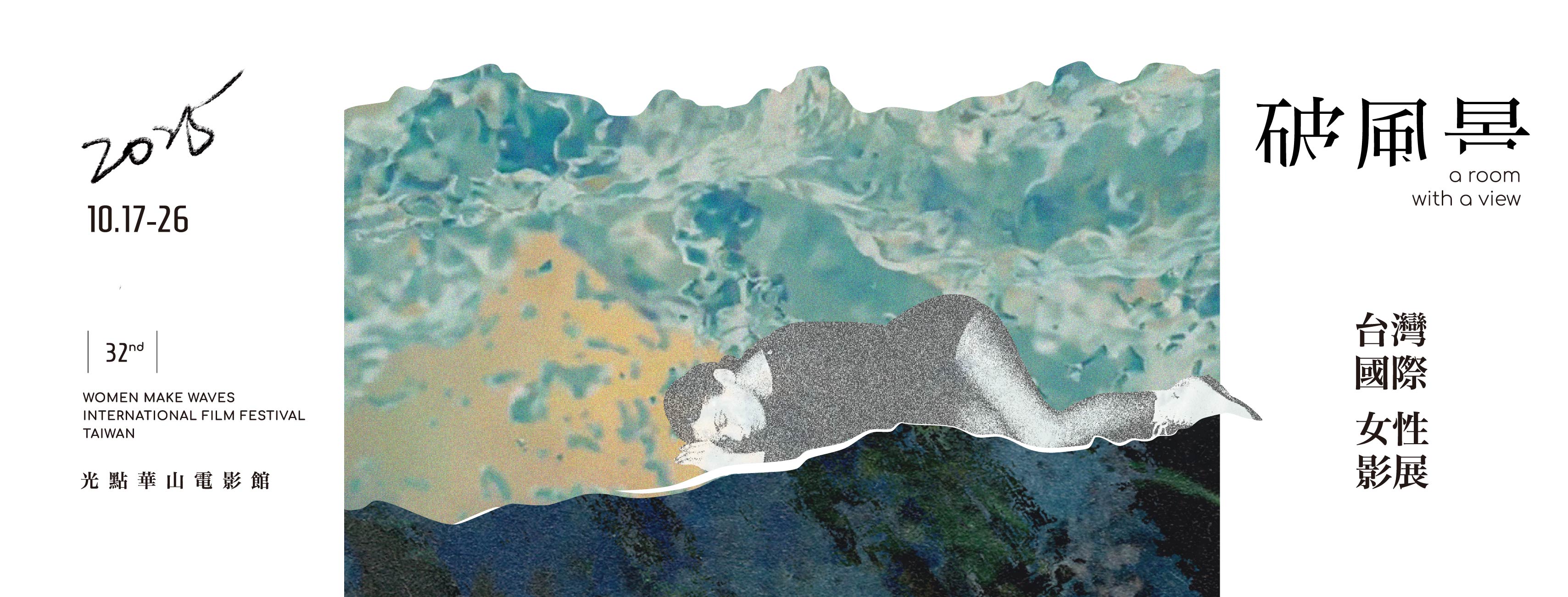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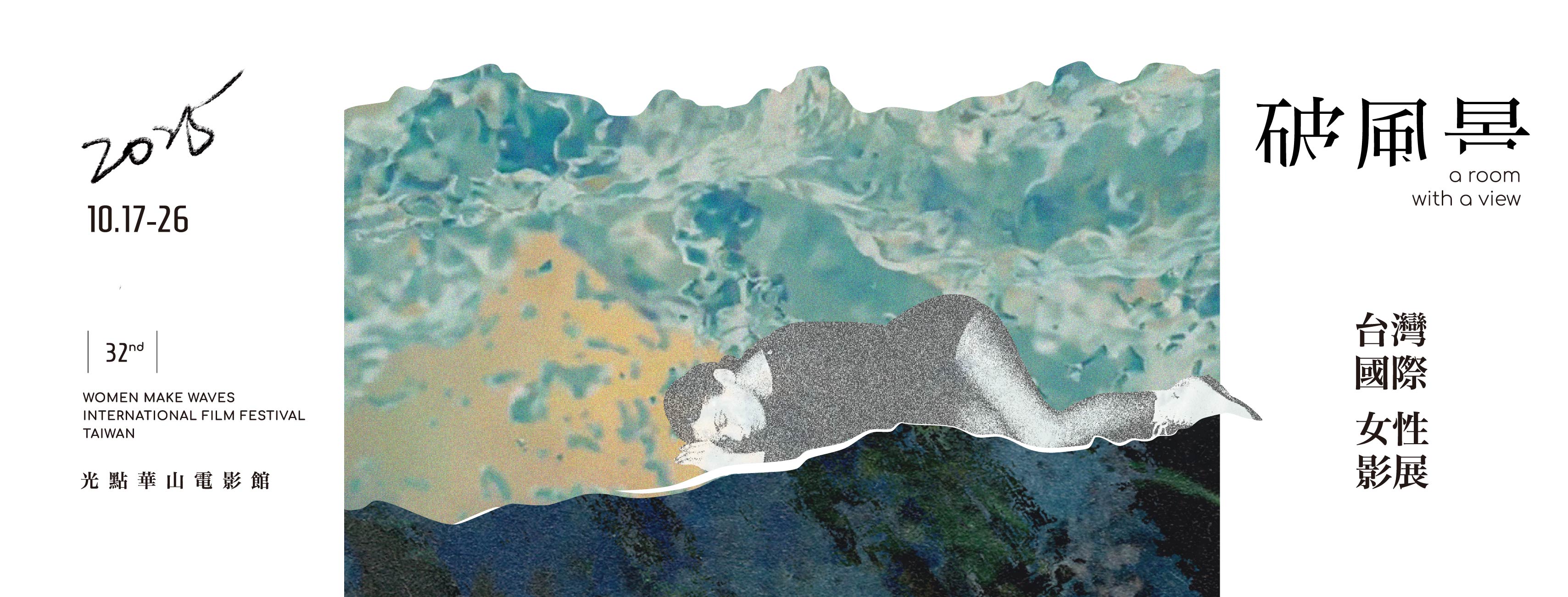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時間:2025 年 10 月 19 日
地點:財團法人三創育成基金會(共想咖啡吧!)
主持人:女性影展策展人 陳慧穎
主講:克萊爾.阿瑟頓
文字紀錄:楊昀鑫
慧穎:謝謝大家今天來到大師講堂。克萊爾.阿瑟頓從 1980 年代就已經開始從事剪輯,從IMDb 上的數字可以看到她剪輯過 50 部以上的作品,但我相信一定更多。我剛剛初步問了阿瑟頓,知不知道她自己參與了多少部影片?她其實也有點不太清楚。
與艾克曼合作外,阿瑟頓也跟無數資深導演、新銳導演合作。參與作品類型橫跨劇情、紀錄、實驗。除了電影外,她也有參與一些錄像裝置創作。錄像裝置的合作,則是從跟香妲艾克曼合作時就已經開始。
2019 年時,阿瑟頓在盧卡諾影展獲頒一個專門給幕後影視從業人員的獎項——Vision Award Ticinomoda。這是非常重要的肯定,她更是首位獲得此獎項的女性。
今天實在很開心能夠邀請她進行大師講座。這個講座是搭配今年的【焦點影人:香妲艾克曼】。我想那我們先從阿瑟頓跟香妲之間的合作開始聊。
初識艾克曼
慧穎:在《故鄉在彼方》(Là-bas) 的映後座談, 阿瑟頓有簡單提到,最一開始跟香妲合作是《Letters Home》(1986),她們認識的機緣跟她在西蒙波娃影視中心工作有關。
先請阿瑟頓從她最一開始跟香妲的相遇開始。請問妳第一次接觸香妲時,對她的第一印象是什麼?以及是怎麼樣的契機,開始發現自己好像可以試試看剪輯這件事?
阿瑟頓:謝謝大家來今晚的講座,也謝謝慧穎的介紹。我跟香妲是在 1984 年認識的,當時我們一起做一部舞台劇的拍攝。那時候我是被派去擔任攝影技術層面的協助。請我去的是黛芬・賽麗格(Delphine Seyrig),一位相當有名的女演員(有參演艾克曼的《珍妮德爾曼》,本身也是導演)。
我過去後,就在現場架腳架。攝影器材都架好了,本來應該是香妲自己要來拍,我幫她對焦。但在拍了兩分鐘後,她就覺得今天感覺不對,於是就請我拍,改由她來負責對焦。
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我當然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機會發生,我也非常驚訝。而且當時我很年輕,才21歲,真的沒有料到會如此榮幸。但我當下沒有想太多,就專心在我的拍攝工作上。
非常有趣的是,每次我的鏡頭可能想要往左轉、往右轉,或想要 zoom in 特寫某個地方時,香妲都正好要給我下一樣的指令。很快地我們就發現——我在這邊引用她當初說的——我們在同一個時間都會感受到一樣的東西、想到一樣的想法。在拍攝結束後,她跑去跟黛芬・賽麗格說:「今天這個小朋友是誰?我覺得她很棒,我想要繼續跟她合作。」這就是我跟香妲相遇的故事。
我自己也蠻喜歡我們相遇的這段故事。第一,當然是因為這對我來說很有意義、很動人;第二是,我想,透過這個故事,大家也可以稍微一窺香妲的為人,以及她的工作方式。因為香妲當時完全沒有先過問我的學歷或工作經驗,她就是全然地相信,那個相遇的當下帶給她的直覺和感受。而我也很喜歡她沒有過問我的背景或學歷,她就是很相信,覺得很喜歡我這個人、很欣賞,想要跟我合作。我想,從這一點大家就可以看出香妲這個人的為人與個性。
當然,在相遇後,我們開始一起合作了非常多不同的作品。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直都保持像剛才說的,非常單純、純粹的合作關係。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每次的意見都是百分之百一樣的,而是「我們想要把電影帶到什麼地方」這方面的想法,是一直都很一致的。
香妲她很喜歡用兩個小故事談我跟她的合作關係。第一個故事是,我們會一起看拍攝下來的各種素材,在看的時候,我們需要決定這顆鏡頭要留多長、什麼時候要喊卡。有趣的是,我們之間有個小遊戲,如果我們覺得時間到了、可以剪了就要拍一下桌子,如果我們手拍下去那個時刻是一樣的,代表我們的想法是非常同步的。
至於第二個小故事,因為我們通常是在早上一起看素材,有的時候針對片段的長度,我會覺得太長,而她覺得太短。即便我們兩個的意見不一樣,香妲認為這代表我們還是有一定的共識——也就是我們兩個都覺得這個片段的長度是不對的。
在今天《奧邁耶的癡夢》(La Folie Almayer) 的映後座談,我有回答關於剪接和電影節奏韻律的問題,這邊就先稍微再提一下。關於感覺對、還是不對,我認為真的要做了才會知道。而過程中要全然的相信自己的感受,自問:「這個感覺對嗎?」如果不對的話,是太長還是太短?並且要不斷的去嘗試,也適時的遺忘,並重新發現。
慧穎:香妲的作品當中確實充滿了韻律與節奏,聽阿瑟頓分享工作過程中有這樣的——可以說小遊戲也好,或是這樣的默契,真的很不可思議。
與艾克曼的工作模式
慧穎:阿瑟頓跟艾克曼相遇在 1980 年代,也就是艾克曼已經拍出《珍妮德爾曼》 (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 了,簡單來說,他們相識是在艾克曼已經成名之後。下午《奧邁耶的癡夢》映後時,阿瑟頓也有簡單提到,他們合作的《巴黎情人,紐約沙發》(A Couch in New York) 已經算是一個蠻大的劇情片製作,香妲需要去說服各方,請阿瑟頓來擔任剪輯師是個正確的選擇。從這些小小的點滴,都可以感受到剛剛阿瑟頓所講的「信任」。
除了剛剛先談到的一點與艾克曼的合作過程,想進一步詢問,因您跟香妲合作多年來累積了非常深厚的默契,是否可以簡單的分享妳們的工作模式?除了早上看毛片或素材之外,請再多分享妳們又是如何在剪輯室當中梳理,並找到一個切入點的呢?以及根據我曾看到的訪談,很有趣的是,香妲從來不會說「我有一個想法」,而是會說「我有一個什麼樣的感覺......」。您跟香妲之間的溝通方式令人好奇。妳們是如何談論眼前所看到的素材?
阿瑟頓:我想分享我們合作《巴黎情人,紐約沙發》的故事,不曉得在座各位知不知道?我其實是半個美國人。這件事情不是非常重要,但跟我即將說的故事有關。
《巴黎情人,紐約沙發》一開始的設定是個「浪漫喜劇」,片子剪出來後,製片都非常喜歡。可是到了發行商這一關,才遇到了一些麻煩,他們覺得這不是浪漫喜劇,因為它開場的地方看起來更像部「驚悚懸疑片」。這也是我喜歡香妲的地方,她在《奧邁耶的癡夢》開場也帶給人這種令人摸不著頭緒的感覺。總之,發行商就回頭跟香妲說:「請妳跟一個美國的剪輯師合作。」他們可能覺得剪輯風格的差異來自國籍或是文化問題。然後,香妲就回答他們:「但我的剪輯師就是美國人啊!」我很喜歡她這樣回答。
在剪輯工作上,她的工作方式其實不是每次都一模一樣。有些電影會讓她比較緊張,但有些她就會比較放鬆。不過,她一向都是個非常直率、也非常單純的人。她如果那一天特別不耐煩,或者很累、想慢慢來,其實我都感覺得出來。她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很順利地表達出自己的感受,但她會用各種方式讓我知道她的狀態。
比如說,有些片她可能會覺得,在剪輯這部片的過程中,我們每天都要出去吃午餐。她是一個很容易餓的人,大概十一點半肚子就會開始餓、想吃午餐,通常我們就會去吃義大利麵。有時候,她甚至一天會吃兩頓早餐。如果那天沒有那麼餓,第二頓可能就只吃一半。有些日子,她也會特別想早點休息、早點睡。
我們一起看素材的時候,通常是在她家。她家有兩層樓,因為家裡的東西常常搬來搬去,有時候素材是在樓上看,有時候是在樓下,她如果想要休息就會去另一層樓。她在剪輯某部片時,也曾決定每天都要自己煮飯。於是,她就會忙進忙出,去買東西、煮菜。
她真的是一個非常單純,也非常慷慨、樂於分享的人。像我們兩個都會抽菸,但我個人通常是下午才會抽。如果我早上看見她在抽菸,她還會特地跑到窗邊去搧風,說:「妳看,我有把空氣弄好比較好喔!」還有,我剪接時如果一直待在黑暗裡,我的眼睛會不太舒服,有時候會需要一點光線。但她家的燈泡總是會有些狀況,她就會說:「欸,我剛好要去買燈泡,要來修一下燈。」她其實是一個滿好玩、也滿好笑的人。但一旦開始工作,她就會非常專注。
而一旦進入工作模式,可以感覺到她是用整個身體在經歷、在體驗這些畫面。有時情感會非常強烈,有時則比較平靜。有時會看到她離畫面很近,有時她又會刻意拉開一點距離。像《奧邁耶的癡夢》當中,有場戲是女主角妮娜在船上說,她不知道怎麼學會乖巧聽話。香妲當時在看著這段毛片,就對我說:「我發現我是為了這場戲才拍這部片的。」她在看素材的過程中,常常會重新發現一些她之前沒有注意到,或者沒有意識到的東西。她總是保持非常開放的心態,也非常樂於接收這些未知的東西,所帶來的驚喜。
她也從來不會對我說「妳應該要這樣做」。她在意的,是我們兩個對影像的感受是不是一致的。只要我們都覺得「對了」,那就是對了;但如果我們的感受出現落差,那也代表這邊還有需要調整或修正的地方。
在看素材時,我們幾乎一直都待在同一個空間,一起經歷這個過程。但實際進入剪輯階段,有時我會需要一點自己的時間,自己先處理剪輯再給她看。但她一定會跟我一起看,而「陪我一起看」這件事,對我來說也非常重要。她在這個過程中講出的話,不只對我來說很重要,常常也會給我很大的幫助。很難明確說她做了什麼,但光是她觀看的方式,就能給我很清楚的方向和指引。
談到我和香妲合作的故事,真的多到講不完。每次一聊,又想到一些新的事情。但我覺得有一點非常重要,很想跟大家分享——也就是香妲從來不會愛上她的影像,她也不會對特定影像有任何執著。即便她有喜歡這場戲,就算是一場再重要的戲或畫面,她也總是保持開放的態度,隨時抱著可能會把它剪掉的心態,不會在心中過度去美化它們,也不會過度崇拜它們,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在剪接的過程中,曾多次嘗試把很重要的戲拿掉,然後去感受、去觀察,這樣處理是否會帶來更強烈的情感?還是反而沒有。有時候我們也不確定,有時會放回去,有時會先拿掉,也許放個兩個禮拜後再放回去,有時在那時你才會真正明白它的重要性和意義性,以及為何要特別為這場戲保留空間。像在剪剛才提到的《巴黎情人,紐約沙發》(A Couch in New York) 時,我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我覺得這點真的很關鍵,香妲從來不會執著於任何特定的戲或影像。對她來說,這部電影最終完成的全貌永遠是最重要的,電影的全貌勝過任何一個單一畫面。
合作作品中最挑戰與困難的經驗:《巴黎情人,紐約沙發》、《東方》
慧穎:您和香妲從很早期就開始一起創作,也陸續合作了許多重要的作品,除了剛剛提到的劇情片,其中還有像是《東方》(D’Est)、《國界彼方》(From the Other Side)、《故鄉在彼方》(Là-bas)等紀錄片,也橫跨了不同的形式。想請阿瑟頓分享,在這些合作經驗裡,有沒有哪一部作品對妳來說特別具有挑戰性?或在剪輯過程中遇到很辛苦的經驗呢?
阿瑟頓:如果說到比較有挑戰或覺得比較困難的,要回到《巴黎情人紐約沙發》(A Couch in New York) 這部作品。這是一部預算非常大的劇情片,因為女主角非常有名,片酬也很高。相對地,也讓香妲感到很緊張、承受了很多壓力。
那時候製片跟她說:「妳是個天才,一定可以創造出在商業上非常成功的電影。」她聽了很開心,香妲自己也很希望能拍出一部商業上成功的片子。但對她來說,對商業成功的渴望,並沒有超過、也沒有強過她自己和電影之間的關係。她和電影的關係,還是最重要的。
在剪輯的過程中,我們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當時製片還特別要求我們換配樂,用不同的音樂試試看。因為那時不像現在可以直接傳檔案,他們給了我們一大堆錄音帶。我拿了那些錄音帶給香妲,結果她不想聽。我就說:「等製片問起來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說『我們聽過了,覺得不適合』。」她當時答應我說好,結果等製片真的來了,一進門,香妲就頭抬高高的對他說:「我告訴你,我們根本就沒聽你們給的音樂!」我在旁邊覺得又緊張又好笑。
從這個故事,大家也可以看出她的個性。我覺得這很重要,你如果沒有自信、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是沒有辦法拍出好電影的。很多時候,沒有強大的自信,就沒有辦法去回答來自外界的質疑。他們會問你:「你確定這樣是對的嗎?」、「你確定這樣做是最好的嗎?」如果你陷入自我懷疑,你可能連你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
因此,有這樣一個很強大、很篤定的心智在工作過程中,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有時可能會覺得很舉步維艱、很難進行下去;有時可能會覺得需要放慢腳步、需要多點時間。總是會碰到很多質疑,不管來自外界或是自己的。
我還記得在創作裝置藝術作品《東方,在虛構的邊界》(D'Est, au bord de la fiction,1995)時,這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我盡量簡單說明。《東方》本來是香妲在東歐拍的一部電影,電影裡是完全沒有台詞的。當初我們一起做這個裝置藝術,就是把電影轉換成空間裡的影像裝置。這對我來說,就是全新的挑戰。
我們把電影分成 24 個小部分,在不同的螢幕上面播——我現在說的是簡單版,實際上更複雜,只是讓大家快速理解——由於我們以往都是「在時間上做剪輯」,但這次,我們等於是在「在空間上做剪輯」。很快地,我們就發現好像缺少了什麼東西。因為在電影這個表現形式中,時間是線性的,會有開場、中間、結尾,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時間順序,慢慢建構出一些張力。但在這個處理空間的裝置裡,它比較像是以四分鐘重複播放的影像,因此這個張力是在於「空間的穿越」(voyage of the space)。
回到剛剛說的,我們覺得它少了些什麼,於是發現,它缺少的正是「另一個空間」——畢竟我們是在「空間上做剪輯」,我們感覺它需要用文字、用語言來表達。但到這個階段才有這樣的發現,就讓執行非常得困難,因為電影的版本本來是沒有文字的。而且,香妲之前也從來沒有用文字去描述過,她想在《東方》這部電影,或這些影像裡,帶給大家什麼樣的情感。這也是另一個,可以讓大家知道我們是怎麼合作的例子。
剪輯之外的策展經驗
慧穎:很高興阿瑟頓提到參與錄像裝置的合作經驗。其實香妲的作品,算是蠻早進入美術館的。而《東方》這件作品,剛好今年在北美館的〈開放式結局〉也有播放,也許在座有些觀眾剛好有看到。
阿瑟頓在將艾克曼時間性的作品,形塑成錄像版本這件事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近期,阿瑟頓有策劃一個關於香妲的展覽,叫做《Face the Image》。很巧合的是,其中一個展出剛好是這週閉展。雖然是很小的巧合,但也可以看出阿瑟頓非常活躍地參與這些工作——從電影,再到思考它在另一個場域當中如何呈現。
也想請阿瑟頓稍微聊聊這個部分,您在思考不同媒介時,又是如何展開的?
阿瑟頓:當初有個美術館請香妲做一個可以在藝廊或藝術空間展出的作品,她也欣然接受了。因為她一直都很喜歡接受新的挑戰,但她跟美術館說,為了做這個作品,她要先拍個電影。當年找資金並沒有像現在這麼困難,所以找到資金後,她就在兩年後完成了《東方》 這部電影。
電影拍完後,美術館跟她說:「我們現在有錢來做這個裝置藝術了。」但其實,香妲早就完全忘記,直到人家回頭來找她才想起來。就像我剛才提到,她是個很好笑、很好玩的人。很多時候我們在聊她時,都只講比較嚴肅的話題,比如政治與歷史,常常會忘記她這一面。我也希望讓大家知道,她這個人的個性其實是很好玩的。
在拍《東方》之前,她有十年的時間一直很想去東歐,所以也是個機緣。這部片就是穿越東歐一路到莫斯科的旅程。但也因為我們都很喜歡這部片,因此當我們要將它做成裝置藝術時,過程變得更加困難、有點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一開始,我們先拷貝了一份影帶,然後再從這份影帶又拷貝一份。我就將手上兩份拷貝放在不同的螢幕上,併置去觀看。我想看看同一部片在同時間出現不同的影像會有什麼效果,有時左右螢幕上會出現一樣的影像,有時一邊比另一邊還要延遲;有時一邊是靜止的,另一邊則是移動的動態畫面。
後來我們發現,還需要第三個元素。只有兩個(螢幕)的話,不是重複、一樣,就是對比,我們需要第三個去增加層次。最後呈現出來,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樣子(實際總共24個+1個螢幕,分成8排,每3個螢幕併置)。這在技術上也非常困難,因為要同時呈現不同的螢幕播放不同的內容,需要做很多拷貝。
但香妲很喜歡,也很享受這個創作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為此發展了一些新的技術,而她也從中感受到自由和自信。對她來說,每次做這種裝置藝術委託,她都非常開心,因為這也讓她重新去發現,也像是回到當年拍《珍妮德爾曼》時,那種年輕、無畏、充滿自信的感覺,甚至還不太明白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情,那同等對事情的重新發現感。香妲很喜歡裝置藝術帶給她的自由,很重要的一點是,她可以在不受拘束的情況下,去表達對這個世界很多的看法和想法。而當我們把影像剪成更短的片段時,它散發出來的訊息其實更強烈。
我剛才提到,覺得好像少了什麼,後來結論是,我們需要另一個空間。這部作品已經有兩個空間:第一個是16釐米的影帶(即電影版),第二個是同時播放的24個螢幕。那麼第三個空間,我們當時覺得需要加入文字。(加入阿瑟頓所說的第三個空間,最終《東方,在虛構的邊界》這件作品,是一個25頻道錄像裝置)
這也是香妲第一次,她想用文字表達這些影像激起了她什麼樣的情感、讓她想到了哪些事情。其實影像本身很單純,比如很多人在等公車的畫面,但她在觀看時,可能會想到其他人、其他事,或是些與歷史有關的情況。
因此,她寫下了在我看來最美的東西之一,《The Twenty-fifth Image》(Le vingt-cinquième écran)。它叫做第25個畫面,因為是第25個螢幕上,配合抽象感的影像播放。
我也簡短提一下我的策展經驗。四年前,我受邀在西班牙巴塞隆納策劃一個跟香妲有關的展覽,現在剛好正在巴斯克地區展出,但只到明天。這麼多年來,其他關於香妲的展覽我都有參與,因為我知道要怎麼呈現她的作品。但當我自己當策展人時,感受完全不同,對我來說,好像又是一種「剪輯」(edit)的工作,因為我必須去思考不同元素在空間中的呈現方式,去感受它們。
我非常喜歡這個過程,會一再回到空間裡去感受並嘗試新的方式,去想像、去調整。在這次的展覽叫做《Face the Image》。雖然展覽只到明天,但這個網站會持續存在,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站查看,上頭有英文、西班牙語和巴斯克語版本。
這是展覽的小冊子,裡面有很多內容(現場展示冊子)。主辦方做了我的專訪,我在這之中非常鉅細彌遺地講述、說明,當初這個展覽是怎麼策劃跟執行的,內容都收入其中。在這邊,我還想跟大家分享小冊子裡的一幅水墨畫。當時編輯問我最喜歡哪一幅水墨畫,我選了這一幅(展示該頁圖片),於是編輯就把它編進了小冊子裡。畫裡面雖然沒有太多額外的訊息,但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感受它帶來的情感跟情緒。
【Q&A】
Q1:我想請教的是,法國著名演員黛芬·賽麗格,她不但演出過亞倫·雷奈的作品《去年在馬倫巴》(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1961)以及《穆里愛》(Muriel ou le Temps d'un retour,1963),她自己也導演過一些紀錄片,這些紀錄片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於關懷女性,尤其是女性主義和女同志議題。請問,當初香妲邀請這位女演員主演,是因為欣賞她作為傑出、偉大的演員,還是因為認同她對女性主義和女同志議題的關懷與貢獻?
阿瑟頓:關於選角的問題,當初香妲希望由黛芬・賽麗格來演出,正是因為黛芬・賽麗格作為一位女演員的狀態。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她是知名或一線女星,而是黛芬・賽麗格更是一位Diva級的女演員,因此她希望要這樣氣質的演員,來演出片中角色,從事洗碗或做家事等等,她認為這會帶來很強烈的感受。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黛芬・賽麗格的一舉手一投足都非常優雅。選擇她來演出這些女性角色,也在某種程度上也呼應她們的角色特質。
Q2:《奧邁耶的癡夢》映後座談中,阿瑟頓提到對「紀錄片」這個詞,某些部分還有所保留、想再多思考。也提到,拍攝過程中仍有很多創造性的空間。想請問,能否就這一點,分享得更深入或更廣一些,談談她對創作過程的思考與觀察?
阿瑟頓:謝謝您的提問。我下午有提到,其實我不是很喜歡「紀錄片」這個詞。尤其在法文裡,對不熟悉電影圈的人來說,這個詞可能會讓人覺得這是一部只講特定資訊或主題的電影,有時候我不太喜歡這樣的定義。
我自己其實不太喜歡把電影硬性區分為紀錄片、劇情片。對我來說,電影是一個活的、當下的體驗,它能帶給觀眾很多自由。當然,也有另一種電影,它比較含蓄、規矩,比較沒有那麼自由,那對我來說相對就沒有那麼有趣了。
我認為電影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參與。我們創造一個空間,讓觀眾在裡面去思考,陳述自己對這件事的想法與觀點。而製作電影、讓它被觀看,其實也是一種參與政治的行為。
Q3:因為阿瑟頓剛剛有提到,香妲其實是一個非常天真、幽默的人,我想延伸問一下,您過去有沒有合作過性格和香妲非常不同的創作者?如果有的話,在那樣不同的相處模式下,會不會影響到妳觀看素材、或是在剪輯時思考影像的方式?還是說這樣的差異也會反映在最後完成的作品裡?
阿瑟頓:當然,每次和不同導演合作的模式都不一樣。我這個人的好奇心比較重,所以我一直想去發掘、觀察新的事物,不管是人、空間,甚至是說話的語氣等等。每一次和不同導演合作不同作品,其實都是段不一樣的旅程。
比如說,香妲離開之後一年,我就認識了Éric Baudelaire,他的個性和香妲非常不同,但我們也建立了很深厚、緊密的合作關係。和他工作的時候,他給我的訊息可能就只有他說出來或畫出來的那些部分,但我必須用更多的力氣去想像他沒有明說的東西,然後透過這種方式去理解他、理解作品。
我覺得,不管和哪一位導演合作,最重要的還是我們一起做剪輯、一起看片、一起創造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整個創作最核心、最珍貴的部分。
最後,我想再回應一下。剛才有提到王兵導演的作品,其實對我來說,他和香妲的電影都在處理生死這類的議題。雖然他的個性和香妲很不一樣,但我從他身上感受到的生命力和投入的程度,其實同樣非常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