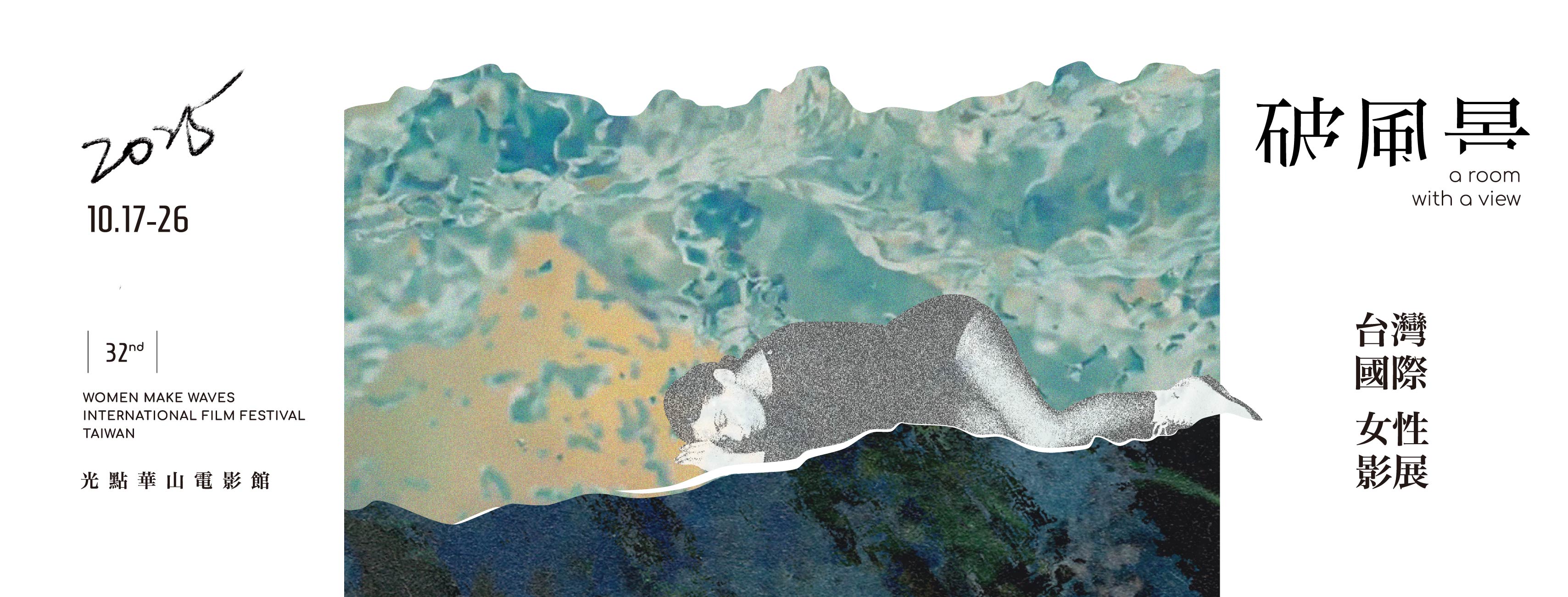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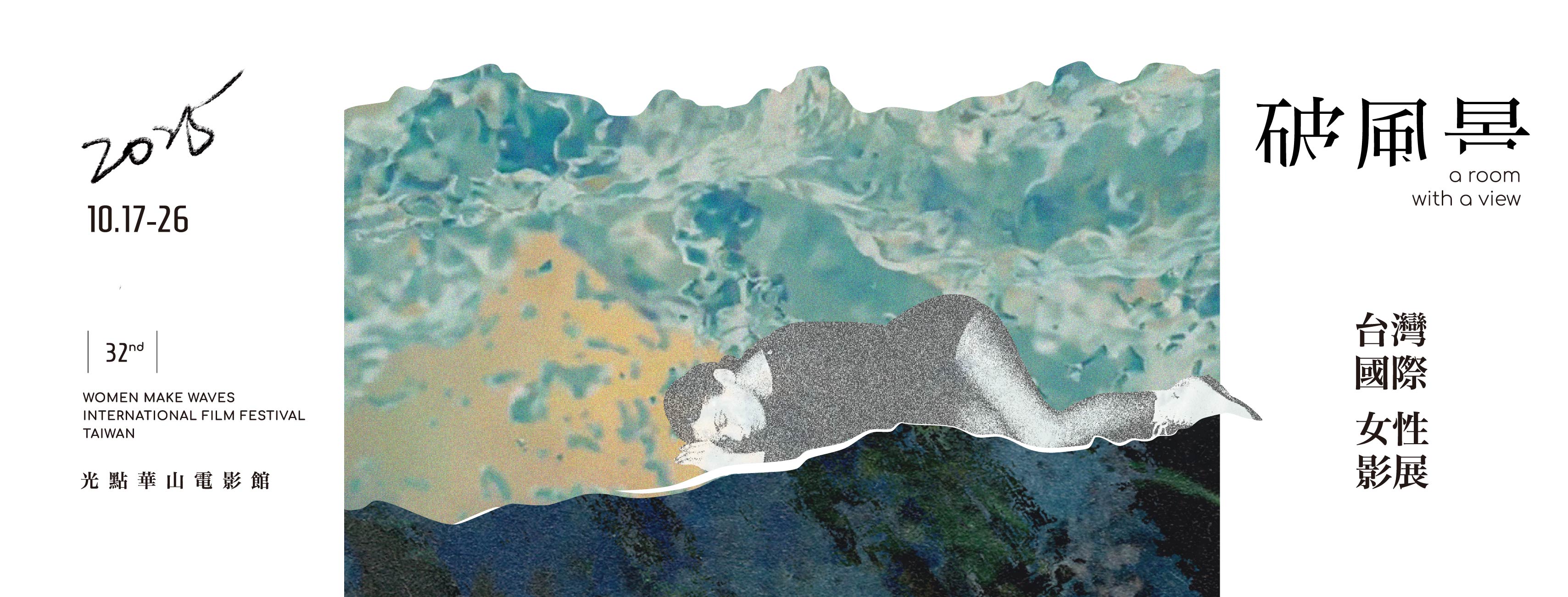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時間:2025年10月25日(《拍電影的女性們》映後)
地點: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第六、七屆理事長 范情
與談人:導演 熊谷博子 KUMAGAI Hiroko
文字記錄:魏安琪
范情:大家午安,我是范情,台灣女性影像學會2014年到2018的理事長。今天非常榮幸有機會為大家主持這一場映後,《拍電影的女性們》是非常難得的紀錄片,我們也很難得的邀請紀錄片的導演熊谷博子女士來到現場。先歡迎熊谷博子女士。
熊谷博子:大家好,我是熊谷博子,很開心大家特別過來看這部電影,也很開心能夠遇到大家,謝謝。
《拍電影的女性們》拍攝動機與構思
范情:我看了這部電影三次,我第一次看的時候,心想:「哇!怎麼會有這樣一部電影,讓我這麼喜歡」。第二次是前天在戲院看的,我非常感動;而今天再看一次,我則是非常激動。這部電影不只談到了過去日本女性導演的經歷,也連結到了女性影展。
談到爬梳早期女性導演的歷史,這幾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其實也做了不少努力。比如,曾放映過世界第一位女導演──愛麗絲·吉·布蘭奇(Alice Guy-Blaché)的作品;針對台灣導演的部分,我們也爬梳了早期女性導演如李美彌(代表作如《未婚媽媽》、《女子學校》)、楊家雲(代表作如《瘋狂女煞星》)的作品。也很棒的是,2022年,台灣女影放映了日本導演田中絹代的作品,同一年還放了韓國較早期嶄露的女性導演,申秀媛的作品《女影人生》。
《拍電影的女性們》這部2004年拍成的電影,能在2025年的今天因緣際會於女性影展放映,真的非常難得。就我所知,這部電影在2004年放映後,去年又於東京影展的研討會上重映。我們暫且不談其中的原因,想先請導演和我們分享,當時為什麼會拍這樣一部電影?是什麼樣的機緣?而這些導演又是在什麼情況下進入到這部影片中的?
熊谷博子:《拍電影的女性們》是為紀念第15屆東京國際女性影展拍攝的,可以說是一部紀念性的作品。其實在影展的第一屆,日本的女性電影導演只有一位(參展),就是羽田澄子。到第15屆時,曾參展的導演人數已經越來越多了。像我自己,是在第三屆時參加東京國際女性影展。基於這個機緣,策展人高野悅子小姐便問我:「我們要不要為這個影展拍一部紀念性的電影呢?」對我來說,我拍這部電影並不只是想記錄「有一群女性在拍電影」,而是想呈現──女性拍電影,其實同時是在與時代、社會,甚至與自我進行一場戰鬥。對我而言,這部電影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奮鬥紀錄。
范情:我在看這部電影時,有很深的感觸。這些導演在片中談到的議題,讓人感受到拍電影這件事並不像寫作、寫詩那樣單純的創作,而是牽涉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政治、經濟、個人所要突破與堅持的種種。政治上更涉及「性別政治」,而文化中女性的形象與角色所面臨的限制,也使拍電影變得更加艱難──這樣的困難真的不是一般創作能相比的。
接下來請問導演,正如您剛剛提到,這部片不只是拍女導演而已,那在構思時,您是否有先思考過,希望呈現她們的哪些面向?有哪些部分是您特別在意的?有沒有在訪問過程中發現一些原本沒想到、但特別讓您印象深刻的地方?
熊谷博子:是的,在這部電影裡,我訪問的對象其實都是在這15年間曾帶著自己的作品去參加東京國際女性影展的人。無論是製作人還是導演,我問她們的問題其實都相同,但每個人的回答卻因為所處的時代與環境而非常不同。這種差異與獨特性讓我相當驚訝,也非常興奮。每次訪問不同的對象時,我都抱著興奮與期待的心情進行訪談。
范情:我很好奇,妳問她們的問題有哪些?
熊谷博子:譬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訪問了一位製作人飯野久,就是《黑雨》(今村昌平,1989)的製作人。讓我非常驚訝的是,她竟然要在兩天之內籌到2400萬的資金。這對導演來說其實很難想像,像她這樣的製作人角色,在背後做了多少工作。因此,當我聽到這個故事時,真的非常震驚。還有一位澀谷昶子導演,她在片中提到,當她在片場喊「要開始囉!開拍!」時,竟然被其他工作人員說:「蛤?我們的導演居然是女生?」接著就把燈光全部關掉。即使在這樣嚴峻的狀況下,她仍然堅持繼續拍電影,我從她的精神裡得到了很大的啟發。
至於我實際上問的問題,其實都一樣,我會問:「妳在進入電影產業時遇到了什麼困難?」、「你怎麼處理?又是怎麼跨過這些困難的?」大家給我的答案都不太一樣。還有一位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植平多鶴子小姐。她一開始是做場記的,當時隱瞞了自己已婚、有小孩,並且生病的狀況。後來,她發現自己必須要找一個能自由調整時間的工作,於是決定要當導演。但當她決定當導演時,必須去說服身邊所有男性工作人員,曾經花了三到六個小時,去逐一說服每個人。我聽她講這個故事時,心裡便想:「如果是我,能做到嗎?」這次訪談讓我非常驚訝。
熊谷博子的個人經驗與電影創作之路
范情:導演直接切入了女性在電影產業中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這些狀況在片中也都能看到。而在電影裡,大家有注意到嗎?熊谷博子女士本人也有出現,她的作品《阿富汗之春》(1989)曾在第三屆女性影展中放映。這邊我也補充介紹一下,熊谷博子導演的名片上寫的是「Documentary Journalist」,也就是紀錄片導演兼新聞記者。她在1970年代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後,進入電視公司工作,參與了許多邊緣議題的拍攝,如戰爭與社會紀實。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作品,是她要求政府將原爆時期的影像歸還給日本人民。因為當時這些影像被美國政府壟斷,而這樣的舉動,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直接且具有正義性的行動。1985年之後,她成為自由工作者,陸續拍攝了關於礦區女性等議題的紀錄片。
在《拍電影的女性》中,有一點讓我特別感動──熊谷博子導演提到,她過去拍了許多一般女性不會選擇的題材,她必須勇敢地進入戰區、礦區去拍攝。包括她2024年拍攝漢生病紀錄片在內,她逐漸發現自己對普通人的生活並不熟悉。因為這樣的體悟,她開始回過頭來關注身邊的世界。她說,早年曾覺得拍小孩、拍生活瑣事、拍女人做的事不是自己想做的題材,但如今她重新回到了這個領域。
我想請問,就妳個人或從女性影像創作的角度來看,妳覺得這其中的意義是什麼?
熊谷博子:首先,非常感謝您這麼詳細地調查了我的資料。回到自己的個人經驗,因為我的祖父是軍人,其實我父親是在台北長大的,我的伯父、伯母,也就是父親的弟弟、妹妹,也都出生在台北。也因此,這次我來到台灣,心情其實是很複雜的。
我小時候常聽到祖父和父親談話,他們聊的內容大多與戰爭有關,但他們並不會反省日本在戰爭中做過的錯事。反而還帶著一種懷念的語氣說:「戰時的什麼、什麼很好啊……」他們也常提到喜歡台灣、喜歡台北。這讓我從小就產生疑問:「為什麼我的家人會覺得戰爭是件好事?」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影響,我後來想成為一名記者。
當我去阿富汗時,正值蘇聯撤軍之後,我每天都看到有人死去。久而久之,我對死亡變得麻木,只覺得「人死就是戰爭的一部分」。回到日本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竟然對「死亡」這件事失去了感覺。後來我結婚、生子,才慢慢開始關注身邊的事物,理解照顧家庭、養育孩子的重要性。以前我認為那只是女人或小孩的事,與我無關,但當自己親身經歷後,我體會到那份辛苦,也明白人際關係與社區連結的價值。於是,在思考與追蹤議題時,我的觀點也因此逐漸改變。
范情:對,導演在片中提到,她在拍《阿富汗之春》時,從伊斯蘭《可蘭經》中得到啟發,提出「右手拿著攝影機,左手抱著小孩」的口號。我也想到,在台灣1970年代,有一位早期婦女運動者呂秀蓮女士,她在《新女性主義》中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她的口號是「左手拿鍋鏟,右手拿筆桿」。我覺得這兩者有點異曲同工之妙。這當然是個巧合,但也能感受到,正如導演所說,這樣的口號看似有力量,但實際上要做到卻非常不容易。
我也很好奇,導演曾提過您拍過一部與生育有關的作品,好像也曾進入東京女性影展。相較於您拍攝許多戰爭或邊緣題材,這部作品是否可以被視為「一手拿攝影機、一手抱小孩」這個理想的具體實踐?因為當我們談到女性導演拍電影,以及進入產業的困境時,常聽到有人說:「等我把小孩照顧好、孩子長大後再拍電影。」但現實往往不會等人。那導演當時是怎麼面對「照顧」這個角色與課題的呢?
熊谷博子:第三屆東京國際女性影展,我帶了《阿富汗之春》參加。當時的記者會上,聚集了各國的女性導演。有個記者問了個問題:「妳們既然是女性,要怎麼一邊顧家、一邊拍電影?這兩件事有辦法兼顧嗎?」
那時,一位攝影師回答,如果是編劇的話,可以在家裡寫作,兩邊都能兼顧;但如果是攝影,就必須到外面工作,根本不可能做到。另一位外國導演則說:「對我來說,工作人員就像家人,所以我不需要再結婚。」
輪到我回答時,我想到伊斯蘭世界的一句話:「右手拿著《可蘭經》,左手拿著劍。」於是我脫口而出:「我右手拿攝影機,左手抱小孩。」但我後來發現,這句話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非常困難。
我個人認為,不管事情多小,重要的是要持續去做。幸好隨著科技進步,攝影機越來越小,女性也能自己拿著拍。而後來的電視產業,也出現一些規模較小的公司。如果要和他人合作,就得配合時間,但當時我要照顧孩子。因此我後來盡量自己拍、自己編、自己剪,在小電視公司製作節目,並且不斷持續下去。
至於為什麼會拍到「生產」這個畫面,是因為那時遇到一個企劃,內容是關於東京的一條老街「巷島」與德國一條古老街區的交流。主題是「不要因為老舊就拆毀,而要珍惜與保存」。在那個企劃中,我遇到了很棒的人,便很想拍下這個過程。
回到拍攝生產的畫面,那次真的非常困難。攝影師是資深前輩,我們合作多年,但整個團隊全是男性,像錄音師是四十歲單身男子,助理則是二十歲單身男子。我原本預測這位媽媽會提早生產,結果卻晚了,他們因此責怪我,甚至說我是騙子。
好不容易拍完進入剪輯階段,剪接師又是五十歲單身男性,他說:「為什麼要拍這種東西?我完全看不懂這鏡頭的意義。」他覺得這段應該兩秒鐘就該結束。我努力說服他,但最後他甚至不高興地離開團隊。幸好,後來加入一位有育兒經驗的男性,他能理解這個畫面的意義,協助我們順利完成。正如電影裡所說,每一部電影背後都有許多故事。
【Q&A】
Q1:謝謝導演帶來這麼多啟發。片中訪問了許多閃亮的女性,想請問有沒有哪一位受訪者在約訪時特別困難?是否有在女性電影發展中有重要地位,但婉拒了採訪的?
熊谷博子:我在拍這部電影時,受訪的對象多半是對電影產業抱有非常多想法的人。能夠把她們一直想說、卻說不出口的心聲記錄並呈現出來,讓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大家也都很開心、很支持我完成這部作品。
至於有沒有覺得可惜、但沒放進電影裡的畫面?有一位剛也提到導演澀谷昶子,她的作品《挑戰》(1964),曾在坎城獲得短片金棕櫚獎。不過她在剪輯過程中一直不滿意,在截止日期前仍堅持地說:「我還要再來一次。」她不斷重新剪接,最後完成的版本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那一部。不過這段過程我沒有拍進電影裡,覺得有點可惜。
Q2:導演您好,我是台灣女性影展以前的策展人之一。今天看了您的片子,我想表達我的敬意。過去三十多年來,台灣女性影展放映過許多日本女性導演的作品,例如濱野佐知,以及剛剛提到的田中絹代導演。我自己在策展亞洲女性影展的經驗中,也曾遇過東京女性影展的大洋竹子小姐,台灣與日本之間其實有很多交流。
這部影片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以前認識的日本女性導演作品多半是劇情片或長片,但今天發現日本也有像您這樣拍攝新聞性、紀錄性題材的女性創作者,這非常重要。看完這部片,我覺得像是上了一堂很豐富的課,真的非常感謝您。不過容我問一個稍微尖銳的問題,請您多包涵。
我覺得您的影片切入角度很好,能夠同時看到日本社會、文化以及導演自身的挑戰。不過我也注意到,儘管片中的女導演們表達了對結構與環境的不滿,或提及所受的壓迫,但影片中幾乎沒有直接使用「父權社會」或「父權壓迫」這樣的概念或字眼。這點讓我覺得很有趣。
今年台灣女性影展的策展很棒,把您的片與另一部挪威導演的作品《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放在同一單元。那部片的角度很明確也很單一,對父權體制有強烈的批判,從電視台到媒體文化都在反思。而您的影片則比較多元、更女性化,也帶出豐富的訊息。兩部作品各有千秋,但我很好奇,為什麼您的片子在製作時,沒有更強烈地批判父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但這是我的觀察與感受,謝謝。
熊谷博子:您剛剛提到的《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我今天早上也來看了。那部電影的素材是1973年拍攝的,當時女性主義才剛開始發展,與我的拍攝年代不進相同。我在拍這部電影時,更想聚焦於每一位電影人的內在──她們怎麼思考、怎麼奮鬥。如果我們今天再回頭看,就會發現,不僅是電影產業,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女性所面臨的處境與片中所談的仍舊相似,這是個至今仍具共通性的課題。
女性影展的意義
范情:正如導演所提到的,其實我們之間有文化與時代上的差異。我自己也很想知道,日本的婦女運動發展,與日本女性導演、以及東京女性影展之間的關係。
東京國際女性影展從1985年開始,幾乎與東京國際影展同步,但在2012年結束。1985年時,台灣還在戒嚴,過去的日本女性影展曾是我們學習的對象,但它卻再2012年戛然而止。這當中的原因我也很好奇,只是今天沒有時間深入。不過有趣的是,去年東京影展又重新放映了這部電影,並舉辦了一場跨世代導演對談的研討會,我覺得這可能也是一種新的跡象。
今天我們不僅與過去的女性導演產生了縱向的連結,也與日本電影史中的女性導演產生了橫向的交流。現在就先在這裡畫下句點,請大家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熊谷博子導演,以及她帶來的這部作品。
熊谷博子:謝謝大家這幾天的參與,我也從各位身上得到了許多感動與勇氣。應該是我才要感謝大家,真的非常謝謝。
范情:很多事情往往是結束、消失之後,才會讓人明白它的意義。我們現在其實還蠻幸運的,台灣女性影展已經來到第32屆。最後,我想請問熊谷博子導演,從您的經驗來看,女性影展的意義是什麼?可以給我們一些指教嗎?
熊谷博子:因為很少有機會,能讓一群女性工作者、電影工作者聚在一起。在這樣的場域裡,大家能夠有共同的空間分享彼此的資訊與感受。雖然外界有時會說:「這群人聚在一起就是在講壞話、發牢騷。」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這些人其實對現實狀況都有非常具體的意見。我覺得有這樣的場域,讓大家可以交換意見,進而得到啟發,思考我們下一步要怎麼走,然後再往前移動,這是非常重要的。
范情:謝謝導演。導演今天也帶來了第25屆東京國際女性影展的場刊給大家看。為什麼要有女性影展?因為它能讓我們看到女性的視角,看到女性真實的樣貌。而要讓這一切被看見,也需要觀眾的支持。請大家多多支持,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