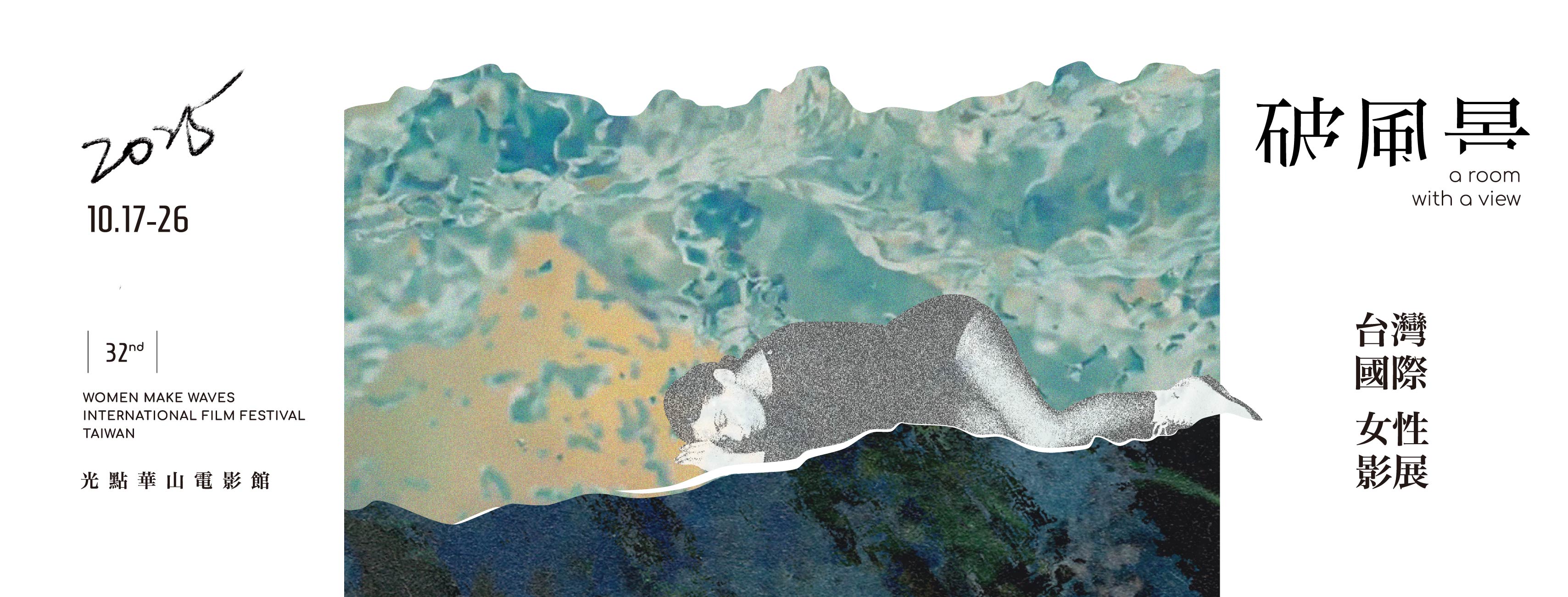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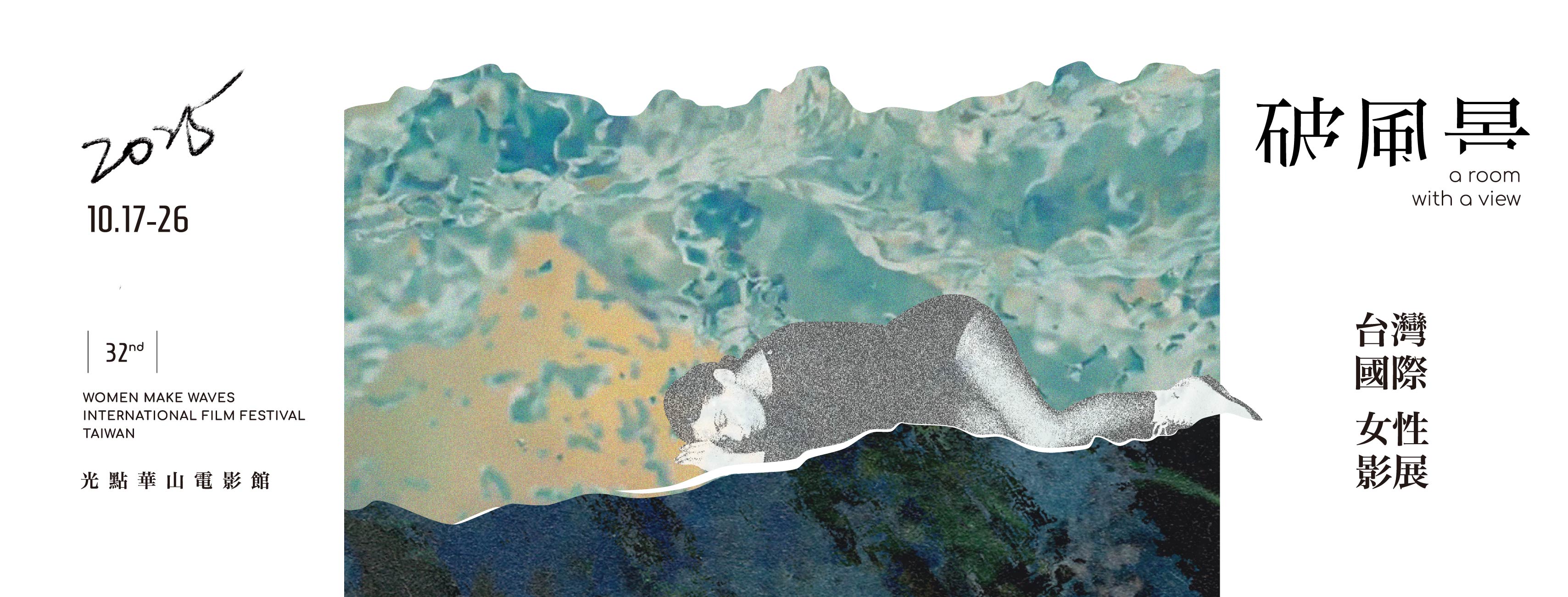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時間►2020/10/24 (六) 16:00-17:30 地點►光點華山2F藝文廳 講師►Lidia Peralta Garcia 講題►Women’s filmmaking: from Spain to Taiwan - from Taiwan to Spain. 珮嘉: 謝謝大家來參加大師講堂,今年在疫情之下非常難得有國際影人出席,而且還隔離了十四天。交流過程中發現Lidia來台有很多目標跟使命,想多認識台灣女性影像創作者、紀錄片工作者、編劇、導演。她今天也會分享身為影像工作者的經驗,歐美產業現況等等,希望能和大家交流。 【Lidia對於女影的初步研究】 Lidia:先講我是如何開始研究台灣女性工作者。臺灣外交部有提供獎學金計畫給來台研究的學者,而今年主題之一是性別,因為我過去在西班牙跟摩洛哥都是研究這個主題,於是我就想來台灣做類似的題目,開始找資料之後就找到了女影。 女性影展是由女性影像協會創立,官網很詳細、很有組織,對做研究很有幫助,也有英文版。我想從國際、西班牙人的角度來看,了解台灣影人如何描述社會、對什麼議題感興趣、女性影人的處境,與我們的共同和相異之處? 我9/11來到臺灣,隔離十四天是很好的研究時間,過程中我發現我對台灣認識很少。開始研究之後,也發現台灣歷史和西班牙歷史有不少相似之處,西班牙在1936-1939內戰,結束後也經歷了長達四十年的獨裁政權,1975民主化之後,女性才漸漸開始獲得權利。 我現在研究的階段是先從量化分析開始,接著會開始做一些問卷調查。很感謝女性影展讓我接觸到影人們,她們也很樂於和我分享幕後內容。第三階段我會訪問影人,更深入了解他們拍片的理由、電影的影響力等等。 2014年是女影第一次舉辦臺灣競賽,我的研究也就從這年開始,目前我研究的清單裡有146部影片,包括59部劇情片,49部紀錄片,也有實驗和動畫片。我發現女影比較聚焦於短片,大多數劇情或是紀錄片都是短片,我覺得短片很能看到導演潛力,像是《幽魂之境》就能看出導演對光影、隱喻的掌握很棒。 我發現大部分的片子選擇聚焦在兩位主角,很多在處理家庭關係,再來是朋友。一共有38部處理家庭關係,其中11部是母女,9部是手足。另外,也有很高比例處理衝突和矛盾、世代隔閡等,犯罪的部分則較少。 實驗片的數量最少,也很少處理記憶的主題,但講述歷史的時候導演都傾向用實驗性的手法。動畫則較常出現是童年回憶、家庭關係,或是較禁忌的主題。劇情片中長片比例較少,出現的時候比較是商業導向。我看到好多部讓我驚豔的短片,還有很多新銳影人的潛力,像是《日正當中》的導演王逸鈴。 我最喜歡的都是紀錄長片,像是《日常對話》、《再會馬德里》和《逃跑的人》,都是花了好幾年拍攝,和拍攝對象的距離都很親密,揭露了秘密或是情感,也能看到角色成長或內心掙扎與創傷。 【QA 環節】 Q:臺灣年輕女性拍片情況,相較歐美或西班牙有什麼不一樣之處嗎?您有什麼觀察? 我對西班牙和摩洛哥較熟悉,比起相異更多是相似之處。摩洛哥女性開始有機會拍片時,會開始模仿男性拍攝的方式,想證明她們有能力處理一樣的主題。後續二三四五代,才開始發展出自己風格,在文化上,三國女性的經歷其實滿相似。 摩洛哥電影學校和西班牙比起來較少,他們有很多電影節,難民、女性議題都有,主題都很特定,但培育電影人的訓練體系較少。西班牙和法國的差異也很大,因為公共政策支持和資金充足,所以法國人很小年紀就開始學習看和製作電影,長大會進戲院看電影或是拍片就比較多。 【分享個人創作經驗】 我是紀錄片導演,想分享電影如何產生影響力。不知道在台灣能不能看到《roots》這部八零年代的影集,在講非洲奴隸狀況,我小時候很愛看,常讓我掉淚。多年後我在研究西班牙移民時重看,還是深受感動。我對非洲有很強烈的感情,大部分的片子都在非洲拍攝,也做了很多相關研究。 提到非洲女性的時候必須記得多樣性,很多人覺得非洲是一個大國家,文化和人種是單一的,我的紀錄片就是希望對抗這種刻板印象,這是我的個人信念。以下分享一些我之前的影像作品: ●《The caravan of the manuscripts from Al-Andalus》: 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十五世紀離開,帶走很多歷史資料到非洲,這部片追溯了他們從西班牙到西非的遷徙之路。 ●《The Ulysses of the 21st Century》:關於十五位摩洛哥導演的紀錄片,拍他們如何用影像講述移民。 ●《A House Of Bernarda Alba》:八個吉普賽女性演舞台劇的故事,因為吉普賽人的社會很父權,所以這在西班牙是很獨特的現象。 【分享西班牙產業現況】 西班牙也有婦女電影與視聽媒體協會,但女性從事電影工作目前還是少數,劇作家跟製作人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幾位西班牙出色的女性電影工作者,和一些他們在拍攝的電影。 ● Pilar Miró ● Icíar Bollain ● Gracia Querejeta ● Isabel Coixet 也和大家介紹一下西班牙的女性影展: ● film de dones(1992-2020)是第一個女性影展 ● zinemakumeak gara!(1995-2020) ● Festival Cine por Mujeres 有雙關意思:由女性所拍也拍給女性看,今年因為疫情關係,一半線上一半實體 ● Berdache Gender Art festival 【QA 環節】 Q: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女性相關電影有哪些? 《Te doy mis ojos》很有影響力,在講女性和伴侶之間的心路歷程,為何無法離開施虐者 《La boda de Rosa》較商業化,但也很好看,女主角想辦一個和自己結婚的婚禮。 當然啦,還有阿莫多瓦導演的片子! Q:西班牙對於挑戰政治、社會氛圍的電影接受度如何?拍片的經費來源? 如果就性別議題來看,性別研究在西班牙正經歷黃金時期,很多大學正嘗試把這些論述帶入課堂中,觀眾現在對女性議題更了解,電影生態也慢慢開始改變。我們有國家電影學院,會撥固定資金給長短片、紀錄片、動畫、實驗片,導演可以申請資金。這幾年嘗試包含數位互動性的片子,也正開始流行。 Q:您是拿到外交部獎學金來台研究,西班牙有類似機會給台灣電影工作者嗎?有沒有什麼機會能讓台灣影像工作者把作品送到西班牙參展? 拜託要把作品送到西班牙參展!西班牙有很多影展,我可以推薦哪些片子適合什麼類型的影展,因為各種類型影展都有。很多臺灣影人好像比較不會多投國外的影展,但我很鼓勵他們去多探索更多影展。 學術交換的部分,歐洲現在疫情比較嚴重,但應該還是有些機會,像是教授可以和臺灣的大學交涉讓台灣學生過去交換。 文字紀錄:曾新雅 攝影:蕭宇彤
時間►2020/10/18 (日) 13:30-15:30 地點►光點華山2F藝文廳 主持人:羅珮嘉 女性影展策展人/選片人 講師: ✶林婉玉│紀錄片工作者/導演、剪輯師 ✶黃惠偵│獨立影像工作者/《日常對話》導演 ✶黃怡婷│奇蹟光影娛樂有限公司 監製/負責人 ✶賴珍琳│一顆星工作室製作人/《野雀之詩》製片 今日女影主辦的論壇——女性影像創作者職涯甘苦談,邀請了四位在影像工作領域各有建樹的女性,來聊聊工作職場上的奇聞軼事及辛酸血淚史!特別的是,她們不僅著力在事業上打拼,同時也都是幾個孩子的母親,論壇現場除了歡笑與哽咽聲(?)外,還有各個年齡段的孩子兼具魔性及逗趣的嬉鬧聲! 史上最魔幻寫實的論壇現場,無論是恐婚、恐育或是渴婚、渴育的職場女性們,都能得到許多收穫與鼓勵的姊妹掏心大會! 「平均每七年,一位女性導演才能產出一部作品。」女性影展策展人羅珮嘉率先開場,講述她之所以想舉辦這場論壇的原因:多年擔任策展人看見了台灣女性影像工作者的年齡斷層,到底消失的中生代女性從業人員去哪了?!有些問題想邀請今日四位好姊妹回答。 姊妹一號——林婉玉:剪接師,紀錄片導演,經常與劇場藝術者或表演藝術家合作,九個月新手媽媽,正在深刻體驗同時當媽媽與做影像創作,目前傾向自己接案。 姊妹二號——賴珍琳:NGO組織策展人,成立一顆星工作室,監製過許多電影,夢想自己可以一邊當獨立製片一邊帶小孩,用畫面比喻就是背著小孩下田的農婦,帥氣又強悍! 姊妹三號——黃惠偵:做過社運團體幕僚,目前為獨立影像工作者,作品有2016年的《日常對話》,打從一開始就堅決帶孩子上工,乖巧懂事的女兒現在儼然已變成媽媽特助! 姊妹四號——黃怡婷:從實習生做到自行創業,閃亮的強人一枚,39歲做高齡產婦直到進產房前一刻還是心繫公司營運,相信無論何種困難只要面對就有海闊天空的一天。 〈論職場媽媽的時間分配〉 眾姊妹不僅在行業中身兼多職,回到家還要擔當母親的角色,一天24小時究竟是怎麼完成那麼多事的呢?意外的是她們都搖搖頭說自己不擅長時間管理,原因是工作本身獨立性高,本來就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有了小孩以後工作與生活的界線更加模糊。 珍琳用一個充滿違和感趣味的畫面比喻:「一手拿著筆寫批判一手拿著鏟炒青菜。」但違和感只是來自於家務事與工作一分為二的刻板分工,事實上許多人都在努力做到兩不耽誤。珍琳提到自己很喜歡的饒舌歌手蛋堡,是台灣饒舌界有名的女兒癡和奶爸,今年還出了一張專輯《家常音樂》就是爸爸與歌手身份合而為一的心血結晶。 而怡婷更表示從前因為想在客戶面前維持專業形象,就不敢因為孩子的事情而中斷會議,但後來發現問題不在需不需要分神照顧孩子的狀況,而是與客戶溝通的藝術:「當我必須分配時間給家庭的時候,並不代表我不能好好完成這個專案,擦完小孩屁股上的大便,轉頭還是可以幫客戶拍好美食節目,我會用行動告訴客戶這一點。」 惠偵則說自己本來是工作狂,家裡公司兩點一線,但是有了小孩以後反而促使自己走出這個迴圈:「有了小孩後反而眼界更開闊,為了小孩走到以前不會去的台灣各地,才發現以前只是在生存而非生活。」生活對於一個影像創作者來說是寶貴的生命泉源,孩子同時成了拓展生活與工作的契機。 但當然身邊多了一個無自主能力生物還是改變很大的,常常爆肝剪輯的婉玉說:「以前會直接熬夜到早上,現在就必須學會規劃。」因為九個月大的孩子半夜會醒來多次,導致沒有一塊自己完整的時間,事情要像填縫隙一樣填進去,現在的剪輯工作要依靠大量的筆記。 在孩子們四處衝撞發出玩鬧聲的背景中,神色自如談笑風生的四位女性,散發著「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我發光」的沉穩魅力,但是她們敘述的日常無疑是艱辛、驚險、充滿挑戰的,工作與家庭孩子如何能裡外一把抓?她們給的答案不是成為時間管理大師秘方,而是不放棄任何一個選項的堅持。 〈論職場媽媽的生育二三〉 經歷懷孕生產是一段特別且私密的經驗,尤其具有多重身份的職場媽媽,懷孕的過程肯定更加「難忘」。怡婷直到進產房前都還在精算公司的各項業務,珍琳更表示:「一孕傻三年在我身上真的有,拿著一個預算表二十分鐘過去還看不懂。」婉玉也描述了哺乳期的痛苦,特殊的身體狀態連帶著作息以及生活習慣都有巨大改變。 這個話題引發現場媽媽們的一致共鳴,惠偵大嘆應該倡議文化部規定劇組把褓姆費編列在製片費中,不改社運人士本色的發言,帶起一陣笑聲。不過這笑中帶淚的建議,確實是職場媽媽們心目中的渴求之一,即使談話中透露台灣影像產業的平權思想已愈來愈普及,但有孩子的媽媽和爸爸們,在工作環境中還是需要更多實質的理解與幫助。 珮嘉提到三分之一的女性影像工作者,因走入婚姻而放棄職涯,為了照顧孩子而離開業界的比例甚至更多。被稱為「倖存者」的現場四位女性提出了她們的看法,惠偵說:「我必須工作,因為如果我沒有一個完整獨立的人格,那我就不會是一個快樂的母親。小孩很可怕,他們其實都可以感覺得到。」珍琳也表示認同:「生小孩之前我是個天生的社畜,反而是懷孕後漸漸開始想做一些瘋狂的事(成立工作室),覺得如果不能誠實回應內心渴望的話,以後也不會了,這也與剛剛惠偵說到更完整的人格有關。」 當今社會上仍有不少人會將職場媽媽評為「自私的母親」,兩位姊妹方才的說法,就是最有力的翻轉。建立健全的自我價值對她們來說,是同時對自己與孩子負責的表現,而導演、剪輯師、策展人、創業人等角色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怡婷分享自己的媽媽也一直都是business woman,從來不會說床邊故事也不會每餐在家煮飯,但卻帶給她無與倫比的正面能量,以及對其興趣夢想的支持,這也是她期許自己能帶給孩子的。怡婷說了一句話足夠總結這些職場女性的人生故事:「對我來說遇到困難面對就是了,我蠻確定自己想要什麼狀態,也很堅持走下去。」(珮嘉:「所以你不會被動搖?」怡婷:「因為我也不會別的了。」)(超...坦.....蕩........) 〈論職場媽媽的耐性極限〉 (來到了QA環節)首位發問者是惠偵的小特助(大女兒):「......(拿著麥克風沉默非常久)......你們會打小孩嗎?」 (現場炸裂) (惠偵:女...女兒???) (怡婷:......趕快回想......) (珍琳:這孩子太會問了吧?????) (婉玉:不愧是特助......) (以上為設計對白) 怡婷:「輕輕拍有,狠狠打沒有。」(輕鬆過關) 婉玉:「還沒有,我小孩才九個月大。」(這局我贏) 惠偵:「我...我有沒有打過你?」(特助:「沒有。」)(那你???) 珍琳:「有欸我有......。」(看來是你的場了) 珍琳:「我還滿常是失控的母親,會大吼,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也在學習怎麼跟孩子相處,現在是稍微找到平衡了,因為兒子已經脫離史前人類狀態,開始到會溝通的年紀了。但還是找不到方法阻止他吃鼻屎!」 怡婷:「聽說吃鼻屎會變聰明欸。」(謝謝你怡婷) 惠偵:「我沒有打過小孩,但她不知道哪裡學來一個大絕招,我們有一次去逛百貨公司的兒童玩具區,我想帶她回家了但她不肯走,我才剛拖著她的手拉她,她就大喊:『媽媽不要打我,拜託不要打我!』叫到旁邊的人都在看,我就不敢再拉她了。」(特助.....就是...特助......) 〈論職場媽媽的生存雞湯〉 怡婷:「經歷當下一定很suffer,但當你一拍完(工作)就夢一場啊,會過就是會過。39歲生小孩才發現生小孩真的蠻好的,對小孩的愛跟對父母、對伴侶的愛真的不一樣,是一種不同的感受。如果你想創作或人生要有新突破,生小孩也可以是新的動力。不要害怕有小孩會有什麼綑綁,其實遇到就是去面對。」 惠偵:「真誠的說,生小孩有困難,沒生就沒困難嗎?其實沒有,當然生兒育女影響還是很大,但無論如何人生計畫隨時都會改變,只能見招拆招,關關難過關關過,小孩只是人生考驗的一種。」 珍琳:「不只是生兒育女,任何想做的事情都應該去做,差異是在任何事情都不會照著你的想像,但也是如此人生才有樂趣。」 婉玉:「懷孕到現在的過程真的覺得有個女性的身體好有趣哦!當一個生理女性可以體會到很多奇妙的感受。說女導演七年才有一部作品,我現在剩兩年(笑),希望有機會可以完成。害怕進入婚姻或害怕生小孩也是屬於女性的生命經驗,不要擔心就去感受。」 文字紀錄:李宛軒 攝影:陳玟潔
時間:2020/09/30 (三) 19:30-21:00 地點:阿嬤家 2F女力空間 主持人 : 羅珮嘉|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策展人 與談人 : 陳穎|台師大、世新大學兼任講師 雀雀|影評人 陳穎 : 我非常喜歡女影這次的主題—「未來的模樣」,我覺得「她的失敗美學」單元跟近年酷兒研究的潮流很接近,我今天也是想從這個方向切入。當我嘗試在這些片裡找尋失敗的元素時,就一直在想到底是誰定義失敗這件事? 失敗又跟性別有什麼關聯? 什麼叫做一個失敗的性別? 如果我們回到主流講失敗的話,當然它的另外一面是成功,那這條中線是誰去畫的呢? 大家對成功女性的定義可能是社會對女性所期待的理想形象,認為女性應該要怎樣做、應該要成為怎樣的女人。我覺得無論酷兒或是女性主義去談這件事,都是希望可以推翻這個成功的定義,不是只有被社會所認可的樣子才是成功,我們也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女性形象。 《逃跑的人》 陳穎 : 這部紀錄片是關於一位越南的逃跑移工,導演花了八年的時間去追蹤故事中的主角,她在台灣停留了十四年之久,在這期間都無法與自己的家人相見。 看完這部片才知道原來台灣有七十幾萬的移工,其中有好幾萬都是逃逸的,他們逃逸的原因可能是遇到不好的薪資待遇,或是原本的雇主不續約,他們又急需用錢,只好選擇逃跑再找新的工作機會,因此他們不能以正常身份回越南。 我覺得如果要說成功的話,裡面的主角是成功的,畢竟她在台灣成功生活下來,也逃過移民署的追捕,並在這裡建立了自己的圈子,使用社群網路來聯繫同樣在台灣的移工或逃逸的工人。但以失敗來說,就要回溯到社會加諸在女性身上的期待,大眾可能會認為她不是一個及格的媽媽,因為她離開家庭很久,或者是她逃跑這件事帶給人一種非法、不太好的觀感。 我們可以反思什麼是幸運或不幸運?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失敗? 我認為成功的反面不一定是失敗,它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關係。回到這個故事本身,她其實是有點後悔自己沒辦法當一個好母親,但從她的生活經驗看來,已經使得女性的定義變得更寬廣,她可能兼具多重身份,也可能是不及格的母親,但她還是愛她的小孩與家庭,這些東西呈現出非常立體的女性形象。 《同一個屋簷下》 陳穎 : 這是在「她的失敗美學」單元裡,我最喜歡的一部片。導演用很清新的手法去講述一件沉重的事,敘事方式很可愛。這部片是導演以旁觀者的角度,拍攝自己的母親為何在老公過世之後,還要繼續照顧討厭、難相處的爺爺,她列出很多可能的原因,譬如說是不是因為錢?或是不習慣改變?還是不捨得這個房子? 從中我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們說多元成家是打破異性戀這種一男一女的結構,但其實有另一種型態也是多元成家的一種,它並不一定是同性戀,而是可能有很豐富的家庭成員。這部片中,她的媽媽面對的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夫家那邊的家人,這可能也是一個多元成家的案例。 這個故事其實就是講導演認為她的媽媽應該獨立、離開這個家,但他們同時又保持著某種關係,彼此間並不是完全撕裂的狀態。我覺得這其中的曖昧是我們可以去研究的,去找到一個跟家庭和平共處的方法。 《長夜驚魂》 陳穎 : 這是一部劇情片,你大可想像這部是黑道電影,裡頭會有黑幫份子、有被他們控制的女人,他們用綁架的方式逼那些女人成為妓女來幫他們賺錢,這部正是圍繞著被迫成為妓女的女性故事。 導演所選擇的女性形象是非常陰柔、漂亮的,符合男性會喜歡的女性。回想過往的警匪片,你會發現裡面的漂亮女生都是在尖叫、等待被拯救,但不同的是,這部片的女主角不是一個被動的角色,很顯然導演在做一種性別上的翻轉,帶有反抗父權社會的意味。 片中說 「現在是人口販賣最嚴重的時代,根據數據來看全球大概有兩千一百萬的人是性奴隸」,導演想藉由劇情片來關注這個議題,無論你是帶著類型片的興趣去看,還是你對人口販賣有興趣,這部片都可以滿足你。 《莉蒂亞蘭奇:戰爭永不停歇》 陳穎 : 這部片是關於70年代在美國當地很有名的一位歌手,當時有一波很短暫的無浪潮運動,她作為歌手外,還是一個詩人,她的歌詞裡面有一句話讓我非常震撼,她說「她不需要性愛,因為她就是活生生的一部色情片。」 Lydia Lunch是一個非常外放的女生,她在一開始便說自己在13歲時,遇到一位司機開到半路叫她下車,並用槍指著她的頭,要求她去舔車子的輪胎。這算是某種程度上性侵的案例,實在令人無法想像。 很特別的是,這件事沒有讓她感到不舒服,反而讓她發現自己是有力量的。她把這個受害經驗解讀成自己有性的力量,從她的音樂創作來看,她一直都在主導著自己的力量,她沒有內化這個傷害,反而把它變成對外的武器。這部片可以提供給同樣是受害者或是會內化傷痛的人,看她是如何以受害者的身份去反抗、面對這一切。 《孟加拉製造》 陳穎 : 在孟加拉有個傳統是女性很早就要結婚,其實有很多文化都是這樣,包括在英美的幾百年前也有這樣的觀念,當時的女性是不被允許工作也不能繼承財產,若不出嫁的話,在年老時會沒有人照顧。 這部片的主角因不願嫁人而逃家,但逃家後還是有結婚,老公是一個不工作的廢人,家庭的經濟重擔都在她身上。她除了在家庭裡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就連在工作場域也受到資方的剝削,比如說被迫在工廠加班,睡覺時不能吹電風扇等等。後來她發現其實是有法律可以保障工人們的權益,只是從來沒有人看得懂這些法律,於是她開始排除萬難的成立工會。 在這裡可以看出男性與女性不一樣的地方,如果今天是男性受到剝削,周遭的人可能會說那就去爭取合理的薪資啊!但如果角色變換為女性的時候,你會發現女性身上被貼了很多標籤,有人會跟她老公說要管好你老婆,不要讓她搞什麼公會,或是跟她說女人又不懂法律,搞這些要做什麼?甚至在工廠裡原本支持她的同伴,都因連連受到打壓後,也會開始罵她。因為性別,讓她受到更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 片中也有談到官僚體制對勞工其實是不友善的,它可以帶來很多反思。無論你是關心孟加拉的工人或是你想看一個女性如何受到這些壓迫後還能站起來反抗,這都是一部非常豐富的片。 陳穎 : 我覺得這幾部片都告訴了我們這個社會所加諸在女性身上的期待,比如說一個完美的妻子、母親。像是前陣子過世的竹內結子,很多人肯定她是一個好的女星,但同時也責備她沒有當一個好的母親,認為小孩子很可憐。我覺得小孩雖然很重要,但女性的生命並不是為了小孩而活的,應該說她不只是為了小孩而活。如果從這個角度去反思,這幾部片都是不符合社會所期待的女性形象,但她們都嘗試去找到屬於他們的生活方式。 最後我想分享一位酷兒學者曾說過的話,她說 : 「如果成功是這麼的辛苦,必須付出我的所有,那我去追求失敗會是更有滿足感的。」她把失敗定義為不符合社會的期待,比如說你可能沒有達成一些事、做不到一些東西、沒辦法成為某個人、不知道要幹嘛等等的失敗經驗或情緒。她認為這些失敗其實是有創造力的,它們可以創造一些不同的方法,讓你生活在這個世上。我覺得創造力重新定義了失敗這件事。 這非常符合《莉蒂亞蘭奇:戰爭永不停歇》的主角,她其實就是在追求失敗,當時的無浪潮運動本身就不是在追求流行,如果你去看這部片就會知道那是用一種唱讀的方式,而不是大眾對於音樂的期待,裡面講到他們並不想追求社會所定義的完美的理想。 《一伴》 雀雀 : 這是一部把我的價值觀砍掉重練的紀錄片,它談及女性身障者該怎麼表達自我情慾的需求。光是看女性討論性這方面的事就是一件很衝擊的事,一開始她們說社會都認為她們是不應該有性需求的人,或者是覺得她們的人生不會接觸到那方面的東西,我覺得其實整個文明社會就是大型的閹割性的現場。 平常我們都是聽別人說青春期的男生很色,很少人會說青春期的女生很色,但套用性平的觀念來說,應該是青春期的男生、女生都一樣色,會有這樣的情形是因為女性普遍被認為是不能談色的。 看到這部片裡女性能對性侃侃而談,正好和這個社會的性教育有極大反差。裡面是很健康的看待性需求這件事,你會發現整個社會的氛圍會把健康的事視為不健康,就像可能會有人跟你說你不能吃飯因為要瘦、你不能談性、你要加班工作不能休息等等,這些形象都是被社會吹捧、創造出來的,而忽略了個人真正的需求。 《前世情人的情人》 雀雀 : 從台語片中可以看見當時戀愛必須要門當戶對,婚姻不是你可以決定的。劇中由吳朋奉飾演的爸爸,就曾為此抗爭過。當他成為父親之後,發現女兒交了一個女朋友,但他不知道怎麼面對這樣的事,因為他當時也捍衛過自由戀愛,但現在變成女兒在爭取自己的戀愛權益時,他如果阻止女兒,那就與當時阻止他的人沒有什麼不同了。 《大冒險鐵路》 雀雀 : 這台列車就像個小型社會,裡頭存在著階級制度,有權有勢的人每天都過著酒池肉林的生活,而主角選擇掩飾自己低階人士的身分,在裡面當服務生服務那些高階人士。後來有位小女孩被人發現她是偷渡進來的,當下主角被迫做出抉擇,他應該繼續偽裝自己去幫那些人驅逐與他相同身份的人? 還是跟小女孩一起離開? 當你面對自我認同的難題時,敢不敢承認自己最真實的身分及狀況? 《成為母親的我們》 雀雀 : 這部片裡可以看到兩位年輕媽媽在學習怎麼當母親,修道院的修女也會幫她們照顧小孩,那些修女給人的感覺就是社會上所認為的好媽媽的形象,以至於到最後,其中一個比較愛玩的媽媽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不配當媽媽。當她離社會所定義的好媽媽形象越來越遠時,還有沒有勇氣去搶回媽媽的身份? 在這段掙扎的過程中,身為觀眾會隨時擺盪在要不要批判她? 或者是可以同理她的心情?而男性在這部片是從缺的,男人從頭到尾都置身事外,他非但沒有被罵,也沒有被問要不要當爸爸,反而是女主角要承受社會加諸在她身上壓力。 整部片透過兩個處境不同、選擇不同卻又相似的媽媽,加上具詩意、文學性的敘事語言與取鏡的手法,呈現出修女與媽媽之間的互動。從他們沒有對話卻玩在一起的過程中,可以感覺到多元成家的修女與母女的關係是成立的。 《海的另一端》 雀雀 : 菲律賓是一個世界上很重要的女傭輸出國,他們的身分地位在菲律賓是很崇高的,因為他們創造了菲律賓的經濟奇蹟。裡面紀錄的是一個訓練班,教她們在國外工作的時候,如何當好一個女傭。訓練班會設計很多情境演練,像是遇到被雇主責罵、性騷擾或是被要求很多工作而不能好好睡覺時,該如何面對這類事情。我覺得那個過程好像不是在訓練他們,而是在做心理療程、心理建設,好讓他們在出國之後遇到類似的事就可以懂得應對。 文字:游欣慈 攝影:陳品瑄
時間:2020/9/18 (五) 19:00 – 20:30 地點:光點華山2F藝文廳 主持人:羅珮嘉|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策展人 與談人:王允踰│法國在台協會 影視推廣 史惟筑│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開場】 女性影展今年有八個單元,其中「法國先鋒派女導演特輯」與「焦點影人:琪拉・穆拉托娃」單元,影片洽談、修復過程皆非常不容易。策展人羅珮嘉提到,尤其焦點影人這個單元非常難能可貴,女影跟烏克蘭國家電影中心談相關授權時,他們剛好面臨破產危機,若危機沒有好轉,這次在台的播映,很可能會是烏克蘭國家電影中心的最後一次。 今日很榮幸邀請到王允踰與史惟筑,來談談這兩個歷經重重困難的經典單元。 【談談焦點影人:琪拉・穆拉托娃】 影史中不該被忽略的導演:琪拉・穆拉托娃 史惟筑:我們念電影出身的,的確會學習如何批判電影、影像,但我們對「歷史」好像就不夠批判。學習過程中,電影歷史書籍告訴你誰誰誰很重要,我們就接受了,卻沒有想到:「為什麼歷史裡面沒有女生?」這次看了穆拉托娃的影片,就好像在我頭上巴了一下,為什麼我不認識這個人? 穆拉托娃1934年出生,她成長經歷政權變動,身分是跟著政權變化的。從俄國沙皇時代的羅馬尼亞人(現今:摩爾多瓦),到蘇維埃政權確立,她變成了蘇聯人,1991年蘇聯瓦解,她又變成烏克蘭人。 當時蘇聯政府,將電影視為重要的政治宣傳工具,謠傳當時文化部長看了穆拉托娃的電影,覺得影片中呈現小人物寫實、黑暗的面貌,不符合社會主義的面貌(大家都要穿得整齊乾淨,過基本的好生活),所以她的電影就被禁播了。 穆拉托娃畢業的學校格拉西莫夫電影學院(VGIK),也因為這個政治因素影響,將她的學位撤銷。即便後來在80、90年代,她的藝術成就慢慢被社會肯認,學校依然沒有將她的名字掛上去,同時她在敖德薩電影製片廠的製片職位也被降級為助理。喜愛拍攝電影的她,那段時期是非常沮喪、痛苦的。 影像中的浪漫 史惟筑:《衰弱症》提到戈巴契夫時代的經濟政治轉變,帶給人民一種存在的焦慮,裡面演員的表演都是歇斯底里、很極致的。當然,也被禁了(笑)。而《寬廣的世界》中,我覺得導演是認同社會主義這個政治的,她用共產青年團在工地工作的畫面,營造她自稱「工地美學」的畫面,裡面角色台詞很有趣,也一直在電影中重複:「我們將興建大大小小的房屋,但最重要是讓幸福得以成真,工廠是無法生產幸福的.......世界上沒有比愛情更美好的事情了。」 許多影像評論會用「影像敘事上的解構」來形容穆拉托娃。她電影中的人物關係經常四散在剪接當中,都是片段式的。建議觀眾觀影時可以放開一切,就讓自己跟著穆拉托娃影像走。 【談談法國先鋒派女導演特輯】 王允踰這次跟我們聊聊,關於「法國先鋒派女導演特輯」中五個主題:歷史第一位女導演愛麗絲・吉、女權主義電影開端《微笑的布迪夫人》的導演潔嫚‧杜拉克、《唐卡洛》兼任導演、編劇、演員的默片一姊穆西多拉、有如早期迪士尼歌舞奇幻動畫的《魔王》導演瑪莉路易斯・依莉貝,與將七百多部巴黎歷史影像剪輯而成《巴黎1900》的妮可・韋德雷斯導演。 歷史第一位女性導演:愛麗絲・吉 王允踰:愛麗絲・吉一開始是高蒙的秘書,她跟高蒙一起去看了盧米埃兄弟電影的放映會,深受啟發,並主動跟高蒙提議,開始嘗試自己主導拍攝電影。 這次選了愛麗絲・吉的13部短片,其實你從電影的年代跟時間長度就可以推敲出當時電影史的發展。愛麗絲・吉的《歌劇院大道》這部短片製作過程中,她發現了攝影機可以倒轉,所以影像有些運動是向後而不是向前。更有趣的是,因為早期的電影底片易燃,在拍攝歌劇院過程中突然卡片,愛麗絲・吉暫停拍攝並再開拍的這個巧合,發現了「跳接」的剪接技巧,這些實驗手法在《催眠診所》中也運用得淋漓盡致。另外在《愛麗絲吉拍攝留聲景電影》當中,你能看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的嘗試——一邊是留聲機在錄聲音,一邊是攝影機在攝影。 拍攝超現實電影的女性主義者:潔嫚・杜拉克 王允踰:關注女性議題的記者潔嫚・杜拉克,後來開始關注電影藝術性與娛樂性。她導演的電影《微笑的布迪夫人》,是我覺得是一部「很當代」的片,描寫一對無愛夫婦的生活。太太喜歡看雜誌,其中還有雜誌網球選手走向太太示愛的幻想畫面。(笑) 【Q:最推薦的片?】 史惟筑:我推薦我最愛的《寬廣的世界》,因為是一部很浪漫的愛情故事唷!(笑) 王允踰:大螢幕看修復,真的是完全不一樣,機會真的難得!要選一部最推薦很難欸。(編註:就是都很推薦,歡迎買套票的意思!!!) 文字整理:何睿平 平面攝影:林楨
活動日期:10/12 SAT 活動時間:14:30-16:30 活動地點:光點華山2 樓藝文廳 與談人 ✶羅珮嘉 Pecha LO│女性影展策展人 ✶孫明希 Maisy Goosy Suen│《女人就是女人》導演 ✶黃欣琴 Mimi Wong│《女人就是女人》監製 ✶黃鈺螢 Sonia WONG│「女影香港」創辦人 Sonia:我是Sonia,香港女性影展的創辦人。香港女影已經沒有再辦了因為沒有錢。 組織現在在做的比較holistic,不只電影,還有文化藝術的節目,目前woman festival至今第二年,電影節只辦了一年。 珮嘉:台灣女影很幸運辦了26年,我們幾乎都是全職在做影展,但Sonia是還有全職的。 Sonia:我是在大學教性別的。 孫:我們是全女的劇組,電影、工作人員都是女性,這個題材得到經費也很困難。等下也有很多這方面的事情要分享。 Mimi:大家好我是Mimi,中文名字是黃欣琴。香港女性電影人士不多的,要把他們集中在一起拍一部片是很困難的。要找到每個工作崗位都有個女性,過程是很艱鉅的。Sonia也幫了我不少忙,找人的時候他幫了很多忙。 珮嘉: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女人就是女人》這部片。 孫:《女人就是女人》是我們在2017年拍的一部電影,關於跨性別女性在香港的處境。一個主角是青春期在學校遇到要出櫃的過程,另一位是在婚後被先生發現身份。這部電影是關於兩位跨性別女性,在人生不同階段會遇到的困難。 珮:當時收到這部片很驚艷,也覺得很心疼。選片這麼多年,覺得在香港很少遇到這種電影,想請問你們為何會想拍這部片? Mimi:拍這部前已經和導演拍了不少短片,都是關於跨性別的。很多跨性別人士答應拍了,之後卻不想將自己以前的情況表現出來,不想讓自己的過去被人看到。所以有一部份的片子,拍了卻無法放出去,我們的心血都沒辦法被看見。 而且很多跨性別女性請他們來說自己的故事,他們都不肯。即使拍了片,卻不肯播出來。我想要拍一部片讓人知道跨性別人士在香港的真實情況,而這個需要透過長片才能讓人知道。 香港其實也是有人拍這個主題,但沒有跨性別人士自己拍。我覺得跨性別要自己說自己的故事,不然這些故事都沒有人知道。我認為跨性別女性和女性是一樣的,就跟片名一樣,女人就是女人為什麼要分類? 孫:剛開始跟Mimi合作拍的短片都是紀錄片,香港人比較少看、接受度沒有很大。另外一件事是,很多香港跨性別人士不願受訪,因為怕露面之後會被在網路上攻擊,或對日常生活造成困擾,所以他們不太願意受訪,受訪之後也不太願意被播出。 趙凌風的角色,會特地選跨性別女性演員Tomo,是因為覺得香港歷史上還沒有跨性別的演員,所以希望由跨性別的人士來演跨性別。 另一位主角宋紫洳則是由順性別人士李蕙敏演的,很多香港跨性別女性都是以男性飾演,這次選了順性別女性來演,希望能突破刻板印象。 我們在製作團隊裡,除了Mimi是跨性別外,有演員是跨性別,然後在劇本構思的時候還約了20多位跨性別人士做訪談。 珮:台灣也很多都是非跨性別拍跨性別,這其中常常會有很多刻板印象。香港之前就是《翠絲》,台灣是《阿莉芙》,但幾乎都是找人來演,不是真的由跨性別演。所以這部片其實有很多突破。另外一個層級,監製Mimi本身也是跨性別。 Mimi:我本人也是跨性別人士,55才出櫃,56歲做手術,現在已經過了9年了。 珮:您本身也打破了電影的遊戲規則,在55歲出櫃,之後選擇以女性的身分踏入影像產業,真的很不簡單。我有上去看你們的fb,其實大部分的反應都不錯,但也看到有很多歧視性的攻擊。 孫:香港這部片上映的時候受到的攻擊很多都是網路上的。比較好的是在放映的時候,有位跨性別的女兒帶媽媽來看,媽媽看完問了一個問題:其實你們做完手術會很舒服嗎?他們有因為這部片多了溝通,也比較了解自己女兒的心態。 Mimi:如果沒有這部片,這跨性別的女生都沒有機會出櫃,她以前都是男裝打扮,看了這部片變成一個機會,可以正式和媽媽出櫃。 孫:攻擊肯定是有的,但如果沒有這部片,就不會有一個平台讓這些聲音被聽見,我們也沒有可以反駁的機會。 Sonia:對,如果我們沒有開始做這件事情,這些很難聽的話就不會被說出口,我們就不會知道原來這些人是這樣想的。現在話被說出來了,我們就可以想想要如何改變他們? 其實你在拍這個紀錄片之前有沒有想到,其實香港有這麼多跨性別人士不願意講出來? 珮嘉:問題再放寬一點,我其實很想了解到底香港性別意識的狀態和處境是什麼?我們都覺得香港好像很開放? Sonia:沒有很開放。可能我們出生的年代和圈子都不同,所以想法都不同。我是2013年開始想做女性電影節,那時候超年輕的23歲大學剛畢業。第一個想到就是跟公部門政府要錢,但很難的就是香港其實有個關心婦女的部門,什麼婦女福利一個非正式的部門。但裡面的人都是一些很保守的女性,他們也沒有什麼錢給我。 我們就在想這要是一個電影的項目還是性別的項目,香港其實沒有很多funding可以做電影教育,錢也沒有拿到。另外電影發展基金則是用來拍電影的,我也不符合。後來想申請藝術活動,但也很難拿因為我們是做電影。後來還好一年之後拿到了,但在面試的時候全部都是男子,跟我說香港的性別已經很平等了,還問說你們都放女性的電影會不會是在歧視男性呢? 後來還好有錢了,但因為要先墊錢,政府是一批一批給,最後很慘很辛苦。另外一個就是香港大部分的藝術或電影的funding都是自助項目,不是一個計劃組織本身,那造成的問題就是我要打工,其他都是志工或短期幫忙,沒有sustanebility,就是很慘。 後來有 HeForShe,他們說很支持,但是後來錢都給了LGBT影展那邊。因為公部門覺得性質差不多,就把錢都給他們,結果變成我們(同溫層)裡面有很多競爭,我覺得就是很可悲。 珮嘉:台灣也是想要做性別影展的愈來愈多,酷兒影展、婦女影展……我們的補助愈來愈下降,但要想辦法自己賺錢又被嫌太商業化。我參加過幾次香港的酷兒影展,他們很盛大,應該資金其實不少啊? Sonia: 好像有比較多銀行跟投資公司,跟有出一些LGBT產品的公司願意贊助他們,反而是女性這部分比較困難。 珮:問題回到劇組。你們剛剛有提到找資金很困難,困難是什麼? Mimi:我們也有去找那個資金,說我們有拍一部全女性的電影,可不可以給一點基金。但他們就說我們拍片是要拍好片,不管是男是女,你們的片是好片我們就支持,但你們沒人有經驗,我們怎麼支持你們拍片? 政府就說要推動電影發展,但我們真的有心做這件事政府卻說不,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 Sonia:真的藝術發展局的人非常非常保守,結果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能拿到的都是一些有名有姓的明星,他們就知道啊這些人有經驗名氣,所以比較不會虧錢。結果變成都在補助一些根本不需要補助的人。 珮:這樣真的會造成香港一些斷層,新銳導演什麼都拿不到資金。 Sonia:你看香港電影都是什麼古天樂、劉青雲,都他們幾個人,過去20年都是他們做男主角。就是不論是私人公司或是政府都覺得這樣投資很安全,導致香港都沒有創新的動力,然後就讓我們都很困難。 珮:那既然困境已經那麼多了,導演跟Mimi還是那麼堅持要做這部全女班的電影,那我看報導好像說你們的劇組有確保LGBT的名額,那是真嗎?還是假新聞? 孫:應該假消息啦,但我們的確劇組有很多LGBT。不過我們一開始就是要全女性的劇組,就像剛才說的,香港比較少電影職位是由女性擔綱,既然我們要做一部跨性別、小眾的電影,那在電影工業裡面現在還是男女不平等,就希望找女性工作人員一起拍片,證明女性也有能力做一部好電影。 珮:有沒有除了香港政府之外的管道可以找到經費? 孫:我們其實嘗試了很多管道,找了很多相港的NGO,但他們其實已經沒什麼錢。我們還有從國外女性電影的基金,就是到處拿一點。工作人員其實都拿很低薪,是以半志工的方式把這部片子完成的。 Mimi:如果我們已正常的價格請他們,可能成本會多很多倍。 這是香港第一部全女班的電影,一天開工開16個小時,他們好像都不用睡覺,而且一分加班費都不收,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能把成本降到最低。 孫:片場有很多人很辛苦,尤其我們的副導演常常在片場穿了睡衣就出來,回家還要處理文書。 Sonia:台灣學電影的比較多,香港只有兩家學電影的學校。很多電影崗位不接受女性擔任,例如攝影師、電工等等。 Mimi:我們連電工都是女生。 Sonia:香港商業電影的女導演是十根手指能數出來的,只有許鞍華比較有名。很多人覺得覺得你(女生)這個工作做不來,或者是說你來兆頭不好。 不知道你們在台灣電影圈有沒有這個經驗,例如女生讀導演或攝影就會被推去作別的,剪接啊美術啊監製啊,就不讓你做這些職位。或是你做了卻不被信任。 珮:現場觀眾有沒有可以分享的? 觀眾:我之前有做過劇組,想嘗試當導演,卻被勸去當演員。因為要跟市場的趨勢啊什麼什麼的,聽起來就覺得很灰心。 珮:我以前在劇組也是被說女生不能碰攝影機,因為會帶賽。這裡面太多的牽制了,決策者都是投資的那些政府單位,他自己本身就沒有性別平等,裡面很多都是中產階級老男人,他們就不懂跨性別電影。但現在像柏林影展,從評審、programmer都有在強調性別平等,都有慢慢在改變。 現在開放問題 觀眾:有幾個問題想問講者, 1剛剛有提到《翠絲》,雖然拍得不是那麼真實,但你覺得至少對於觀眾去理解跨性別,那是不是踏出去的第一個門?覺得這個門跨出去之後,有沒有感受到這讓跨性別的故事在華人社會中有更多的表現。 2您提到在宣傳的時候有遇到很多阻礙,包括政府部門不支持,但跟《翠絲》比較,演員是很有名的也演過很多動作片的,那不知道你們在宣傳《女人就是女人》的時候採什麼角度? 3最後一個問題是,我有去過trans gender art fest,30%電影工作者都是跨性別的,包含演員跟幕後的製作人原跟導演,想問你們覺得台灣和香港,有沒有這麼多的人才可以接這些職位? Mimi:《翠絲》那部片跟我們的片是不一樣,從非跨性別女性的角度去談跨性別角度是不一樣的。 《翠絲》說好像跨性別女性都會從小喜歡女性內衣,好像強調喜歡穿女裝啊什麼的。但真正重要的強調是女性的內心,而不是這些外在的東西,這不是重點。《翠絲》很多什麼把門關起來穿女性的內衣,好像就很舒服啊,我覺得跨性別不是這樣的,看了就覺得很奇怪。 還有另外一個場景,他第一次出櫃的時候還幫他穿紅色的頭髮,我是覺得如果是跨性別第一次出櫃不會把自己扮成這個樣子的。 我就覺得他們好像用了很多香豔的元素,但我們這部片是用一個寫實的方式。如果從娛樂性來看電影的話,我們是會被《翠絲》比下來,如果從真實的角度看,我覺得他們不是描述一個真正的跨性別女性。 從推廣上面我們是佔了下風,因為片子沒有這些元素可以吸引很多人,因為《翠絲》那部片的主角那麼男子氣概要怎麼變成一個女性,這本身就是一個宣傳。 孫:很多跨性別看完《翠絲》都覺得不太貼近真實的情況。《女人就是女人》在香港和《翠絲》的上映時間非常近,很多人是看了《翠絲》的電影才看《女人就是女人》。所以很多人是看了《翠絲》才開始關注跨性別這個議題,在香港也有一場是兩部片的導演一起做的映後。 我一部份很喜歡《翠絲》的美術啊電影手法,但就像Mimi說的,當你真正了解跨性別的時候,有一些就是會比較脫離現實,就是比較不那麼真實。 然後再宣傳上面其實也是要謝謝《翠絲》啦,因為我們就是小本嘛,做一個電影要那麼多資金去做宣傳,他們上映的時候我們同時上映,大家會比較去關注跨性別,就是會呼籲大家也來看看《女人就是女人》。無論喜不喜歡我們的電影,也是來看看嘛,一次看兩部電影去比較。 珮:所以主要是以口碑宣傳? 孫:對,比較多。 珮:剛剛也有提到一個滿有趣的點,其實現在LGBT的電影很多了,其實題材也都拍到爛了,那但是也有滿多跨性別電影的出現。 觀眾:我補充一下,就是其實這段時間,在美國這5、6年來有愈來愈多的社會運動跟人權運動,特別是Trans lives matter因為就是很多美國跨性別女性,他受到很多的暴力或者是謀殺,這個議題其實是有一些之前在大螢幕上成功的讓大眾知道。 那其實是跟著整個美國的這個好萊塢電影其實是有更多的機會給這些非裔的、亞裔的、拉丁裔的這些藝人還有導演,可以有更多的舞台空間,因為有這些議題,帶了更多好萊塢的製作人跟製作公司決心,還有很多跨性別的人透過選角脫穎而出,是可以被重視的。那這一波在美國的時候都可以感受到,就是有非常多很強的力道,在推整個跨性別的運動,包括影展,好萊塢本身,還有一些有線電視台。 所以不知道說,當然美國跟亞洲的同志運動有很大的差別,畢竟他們有50年的歷史,若華人社會有更多跨性別的故事,有沒有這麼多人才可以stand by?要怎麼樣讓大眾被說服,讓這個議題得到更多的重視? 我會這樣說是因為,我自己有一個gagaoolala的平台,我自己是很強烈的邀世界各地跨性別的電影到我平台上,因為這個議題是非常的重要,但在點閱的方面遇到很多的阻礙,所以今天特別來想聽台上的一些分享者可以交流跟一點建議分享,謝謝。 Sonia:美國在影視方面,這些LGBT議題能比較蓬勃,是因為我們這些人自己比較願意去支持。我們在香港,很困難的工作就是要說服觀眾這真的是值得去關注。一開始的時候很多給我們錢的人都沒有女性,都沒有能認知到,其實你作為女性,你支持這樣的電影是很重要的,後來才能去說服男人這跟他們也有關。我在說服女人,我在講的議題跟你有關也很困難,如果在這個前提之下,沒有觀眾支持,我們就沒有partner and power。 為什麼有很多公司在近年變得很支持這些LGBT活動?是因為他們知道pay equality是很賺錢的東西。當然我們心裡很希望相信那些人是真心在支持平權的,但是很多時候他們心裡面有沒有真的在支持平權我們不知道,他們那些公司的public image都很喜歡做成我們很支持LGBT啊我們很friendly,特別是那些大的投資銀行,因為他們知道,在裡面工作的高層,很多人都是LGBT,要是你公司的LGBT friendly做得不好,他就到別的公司去做。就是有這樣一個leverage,他們錢夠多,或是他們在公司裡的post夠重要。 所以有很多公司,像是Burberry出彩虹衣服啊,因為他們知道這個sector好賺。我們怎麼把自己的錢去用到一個地方,這也跟我們香港最近的民主運動有關。就是我們用我們自己的錢去投票,然後我們有足夠的leverage去站出來說我支持LGBT、女性、民主這樣子。 我覺得中間有這樣一個關係,然後很多在娛樂圈和影視產業的都是LGBT,但他們有沒有辦法以LGBT的身份站出來,我覺得還沒有這樣一個空間。雖然身邊的人都知道,他們在自己的空間也有做LGBT的東西,但在公開電台節目站出來,目前只有一個。人是有,但就是有沒有那個空間,而觀眾有沒有那個支持,讓他們可以站出來。我覺得還有一段路要走。 珮:我想回答一下剛剛的問題,我做女影這麼多年,我覺得談情慾流動、LGBT的電影,我自己的歸類有個叫偽同志片。就是帥帥的俊男、帥帥的美女談談戀愛很吃香,這個在主流市場或是女影,票房都很好。可是談到,性別的流動的時候,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很大的門檻,就是有觀眾會說「我很喜歡看酷兒電影喔,但是跨性我要想一下」這是另外一個門檻,那我覺得當然也有在慢慢改變,去年我們在放閉幕片的時候,也是有很多人抗拒。但慢慢地近來,我就發現一個問題,LGBTQ的電影工業裡面,也有不同的類別歧視問題,就是不只是外面的在歧視跨性別,連圈內比如說L、G,在談跨性電影的時候,他也不一定是站在同等的立場。所以針對LGBT電影的發展,我覺得台灣要在發展跨性電影,還有好長一段路。 Sonia:在同志電影圈也有歧視。我有認識朋友在香港同志電影節做選片,女性在那邊爭取播女性的電影很難很難,就是他們就說你們的電影都不賣錢,或是說你的電影都不好看,誰要來看兩個女生的電影。很多時候就發現,其實在LGBT之中,除了性取向之外,還是有很多關於性別的問題。 珮: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其實我認識很多優秀的跨性別演員,但是現在找他們演戲,還是要再演跨性別,他可能也被迫自我標籤,這也是我遇到的一些演員的處境。 還有人要問問題? 觀眾:想問一個蠻無聊的問題,就你剛剛說你去審查的時候,有人說你有歧視男性的嫌疑,面對這種白癡你那時候是怎麼應對? Sonia:我那時候沒有很兇開罵,我就23歲,也沒有特別努力說服他。我有沒有刻意說服他,心裡想說反正他是個老男人他就會死了,我也比較漂亮,沒關係他會被淘汰。對這種白痴說什麼很厭女的話,我就會心想你以後的性生活與會很糟糕,就是以這種心態去面對。 從那個project到現在,情況有變好一點。我覺得女性議題的接受度從2013到現在覺得有進步,觀眾自然而然也會來,不用特別說服他們。比較明顯的是媒體不用特別說服,我就覺得整個社會的氣氛有比較好了,經過這7年。另外有個分別是我超多學生都去做媒體了,所以訪問我們的都是他們。就是媒體裡面會需要一些我們的人啊。 觀眾:想問導演你待過之前工作人員是男性的劇組嗎?身為女性當導演感覺會遇到什麼困難?你會抱持怎麼樣的心態? 孫:其實很抱歉我其實沒有遇到什麼太大的困難,可能我出生比較遲。之前有待過男性主導的劇組,雖然還是有說女性不能碰機器的箱子還是有啦, 但如果有九成的人都是女性,其實溝通上是比較容易。然後我們如果是要拍一些intimate的場景的話,全女性的工作人員比較容易拍攝到。其實我覺得男性和女性可以做到的東西都一樣啊。 Mimi:我覺得我是沒有選錯人(導演)啊,雖然電影發展局說這個人沒有經驗啊,但他拍出來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好。 珮:有沒有特別想要說的部分? Mimi:可不可以反問在台灣的情況?跨性別啊?女性電影啊?如果在台灣做同樣的事會不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珮:我們的確還沒有出現這樣一個劇組,全女劇組談跨性別,這部分你們的確是先。但我覺得以普遍風氣來講,台北的風氣是很好,現在我們想要做的事,女影的使命是如何走入偏鄉?就在場這些人都不是問題啦! 觀眾:之後香港會不會受到中國的影響,對這些電影題材會有所阻礙? Sonia:其實還沒到那個地步,這種題材就已經受到很多阻礙了。應該這樣說,在香港就是租金很貴,所以有電影院的公司就是少數那幾家,這種沒有票房保證的片在商業院線上映很困難,商業就已經把小眾的片隔開了,可能給的放映時間就很差啊。像《十年》可能你們也有聽過這部電影,這種政治題材,才真的是無法上映,他們就只好搞社區放映。 我覺得商業上遇到的問題比較大,我們這種題材的反而不會說你在搞革命啊。 孫:在放映上真的遇到很大的困難。 珮嘉:原本做這場是希望promote《女人就是女人》,結果現在已經完售了。那原本今天還有一位要來討論的是《非自願測試》的製片的劉品均,但他今天臨時無法參加,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明天可以去映後問他。
2019.09.28(六) 14:00~15:30 女書店 主持人:羅佩嘉|2019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主席 與談人 : 王如玄│律師 長年致力於性別平等工作,關注於婚姻暴力、職場性別平等、職場性騷擾等議題。 范情│長期關注婦女與媒體、教育、文化 愛荷華州立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曾任女性影像學會理事長。 圖/講師范情(左)、王如玄(右) 王如玄: 我會特別想關注女性影展,是因為我曾打過台灣第一屆子女探視權的一個案子。當時我提出各種國外案例,為這位媽媽爭取孩子的探視權,法官還是不肯判。結果有一天開庭法官非常兇,跟當事人的先生說:「給她看一下(孩子)會死啊?如果有一天小孩子死掉,大家都不用看了!」後來才知道法官看了一齣有關探視權的台劇,非常感動,隔天就改變了判決,並主動幫忙當事人寫協議書。我當時見識到戲劇是有威力的,起碼在那個案子裡,當事人得到了公平正義。 《同境相憐》 王如玄:全世界女人的處境都受制於當地的習俗觀念,不論是電影中的阿富汗、以色列甚至台灣,這些對於女性處境的影響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我在這部電影中尤其看到宗教對於性侵害的影響。 《同境相憐》是一個家庭亂倫的案件,受害者向宗教團體尋求協助,卻只不斷被要求禱告,在系統中能得到的幫助非常少。家人甚至建議她把孩子生下來作為被性侵的證據。最後受害者透過媒體、社會運動讓事件獲得關注,這和台灣許多經驗非常類似。 片中有一句話讓我很感動:「在那個國家(阿富汗),每個女人都有一百個主人。」男人們認為自己有替女人發聲的權力,因此這些女人的故事深埋在地底,要說出來何其困難,並且會遭到整個家族的追殺。而性侵後要經歷的司法途徑,那種一再被要求重複陳述、舉證的狀況,對每個當事人都是非常漫長的。在電影中會很深刻的感受到那種一路走來的辛苦過程。 圖/《同境相憐》劇照 《以鳳凰之名重生》 王如玄:事實上也有男性對男性的性侵案事件。本片的故事發生在以色列,描述一個孩子小時候遭到性侵到現在三十幾歲,成長的過程中所受到的煎熬。片名《以鳳凰之名重生》代表主角希望經歷這個過程後可以重生,他用唱歌的方式講述自己的遭遇,並從中找出力量。 在片中也再次看到宗教對性侵害的影響。眾人期望能透過宗教來改變加害人,並希望受害者禱告而不是把事情說出口,但事實上宗教展現的力量還是有限。不同的宗教在性侵的議題上,都有各自的課題要去面對。 台灣看似進步,但在處理相關問題時還是有很大的局限。例如加害者中心應該設置在何處?人權的議題?台灣在這塊會有很多不同價值的爭論。相信在觀看完本片之後,對於受害者的影響和加害者的處理方式,我們都可以做進一步的思考。 圖/《以鳳凰之名重生》劇照 《非自願測試》 王如玄:大家可能很難想像毒品在性侵案中發揮的程度。我的一些當事人在事後調閱監視器時,發現當下他們都是自願跟加害者回家、上樓梯,醒來才意識到發生什麼事,這些都是毒品產生的影響。台灣刑法在做修正時,規定只要對食衣住行產生重大影響,都列入加重強制性交。當時有很多人反對,認為比起侵入住宅、運輸工具上性侵,下藥等方式看起來傷害較小,但事實上醒來後所造成的傷害是一樣的,並且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無形的負面心理影響。 圖/講師 范情 范情:我看影片時,很不喜歡看到女人又是被害、可憐的角色。但這幾部影片中沒有哪個女人是處於可憐的狀態,他們有想法、有專長、有自信,但提到事發原因,這些女主角都說:我不知道。但就是發生了。她們都是可以承受狀況的人,且是所謂21世紀、經過200年婦女運動洗禮後的女人,為什麼會不知道事情是如何發生的?這也是今年這幾部電影中我認為非常棒的地方。 我和王律師做婦女運動至今超過三十年,身為遊行者,很多時候會使用簡短有力的口號,例如:是就是是,說不的時候就是不,可是事實上很多事情根本不是這樣子。我很高興有這樣的電影能讓我們進入真實的情境,而不是停留在口號上。 一般受害者很難願意將事情說出口,就算願意說,也不容易說到重點。而這些女導演很清楚知道重點在哪,重要的不是吃藥後在床上發生什麼事,而是後面的test pattern。片名的test很有意思,這個test不只是驗傷做的測試,而是各個層面的,包含了受害人的遭遇,以及後續她與朋友、親密愛人的關係。 而覺醒並不真的是「一覺醒來」就達到的,它中間絕對有來回拉扯的過程。 而事發之後,對於受害者的男性伴侶也是一種test。我們也可以觀察專業醫護人員在做詢問的方式,跟愛她的男朋友之間有什麼樣的差別。所以我很鼓勵在座的生理男性、女性,都可以去看看這部電影。 王如玄:在男性伴侶堅持追究責任時,我們可以回到對於被害人的尊重這件事,並思考:你要的正義到底是誰的正義?對於男朋友來說,他很認真努力在為被害者尋求正義,但當下對於受害者來說已經超過負荷範圍。如果你們周遭朋友遭遇到類似狀況而向你傾訴時,你們會用什麼態度和方法去傾聽?我想看完這部電影你們就會知道怎麼做。 圖/《非自願測試》劇照 《少女的私密告白》 王如玄:這部片講述一對堂姐妹殘忍的受暴經驗,其中一位是騎腳踏車出了車禍後,被肇事者假借送醫名義性侵。另一位則是遭遇家庭亂倫。 圖/講師 王如玄 其實性侵後告訴朋友,對被害人來講是一個復原的過程。我常常處理到類似的個案,都和性侵害修法有關。最近有一個個案是受害者在小學時聽了性侵害教育課程後,才發現自己小時候被爸爸性侵。受害者把事情告訴自己的朋友,兩個人抱頭痛哭卻沒有報警。直到她國中再次接觸到性侵害課程後,自己到警局報警,當時小學的朋友就變成了重要證人。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到向朋友傾訴對於事件的正面協助。 另一個個案是受害者十年前下班回家,被人跟蹤回家後遭到性侵。十年前就已經有性侵害防治法,因此受害人報警後接受了完整的採證流程。最後雖然沒有找到加害人,但對加害人的精液做了建檔。十年後加害者因另一件性侵案被抓,兩起案件得以一起偵破。我們的犯罪防治法即便進步,當中還是有很大的問題,這起案件最後因不符合被害防治法的時間,而無法對受害人做金錢上的協助與補償。看到這些案子會讓我想到,現實的機制下還有許多不足的地方,應該要進一步做改變與調整。 圖/《少女的私密告白》劇照 《歐娜的抉擇》 范情:性侵害已不是新的議題,但在2019年的女性影展來看這些影片,有什麼不一樣? 十九世紀第一波婦女運動爭取工作、受教等權利,第二波婦女運動強調於性和身體的控制權,包括性騷擾也在談論範圍內,但這些問題並沒有被解決。到二十一世紀的me too,有人認為這是第三波婦女運動,這讓我們思考當女人有工作、有專業、有自信之後,在職場上、婚姻家庭之中,還要找回什麼東西? 我們回到性騷擾這個名詞是怎麼定義出來的。1975年,康乃爾大學中的女職員為了聲援女同事是被老闆性騷擾,因此她們談論各自在職場中被騷擾的狀況,之後才出現了「性騷擾」一詞。 在本片的劇情中,女性員工表現好、賺了很多錢,老闆說:「我們去喝一杯吧!」但這和男人與男人去喝一杯的情況,會不會不一樣?這些都是一般學校在鼓勵女性擁有專業的同時,所忽略的更細緻的東西。 我認為現在女性碰到的狀況是:當我們進入職場,看見那些彬彬有禮、欣賞出色女性的男性同事時,這之中公和私的界線該如何拿捏?這也呼應了今年另一個單元主題:灰色,我們如何看待這樣的灰色地帶?這幾部影片都細緻的描繪出覺醒的過程,以及該如何保有自覺和自我,我覺得導演和編劇都太棒了。 圖/《歐娜的抉擇》劇照 《多莉安的幸福人生》 范情:多莉安是個學有專精、家庭婚姻美滿的人生勝利組。她在劇裡呈現出非常有自信的樣子,但後來發現媽媽有外遇的對象,她爸爸媽媽的關係也對她產生影響。大家在觀看這部電影時同樣可以注意覺醒的過程,當她與每個角色互動時的表情和回應,以及她如何在繁忙的工作及家務中,找出屬於自己的東西?這些過程如何導致她最後作出的重大決定? 圖/《多莉安的幸福人生》劇照 《失控家族》 范情:在本次影展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控制。控制就是權力的展現,在我們談不論是性侵或性騷擾,其實都是權力關係的問題。《失控家族》雖然描述的是手足情誼,但同時也呈現了親密關係中的權力平衡、控制與依賴之間的關係。有些人表象是可以照顧別人、被依賴的對象,事實上他們可能也依賴著這種被依賴的關係,這是一種很特別的狀況。但可以看出片中的手足依戀是非常深的,我也很推薦這部電影。 圖/《失控家族》劇照 【Q&A】 Q: 我曾在論壇中看見有性侵受害者發文,描述她在反覆陳述的過程中感到崩潰而放棄追究,卻被底下的網友留言指責沒有盡到追究責任,可能導致下一個受害者的產生。我覺得很疑惑,受害者是否需要承擔追究的責任? A: 王如玄:就制度面來說,這是性侵應該屬於公訴還是告訴乃論的問題。但回到性侵害犯罪的部分,我覺得一定是被害者自主。因為我們外面的人很難去理解被害者的壓力和意識。 我舉一個家暴的案例,我有一個當事人是家暴受害者,她來找我時全身都是老公燙的香菸疤,我就積極地幫她打離婚官司,一審也判雙方離婚,對方提出上訴。之後我遲遲沒有收到上訴開庭通知,後來才知道當事人撤回起訴了,這樣連一審的離婚判決也沒有了。打電話問當事人,我就說這種丈夫怎麼能要呢?結果是因為訴訟期間卡到過年,當事人過年回娘家,卻因為當時「女兒大年初一在娘家會帶衰」的觀念而坐立難安,最後決定撤回起訴。我們追求公平正義,卻很難去體會當事人當下的感受。 范情:要提醒身邊的人,尊重當事人的感受。另外,回到我們談到的覺醒之後,當事人是否有可能透過這樣的事情去找到這件事對自己生命的意義?重要的是事件之後,如何讓往後的人生更加被自己所控制? 圖/觀眾提問 Q:最近很多人在討論懷孕八週以上禁止流產的議題,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A: 范情: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健康。這回到了我們談的control的問題,誰要來控制我們的子宮? 王如玄:我們的優生保健法是一定要修法的,像是現在規定已婚女性要流產需要雙方簽名,但我有當事人已婚懷孕後發現老公外遇,於是偽造老公簽名去做人工流產。這下子有多慘,她先生通姦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她偽造文書要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認為身體自主權一定是優先的,但台灣優生保健法都還沒有修案,這其實是對女性自主一個很大的影響。我不是念醫學的,所以對這部分還沒有搜集很多資料,但我認為還是要回到女性自主權及健康為原則。 圖/觀眾聆聽講師分享 文字記錄:李佳蓁 攝影:張至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