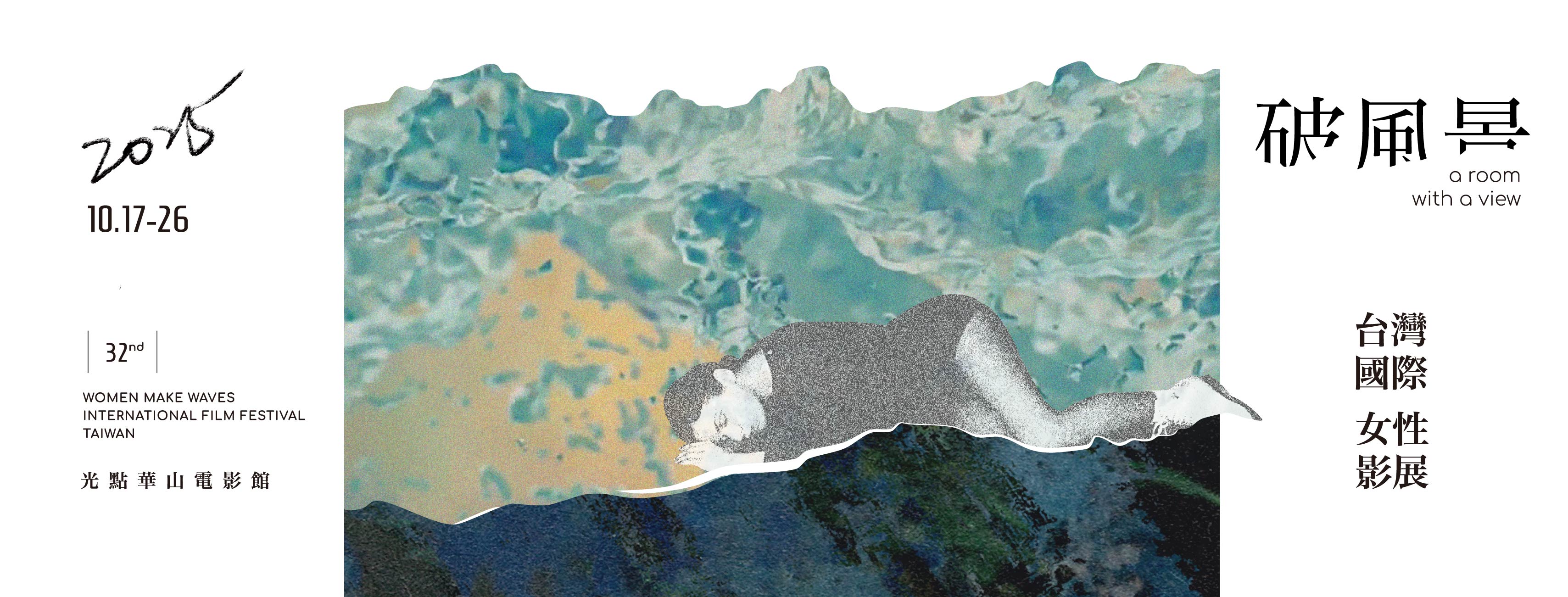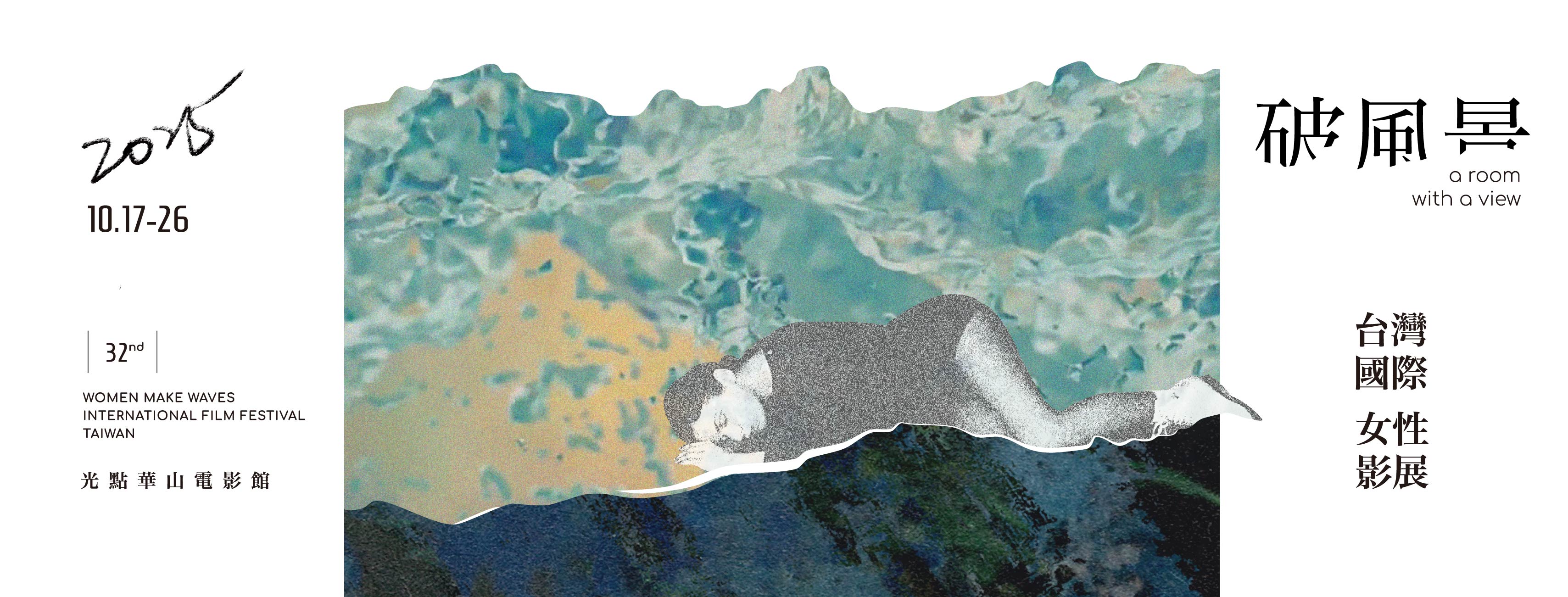實驗電影民族誌學家始終龐克——佩姬.阿維許
文/劉行欣(藝術家、導演)
很高興聽到今年女性影展以佩姬.阿維許作為焦點影人。記得初次見到阿維許大約是2016年在加州藝術學院,當時他作為參訪藝術家來到學校放映和座談,一時間大家都被這位謎樣而多才的電影實驗者給震驚了。阿維許不僅是一位想法風趣大膽的女性主義者,更是一位堅持不懈的實驗影像修行者。
阿維許的作品橫跨四十年,媒材運用從超8、16mm、Pixelvision、拾得影像、挪用影像、電玩、VR、到數位媒材等。作品美學和類型遊走在非傳統、非商業、非工業的邊緣。在他的電影中找不到傳統的取景、打光、演員、腳本;類型互換混合更是超越了紀錄片、敘事片、散文電影等單一劃分。不僅僅在技術上琢磨,阿維許的每一部作品更像是一則人生提問,或者反思。從阿維許的鏡頭下,我們可以觀察到身為一位女性,生活在當時美國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地緊抓住每一個精準空間去思考性別問題,如何在流行文化或社會傳統框架中試圖跳脫。阿維許彷彿一位穿梭於家庭與街巷中的電影民族誌學家,鏡頭是敞開胸懷的,但目光是犀利的,他的每一個影片都是一篇觀察筆記。於是從交疊並置的影片文本中,我們漸漸地走近這位影像實驗者。引用他自己的話說:「拍攝風格是沒有專業觀察者的民族誌電影,沒有父親的家庭電影」。
阿維許喜歡讓女性講述女性的故事,而拍攝地點,很多就是在家裡。家庭,是很多女性創作者的私密花園,他們對家中的每一道部署,如地毯的毛色、角落的蜘蛛網、洗衣機的運轉速率、冰箱的噪音分貝、尿布和故事書、每一個歡樂的節日、每一處瘀傷刮傷等,都瞭若指掌。家庭電影作為一種創作手法直接地去對抗資本主義主導的工業電影,排除了傳統的磅礴大場景、專業打光、職業演員、劇本排練、市場操控等,反之,創作者手中有的只不過是一台可以單人操作的相機,拍攝出的畫面也總是不完美的,狹小侷促甚至經常呈現出粗糙感,但也正因為這樣的條件構成,家庭電影的形式是最真實自由的。因此,作為一種創意形式,它可以超越限制,為那些在政治或經濟上沒有足夠能力的人創造拍攝電影的機會與可及性。
阿維許特別關注女性如何被呈現的政治性問題。不雅、淫穢、粗野、性奔放等等,這些負面字眼長久以來把女性形象綁得死死的,讓女性陷入了自我認同的困境——女性總是被塑造得「很美」。而阿維許的電影,不只是要對這一切提出反駁,更要強調女性的自由與享樂。在他的故事中,女性不是被動的,女性不一定是溫柔端莊,女性也可以是反叛角色,女性畫面可以是不美麗的(甚至可以是骯髒醜陋的、不被喜歡的),女性裸體不一定要美得像擺在美術館的陳列品,裸露也不一定就是主流電影中那樣唯美浪漫的,性不是羞恥的字眼,性不是秘密,性器官本身沒有罪惡。阿維許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作品,若是有些驚世駭俗,也絕對是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揮出的一記有力反擊。
然而,僅僅反抗是不夠的,還必須有效地扭轉——反轉或除去女性的「被注視性」——即看與被看的固定位置,反轉傳統好萊塢電影文化中女性作為被觀看的性客體,改變女性一直以來屬於被動的存在。阿維許在他的一次拾得影像實驗中對色情片重新檢視再創作,成功地反轉了女性角色的地位、客體與主體的關係,並且由原本的男性注視轉變成由女性導演呈現女性情慾。而當初被丟棄的膠卷因受雨水淋透,表層薄膜經過腐蝕之後,竟然脫落出了一襲絕美地令人幾乎窒息的顏色,宛如皮膚新生。
進入數位時代,阿維許也不例外,透過錄像提出了自己的觀察、擔憂和思索。虛擬世界中,人與人之間差異乍看不再那麼絕對,對於性別的超越也有著無限可能,可是,很快地諸多問題也跟著來了:科技強化後的人造世界變得冷酷無情;地球上各種污染指數上升;戰爭一觸即發;暴力藏在各個社會角落;虛擬外和虛擬內兩者界線逐漸走向模糊。阿維許從無邊無際的網路中採集素材,擷取電玩畫面、網路新聞片段、虛擬實境影片、以及電腦生成影像,雜揉出他的社會觀察報告,創造出奇異的人工合成影像空間。操作者、玩家、觀者、被操作者,所有界線越來越模糊,這不正反映了我們現代生活的寫照嗎?
阿維許的作品總是離不開生活,離不開對生活如實的觀察和反射。四十多年的跨度,阿維許還是如同最初始的自己,是個手持相機的民族誌學者,渾身上下充滿活生生的氣息,即使觸及死亡也是活生生的。他有時好奇,有時幽默,有時龐克、有時困惑、有時悲傷、有時浪漫,但更多的時候,他充滿不安。而他用實驗電影讓我們看見了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