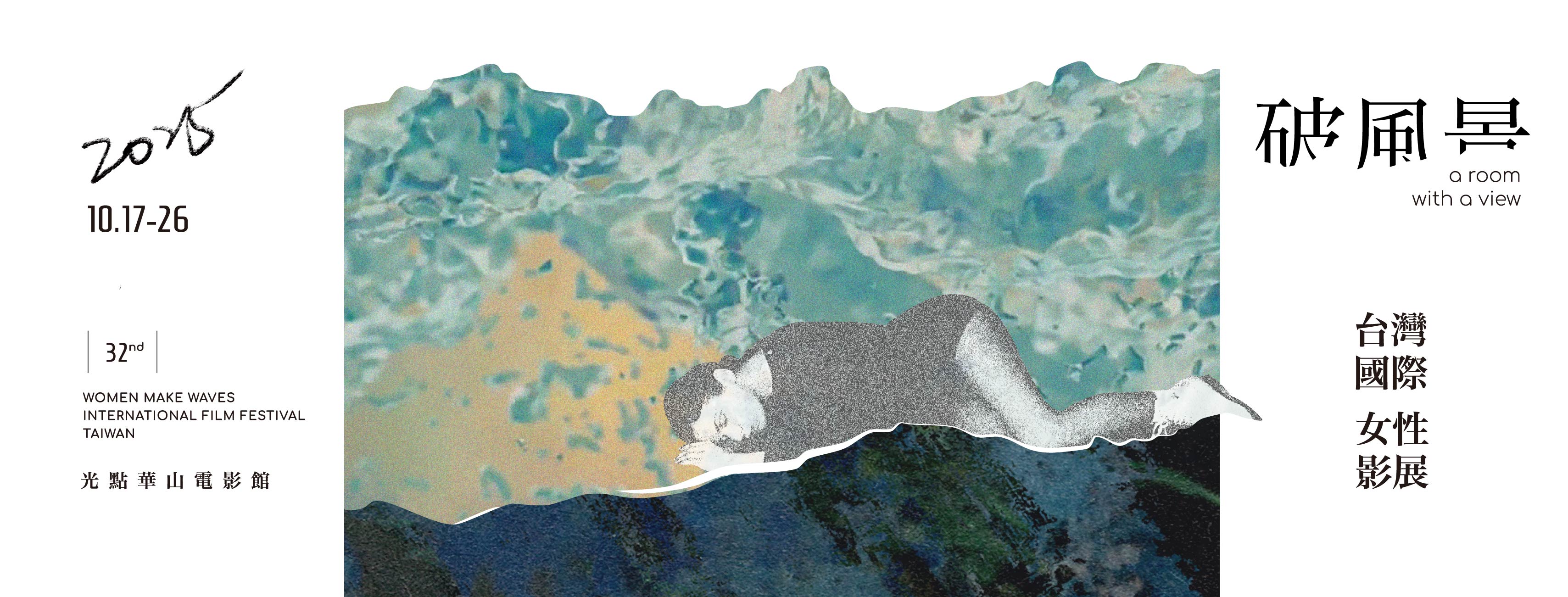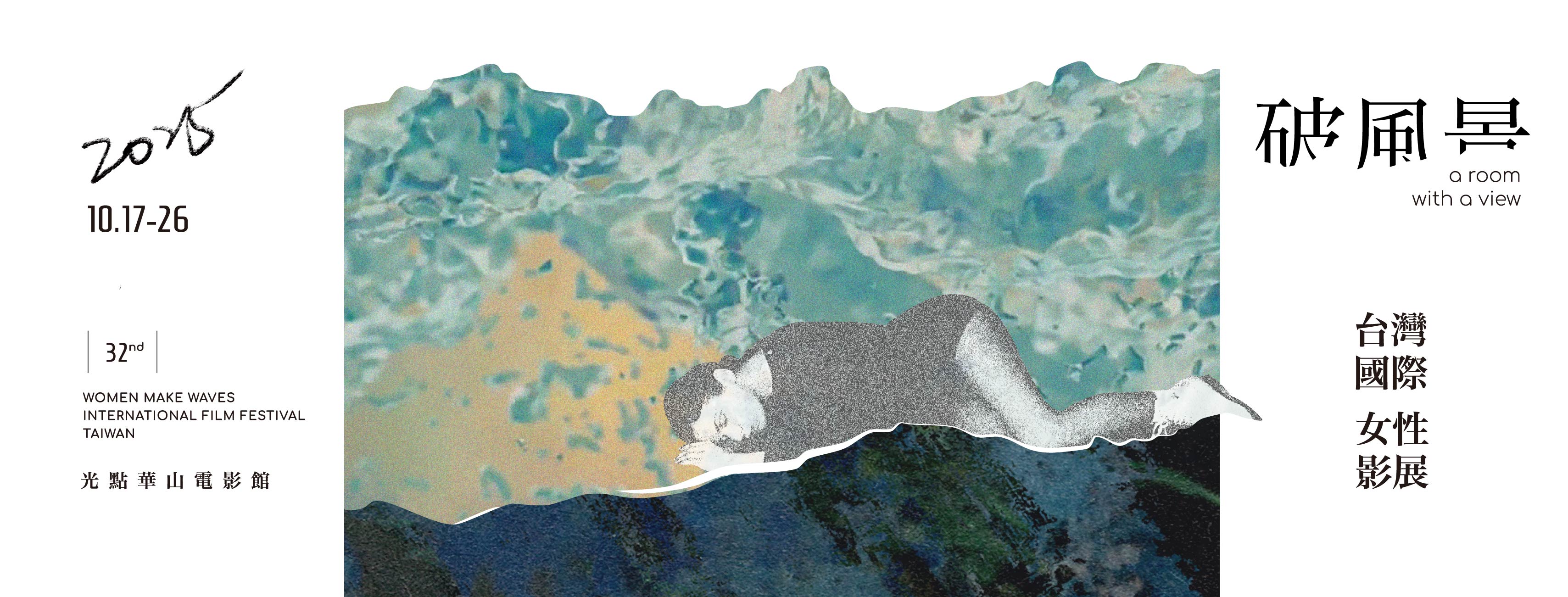歷史無法壓縮,她們不再缺席:在記憶的編碼中植入複音訊號
文/謝以萱
1975年十月的冰島,發生一件特別的事。超過九成女性選擇停止工作——不只是有薪職場,也包括無酬家務與照顧勞動。這場史無前例的全國女性集體「休日day off」,讓整個社會第一次看見:原來所謂的日常運作,是建立在她們無聲卻堅韌的支持之上。
五十年後,導演帕梅拉・霍根拿起攝影機,完成《那一天冰島靜止》。她的鏡頭帶領我們回看這場似乎行動劃一的罷工行動背後有多麼不容易,那不是「個人不去工作」的問題,而是一種得承擔被解僱的風險,逆著社會集體的慣性,必須向家人甚至自己解釋的激進決定。當鏡頭拉近,透過當年參與者的回憶重返歷史現場時,每個人的立場與選擇都不盡相同。影像裡的她們,有著不被大歷史簡化的堅持,當年尚年輕的她們,以不在場去製造一種巨大的存在感。如今這部影片,替冰島的女性留下了第二次在場的機會。
這不只是歷史的重述,更是一種補遺,一種對記憶與歷史敘事提出的質問:如果我不說,誰還記得?如果我記得,那是不是一種責任?這樣的責任,在艾蜜莉・姆克提欽的《不存在的從前從前》中有著充滿後座力的展現。
片名像是一則亙古神話的開場。但裡頭講述的,卻是最殘酷的現實:一個國家怎麼從地圖、從世人的記憶中消失?
2024年1月1日,因著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存在多年的領土爭端,阿爾察赫共和國遭亞塞拜然入侵後,正式從世界地圖上被抹去,片中主角也面臨迫害與流亡的命運。這部影片成了見證國家滅亡的影像遺書。導演不以聲嘶力竭的畫面來描繪創傷,她讓鏡頭停在揉麵的雙手、聽收音機的背影、母親抱起孩子的瞬間;她拍的不是戰場,而是被戰爭纏繞的四位阿爾察赫女子的日常——那是不斷消失中的生活證據,也是最堅實的抵抗。
這份抵抗,也來自導演自身的家族歷史。曾祖父母因種族屠殺被迫離散,父母移民美國,如今她帶著身孕,在拍片期間重新學習母語,只為了能將這段文化傳遞給尚未出生的孩子。攝影機成了延續記憶的工具,也是一種政治行動試圖探問:如果沒人記得,那一切是否曾經發生?
這是一場關於「如何被看見與記得」的辯證。當歷史不是由單一個人英雄式地寫下,而是由成千上萬個匿名的選擇層疊而成,我們要如何看見與記得?當記憶不再是線性,而是多重層次的沉積,我們是否能在層理裂隙中找到與自己連結的入口?有時,記憶與歷史的起點,不是某個年份或條約,而是在於某個人從照片裡看見了母親的年輕臉孔,或在泛黃的 VHS 錄影帶裡聽見了熟悉卻陌生的曲調。
在《女人世界》中,導演楊圓圓翻找的不是國家檔案,而是母親衣櫥裡留下的舞衣。這部歡快的影片是段文化尋根的旅程,也是翻玩影音檔案的恰恰舞步。她追隨著好萊塢的女性先鋒影人伍錦霞的腳蹤,來到舊金山唐人街,在這裡,她尋見一群華裔女性在築夢、謀生之間搖曳的身影。舞台上的歡笑背後是對種族邊界的沉默;被邊緣化的女性身體,是城市記憶中最容易被裁剪的畫面,因此導演以鏡頭記錄下那些無法言說的歷史餘波。
長期關注社會議題及邊緣群體的黛博拉・克雷格,與昂丁・拉雷和約格・福克勒共同執導的《敬!莎莉》則是以紀錄片作為載體的行動主義式運動。莎莉.吉爾哈特是美國1970、80年代女性主義和酷兒運動的先鋒,雖與哈維.米爾克並肩爭取同志權益卻少為人知。電影並不將莎莉簡化為一座形象固定的烈士紀念碑,她性格的多面向成為電影最真實的核心,電影透過訪談多位當年參與性別運動的女性,以私密的視角勾勒出莎莉充滿生命力、幽默感和溫度的人物性格。這是一段她們所共同走過的歷史,電影的製作也展現未竟的歷史如何可能接力敘事。《敬!莎莉》的製作幾乎仰賴小額群眾募資,這顯示了她的精神在當代社群中的力量,仍持續激勵新一代的行動者。
除了電影創作對邊陲歷史的重訪,我們也看見電影介入影音檔案,探問女性與身處多重邊緣的敘事位置可以是什麼,可以在哪裡?
多明妮克・卡布瑞拉的動人作品《堤的第五個鏡頭》,從影史經典克里斯・馬克《堤》的第五個鏡頭出發。導演的表親在這部完成於1962年的《堤》中驚見自己與家人的身影,遂引發這趟既是影史考究,又是家庭電影的追尋之旅。家人們共同看著投影出來的《堤》憶當年,從那小小的影格深掘出潛藏的情感與動能,這不只是對影像檔案、歷史詮釋的改寫,也不只是解構,亦是一種深層的跨時空對望與交會,鬆動原本單向的凝視,進而建構、延綿展開成多向度、眾聲喧嘩的對話。
視覺藝術家多拉・加西亞的《愛在革命蔓延時》則是對歷史政治和女性主體的一次直接召喚。她從馬克思共產主義革命家亞歷山卓・柯倫泰的思路軌跡出發,藉由她的書寫與檔案文件,看見酷兒與女性主義運動跨越時空、異地結盟的潛能。多拉・加西亞不試圖重現那已然逝去的左翼黃金年代,而是藉由私密的聚集、街頭的政治集會,從當代讀者、表演者、政治行動者的角度,把那段未竟之志帶進今日拉丁美洲正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運動者的肉身與聲音之中。這部電影像是一封從檔案室中撿拾遺落的革命情書,又或是一場遲來的政治召魂術。
這些多聲共存的集體力量,讓電影本身成為一場實驗性的辯證場域,而非封閉的歷史論述。這些作品重新召喚、鬆開原本幾近遺漏、僵固的敘事現場,開展出更多對話與感知的多向時空;藉由電影的創作,聲音與影像的部署,我們得以共同望見曾經被遺忘、被排除的身體經驗,共同體驗觀看位置上的重新佔領,也正因為那些非線性、斷裂破碎、模糊的身體經驗,使得另一種史觀、另一種在場方式得以趁隙而入。
謝以萱 HSIEH I-Hsuan
從事電影策展、評論與研究。關注當代亞洲電影與視覺藝術的辯證與實踐,以及電影放映如何成為開啟對話、撬動現實的空間。現為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新加坡影展選片人;亦為台灣影評人協會成員,《紀工報》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