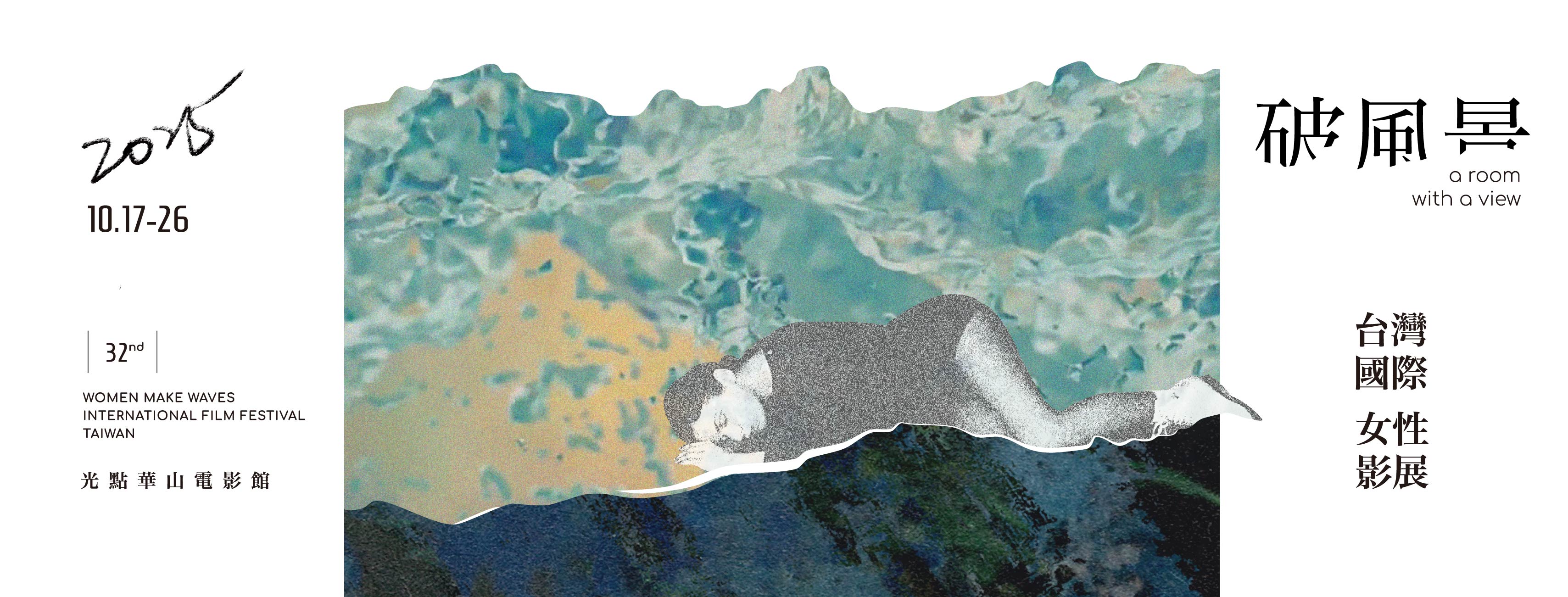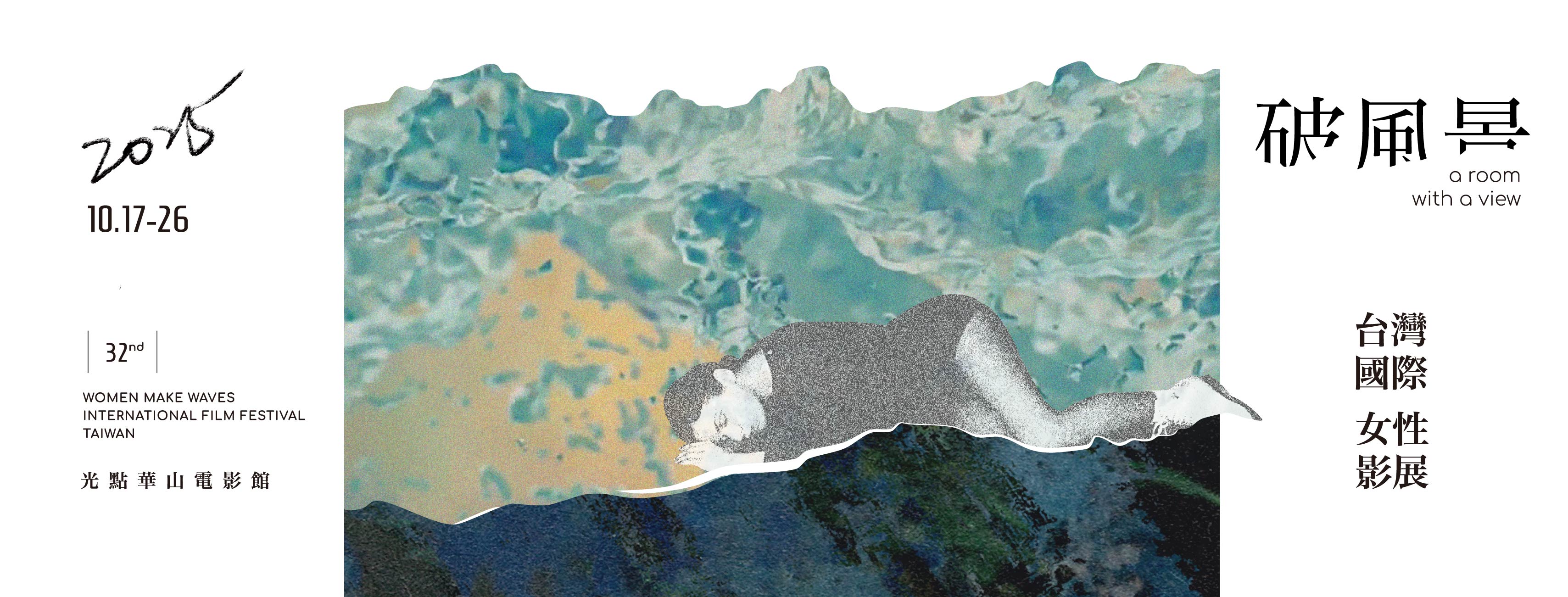存在、見證、執迷——香妲・艾克曼的感知電影
文/謝淳清
觀眾必須是真正的他者,電影不該是部吞噬吸納觀眾的機器。
這也是為何我的鏡頭藉由那樣的正面構圖或時間重組,去形成一種體感經驗。
觀眾不該忘記時間,不該被故事吞沒。
——香妲・艾克曼
艾克曼的電影,或許可以被概括為一種節制的影像存在形式,在此存在中,誘導的成份幾乎沒有,觀眾既無法順暢地消費劇情,亦難產生心理投射;其影像中的苦難,不是為了引發認同,而是要求觀眾去承擔其中的疏離、難耐甚至苦痛,去意識到那潛藏於生活處境裡,無從解釋卻又無法迴避的沉重。換句話說,觀看本身,不是擷取資訊,不是試圖佔據敘述及其主體位置,而是一種見證、一場倫理試煉,使那受壓抑的、無法說出口的,得以現身在場。如早期代表作《珍妮德爾曼》透過靜態長鏡頭,呈現女主角反覆的家務。電影從敘事工具轉變為感知場域,觀眾經歷那沒有戲劇化與解釋性,卻逼近崩潰的疲憊與消磨。沒有救援、無從安慰,觀眾在凝視中失語、承受。
《安娜的旅程》將這感受,延伸到一種孤絕的漂泊。片中,不斷離去的地景、無生氣的光線運用、對話的無效或冷漠,領觀眾隨導演安娜旅行,目睹她未完成的會面、不曾抵達的親密。即使敘事借用公路電影的結構,卻悖離此種類型片典型的內在重塑與救贖。觀看,受挫於安置感的未果、被終止的揭露,一如安娜的無歸屬。在她與母親的相聚中,柔情表面下是不起衝突的沉默。面對女兒一段同性愛戀的傾訴,母親僅是聆聽,沒有回應給出,彷彿烙下情感界線於無聲中。這道無法言說的裂痕,隱約對照著艾克曼與其母之間不可化解的代溝,源於後者的緘默:這位集中營倖存者,終生不願提及家族記憶,任由這道禁令將人孤立、封鎖。這或許也反映出何以在艾克曼的作品裡,關係的意義總是破碎,母親的空位幾乎在場,而她透過電影,創造出一種觀看與存在的交互建構。
《故鄉在彼方》為這建構,賦予純粹性。此片攝於艾克曼旅居台拉維夫期間。在這個爭議性的政治地帶,鏡頭沒有選擇激進主義式的題材,反而長時間定格拍攝窗外的一般住家與居民。艾克曼本人的畫外音,說著家族點滴、日常生活或是電話接聽。憶起小時候,母親不允許她到外面玩,導致她養成長時間凝視窗外的習慣,甚至陷入自我封閉。這個兒時的觀看行為和限制,成為這部片的視覺框架與原型,讓片中的觀看,不只等同於一種存在狀態,更在這無事發生的緩慢感中、非敘事的時間性裡,形成強烈的存在重量。視覺與聽覺、室內與室外之間的脫節,阻隔了對於現實地理意義的理解。「以色列究竟是應許之地,或只是一種新的流亡」——在這晦澀的彼方,敘述者是否抵達了自己的歷史、國族記憶、母親和創傷?
這種情感斷層的根植、彌合尋求的失落等母題,使艾克曼的作品潛藏著深刻的結構性悲傷。其文學改編作《愛的俘虜》、《奧邁耶的癡夢》,與其說是對普魯斯特與康拉德的文本詮釋,不如說是通過小說裡的文化與歷史,再次演繹她的核心命題:對於一種無法連結,卻又無能撤回的情感的執迷。男演員史坦尼斯萊斯・莫哈(Stanislas MERHAR)分別在兩部片中飾演的「執迷者」,有如鏡像的兩方:一是被佔有慾所俘虜的中產階級、一是迷失於殖民幻象的輸家。女主角們被賦予相較於原著更大的力量,不是出於行使權力,而是以不可穿透性與抗拒,對父權社會的凝視、文明話語的馴化,進行逆襲。兩部片自開場即分別以失衡視角、異質性元素,解構文學心理描述的濃密。此外,《愛的俘虜》自希區考克《迷魂記》摘取靈感,用以營造迷惑與象徵,是值得一提的插曲。
如何存在、如何彌補情感,是艾克曼作品一貫的探究。受地下電影、行為藝術、新浪潮等影響,她於1970年代的母語期電影如《轟掉我的家鄉》、《房間》、《我你他她》,即已觸及存在的不確定性、親密關係的困局。1980年代後,兩部以青春為主題的電視委託《我餓,我冷》、《1960年代末一名布魯塞爾少女的肖像》,刻畫少女的城市晃遊。前者以近乎嬉戲的調性,將飢寒感受作為身體與世界的交流,召喚對自由與親密的渴求;後者以半自傳語境與手持攝影回應新浪潮,表現68世代,以及困於身體、情感裡的寂寞。而同樣以流動為基調的《長夜漫漫》,讓人聯想起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舞作。身體成為情緒、欲望的事件,而非角色代言;一幕幕感官細節交織的情境,不倚賴敘事主軸,卻貫穿以情感的張力,在愛戀之間迴盪、往復。
身體的停佇、鏡頭的逡巡、語言的重複、主題的執著等特質,瀰漫於艾克曼電影的形式與內容。短片《在那天⋯⋯》沿用《房間》的空間循環拍攝,佐以個人旁白的緊湊變奏,返身書寫電影與記憶的傷口。就像她曾以文字揭露:「我是個精神上反覆糾結的人。這點我清楚。有時甚至因為擋不住糾結而自我厭倦。我的人生漫長,因而是場漫長的反覆糾結」。艾克曼在其電影的重述中,令生命的遲疑與拖磨顯露,觀看失去安頓,無語的時間化成不止息的等待,以一種近乎哀悼的節奏。
補記:此單元尚包含一部以艾克曼及其作品為主題的紀錄片《暴風中的無名風景(致香妲・艾克曼的兩封信)》。此片採用非常規的敘事方式,重訪艾克曼遺作《非家庭電影》及《故鄉在彼方》中的場景,以呈現當時被遺漏的面向,藉此讓這部紀念艾克曼之作,不停留於致敬,更延伸、轉化為一場對於當代政治、倫理困境,以及影像責任之間的深刻對話。
謝淳清 HSIEH Chwenching
畢業於日本東京多摩美術大學,並於法國公立東巴黎大學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專攻實驗電影、身體論述、性別研究、表演藝術。從事影像創作、寫作、口筆譯。現為世新大學廣電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