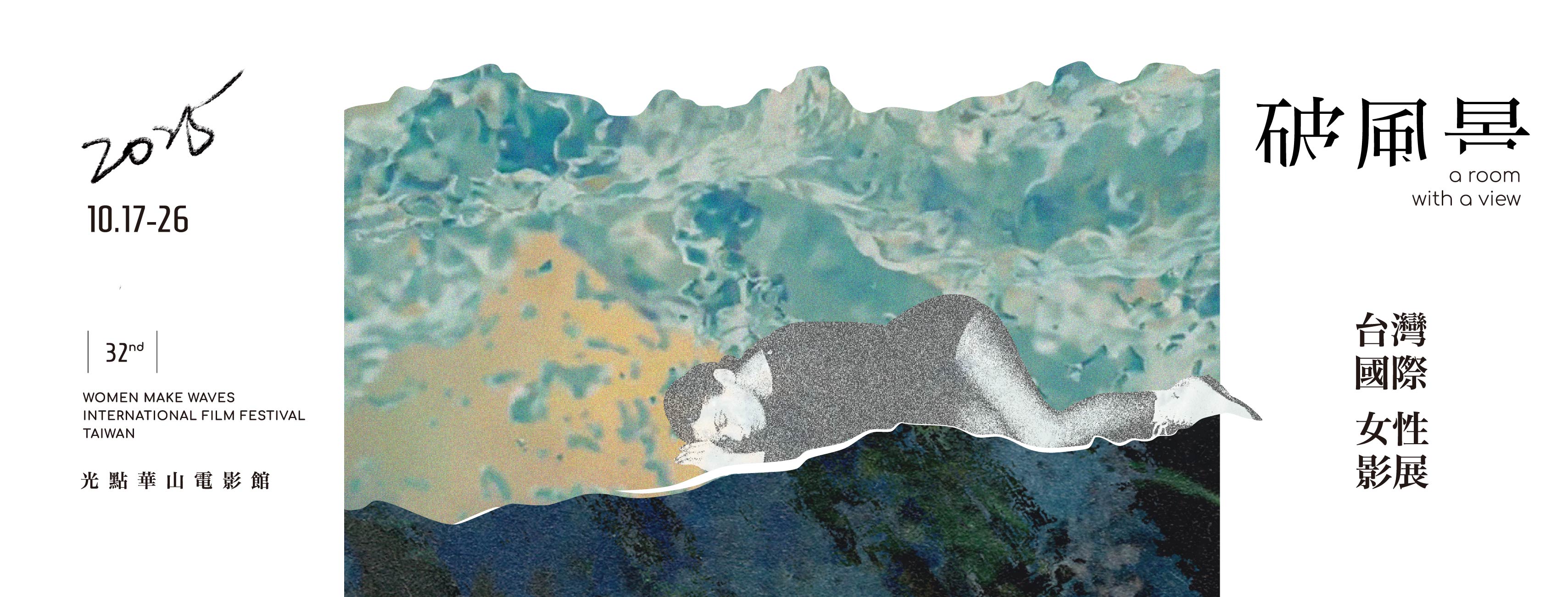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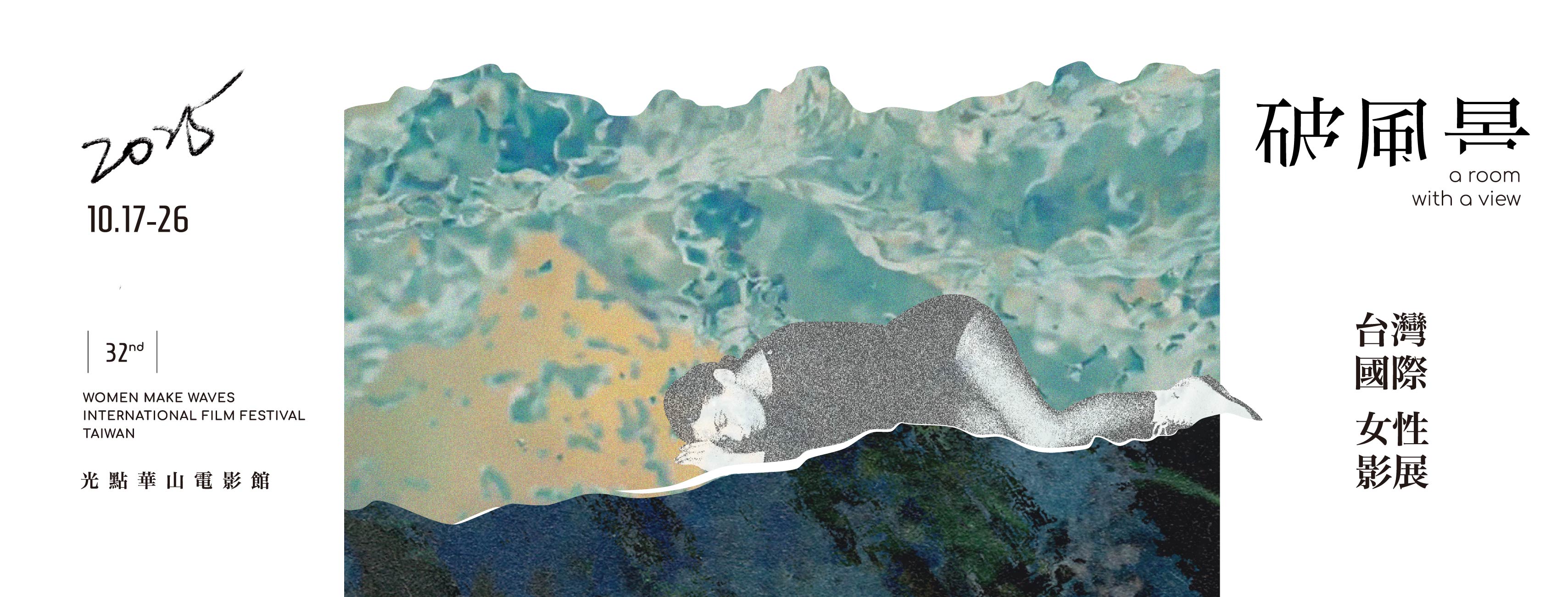
文:林巧棠 原文刊載於釀電影 先說,本文題目是出自作家林佑軒在某次作品討論會上的發言。大意是:「即使某篇小說的題材都很常見,只要處理得好,老梗也能長得鬱鬱蔥蔥。」我就借來一用了,在此致謝。 如果「哭笑臉」這個 emoji 有一部代表作,大概就是《多莉安的幸福人生》這樣吧。女主角多莉安有美滿家庭,老公帥氣有為,兩個兒子健康可愛。乍看人生勝利組的她,隨著劇情推展,人生拼圖開始一塊塊碎裂。 這雖然是處理女性獨立自主常見的敘事方法,但全片總在令人意想不到之處出現轉折,讓我看得很開心。 在角色塑造上,多莉安是獸醫,冷靜理性正是她的工作需要。從多莉安的媽媽對女兒的批評可以看出,這樣的個性是先天因素加上後天養成的。媽媽對她說,「你有傑隆,真好運,但你卻不知足。你如果不是這麼陰沈又固執,你跟傑隆的關係就不會這樣。」當時正在和多莉安爸爸鬧離婚的媽媽,以為女兒的幸福人生一如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完美。 離婚的起因是媽媽疑似有了新男友,高齡六十八的爸爸受不了這個打擊,把媽媽趕出家門。身為女兒的多莉安好像不得不參與這場戰爭,她幫忙傳話、幫忙回不了家的媽媽拿衣服、讓媽媽借住在自己家裡(距離忽然拉近,導致母女二人衝突升高)。但是她又沒辦法真正調停爸媽的衝突。多莉安一直說「我不想介入,你們自己去談。」電影前半的鋪陳,會令人摸不清多莉安到底是太理性還是冷漠,也難怪爸爸要責怪刻意中立的女兒:「你到底站在哪一邊?!」 《多莉安的幸福人生》劇照/女性影展 要我說,也許她只是沒有力氣站在任何一邊。多莉安疑似乳癌、先生和同事好像在搞曖昧、大兒子在校表現不佳、爸媽又鬧離婚,多頭馬車的她瀕臨崩潰邊緣。 劇情走到中間,多莉安跟先生傑隆長久以來的心結終於揭曉:傑隆和同事其實早就外遇過了。雖然戀情已經結束,但似乎並沒有人想要避嫌,他們還是在同一個地方工作。觀眾看到這裡會更清楚地發覺,片名的「幸福」二字,真的是一個大大的反諷,也會更明白多莉安的冷靜自持,其實已經是她努力隱忍的結果。 不過,雖然導演處理的是中產階級少婦的困境,本片並沒有因而沈重。相反地,有兩大元素讓整部片的氛圍提升到幽默輕鬆的層次:女主角的演技,和手術中的動物。 先說女主角吧。飾演多莉安的女演員 Kim Snauwaert 簡直是尷尬笑之王,在一場多莉安和麗絲貝(傑隆的同事,也是曾經外遇的對象)同桌吃飯的戲中,麗絲貝幾度向多莉安裝熟賣好,多莉安臉上的尷尬笑堪稱一絕。多莉安的個性正經,但就是因為這樣,在緊張嚴肅的地方,她的笑容跟表情才更有力道,更加說明了現實人生就是這樣──即使那個上過你老公的賤人就坐在你旁邊,該笑的時候還是得笑。 《多莉安的幸福人生》劇照/女性影展 再來是動物的部分。我一直認為讓多莉安擔任獸醫,是一個絕妙的安排。動物的肢體,尤其是各種側拍或直拍動物頭臉四肢的鏡頭,為電影畫面增添了幾分荒謬的感覺。而導演更是巧妙地將人際的衝突,以有形的傷口──獸醫開刀的場景──來呈現。當多莉安爸爸跟女兒談論媽媽的外遇時,多莉安正在為一隻狗切除腫瘤。開刀的場面是冷靜的,時不時穿插「給我止血棉」這樣的句子,但手下的世界卻是血淋淋的,彷彿他們被撕裂的家庭關係。 電影後半,多莉安在手術途中暫離,去處理爸媽的世紀大吵(再不過去房子就要被拆了),沒想到她才剛回手術台,狗居然醒了,飼主超級崩潰。當她被驚慌逃走的狗狠狠咬了一口之後,她所努力維持的假象也隨之潰散。這裡可說是全片最重要的轉折點。 回家之後,多莉安一邊練跆拳道,一邊和先生坦白:「我和客戶上床了,還有我生病了。」電影至今埋下的幾段衝突終於爆發,多莉安對著鏡子一拳一拳揮出去,雖然對話的對象是先生,但對鏡揮拳的她,彷彿也在打碎過去的自己。 《多莉安的幸福人生》劇照/女性影展 幾場重要的動物手術串起了劇情線。最後一場經典的手術戲,是多莉安為母馬接生的戲。電影前半鋪陳她的診所專門醫治家犬,有時還有鳥。多莉安怕馬,因為她曾經被馬弄傷過,耳上還留了疤。但診所卻老是接到爸爸的老客戶打來的電話,要求她去看看他家懷孕的馬。多莉安一再回絕,堅持自己只醫小型動物。但是,當她與傑隆正式決裂之後,她又接到了老客戶的電話──母馬要生了!情況很不樂觀。這次她沒有推辭,不管身上還穿著昨夜的禮服,立刻套上長靴飛奔而去。 這是最棘手的案例,最多血多水的場景,也是多莉安成長的關鍵。 接生完畢後,老客戶問她價錢,多莉安卻說不必了。那場戲就停在這裡,對我來說是最意義具足的收尾,因為她已經獲得了比金錢更重要的東西。本片要處理的問題,到這裏也已經差不多處理完畢了。 《多莉安的幸福人生》海報/IMDb 不過,最後還有一個小問題沒有解答,也讓我有點疑惑,就是多莉安自己外遇的問題。當她和先生坦白一切之後,雖然先生立刻關注她的腫瘤,但外遇問題是不可能就這樣被擱置的,而電影在接下來的部分卻沒有處理這個問題。 然而,作為一部女性獨立成長的電影,這部片表現得已經很不錯了。片尾,失去乳房的多莉安剪了短髮,搬離原先的家,展開新人生的同時仍和先生一起養育兩個兒子。雖然剪短髮與離家都是敘述女性自立的電影中常見的手法,但在這部片裡這兩個元素確實有達到應有的效果。短髮讓她看起來煥然一新,也暗示了她從抗拒治療到接受治療的過程。而離家也是劇情上必然的走向,多莉安與先生分居之後二人的關係反而變好了。 本片的結尾真實卻不沈重,以幽默輕巧的方式,處理人生勝利組中年婦女的失控人生。天翻地覆之後,人生還是繼續,也還會繼續。
文:(OR)伊森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網 今年台北電影節「未來之光」單元中,有一部智利女導演多明嘉索朵瑪悠(Dominga Sotomayor)執導的《索非亞的夏天》,講述即將結束獨裁政權的智利1990年夏天,16歲的索非亞居住在一層不變的公社中,友情、愛情,在賀爾蒙與樹叢之間,等待著她的,是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 無獨有偶,今年台灣女性國際影展上也有一部瑞典女性導演安娜艾朋(Anna Eborn)的紀錄片《愛在德涅斯特河畔》,講述五位生活在摩爾多瓦、烏克蘭國境之間,被世人淡忘的德涅斯特少年。 16歲正值豆蔻年華的譚雅,總是圍繞於身邊的四位少男,穿梭於德涅斯特河畔,遊走在蘇維埃仍舊飄動的國境上。深受這5名少男少女吸引的安娜艾朋,決定用16釐米的膠卷,記錄下一個違背21世紀全球化、不被聯合國認可的辟世遺境,與一個恣意妄為的夏天。 愛在德涅斯特河畔,一段停止成長的青春。 安娜艾朋一向對於存在於時空之外的社區、群體有著濃厚的興趣;這種不合時宜、彷彿被世人淡忘的生活模式,深深吸引著她。2013年的電影《原夢山脊》(Pine Ridge),安娜艾朋將鏡頭深入美國南達科他州松樹脊印地安保留區,試圖用獨特的敘事與拍攝手法,改寫世人對這塊貧瘠之地的刻板印象,甚至與烏克蘭一名老婦人分享著瑞典方言。 對觀眾而言,無論是《原夢山脊》、還是《愛在德涅斯特河畔》,都彷彿像是一部「虛構」作品。原因多半在於安娜艾朋所選取與拍攝的對象,多半鮮少人知且處於社會的邊緣。如德涅斯特,它既像是舊蘇維埃體制治下的封建之地,劇中女主角譚雅的五年級弟弟,甚至加入了軍校。它同時猶如脫離軌道、獨自停靠在廢棄軌道上的列車,隨著時間與空間的專換,逐漸沒入世人的眼底。 當安娜艾朋以16釐米手持攝影,如泛黃底片般深入挖掘出少女譚雅等人的浮光片羽時,時間彷彿禁止了,停留在20世紀70年代。甚至在歌曲的選用上,導演都刻意營造出這種遺世孤立、時空錯亂的感覺。 Ph 今天的德涅斯特,國旗上仍揮舞著錘子與鐮刀,甚至在譚雅生活的不遠處,仍有俄軍駐防,觀眾未必能清楚知道德涅斯特的身世,如同那一群孩子們的身世。在時間與歷史的沖刷之下,德涅斯特本身正洋溢著一份不被認同的哀愁。 經典開場與夢境般的攝影。 《愛在德涅斯特河畔》開場,少女譚雅的第一句台詞:「所以你到底愛不愛我」?多少令人聯想起洛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的《瑞典愛情故事》,兩小無猜的少男少女,在明媚田園間眉目傳情,談著青澀的戀愛。電影的頭一幕,夏日的河畔,德涅斯特已美的令人遺忘了它的身世。 瞬時間,我們幾乎遺忘了這是一部有關於德涅斯特的紀錄片;那些青澀的愛戀夏日足跡,更像是雋永的愛情電影。一切貌似如此和諧,如多夢般的仲夏夜;鏡頭跟隨著這群少男少女走過四季,他們彷彿未曾被時代浸淫,只是緊密的貼著彼此,直至分道揚鑣的時刻,哀傷在帽緣下打轉,他們仍高聲哼著歌。
文:吳思恩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網 在21世紀這個我們以為平權進程已經有了一定成果的年代,在電影圈這個我們認為藝術人應有更崇高與前衛思想的場域,綜觀近幾年各大影展的得獎者,除了最佳女主角、女配角等以性別為分野的獎項之外,其他獎項少有女性得獎者。是女性不夠優秀嗎?還是在這個場域女性已缺席了太久? 電影界長期受男性宰制的狀況仍未改善,而這個問題在1970年代黛芬賽赫意(Delphine Seyrig)執導的《美麗噤聲》就已被血淋淋的掀開。 黛芬賽赫意在1975、1976年訪問了美國、法國二十多位一線女明星,她們有些抽著菸,有的坐在沙發,有的倚在床上,彷彿好朋友之間的私密談話,如此自在,卻訴說著這個讓他們如此光鮮而緊縛的電影界。 如果是男性,她們會成為演員嗎?她們在鏡頭下是個人還是商品?她們能扮演的角色被侷限在男性電影從業者希望的模樣。如果是生為男性她們會嘗試任何社會認為只有男性才能做的事情,它看起來危險、過於艱難,甚至冒犯了「常規」。 片中許多人提到了她們在劇本中可以呈現的樣子,她們是妻子、母親、女兒,一切必要存在於一個故事架構的角色。除此之外,她們被塑造的形象孤立而冰冷,她們會為了獲得男人的寵愛而戰,多數人在職業生涯中幾乎沒有與其他女演員對戲的橋段,女人間的友情對於以男性為主的劇情沒有起到支撐的作用而被捨棄,甚至當女人們的友情親暱至一個程度將引起男性的懼怕而被修改。 常有人稱茱麗葉畢諾許(Juliette Binoche)是影壇長青樹,她所主演的電影中常有情慾戲碼,她的身體彷彿與慾望緊緊貼合,不因年齡的增加而褪色,但多數女性卻會因為年齡而被限縮了可以飾演的角色,因為她們被當作性產物,而非她們能夠擁有性所帶來的一切美麗,有時候40歲的女人甚至被排除在劇本之外,年華老去的女人就像老車一般被丟棄,但年齡對男性代表的卻是成熟與權力正當性的增加。 導演的功能應是引導演員更深入地呈現劇本中的情感,但他們之間卻沒有互信關係,多數女演員並沒有在電影中呈現自己,因為那並不重要,她們被要求的只是呈現導演想要的狀態,多數是歇斯底里、瘋狂的,電影是為了打開人們看世界的眼睛,但在一個與世界現況如此違背的場域,如何能呈現多元的今日。當導演、投資者、劇作家都是男性的時候,他們眼裡的社會變得單一,他們打造出了他們以為的世界。 《美麗噤聲》的英文片名是《Be Pretty and Shut Up!》,即是傳統上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這部紀錄片卻是二十幾位女星對著鏡頭侃侃而談,甚至可以說是控訴,無須美麗只需做自己的樣子,無須噤聲因為世界急須改變。
文/米恩 NPOst 特約記者 原文刊載於NPOst 「有性別,無差別?」專題綜觀國內外,距離性別平權的理想社會之遠近。在現代看似進步之下,仍有多少形於外、內裡腐壞之事正持續發生?又有哪些,是女力力圖解放的可循路徑? 「無所不在的性暴力」為此專題的主題一,不論是眾人眼中的弱勢族群女性或是新時代女性,性暴力的威脅仍隨侍在側,無差別的殺戮女性的身體、精神、尊嚴,還有未來。《倖存的女孩》為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開幕片,影展時間為 10 月 4 日至 10 月 13 日。 戰爭帶來集體的傷痛,而「性暴力」又時常成為對付女性的武器,如紋身般,烙印其身,一生無法抹去。《倖存的女孩》是亞茲迪族女孩——娜迪雅的故事,她所經歷的如是,而她需要一遍一遍說出真相。傷口從未癒合,卻仍需不斷被揭開。 娜迪雅被「 ISIS 伊斯蘭國」恐怖份子擄掠、虐待、強暴、輪姦、販賣。她深愛的的家人、族人遭到「種族滅絕」,男人被集體槍決,孩子被強行帶走洗腦成為好戰份子,年長的女人被殺死丟在亂葬崗,年輕的女人淪為性奴,最小的女孩甚至只有 10 到 12 歲。 沒有選擇的戰爭 成為「沒用的人」 一切發生在 2014 年 8 月,伊拉克北部辛賈爾(Sinjar)地區的克邱(Kocho)村莊 —— 一個亞茲迪人(Yazidi)居住的簡樸村落。那時娜迪雅只有 21 歲,青春、自由、夢想才剛要展開。 「身為女性,我很不想把遭遇公諸於世。我更希望我沒經歷過,不必告訴別人。」娜迪雅不希望別人眼中的自己是伊斯蘭國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她有自己想要的人生,她希望別人眼中的自己,是個優秀的裁縫師、運動員、學生、化妝師,或是農夫。 但如今這些不太可能實現了。在伊斯蘭國的罪行未被審判前,娜迪雅的肩上,不僅背負了個人的傷痛,還有亞茲迪族人集體的苦難和命運。 就像難民營裡的男孩,在薄暮下把屠殺唱作一首悲傷哀涼的歌:「我們是你的敵人嗎?你帶走了我們的母親,我們都被俘虜,你讓我們成了孤兒。我們有數以千計的老人死在山上,我們無法將他們下葬……」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娜迪雅所屬的亞茲迪人遭到屠殺,是因為他們的信仰。「亞茲迪教」是個古老的宗教,沒有《聖經》、《可蘭經》那樣的聖書,靠著代代人的口耳相傳延續宗教故事。也正因此,亞茲迪人被伊斯蘭國認為是「骯髒的不信神者」、「崇拜魔鬼」,成為恐怖份子亟欲「清洗」的對象。 亞茲迪人在全世界大概只有 100 萬人,遭到種族滅絕之後,流離失所的亞茲迪人,在全球 6 千萬的難民中,僅佔 50 萬。或許是身為少數中的少數,他們在這場浩劫中被不斷放棄和背叛。先是承諾保護他們的庫德族「敢死隊」,然後是美軍,接著是曾經關係緊密的遜尼派村莊的鄰居、老師、朋友。 在伊斯蘭國位於伊拉克的首都摩蘇爾,當亞茲迪女性被當做性奴販賣,生活在那的人選擇視若無睹,不提供任何幫助。在「大屠殺」發生之後,亞茲迪人沒得到國際支援,聯合國亦未優先處理亞茲迪的難民問題。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甚至從未在國際法庭為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受到審判。 這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不只改變了娜迪雅的外在生活,也徹底改變她內裡所有的一切,「我覺得自己是個沒用的人,因為我莫名其妙就淪為性奴。」 關於沉默 這些娜迪雅悲慟、憤怒和控訴的緣由,也是所有受害的亞茲迪女性的,甚至是遍布全球,在戰爭中承受性暴力的成千上萬個女性的。恐怖分子是直接的加害者,但那些保持沉默的政客、官僚、軍隊、乃至平民,又何嘗不是間接的加害者? 沉默的旁觀者也許有著各式各樣的理由,他們是沉默的多數。而在話語權利的另一端,還有沉默的少數人,他們往往是受害者。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例如性侵受害者,她們大多不敢報警,羞於將真相公之於眾。一方面,暴力本身就等同於噤聲,另一方面,社會結構讓性侵受害者懼怕他人眼光、怕得不到理解、怕正義無法伸張。於是,她們選擇沉默。 對於亞茲迪的女孩來說,她們的宗教禁止婚前性行為。以暴力行為奪走童真,不僅摧殘她們的身體,也摧毀她們的信念。恐怖分子更是一再羞辱她們的信仰,逼她們改宗,加上家人的死亡和種族滅絕,這些女孩身陷於多重壓迫。 她們沒有像男性族人一樣在戰爭中立刻死亡,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受到慢性地折磨、摧毀、損耗、屠殺、消音。 但娜迪雅拒絕沉默。 她的律師艾瑪在《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一書的推薦序中表示,娜迪雅反抗他人賦予的標籤 —— 孤兒、強姦受害者、奴隸、難民,而是反過來創造新身份 —— 生還者、亞茲迪領導人、女權倡議者、聯合國親善大使、新銳作家。 娜迪雅獲救後,原本在德國和其他女孩一起接受心理治療,但這讓她更加痛苦。顯然地,對娜迪雅來說,化解悲傷的最好辦法是將之淬煉成反抗的力量。 但反抗的過程也是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深淵,一次又一次回憶那段難以直視的經歷,一次又一次在公眾面前以冷靜有力之姿訴說真相後,娜迪雅轉過身,面對自身的潰敗,而重建緩慢到像是沒有任何進展,在支離破碎中,漸漸拾起尊嚴和勇氣。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在娜迪雅於國際上不斷的發聲後,聯合國安理於 2017 年 9 月核准決議案 —— 針對伊斯蘭國對亞茲迪人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展開調查。 她不僅告訴了世人他們所遭受的苦難,也證明了少數族群發聲的價值、弱勢生存的權利,以及身為倖存女性的力量。 旁觀他人之痛苦,二度「強暴」如影隨形 整部電影非常克制,沒有刻意強調娜迪雅成為性奴時的細節,而是以紀錄片的形式,記錄娜迪雅在世界各地接受採訪、在聯合國作證、去難民營鼓勵族人等等情景。 「他們是怎麼強姦你的?」、「你對他們說『不』了嗎?」、「你想做什麼?」、「你出名了,這對你有何意義?」娜迪雅無疑是堅強而勇敢的,但當她面對這些問題,她顫抖地攥著手上的一根白線,反覆纏繞、勒緊,流下眼淚也無能為力。 當人們旁觀他人之痛苦時往往欠缺理解,或者說是尊重。娜迪雅在影片中自述,她說這些問題根本不該被問到,她更想被問到的是:「那些女孩的命運如何?」、「難民營的族人情況如何?」、「要怎樣為亞茲迪族爭取權益?」、「如何避免女人成為戰爭的受害者?」 每個尖銳刺人的問題,在獵奇眼光、厭女的普世情節之中,是娜迪雅選擇站出來必經的「鞭打」。事實上,這是性侵受害者都會面對的問題,不論階級、種族、身份、地位。 圖/Akshay Paatil@ unsplash 在美國明尼蘇達,地方報 Star Tribune 採訪了多名受害女性,並在 2018 年 7 月刊載長篇報導〈When rape is reported and nothing happens〉,警方冷漠地讓受害者鉅細彌遺地還原事發經過,在此之後,司法體系則怠忽職守、放棄追訴。 「我覺得我才是那個被調查的人。」「我覺得我被責備了,他並不信任我。」「我覺得我不該報案。」她們在報導中這麼說著。 人們提問,甚至安慰的方式,都可能造成性侵受害者的二度、甚至數度傷害。讓她們不斷回憶那些受害的經過,彷彿讓所有事情一再重演,那些屈辱、不堪、痛苦,每一秒都是煎熬。即使娜迪雅是主動站出來的那個人,也不代表她樂意掏出心底最深的苦難。 無以名狀的敵人 倖存者之戰 強暴屠殺了女性的身體、精神、尊嚴,還有未來。 娜迪雅在書中說自己第一次被恐怖分子強暴時,她並沒有像其他女孩一樣反抗和拒絕,她只是閉著眼,希望一切趕緊結束。「我不像她們那麼勇敢。」娜迪雅想這麼對別人說,但她擔心別人會如何看她。她自覺,當人們談到亞茲迪人的種族滅絕時,似乎只對亞茲迪女孩遭受性侵感興趣,想要聽激烈奮戰的故事。那如果被性侵的女孩沒有激烈反抗呢? 在非戰爭的性侵事件中,也常見這些對女性的提問——為什麼要在深夜出門?為什麼要穿著暴露?為什麼和這些男人在一起?為什麼沒有斬釘截鐵的反抗?為什麼案發後沒有立刻報警?你在猶豫什麼?你是否有所隱瞞?還是你另有所圖? 那些灼灼的目光和拷問,再一次將性侵受害者擊碎。 如果你還記得房思琪。年幼的女孩被老師誘姦,卻在這個世界求助無門,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在網路上求助,卻再一次被成人世界的殘忍無情碾壓。強姦絕對是一種直接暴力,但非直接的暴力文化同時也滲透在日常生活中,這使性侵受害者處於一種結構性的暴力之中。 強暴,更是另一種屠殺。林奕含在接受採訪時曾說:「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房思琪這樣的女孩在忍受著折磨,也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女性在性暴力中沉默。但娜迪雅告訴我們,仍有上千名亞茲迪女性被囚困在伊斯蘭國。 她們被當做戰利品,被使用、轉賣、贈送,她們是戰爭中男性權利最赤裸的延伸。人類歷史上的數次種族大屠殺,亞美尼亞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盧安達大屠殺等等,女性都無一例外地被強暴。 娜迪雅是這場屠殺的倖存者,很難說倖存和幸運是否存在著關聯,但至少倖存者還有機會去控訴伊斯蘭國的罪行,去為族人爭取國際上的援助,去期待有朝一日家園的重建。 娜迪雅很堅定。即便恐怖分子持續對她發出死亡威脅,即便家園早已成為廢墟,即便家人死亡、族人顛沛流離,即便自小看到大的文化已然支離破碎,即便她終究無法成為那個她想成為的平凡、自足、幸福的村莊女孩。 但倖存者仍要戰鬥。
文/Chen Si-yu 原文刊載於The News Lens Midnight nurtures chaos, human desires, crimes, and evil roots. Unarming one’s protective mask, midnight reveals the kind of good and evil that’s much closer to the true self. There’s no better time than midnight to stage a wild act roaring against the world. Midnight Tod (2019) opens with a scene of robbery and cuts immediately to Hao (Yu Shen-hung) who’s riding the bus alone. Having just been fired from the hair salon, Hao takes all his belongings and moves in with Tod (Chang Chih-han), whom he had only met once before. Tod, although annoyed at Hao’s unreasonable move, allows him to stay and the two develop an unexpected relationship. Photo Credit: Midnight Tod / Women Make Waves Film Festival Taiwan "If you can have sex with a dog, which breed would you choose? Husky or Golden Retriever?" When Director Wang Yi-ling was still a film student, her short film Towards the Sun (2016) was shortlisted for Cannes Film Festival’s student competition Cinéfondation. Wang is not unfamiliar with perfecting the chemistry between two intimate characters in her previous film. She again crafts a similar duo dynamic in Midnight Tod with two main characters who have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but share similar fates: The rash, rebellious Hao and the soft-spoken painter Tao are both deeply discontent with life. The screenplay reveals both vividly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lies their slowly changing relationships: An energetic, curious husky rushes into a mild golden retriever’s home – one can only imagine the chaos. Ironically, despite being a central character, Hao’s name is never mention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film; only Tod’s name is magnified in the film title and the viewer finds out its significance through gradual revelations. “Does it make any difference?” Hao asks Tao. It’s also a question the director throws at the audience. Photo Credit: Midnight Tod / Women Make Waves Film Festival Taiwan What does it matter if we make love in the same bed? What does it matter if we buy a plane ticket to France today? What does it matter if we believe in a $3000 telescope that can allegedly look into the future? Hao’s matter-of-fact attitude accentuates Tao’s indecisiveness, reflecting how we confine ourselves with various boundaries. Wang skillfully captures the love between two gay men, and yet develops and layers their interactions into something beyond love – a kind of co-dependence above friendship. Processed in black and white, the film’s monotone highlights the shadow and loneliness on the streets at night, echoing Tod’s charcoal drawings of the midnight streets. From his black-and-white daily life to the foreign streets drawn under his pen, is Tao unconsciously drawing his desire for the future? Do we repress our true desire while living in a monotone world?
文:孟啟融 原文刊載於LEZS女人國 《女人就是女人》,依據真人真事改編。由費20年重建人生後的宋紫洳,及彷若夢了16年性別錯置的夢中人趙凌風,兩人生命故事交織而成。 共享時空的兩人,走著非全然平行的故事線。譜就的,是世代間、橫跨家庭及教育場域間,甚至是不同階段的,跨性別者的多面向生命圖景。 本片以出身保守基督教家庭,更身處基督教體系高中的趙凌風,捕捉尚處於形塑性別認同階段的跨性別青年,所面臨來自家庭、校園、社會的種種壓迫及不友善。成績優秀、溫良恭儉、前途光明等等符合社會期待的特質,從來就不等於身心靈得以自在舒展,因為它本不是代表自我的一切價值所在,甚至反而可能成為困阻;不僅是自我探尋的困阻,更多是對於那些施加非必要預設期待的旁人。除了呈現於家庭教育、同儕老師、校園空間、服儀規範等層面中對性少數的排斥與壓迫外,本片亦以象徵手法,表現生理、心理性別認同出現差異時的自我懷疑、賤斥,最終與傷痕累累的過去共存,並嘗試找出自己最舒適的存活方式的艱辛過程。 宋紫洳所呈現,則是跨性別者隨生命經驗積累不同,所可能面臨不同面向的生活困境。已然完成變性手術,並嘗試穩定經營三人家庭的宋紫洳,考驗她的並不是自我認同動搖的掙扎磨難;亦不是當代職場對性少數的不友善對待,而是二元性別霸權結構下,來自親密伴侶的不諒解及家庭關係的崩塌。不論她如何盡力彌補,以各種行動證明、以或冷靜或軟性的方式溝通,終仍未果。她的經驗提醒著觀者,當我們在檢討個案對婚姻的不誠時,亦不能忽視背後的結構性問題。討論不應陷落於婚姻中的背叛不忠、是非對錯的硬性評判,更應看見是何以讓跨性別者的處境仍然如此不見光?是婚姻制度的內部失衡,更是整體社會的漠視壓迫。 生活不同於電影腳本,不會有絕對的美好或悲慘結局,更多的是受傷、妥協、療傷、續而前進,而有時時間不會治癒一切,真正的成長可能只是學會如何和過去共存並和現在的自己相處。然存於這樣舉目皆問題的時空裡,縱使成全自己非坦途一條,我們亦不應羞恥於自我甚或抹煞自我而存。誠如宋紫洳所云:「我知道我可能是做錯了,但我是女人這件事是一定不會錯的。」,在緩步行於平權路的社會裡,她們從沒有錯,因為女人就是女人;跨性別女人,就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