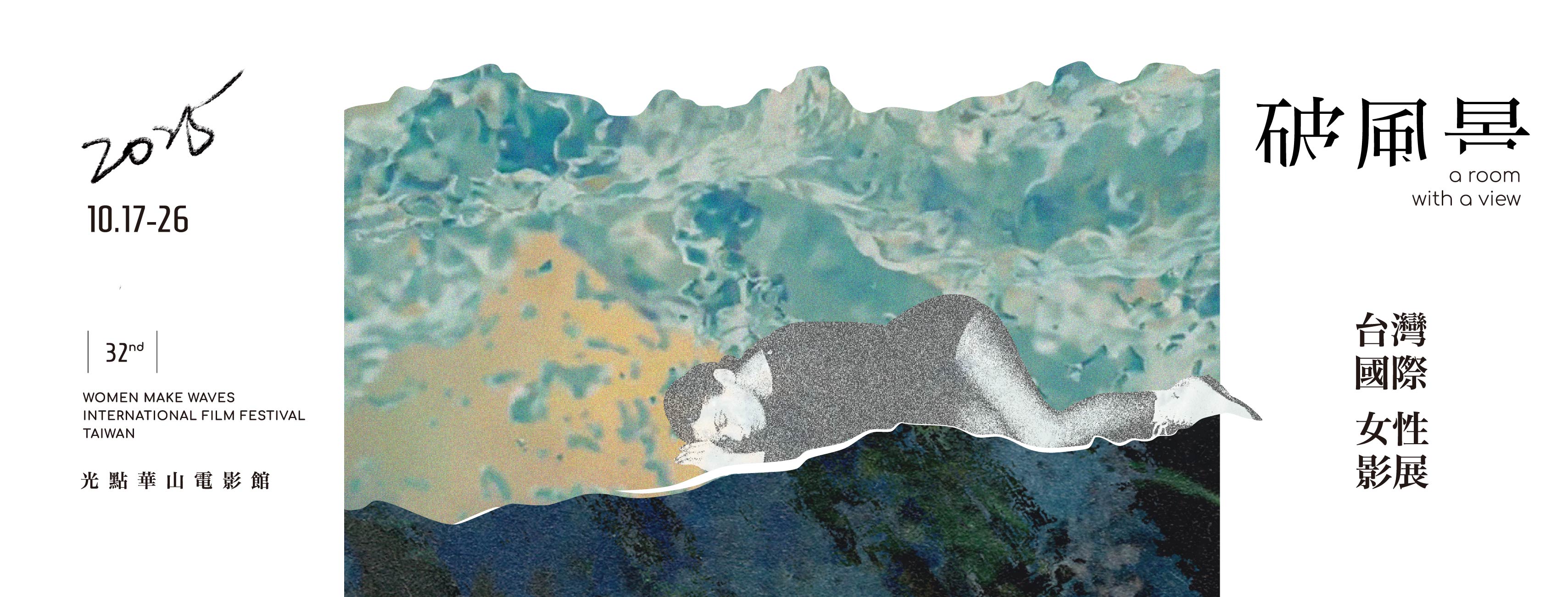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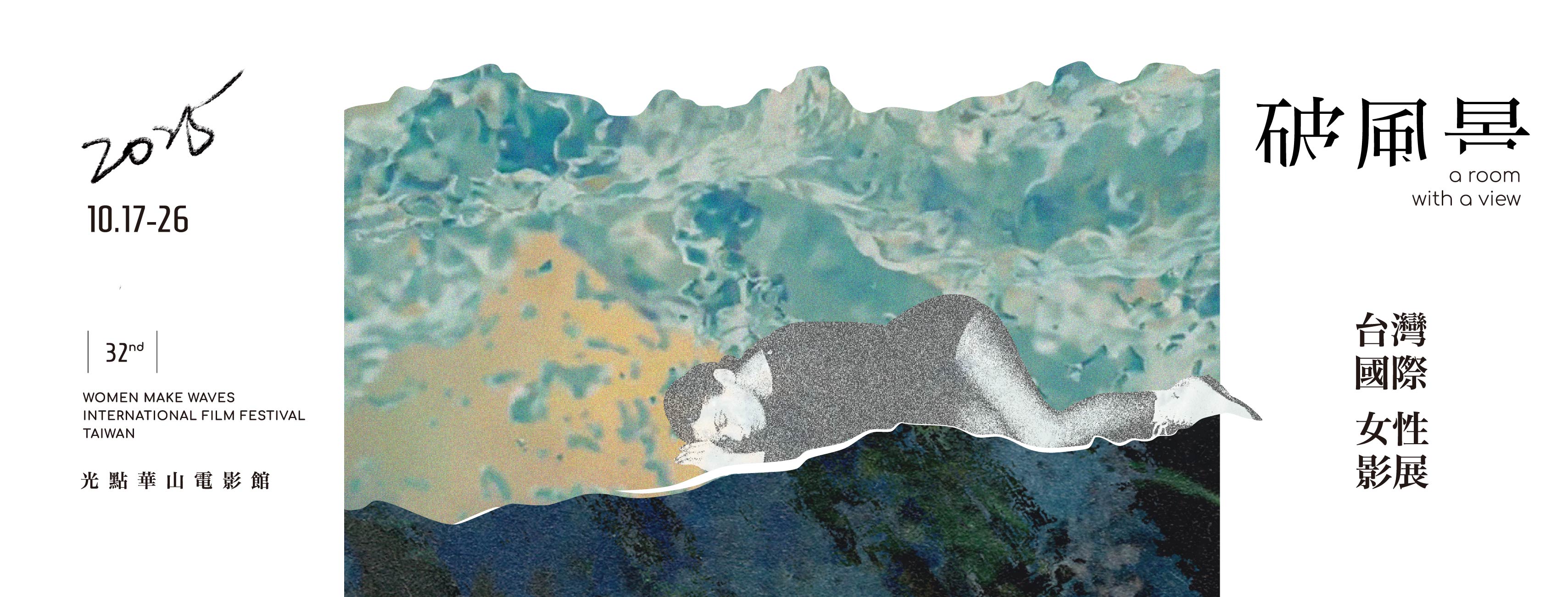
作者:肥內 發布時間:2018/10/01 在愛迪生發明燈泡時,一對叫莉莉和朵拉的孿生姊妹也出生了。正當人們因此開始享受夜的美,她們則面臨分離的命運。在這世紀之初,等著姊妹的是截然不同的生命、電力、無政府與女權的爭取。 作為匈牙利導演恩伊達(Enyedi Ildikó)首部劇情長片,《我的二十世紀》(Az én XX. századom)於1989年拿下坎城金攝影機獎,要不是這個得獎記錄,它大概會更加小眾——IMDb上甚至沒有它在匈牙利的上映記錄。如今,這部曾在影迷間流傳的精品將在女性影展放映,經過數位修復後的影像質地,為它鮮明且夢幻的黑白攝影增色不少。 片中的確安插了一段顯著關於女權的段落,是替革命份子服務的莉莉在一堂講座上聽到的主題;不過,在那裡,演講者終究以一篇報告來證明女性「缺乏理性、無法邏輯思考」,甚至,女性是一種「非存在」。但莉莉並沒有離場,她壓抑著憤怒,繼續留在座位上。 此一與前後情節沒有直接關聯的橋段,看似突兀,卻也不比影片許多地方更不自然;然而它幾乎在影片的正中間,實際上也承載了一個重要的隱喻:它終究引向莉莉的自我覺醒。於是直到後來,當莉莉要再次執行任務——這回,她的任務不再是傳遞情報或炸彈的製造配方,而是拿著炸彈前往一個有警衛駐守、看起來像政府機構的地方。但就在她手持炸彈、吶喊著衝向那棟建築物時,一位長得像那位演講者的人(其實是另一位政府官員),無助地看著她(儘管眼神似乎還有其他的盤算),突然間她下不了手,反而是帶著炸彈離開現場。正是莉莉的遲疑在敘事線的因果關係鬆脫的前提下,仍能看出這裡的象徵性行為。 這也是為何,她隨即逃到了遊樂場的鏡宮,一個十分適合姊妹重逢的場合。她們像是重逢,又像是彼此映現。姊妹倆的重逢像是一次合體,完整了她們的自我,於是影片近末,我們只有看到一個人從一棟尋常的住宅探出頭(放鴿子),此時不管她是朵拉還是莉莉,都沒有什麼差別了。 莉莉與朵拉這對孿生姊妹,映射且重逢於遊樂園的鏡宮 觀眾比較熟悉的恩伊達作品,很可能是去年上映的《夢鹿情謎》(Teströl és lélekröl,2017),這是她繼《魔法師西蒙》(Simon mágus,1999)闊別大銀幕18年後,一舉奪下柏林金熊獎而重新讓她的名字又在影迷間流傳的作品。兩相比較,我們很容易從恩伊達作品中找到一種童話般的氛圍,好比《夢鹿》中的潔癖女瑪麗亞堅信能與她「共夢」的身障者安德烈必然是她命中注定的那個人一樣。朵拉與莉莉的分離,也是在一個仿如童話《賣火柴女孩》的雪夜發生的——她們稍早前也以自己賣的火柴彼此取暖。 於是《我的二十世紀》的敘事也就像童話一般,除了「身分」的連貫性,以及姊妹倆分別都看上的那位男子(片中無人叫喚過他的名字,從片尾工作人員名單推測應該叫作Z)之外,影片實際上並沒有一條清晰的情節線。每一場都像是在「從前從前……」之後的「有一次……」、「又有一次……」。 於是男子Z才會無所不在地出現在各種關鍵場合:在巴黎電流展示會場(他在這樣的場合登場,也充分體現了他被象徵的意義)、在緬甸的橡膠園、在布達佩斯的圖書館邂逅莉莉,在豪華遊艇上邂逅了朵拉(但他並不清楚她們原來是孿生姊妹),終又在炸彈風波未平的時候,由一頭驢子的引導,進到鏡宮見到兩姊妹。 此外,朵拉的漂泊人生顯然沒有一個特定目標。但她的內心獨白會告訴我們她如何挑選男人。莉莉的任務看起來也同樣鬆散,比如當她與其他不曉得是窮人還是旅客擠在很小的屋舍裡,有人趁她睡著時拿走鳥籠裡的情報,究竟是她的接頭人還是敵人,不得而知;她的身分與任務也像是一種純符號性功能。 莉莉與朵拉這對孿生姊妹及其母親 正因為這種童話般的敘事方式,也才會出現一些離題,比如突然岔開來交代一條狗的奇異旅程。或者一隻動物園內的猩猩,向莉莉與Z「講述」牠是怎麼住到這個牢籠裡頭的故事。 影片經常被人貼上「魔幻」的標籤,也源於非常任性且不時出現的畫外音。比如天上的星星們向眉頭深鎖的愛迪生發出呼喊,或者隨著Z走進鏡宮、靠近孿生姊妹的過程中,類似是星星的聲音再次發聲,議論著他的內心活動。也包括上述動物園內猩猩講故事,或者,朵拉的內心話語——我們不禁問:為何莉莉沒有內心獨白呢?——等等。敘述「觀點」不斷游移的結果是,倘若觀眾把這些聲音都當作實存,那麼影片無疑就存在魔幻的成分;而我們也實在無法判斷這些聲音的真實性,最終只能忠於觀影過程中接收到的這些影音訊息。 不過,涉及「孿生」的題材,本來就容易製造出超現實情境,特別是對於劇中那些並不知情的人物來説尤其如此。就像Z在分別面對熱情的朵拉跟含蓄的莉莉時,必然會有奇妙的錯覺。而這種設計也往往讓人直接聯想到如布紐爾(Luis Buñuel,一位徹底的超現實主義導演)的《朦朧的慾望》(Cet obscur objet du désir,1977);但是恩伊達仍舊捨棄了這種現成的參照,雖說她也會用書籍(名為「自然界中的互助原則」)來作為貫串影片的象徵物,而影片收尾在愛迪生的電報系統發布會,也算是總結了二十世紀初期的重要面貌。 電燈、交際花朵拉、無政府莉莉、電報,以及通往大海的溪流,交織出一道二十世紀的曙光。 場次資訊 《我的二十世紀 My Twentith Century》 光點華山1+2廳 10/06(六)SAT 19:30 光點華山2廳 10/10(三)WED 21:00
作者:陳顗竹 發布時間:2018/10/01 蘇.弗迪胥(Su Friedrich)身為 1960 年代末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實踐者與獨立電影人,將 「個人即政治」的理念在作品中深刻地表露。表現形式上,他雜食地取用不同的素材,例如:宗教神像、浮世繪、私密影片、家庭電影、現成影像等,以有別於傳統的剪接手法將之混合,破除電影類型與類型之間、虛構與紀實影像的界線。在內容層面,蘇.弗迪胥則是將自己作為檢視的對象,面對己身的酷兒身份、家族記憶、親子關係、愛情、情慾⋯⋯進行思考與言說。或許正是如此,他的作品總是帶給觀眾一種生機澎勃之感。他藉由展示自我並且以生命經驗作為參照,去對映當代社會以及歷史,指出個人與主流規範之間的隔閡,同時也呼喚其他有相似經驗卻被噤聲的人們——大膽地一點說,蘇.弗迪胥的電影是對變革的號召。 這對於近似經驗的呼聲,我們可以在他早年的作品《冰冷的手,溫暖的心》(以下簡稱《冰》)與 1997 年之作《捉迷藏》裡聽聞。《冰》是虛構的無聲黑白短片。片中一位擁有健碩肌肉、蓄著短髮、明顯像是 Tom boy 的女子走入市井,目睹一個又一個女性坐在街道的看台上,刮除身上的腿毛、腋毛。主角幾次阻止卻總是失敗後,他也坐上看台,開始進行相同的儀式。甚至富含意味地:他持著小刀削起了蘋果。 《冰》雖然以象徵主義的方式呈現,卻不減蘇.弗迪胥對社會規訓女體一事,表達的沉痛抗議。片中有個別具巧思的安排:拍攝圍觀群眾時,畫面快速掃視人群後,短暫地定格在其中幾位男性觀眾的面孔上。導演藉此明白地點出對除毛儀式的凝視是以男性為主體。毛髮濃密的外表在西方傳統中向來被視作力量和膽識的陽剛象徵,例如聖經故事中的參孫,就因為頭髮從未被剪過而力大無窮;相對於此,女性的身體則被期待要無毛而且柔軟。這個虛幻的想像幾乎取代了真實,迫使女人必須違反自然,去改造自己的身體,以順應社會的期待。貌似無傷大雅的小壓迫,實際上無異於電影裡所暗喻的「削皮」。 《捉迷藏》是令人驚豔且難忘的作品。它以虛實交錯的手法,一方面採訪女同性戀者,請他們回憶自己的成長與性別認同的過程;另一方面用虛構的形式,講述一個 12 歲女孩面對初經來潮、發現自己暗戀閨蜜的狀況。《捉迷藏》的敘事其力道強勁之處在於:紀實的採訪影片與虛構的故事相互對証之餘,虛構故事因為其虛構性,而更廣闊地指向了受訪者之外、現實之中,同為女性或女同性戀者被主流觀念吸納又被驅逐至邊緣的共同經驗。此外在本片的行進中,蘇.弗迪胥巧妙地援引其他在電視廣告、主流商業片中出現的女性身影,凸顯他們在陽剛視角下被呈現的單一樣態。 蘇.弗迪胥的企圖並不僅是讓女人從男性凝視下的形象脫身而已,他亦要求影迷在觀看過程中,注意自己的主體性。1987 年的《修女日記》先是以一個女人橫躺在房間看著電視上正播放的,麥可.鮑爾(Michael Latham Powell)與艾默利.普萊斯柏格(Emeric Pressburger)兩位男士所共同執導的、以修女為主角的《黑水仙》為敘事起點。接著導演將鏡頭移近至電視螢幕上,用翻拍、重新剪輯電影的手法,還有在畫面之外持續評論與描述的女性口白,標示出觀眾的身份與視角。在電影的後半段,蘇.弗迪胥更令房中的女人盛裝款款地走上街,去勾引「真的」修女、為畫布上的基督聖像繡上濃妝。這是女影迷對原著電影的延伸創作與反叛,亦是向文本中束縛女性的道德禮教、抹黑姊妹情誼的刻板印象,做出激烈的嘲諷與挑釁。 在《沉浮》、《同根相連》、《無法訴說的羈絆》三部作品中,我們能輕易地察見蘇.弗迪胥「從個人出發」的特色。《同根相連》記述了他母親身為猶太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憶。耐人尋味的是:全片的聲部皆是導演母親的口述,而蘇.弗迪胥作為發問者,其問句只以文字的形式出現。這或許關乎了創作上僭越與否的職業道德:面對受害回憶時,將話語權交付受害者,尊重並將其經驗擺置在不受質疑的權威地位。《同根相連》的畫面主要以導演母親的居家生活、導演重遊故里、製作與拆毀戰前猶太人住所的模型所構成。電影的影像與受害者話語的意象相比,顯得疲弱且無法抗衡。但這份疲弱正是本片最迷人的特徵:令觀眾思考戰爭,去想像他們無法想像的事物。 時隔 32 年後,同樣以母親為主題的《無法訴說的羈絆》中,蘇.弗迪胥將目光從家族的歷史傷疤,轉至母親與自己的關係。在這次的計畫中,他邀請母親拿起照相機,加入創作的行列。1984 年在電影裡細訴往日的女人已然衰老、記不清事物,於是蘇.弗迪胥開始為母親記起曾經共同生活的時光,進而檢視親子關係中的矛盾與衝突。儘管照護過程辛苦、回憶偶爾傷人,女兒對母親的不滿之中,猶帶著溫柔。電影中有一非常動人的段落--導演持著攝影機走入玉米田,試圖靠近母親當年活過的狀態;透過電影裝置,他讓炸彈在不遠處爆破的聲音在耳邊響起。他非常努力地想理解,是什麼樣的經驗,讓母親成為這樣的人?但行動還是以失敗收場。生於美國且處在時序之後的女兒終究無法明白,只得出心疼的結論:「他遭到轟炸,他挨餓,他離開他的家鄉。然後他的丈夫離開了他和三個幼子。」 《沉浮》與前述兩部相較,結構更為複雜。導演以跨媒材的手法,將富含私人記憶的自拍、兒時的家庭電影、他人的私密影片,和屬於公眾領域的電影、電視廣告、基督教聖像畫、紀錄胚胎形成的科學錄影等,交融為一體。同時借著小女孩隱匿在畫面之外的口,道出積壓在心中關於父親拋棄家庭的痛苦,以及身為孩子遭受錯待卻依然戀慕的心聲。由此見,也許影像的來源對蘇.弗迪胥而言並不是首要的關鍵。創作者公開生命經驗之時,亦將自我裂解為多個,分散投射到他者身上;用有情的眼睛,渲染並侵吞屬於他者的影像,改變原意,產出專屬蘇.弗迪胥的獨特語境。 基進女性主義者卡洛.哈尼施(Carol Hanisch)在《美國婦女解放報》中曾寫道:「我們在團體中所發現的第一件事情是,個人的難題即是政治的難題。目前沒有針對個人的解決方案,只能從集體行動去尋找集體解方。」當我們聚在一起看蘇.弗迪胥的電影,或許可以問:所謂被主流隱形的共同經驗到底是什麼?還有哪些是未曾說、未曾見的?又有哪些是看了卻沒看清、說了卻仍可補述的?讓我們帶著問題意識走出電影院,到生活尋找答案吧。讓蘇.弗迪胥真切的呼聲持續飄蕩。用行動,讓自己成為迴響。 場次資訊 《冰冷的手,溫暖的心》(Cool Hands, Warm Heart) 光點華山2廳 10/06(六)SAT 21:50 府中15 10/12(五)FRI 16:30 光點華山2廳 10/13(六)SAT 16:30 《捉迷藏》(Hide and Seek) 光點華山2廳 10/07(日)SUN 13:20 光點華山2廳 10/09(二)TUE 12:50 《修女日記》(Damned If You Don’t) 光點華山2廳 10/06(六)SAT 21:50 府中15 10/12(五)FRI 16:30 光點華山2廳 10/13(六)SAT 16:30 《同根相連》(The Ties That Bind) 光點華山2廳 10/05(五)FRI 21:30 府中15 10/10(三)WED 14:30 光點華山2廳 10/11(四)THU 16:30 《無法訴說的羈絆》(I Cannot Tell You How I Feel) 光點華山2廳10/05(五)FRI 21:30 府中15 10/10(三)WED 14:30 光點華山2廳 10/11(四)THU 16:30 《沉浮》(Sink or Swim) 光點華山2廳 10/11(四)THU 21:10 光點華山2廳 10/13(六)SAT 19:50
作者:汪正翔 發布時間:2018/09/25 最近看了幾部短片:《關於他的故事》(動畫片)、《鄉愁/餘像》(紀錄片)、《曜》(動畫片)與《一如往常》(動畫片),它們處理的對象都跟過去有關,有些是回憶自己的外公,有些是講自己與爸爸,還有的是訴說一條街道與舊市場。看完之後有點怔怔地說不出話來,因為我不曾這樣回看我的家族與身邊的街道,這種「有一大塊的生命我從來不曾面對」的感受讓我有點焦慮,於是我找了一個可以轉移的切口:我發現這一批創作者他們的童年都已經有數位產品了。所以他們是第一代用數位產品審視自己小時候的人。他們對於過去的惆悵摻雜了數位科技與傳統資料(錄像、照片、文獻、口述),然後又以新的數位科技,譬如動畫剪輯的方式,被製作出來。 這是一個新的世代,他們回顧過去的時候是看到影片甚至於臉書,而不只是照片。這對於人自身的認知會有什麼影響?我們會覺得更加地悵然若失,因為過去的影像是那麼的鮮活嗎?還是會很快地習慣,覺得照片跟影片都ㄧ樣?譬如《鄉愁/餘像》裡面就不停地播放小時候與父親玩樂的影片與照片,但是口白卻告訴觀眾真實的生活是如此不堪,那個突兀感既來自於現實與影像的差異,也來自於照片與錄像的落差。 我不清楚答案是什麼,因為我覺得對於數位時代的回望還需要有很長的時間,才能確定它的意義。但我可以肯定的是,當回溯過去的方法越來越多,我們就會越來越相信過去是在我們所掌握的東西之中。拿照片來相比好了:在照片出現之前,我們會記住的事情其實跟事情本身的意義沒有多大的關係,在我腦中有一大部分記憶都是一些完全瑣碎的事情,譬如一個車窗、一個肩膀或是某個馬路。我在想即便我被催眠一百次,我也不相信會發現背後深刻的連結。所以記憶這件事,至少對我而言完全是隨機的。我們會說這件事讓我們記憶深刻,那是我們安慰自己的說法,好像只要滿足了某種條件,我們眼下經歷的事情,珍惜的人事物,就可以在記憶之中有一席之地。 在相機出現之前,人類的思想資源有一大部分是受制於這種毫無邏輯的機制,但這不是很美嗎?我們從無意義的記憶碎片之中試圖重新拼湊出些什麼,好像這些記憶重新又被賦予了邏輯。只是相機出現之後,這件事好像被消解了,至少表面上是這樣。因為我們一旦覺得眼前的事情值得紀念,我們就會按下快門,然後這件事在相當程度上就會被記憶下來。連我記性這樣不好的人,我都好像依靠照片,記得了一些東西。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因為相片或是影片畢竟也只是真實的「片段」,更關鍵的是,有時我們會被觸動,甚至真正地感受到過去的存在,並不是來自於那些有意識的紀錄,而是一些莫名奇妙的細節。羅蘭.巴特在《明室》當中就懷疑那些有意圖的照片根本不曾抓住什麼。所以他提出「刺點」的概念,其實就是一個不能刻意捕捉,無法被邏輯分析,甚至無話可說的照片特質。同時,基於這個「無話可說」的原則,羅蘭.巴特武斷地認為電影太快太多話太有想法,他說他討厭電影。 另一種意見來自於班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他也談到了攝影與電影。相對於羅蘭.巴特致力於區分兩者,班雅明則是把兩者合在一起,相對於古典藝術的靈光。班雅明認為電影與攝影都有一種特寫與蒙太奇的特性,當然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內涵,我們對於電影與攝影的認識更趨於複雜。但是班雅明的重點是在於:這種特寫與蒙太奇的特性,打破了過去相信「藝術品要整體掌握對象」的想法。 他舉例:以前的風景照總是想要呈現一個時空,要把那個異地招喚到觀眾面前,讓觀眾好像親臨現場一樣。又譬如古典的肖像照,試圖去捕捉一個內在的本質,所以看照片的人,就會有一種見照如見人的感覺。這些方法在班雅明看來都像是一種回返靈光的垂死掙扎,他認為在新的時代,電影與攝影那種捕捉細節,或是片段拼接的手法,會帶來一種新的感知。我們會發現這個說法與羅蘭.巴特有多不一樣。以一張 Eugene Atget 拍攝老樹根的照片為例,班雅明讚許他運用特寫的手法。但是在《明室》當中,羅蘭.巴特對於 Eugene Atget 的照片,他的反應是「這與我有何干」。 會有這個差別可以有很多解釋,但是其中之一是兩人對於新技術抱持著兩種態度:一個是相信它會幫助我們留下更多資訊,帶來更完整更奇特的感知,另一個則是憂心新技術會在我們的心靈地圖之中添加各種標記,然後我們更習慣於在這些標記之間行走,卻忘卻了真實其實在這些標記之外。其中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可以逼近一個存在?以《關於他的故事》為例,裡面透過各種方式追溯他的外公的生命,包括口述歷史、肖像畫、照片、動畫等等,班雅明想必會對此感到興奮,而羅蘭.巴特可能只想觀看一張安靜的照片,然後期待有沒有什麼東西會忽然刺中他。 就面向存在這件事而言,有時我甚至覺得羅蘭.巴特談論的「此曾在」跟班雅明要告別的靈光有幾分相似。「此曾在」指相片中的事物必然曾經存在。作為相機的特性,它帶給觀眾雙重的感受:一方面它證實了真實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它又告訴你這個存在已經過去了,所以羅蘭.巴特說照片是關於死亡。而班雅明所告別的靈光,就具有一種似近實遠的特質,譬如照片裡面的人看起來好像真的,好像就在你眼前,但實際上這個人並不在現場,甚至於這個人已經不存在。 (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這兩者的差別。羅蘭巴特所描述的「此曾在」,並非一種再現的藝術觀,而是更接近於現象學的看法。也就是說照片對他而言,並不是用來證明客體世界的真實性,而是真實性就在個人對於世界的意識之中。所以他說照片並不是正確的紀錄,不是複現,而是真實的發散,是一種存在的痕跡。) 回過頭來看那些動畫與紀錄片,我覺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它們好像結合了兩種觀點,一方面作者凝視那個不被「現代」所傷害的過去(宮廟、市場、老街與家族都像是某種現代對立之物),但是另一方面作者運用了各種「新的」、「現代的」技術,譬如剪輯、動畫來描述過去。而作為一個電影愛好者與平面攝影師,我一方面期待各種新的技藝如何訴說我們的生命,同時我想知道這與我們觀看一張安靜無聲的照片,有什麼不一樣。 場次資訊 《鄉愁/餘像》(Spectrum of Nostalgia) 光點華山2廳 10/07(日)SUN 10:50 光點華山2廳 10/13(六)SAT 10:20 《關於他的故事》(Stories About Him) 光點華山2廳 10/08(一)MON 18:30 光點華山1廳 10/12(五)FRI 11:30 《曜》(Wish) 光點華山2廳 10/09(二)TUE 19:00 光點華山2廳 10/12(五)FRI 13:20 《一如往常》(As Usual) 光點華山2廳 10/09(二)TUE 19:00 光點華山2廳 10/12(五)FRI 13:20
作者:吳梓安 發布時間:2018/09/25 七零年代是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在美國東岸蓬勃發展的年代,從男性中心的新左派(New Left)陣營獨立,她們提出性別才是最古老的壓迫形式(而非社會經濟的階級),從母職,家庭,性與工作等層面,展開全面性地對父權體制根本地檢討,各種不同的女性主義與性別運動眾聲喧嘩的年代就此展開。「個人的即政治的」是第二波婦運最著名的口號之一,這句宣言或許最能代表所謂的「基進」——由最基本的社會結構與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檢視並批判父權的意識形態,是如何部署到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毛孔中。 蘇∙弗迪胥(Su Friedrich)亦曾是基進女性主義運動的一員(曾為基進女性主義雜誌《異端》〔Heresies〕製作平面設計),原本學習藝術史,她的電影生涯在七零年代晚期的紐約展開,從著名的實驗電影基地千禧電影工作坊(Millennium Film Workshop)習得膠卷的技藝與實驗電影的語彙。在她的作品中可約略見到Stan Brakhage和Hollis Frampton等實驗電影作者影響,特別是強調電影物質性的結構電影(Structural film)運動,在本屆女性影展所播映的《冰冷的手,温暖的心》(Cool Hands, Warm Heart)和《悠游而下》(Gently Down the Stream)和《同根相連》(The Ties That Bind)這幾部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此派實驗電影運動的影響,諸如手刮底片,抽象化的攝影,音樂性的剪接等。而《悠游而下》,大量使用光學印片(optical printer)技法,強調影像的本體,觀影經驗如同用眼睛觸摸膠卷,並融合手刮底片的文字敘事,將許多實驗電影技法熔冶一爐,而使用夢日記拼貼而成的敘事結構,亦讓人想起實驗電影教母瑪雅戴倫(Maya Deren)充滿夢境與幻想的自我驅魔儀式(而非除魅)。 《悠游而下》裡的手刮底片技巧 二次大戰結束前後開始在美國蓬勃發展的實驗電影,如同相近時期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或許都是涵括太多流派的大傘,除了結構電影,更有解構敘事機器的新美國電影(New American Cinema),重視內心風景的Psycho Drama等流派。而實驗電影的前稱「前衛(Avant-garde)電影」一詞,即是由(衝刺突圍)軍事詞彙借用來的跨領域文化運動,是某種自期將目光聚焦在前沿的藝術的政治運動。運動與門派紛雜,但根本上,早在電影片廠制度誕生之前,實驗電影即是將膠卷與攝影機作為個人的媒材的創作方式。 時代與地緣的關係讓弗迪胥將兩種基進運動結合在她的作品中,然而和當時實驗電影社群內風行的形式與風格相比,她始終保持自主的態度,自言法斯賓達、香妲阿克曼與布紐爾才是她在開始手工製作電影之前的啟蒙1。或許這樣的初心,使得她找到屬於自己的電影語彙。1990年的《沉浮》(Sink or Swim)是這樣極具個人風格的代表作,以半自傳半虛構的成長故事體裁(coming of age),使用既輕又重的家庭電影質地,結合日記電影甚或散文電影的碎瑣敘事旁白,並用童聲配音。結構上使用字母排列,Z倒數到A,製成一部自我認同的百科全書與療癒之旅。而字母的最中央是M,Memory,全片中最長的一段,以閃爍明滅的家庭影像講述兒時記憶的沈重與深遠影響,既親密又遙遠。 在1987年的《修女日記》(Damned If You Don't)中,對形式與內容的翻玩同樣精采。首先以黑白膠卷翻拍《黑水仙》(Black Narcissus,1947年的早期特藝七彩片)的電視螢幕,利用局部特寫與強調電視螢幕的掃瞄線,讓原本的影像產生質變,再加以重製敘事並凸顯原片中的性別盲,而後由自白般的旁白,讓觀眾進入一個被酷兒歪讀的天主教啟靈故事,但到了電影的最後,觀眾才在尺度全開的床戲中恍然發現,這是一個宛若修女夜難熬的女同性戀情慾解放電影。 《修女日記》將特藝彩色片經典《黑水仙》酷兒歪讀成一個宛如修女夜難熬的女同性戀情慾解放電影 弗迪胥的作品靈巧而輕盈地遊走在實驗/紀錄/劇情這些當代電影建制所劃分的類型之間,而除了生猛辛辣的的實驗之外,許多弗迪胥的作品在形式上則相對平易近人,如《公路規則》(Rules of the Road),《捉迷藏》(Hide and Seek),《無法訴說的羈絆》(I Cannot Tell You How I Feel)等,不變的是她的作品,不論虛構或紀實或實驗,始終保持真誠的態度,去接近自己與自身周遭的人們的生命經驗,私人的故事,卻又最能碰觸到難以拍攝的各種議題:宗教,歷史,性別政治等等。2006年在紐約MoMA的弗迪胥回顧影展即是以私電影(Personal Film)為題2,她的生命故事,小寫的私電影,數十年越界而不願被定義的姿態,或許也是由於長年受到女性主義與實驗電影所共有的,個人的政治的基進姿態所驅動。 某種程度上,或許蘇∙弗迪胥銜接了70、80年代的美國實驗電影與90年代的新酷兒電影(New Queer Cinema),特別是後者在形式與內容皆具挑釁的政治性。但在1988年第二屆紐約Lesbian & Gay實驗影展(現為MIX NYC酷兒實驗影展)中,弗迪胥在以基進的形式與內容為主題的論壇中發表了一篇短文《基進的內容就得配上基進的形式嗎?》3,談到這兩者媒合的艱難與是否必要,她的態度是有點悲觀卻又開放的。她以Stan Brakhage為例,認為Brakhage在電影形式上基進,在性別政治上卻相對保守,對所有作品同時要求形式與內容上的基進並不公允。但弗迪胥也說,Brakhage的作品常以他的家庭與妻子為題材,在某些作品背後,過於刻板主從關係總讓她感到壓迫,「像是在看情境喜劇(sitcom)一樣」。 《沉浮》是蘇∙弗迪胥深受結構電影影響的半自傳、半虛構代表作 這種幽默感與氣質,或許是她能從藝術與社會運動的大敘事中脫出的方法,而在當下的時代,或許對「基進」的執念可能也已成為一種壓迫,但她期勉「對自我敘事真誠,對電影媒材的可能性盡力嘗試」。對她而言,生活中的感受,始終比戰鬥姿態來的重要。也因此,在她圍繞著家庭、記憶與童年的作品中,觀眾可能找到更多自我分析與自我建構的坦誠,同時也更能鏡射出自己生命經驗中的認同史。
作者:葉家瑜 發布時間:2018/09/25 既是母親、也是女兒。女人,妳最初初的時候,又是什麼模樣? 《再會馬德里》涉及的主題很多,從偏鄉教育場景、外省老兵現況、乃至於舞蹈家賀連華在舞蹈志業上的掙扎與奮鬥,再到其與父母、子女的關係側寫。她是對偏鄉藝文教育有堅持的老師,是每年赴西班牙進修孜孜不倦的學生,是重視家庭的父母眼中不穩定的女兒,卻同時也是女兒鮮鮮眼中、好似什麼都將她規劃好的母親…… 而她說,她是個藝術家,也是個被寵壞的孩子。 我相信人的一生中,最糾纏、痛苦的問題,通常不是別人做錯的那些事情,而是你自覺「錯了」的那些時刻。賀連華本該有大好的未來,她本該有一場偉大愛情、一份偉大的成就——直到她決定回台,奉子成婚,塌陷進入她真正擁有的命運。而旁人乍見,定會認為是走上母親之路的鮮鮮,擁有比母親更加年輕、健康的身體,12 歲便一人在外公與母親的支持下,遠赴異地。 她走上的是她自己的夢想。然而作為舞蹈家口中「最大的懲罰」的衍生物,女兒鮮鮮這樣的一個決定,在她眼中,又何嘗不是個「再一次」的平行時空?作為子女的時候,我們獨立,而且不願接受干預與拘束;然而作為父母的時候,我們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面目。《再會馬德里》討論的既是夢想中的再會馬德里,作為舞蹈家尋夢終點的馬德里,也是做為母親恐懼起點的馬德里;在馬德里的是無論喜悅或悲傷都難以輕易得窺的女兒,也是擔心像自己一樣半途而廢、前功盡棄的女兒。更是無論如何無法重來的人生。 而作為旁觀者的我們,更多時候是從賀連華的視角、以賀連華對現況的評價來看鮮鮮:連試都不去嘗試的鮮鮮,怎麼可以呢?怎麼可以輕易放棄夢想呢? 這是我在《再會馬德里》中,看見最沉重的課題。母親擔心「女兒若像自己」。正如我自己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的來自母親的壓力,繼承了她的硬骨與自由的女兒,會不會最終與她一樣,對著擁有穩定家庭與事業的親友徒呼負負?然而這樣的愛,卻只讓人在退無可退之際說了:「妳不要把妳過去沒有完成的夢想放在我身上。」 鮮鮮和母親的夢想是如此相似的……是嗎?因為賀連華曾走過那麼相似的ㄧ條路,最終卻走上了通往她眼中真正的成就以外的另一條岔路,因此她能有更堅實的經驗來做她的基石,是嗎?又或者她只是基於一個母親那樣地(如同我的母親那樣地)(如同每一個人的母親那樣地),打磨自己的女兒,要她作人不能輕易放棄呢? 我們無從得知,也或許個人有個人的心思。然而最終幕末,鮮鮮在西班牙的街道上說著:「媽媽有她自己對我的安排,她害怕我受傷害,然後害怕我走上失敗的路,然後我這些可能都知道,我知道我今天可能走的那條路,一定會是失敗的,可是有時候的我就會覺得說……」 「好,那可不可以讓我失敗一次?」 同樣的母女照鏡,在《離巢》中則因為主要視角的轉換,而有了不同的命題。 曉安因為母親要賣掉老房而回到成年後闊別的家,兩個人以母女的身分重新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然而兩人早已有各自的生活,也各自有著難以言說的苦惱。別人的丈夫、命運未卜的胎兒,在那麼乍似風平浪靜卻又轉瞬針鋒相對的日常,兩個最親近的人,竟沒有一個縫隙能共有這些困惑與苦痛。 少少能安穩相依的時刻,只有當母親服藥入睡後,曉安扶著半夢半醒才顯得柔軟脆弱的母親入房,兩人的腳步漸次,終於像一首和諧的樂曲。 《離巢》許多場面相當小,特別日常的場景也顯得特別壓迫,我極喜歡她們在餐廳的那一場戲,曉安掛記著母親先前念著想吃的節目肉圓,但因為店家在彰化便隨意買了家附近的肉圓回來當晚餐,母親看了一眼便說:「這家肉圓我不吃。」而後或許本是出自好意,隨口念了女兒怎麼就拿肉圓當正餐,曉安沒好氣地要她不要再念了,本來只是沉沉鬱鬱的氣氛,便忽然急轉直下,母親尖聲揚起:「妳不幫我查就算了,隨便買個肉圓就想打發我啊?」…… 有時候,某些突如其來的巨大爭論,甚至是事後想想的重大轉折,最一開始的時候,人真的毫無所悉。只是當一個分歧下一個分歧,每次偏離主軸 10 度、10 度又 10 度的時候,事態往往便發展成無法控制的局面。 為什麼親情之間,善與善的連環,最終會走成彼此叫罵的場面?這場面殘酷得讓人心驚,不只是那種限於空間裡滿滿的情緒張力,而是這場景如此地熟悉,簡直像你日常的高度還原。 母親的怒容從鏡中映射,顯得居高臨下而盛氣凌人,然而曉安不抬頭只抬眼的眼神,也冷得令人心寒。下一個場面,角力的局勢便隨著視角而忽然轉換:孩子起身欺近了母親,繞著她周身冷冷地回擊。我們於是看見,她比母親年輕、高挑、健康且美麗,在室內昏黃的燈光下,母親眼下與兩頰的陰影就像她無可抵賴的衰敗與老弱。那些因為同理曉安,對母親蠻不講理而勃發的怒氣,最終仍只能無力地洩了一地。 正如同曉安在老家,一個回神總能恍惚地看見年少的自己,趴在母親肩頭,隨著母親原地搖晃的舞步而心安沉沉。然而成年的她與母親,卻必須重新修正舞步成雙人舞,才能順水地知其每一步的進退。 搬家的那一天,母親遞給曉安一捲承載著她們共有的美好時光的錄音帶,若無其事地笑著囑咐她:過年記得回家。幕末的曉安走在人去樓空的家裡,她勃勃地說著「妳憑什麼把我家賣掉!」的家裡,無限眷戀地低語:「那時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想到我小時候,曾經許過一個願望,我希望自己長大,不要成為像妳這樣的人。結果長大以後,我照鏡子總覺得,我好像跟妳越來越像,長得越來越像,連講話的方式也越來越像,然後我才明白,我討厭自己的地方,是因為妳。而我喜歡自己的地方……」 《離巢》講述的是一個害怕「與母親相像」的女兒的故事,對照著《再會馬德里》,則是ㄧ位害怕「女兒與自己相像」的母親。兩段關係親密的母女,因共享了彼此的人生,而在身上同時有了相同與相異的印記。在那些日常千絲萬縷的交會中,哪些立場與情緒是基於一個「母親」、或是一個「女兒」,哪些又是身為一個純然的「人」?(這有可能嗎?) 我想的是,當我們用「孩子」的觀點在看待我們的父母時,往往都只能看到他們作為我們的「父母」時,呈上的臉面;反之亦然。 而當父母僅能看待我們,作為一個孩子時,就極難理解我們,作為他人之妻、之父、之師、之友……甚至就只是我們「自己」。而反之,也亦然。 場次資訊 《再會馬德里》(Adios ! Madrid) 光點華山2廳 10/07(日)SUN 19:10 光點華山2廳 10/12(五)FRI 17:20 《離巢》(Lichao) 光點華山2廳 10/05(五)FRI 19:00 光點華山2廳 10/12(五)FRI 15:20
作者:施彥如 發布時間:2018/09/25 這陣子的臉書上,被 S.H.E 紀念出道的新單曲〈十七〉狂烈洗版。十七年,完全就是一個人蛻變為少男/少女的年數,然而我(以及那些視 S.H.E 為成長印記的朋友們)早已離少女、青春這一類詞久遠矣——儘管心態上不承認,但花在保養比彩妝還多的預算,已默默代為證實。少女或青春是一種五味雜陳的狀態,引領其中某種人走到「長大」面前,順利通行,而另外有些人則或停頓,或跳躍,去了別的地方。 這回入圍女性影展台灣競賽單元的其中四部片,展現了四種截然不同的、剛冒出芽的(少)女力量,各自有各自詮釋少女心事的幽微、苦痛與不可告人之心底事。身為前少女,我在一些角色裡看到自己,譬如《2號球衣》裡的李望,那女孩與女孩之間矛盾的友誼。 李望加入排球隊已四年,雖總是私下勤加練習,但正式比賽始終坐冷板凳,而她的體保生好朋友江禹韶則是隊上的王牌,靠著天份得心應手。一日與校外比賽,江禹韶睡過頭了,眼看比賽即將開始,教練不得不讓李望上場。李望快速換上她專屬的 2 號球衣,期待她上場的第一場球賽,但江來了,李不僅要坐回板凳區,還得把衣服借給沒帶球衣的江穿。李望在球衣黏上一個「1」,讓原本屬於她的 2 號球衣,變成江禹韶的 12 號。 說不出的壓抑,迂迴、婉轉、隱約卻巨大的渴望,充斥在少女心底。明明是這麼為朋友驕傲的,但為什麼當球衣從 2 號變成了 12 號,心底眼鼻卻有一絲絲酸楚和嫉妒?李是舞台上演樹的那種背景工具人,江是少數可以有台詞的發光主角,樹怎麼可以夢想有一天開口說話? 但李望全說了。彆扭是少女最無法說明清楚的情緒,也是少女唯一擁有的武器。一場長鏡頭讓飾演李望的年輕演員李雪爆發驚人的力量:生氣起來胡言亂語的鬼打牆邏輯,滿溢的情緒一開口就不爭氣流下眼淚。她以為全世界就自己最委屈,沒有人在乎她背後的努力——畢竟在少女的心中,自己就是全世界。所以當一向酷酷的江禹韶開口反擊時,李愣住了。那些貌似輕而易舉的連環奪分背後,是江從小一路念體育班、辛苦訓練換來的,李不過是上大學後才開始接觸排球,又怎麼會知道被練球剝奪成長的痛苦?況且江根本不想打了,她是為了李才上場的。她把球衣脫下來甩在地上,也甩開了對李的在乎與親密。 李的盧小,江覺得靠腰。少女間的吵架要嘛大打出手、扯髮踢腿,要嘛就是醬子,明明是最好的朋友,卻無所不用其極傷害對方,講出一些隔天醒來就完全後悔的話,也完全不給明天的彼此留下台階。 也有一種少女的成長過程,連生氣的時候也無處可發洩。在短片《亮亮與噴子》中,李雪再次成功演活了另一種少女面貌: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女亮亮,為了家計而放棄升學,在色情釣蝦場打工,十八歲這天,她原本規劃要過個值得紀念、轉大人的生日,只是無奈經營酒店的媽媽,又把不負責任的哥哥和前女友生的姪子(噴子)丟給她。十八歲的第一天,亮亮穿著俏麗的短裙,身上卻背著噴子、媽媽包,騎著小綿羊穿梭在卡拉 OK、酒店間,要找哥哥出來面對。 亮亮毫不在乎的表情之下,其實有菩薩心腸。她熟練地幫噴子換尿布,哄噴子入睡,一個不被愛的大孩子愛著一個不被期待的小孩子,這是亮亮能夠給他最大的溫柔。在三十分鐘的短片裡,除了心中 OS,亮亮沒有開口說半句話,但她對生活不公平的怒氣,卻不需要透過話語發洩,少女對抗世界的力量蠻橫又微小,縱使再怎麼不服氣,也只是找到哥哥和現任懷孕女友同居的住所,灑一泡尿在茶几上,然後又心軟,帶著噴子找男友約會去。 我特別喜歡片中導演不著痕跡地埋著菩薩的意象:飾演亮亮的李雪身形微肉,細細的單眼皮也有股菩薩低眉之感;從一開始出現竹南后厝龍鳳宮的巨大媽祖,到亮亮生日和觀世音菩薩同一天,女性的保庇和溫柔的守護,給予這部短片一種輕盈、異樣的輕快;亮亮日復一日刷著阿婆的假牙,清掉拾荒鄰居堵住的排水孔,將那些骯髒的過去的污穢排乾淨,分明是已接近底層又辛苦的生活,但十八歲的亮亮,仍對於未來的日子飽滿期待。 也有些少女,揮別過去是為了迎接未來。好好說再見從來不是輕易的功課,在《133公里》片中,少女在哥哥的堅持下,帶著媽媽巨大的婚紗獨照,和哥哥夜騎回老家,讓早已離婚離家的媽媽在某種層面上,能重新團圓相聚。 兄妹兩人一台摩托車,一個雨後夜晚,一段回家的長途公路旅行,坐在機車上雖貼近,但心中想些什麼,彼此都不願意多談。彷彿過去的事情一切都會過去,只要把婚紗照偷偷掛回爺爺老家,媽媽就會回來了。妹妹明顯不想跟哥哥走這趟,動不動就撇下一句「隨便你」,奧嘟嘟的臉整夜坐在後座吃東西,扛著巨大的婚紗照,她一路吃營養口糧、偷拿阿秀嫂的粽子、便利商店的水、柑仔店的 10 元紅茶,我不禁羨慕少女的好胃口與絕佳代謝,這些都是隨著年齡一去不復返的時代眼淚。 少女和哥哥發生爭執後,一人賭氣下車,偶然路過柑仔店,不知道幾點還沒睡的柑仔店小妹妹,誤以為婚紗照是自己的媽媽,伸出小手摸著相紙,奶音奶音叫著媽媽。少女僵硬的表情軟化,是想到過去自己也是無辜沒有了媽媽的小孩吧?爸爸過世後不僅沒有回去整理遺物,這趟返鄉之旅也不甘不願。對少女來說,家早就分崩離析了,這場大半夜被哥哥拖來上演的何處是我家,她是一點也不領情。然而,小女孩讓她想起了自己,她在便利商店影印了婚紗照送給小女孩,似乎也是安慰過去的自己,踏平起伏的情緒,再坐上機車後頭,迎一段海風前行。 要走往前方,常常出現岔路,有時選錯了,命運將會全然不同。《小文空仔與那隻羊》說了一個誇張的奇幻寓言故事,「拍片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偶然與巧合並非只出現在電影中,也出現在少女迷糊的陰陽差錯之間:一方是學生拍片的現場,故作成熟世故,有槍有黑道有黑道的女人;一方是真實大人的社會,有欠債買兇,有背叛謀殺,兩方交織在一間地方 local 大旅社,而少女小文傳遞的真假道具槍是關鍵⋯⋯ 小文這種迷糊性格,非常有既視感,一股專屬於少女們的熱誠,拚了老命想要做點好事,證明自己,卻總是落東落西,讓身旁的人收拾善後之餘,又不忍多碎嘴責備——是因為看到少女眼汪汪的誠懇,與什麼沒有熱血最多的衝勁,總讓人想到自己尚未被江湖/社會污染的初心吧。後浪純潔地推著前浪,前浪也只好義無反顧地當人肉墊子,接住每個勇猛直前的少女心了。 四部短片看下來,全是少女的心事,是彆扭說不清楚自己心底的感受,講不明白如何不傷害身邊的人;是單純地想要愛,想要被呵護,想要做個別那麼快長大的小孩,如同彼得潘;是想告別過去,彌補傷痕,卻越來越不可能果決;也是跌跌撞撞地想要做好每一件事,卻老是陰陽差錯迎來不可逆轉的災難。 想起歷經滄桑時光的 S.H.E 在〈十七〉中唱著:「十七歲的我們/在哪邊/在未來攤開之前/期待又怕受傷害/是我/和你和你/說著夢想/說著心願。」願每一個少女都有力量,抖一抖身上換毛似的羽翼,又哭著,又笑著,又荒謬著地,走過了青春年少,從少女變成女人。 場次資訊 《2 號球衣》(On the Waitlist) 光點華山2廳 10/07(日)SUN 10:50 光點華山2廳 10/13(六)SAT10:20 《亮亮與噴子》(Babes' Not Alone) 光點華山2廳 10/05(五)FRI 19:00 光點華山2廳 10/12(五)FRI 15:20 《133公里》(133km) 光點華山2廳 10/05(五)FRI 19:00 光點華山2廳 10/12(五)FRI 15:20 《小文空仔與那隻羊》(Revenge of the Goat) 光點華山2廳 10/09(二)TUE 19:00 光點華山2廳 10/12(五)FRI 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