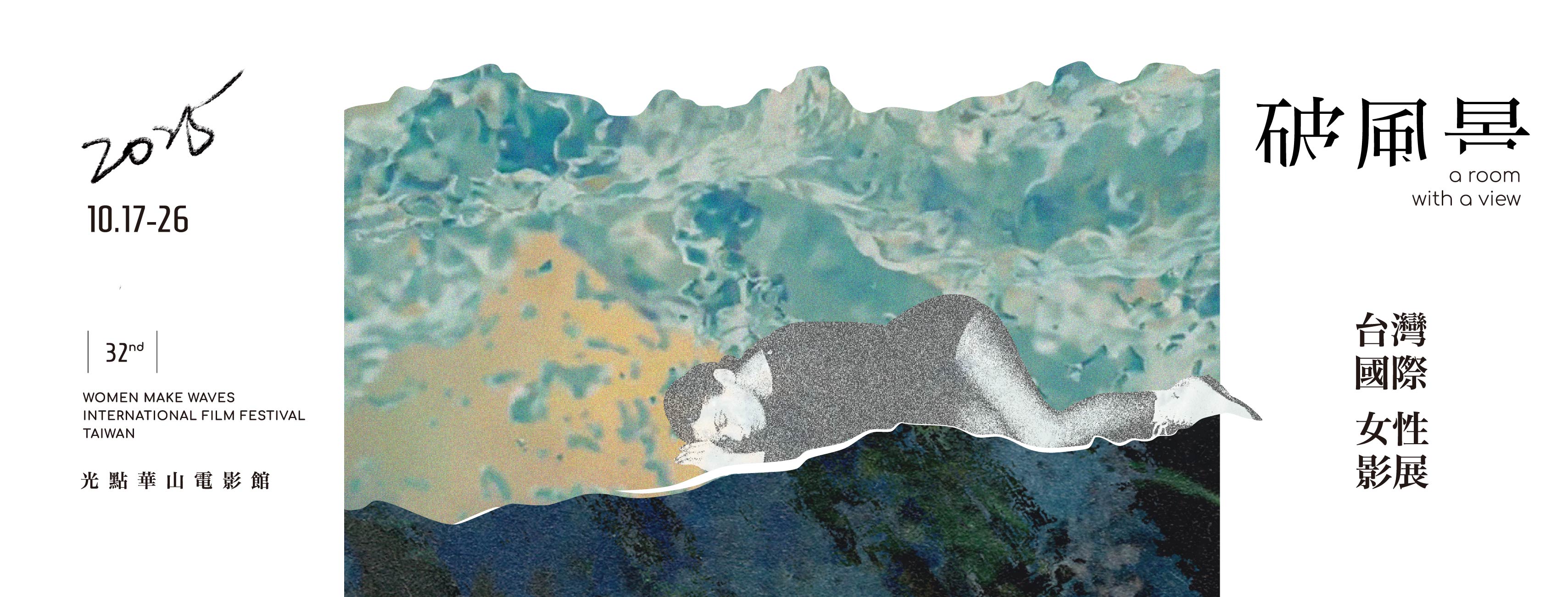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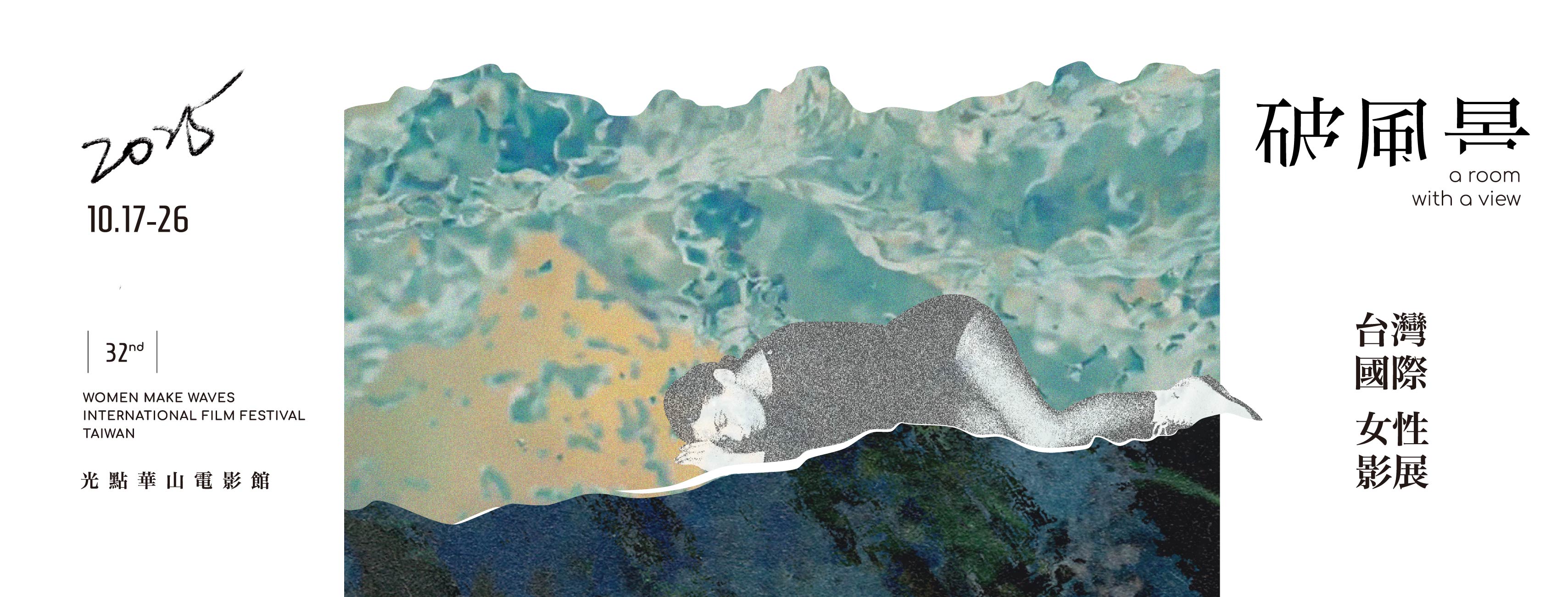
文/沈佳穎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動畫學系 原文刊載於性別力 在《尋找乳房》紀錄片中,有幾個鏡頭拍攝著台灣的街道,街道上大大的廣告看板,當紅的女明星代言著各式商品,光鮮亮麗的女性形象嶄露無遺,這是我們最熟悉不過的日常一景。而導演陳芯宜所呈現的這一幕,卻讓我想到盧森堡行為藝術家 Deborah de Robertis,她在 2014 年到奧賽博物館,庫爾貝的《世界的起源》之前進行名為 ”Mirror of Origin” 的行為表演:她身著金色連衣裙,在眾目睽睽之下,就在名畫之前,坐下,並打開雙腿,以手撐開陰唇。我想,這兩者似乎都在訴說一件事,一種當代社會仍然根深蒂固的,「女性身為被觀看者」這樣一個原始設定。 圖片|作者提供 女性身體被拿來觀看、評論,確確實實還是存在的,各種廣告,傳播媒體,都不斷在宣揚,在一個父權社會結構下的觀看前提,我們的身體應該成為的樣子。《尋找乳房》片中的受訪者人數眾多,都是女性,不同的年齡、職業、身分,探索每一個人心中對於自己身體的認識與認同,從青年世代、剛生產完的母親,到月事已去的婆婆媽媽們,像是開啟潘朵拉的盒子一般,那些從來沒有搬上檯面的問題,看似私密的身體談話,在鏡頭之前,溫柔地被開啟。 圖片|作者提供 身體,一個很自然,很單純的主體,卻是我們最不熟悉的。因為不熟悉,所以不認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母親的自白,她認為她在懷孕的過程中,外界看待她的樣子,僅僅是代表著「生產孩子的容器」。女性身體被社會賦予的價值,已大過最本質的樣貌,但在這樣的框架之下,這些受訪者,似乎也找到生存的最佳形狀。 圖片|作者提供 片中探討了許多話題,包含生病的身體、情慾、性、愛,最後還是回歸自我的身分認同。這也讓我想到不久前看完溝口健二的《赤線地帶》,片中是一群妓院中的女人,雖然在古早的年代,且妓女是人們眼中的下等職業,但是她們對於自己的身體是認同的,不論是維生的工具也好、商品也罷,她們並不是噤聲。在現代,談論自己的身體好像顯得陌生,但是每個人都應該學著更親近、更認識自己,跳脫觀者與被觀者,與身體對話。 導演陳芯宜曾說:「這些事情細微到我們不曉得怎麼去談,但仍一點一點的在影響著所有的事,這部片若要形容為是我的田調也可以,她們這些私密的分享,好像讓我們可以稍微面對這些隱而不談的事情。」《尋找乳房》看似是許多人的訪談集合,卻是代表著台灣現今社會的女性,我們內心最深處的、共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聲音。 圖片|作者提供
文/張力 原文刊載於LEZS 一切都是賀爾蒙惹的禍? SWITCH意味著切換與轉變,《SWITCH》探討著身分認同、性的探索與成長。憶起兒時的回憶,高橋留美子有部作品叫《亂馬½》,主角早乙女亂馬不慎落入女溺泉,從此之後只要碰到冷/熱水,便會「切換」相對應性別。本片正是在述說如此荒誕的設定如何在現實上演,而且是限制級版,當主角迎來性高潮時,便會切換生理性別。 性別的拘束,社會所賦予的紅與藍 對於身分的焦慮,往往與社會所教育的性別認同息息相關。主角在與女孩的「女女」性愛過程中切換了身分,他對於切換後的男性性器感到厭惡,逃進廁所之中,陷入對於性別切換的焦慮,卻在早晨中以不同身分甦醒,腹部上沾滿自己的體液,意味著她也在男性身分下達到高潮。這部分有趣的是,即便面對自己所厭惡的性器,對身體的「探索」還是必然的。 物種的高潮密碼 片頭以兩隻蝸牛的交媾做為開場,緩慢而優雅。高潮是跨物種與性別的狀態。歡愉的過程雖然不同,但終點一致,沉浸於身體抽蓄與腦內啡的分泌不止。這意思是,不論豺狼虎豹或者是海豚,都跟你我一樣渴望瘋狂做愛,但過程的差異也會使體驗完全不同。本片透過迷幻的鏡頭語言來演繹高潮過程,而歷經歡愉後切換身分,似乎也暗喻著物種透過高潮來達到成長;人類的確靠著做愛,活到了兩百萬年後的今天。 主角與女孩的關係結束之後,在派對中看見了外型俊美的男孩,透過鏡頭的凝視,主角耐不住對肉慾的渴望,卻在搭訕過程中得知他是同性戀,便運用自己的「特性」,偷偷切換了身分。這部分是個轉折,意味著主角在探索過後,最終認同自己的身體。當性向與性別「正確」,兩人對上了拍,主角使男孩達到了高潮,殊不知男孩與主角一樣,擁有切換身分的能力,主角呆望著「女方」走去,性別與性向的「正當性」又瞬間一掃而空,場面荒謬有趣。 亂馬絕對不只有二分之一 《SWITCH》運用詼諧的敘事,打破大眾對於性高潮與身分的狹隘理解,誰說只能藉由如同健康教育課本當中,理想的性器完成高潮,那不過是把人類感受的多樣性模板化;如同插頭與插座的關係般冰冷,社會正壓抑著我們對於性愛的想像。在荒誕的背後,本片也探討「慾望」,比起生理需求,填補性慾望上的空缺與得到身分認同更為重要,而身分之間的個體差異性需要相互理解與包容。 探索性高潮究竟是生物本能,還是心靈成長的必然?我想賀爾蒙只是其中一個要素,我們都需要一把鑰匙來解開身體密碼。
文 / 何阿嵐 原文刊載於放映週報 圖/《貝魯特三部曲:家鄉的戰火、童年與我》劇照,圖中人為年輕的喬瑟琳‧薩博 喬瑟琳‧薩博(Jocelyne Saab,1948-2019)就站在一座破落的樓房外,早在「貝魯特三部曲」第二集《來自家鄉的一封信》(Letter from Beirut,1978)時,她已經在鏡頭前出現過,旁白操著一口中東口音的英語,坐在海邊寫信,信中提到南部發生難民營和占領軍的破壞,她並且在信中說,黎巴嫩已不再存在。 「這房子象徹安穩,我無法說什麼,這麼說很憤世,但⋯⋯」 房子被煙燻,如廢墟般毀壞,薩博描述了這種情況,然後探索了被毀的房間,曾經這是她所居住的地方,在房間內準備電影,報導的工作,這座150年的樓房,是她的所有,受到以色列炮火攻擊後,幾乎炸爛到無法辦認,消失在她眼前的,是日常生活,還有過去創作的記錄。 貝魯特三部曲-關於戰爭影像的迷思 「房子也代表了我的身份,正如同所有的黎巴嫩人,失去了房子和擁有的一切,我們不知道和誰求救,也不再知道自己是誰。」鏡頭記錄了她心愛城市蒙受的破壞,黎巴嫩首都貝魯特遭受戰火攻擊,生活無法再正常運作,在這個噩夢般的風景中,所有事物都變得超現實,就像《德國零年》(Germania, Anno Zero,1948)裡的柏林廢墟,或是《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1959)再看不見的廣島一樣。 戰後出生的薩博活在充滿社會變革的時代,黎巴嫩在一戰時曾成為法國殖民地,直至二戰後重取回自主權,但法國文化一直影響黎巴嫩的現代發展,直至如今,假如你走過貝魯特的市中心,也會發現那裡依然是充滿法國色彩的樓房,街上的告示牌標示阿拉伯文和法文,行人滿口法語,黎巴嫩曾經是中東地區最具西方色彩的國度,基督教和伊斯蘭並肩,其後就是我們所知,兩者之間長達15年的內戰。就在1975年內戰之前,薩博開始擔任起電視新聞記者。 或許以Chris Marker和Jonas Mekas來描述她是一場美麗的誤解,我反而想到智利的Patricio Guzmán《智利之戰》(La batalla de Chile 1975-1979),如果前兩者是知識份子和過來人的代表,以影像和自身影響力表達他們對第三世界的關懷,那薩博和Guzmán兩人要面臨的是活生生戰火衝擊,舉起攝影機是迫切地要世人看見國土破滅,在戰爭激烈的狀態,薩博不甘止於表達政治分析,既記錄戰鬥狀態和對局勢的反思,更重要是記錄了戰爭如何影響黎巴嫩人的心靈,要影像回到了電影最原始的本質,對現實直接的描述。 紀錄戰爭讓人感到無能為力,徒勞無功,攝影機好像只不過要企圖搞清楚毫無意義的衝突。她那飽受摧殘的國家早已傷痕纍纍,內戰持續的15年期間拍成的《貝魯特三部曲》,針對這場戰爭進行一次編年史式紀錄,三部電影中,薩博除了觀察自己家園遭受戰爭破壞,她亦將目光投向衝突中的所有參與者,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以色列軍等,相對於《智利之戰》裡強調智利在人民聯盟和右派間的鬥爭,以至左派內部間的矛盾,她想超出一般阿拉伯人的理解,在幾乎所有社會紐帶瓦解的情況下,國家生靈塗炭的邊緣中,不能只針對雙方鬥爭的視覺之中。 從她在第二和第三部曲,也可見更個人化的介入,遠遠超出了戰爭影像要表現的血腥和殘忍,她要走入拍攝對像的心靈,城市深處的歷史痕跡,《家鄉的戰火、童年與我》(Beirut My City,1982)裡的貝魯特,經歷了以色列入侵,這也是三部曲中唯一正面面對戰爭對人的殘害,她提到好友在內戰中被殺害,一具具受到殘害的兒童屍體都在觀眾眼前,另一方面她也捕捉了戰爭的殘酷與悖論,電影後段深入到以色列軍隊展示其軍事實力,暴露出其無以為繼的局面,還有倖存者們面對未來無法生活下去的關懷。 薩博曾說過要通過阿拉伯敘事傳統(亦即意指像《一千零一夜》等的敘事方式,故事一環扣一環連結著),打破西方三一律敘事來觀看戰爭,她認為後者無法處理戰爭狀態,只因戰爭並非是線性式行走,對她來說更重要是在電影中尋找、表達,關於生活的想法和影像,以及生活中隱藏的一切。內戰的複雜性令她要面向雙方的困局,也指出雙方的共同性,沒有落入單純的人道主義,內戰開始時的兩年,薩博一共拍攝了7部短片,在首部曲《永別家鄉》(Beirut, Never Again,1976)中她提到「防止死亡的唯一可行方法就是去戰鬥。」她既同情雙方又感到無可奈何,士兵會因為在光天化日下殺死他的兄弟而感到羞恥,只因為兩人各自選擇在政治立場的對立面,同時拒絕放棄同情對方的能力,從而減輕了自相殘殺的戰鬥力,坦言記錄了這國家的新仇舊恨,戰爭沒完沒了,幾乎沒有想解決的辦法。電影也訪問了其中一位年輕士兵,這位年輕士兵坦白說他希望能和平相處,但戰爭從一開始就有未成年少年參與,「就像孩子們發動戰爭一樣,即使這不是由他們決定宣戰。」另一部教我印象深刻的是《Children of War》(1976)。貝魯特附近的貧民區發生大屠殺,薩博走訪區內倖存下來的孩子們, 借助蠟筆,孩子將眼見的恐怖景像畫下來,電影讓人感到諷刺的是,街上的年輕男孩和女孩們從大人學習到的唯一事物,玩著的,都是與戰爭有關。這些關於孩子的觀察,速寫般表達戰爭如何改寫生活和常理的狀態。 「在邊界和國界中有某種更吸引我的東西,在這個荒誕又充滿分歧的世界中,理想國一直在我腦海中。」戰爭影像往往會令觀眾失去對現實的理解,薩博很明白戰爭影像的殘酷性其實會吸引觀眾,但因此無法了解戰爭的更大成因。所以,作為身處於第三世界國度的創作者,她也將矛頭指向西方世界,在她其他紀錄片中,通過攝影機,出現了脫離了東方主義的觀念,又豐富了地緣政治身份的敘述。不過,她指向西方的目的並不是指責內戰的成因來自於他們,她意圖將黎巴嫩的問題上升到全世界的問題,她的信是寫給全世界所有觀看電影的人,甚至是那些明顯反對她政治信念的人,她的出發點是為了達到公正,真正的和平,她要攻擊的對象是失去同理心的人,即使在戰爭的激烈環境之中,面對敵人的狀態也好,也要保持著。對她而言,失去對其他人同理心的能力,只會注定走向失敗。 盛世的鄉愁與戰爭歸來 如果「貝魯特三部曲」是刻劃國土的安魂曲,那麼內戰完結後不久拍成的《貝魯特狂想曲》(Once Upon A Time in Beirut, Story of a Star,1994)如譜出一首鄉愁曲,在電影誕生100年之際,重訪黎巴嫩的電影黃金歲月,也是對貝魯特這座城市的一次敬意。 內戰期間,整個電影工業幾乎停產,有部份拍攝商業製作的電影導演如Maroun Bagdadi投入紀錄片,也有如薩博和Heiny Srour的初生之犢舉起攝影機紀錄,不過黎巴嫩電影其實早於1929年已拍攝首部無聲電影,在二戰前都以獨立製片的方式運作,未建立出電影工業。可是在60年代,因為埃及電影業國有化後,許多私人製片人,發行人和導演都搬來黎巴嫩,受惠於中東地區的電影市場,開始有商業電影製作。沒有民族包袱,相對開放的創作環境,其中,他們就製作過一系列帶有性解放意味的劇情片,成為阿拉伯世界第二大電影業。更在70年代,成為全部阿拉伯語國家中,電影入場人數最高的國家,更不要說這是西方國家電影製作喜愛的取景之地。 《貝魯特狂想曲》正是回望這段被稱為黃金年代的時期。和平時期的薩博讓我們看到她玩味的一面,遊走在現代和電影世界的場景,略帶輕喜劇的節奏,還有虛實形式,兩位女孩時而扮演記者訪問,又會重演電影演出,薩博借由兩位年輕女孩參觀一家老電影院開始,從開創阿拉伯電影製片人的鏡頭到1930年代法國導演的電影,再到70年代美國電影,回到60年代的貝魯特,隨著在銀幕上遊走,瀏覽過去電影,揭穿這座有「中東小巴黎」稱號之城市的神話故事,再不是與戰爭扣連,一個曾經繁盛、多元文化的國度,有參考好萊塢浪漫電影,亦有東方色彩濃厚歌舞片,薩博重組這一系列影像,最後所寄望的是國家從紛爭不斷的狀態中回到正常的生活。 但黎巴嫩和平時期很快就消失了,2005年的雪松革命,其後的以色列與黎巴嫩衝突,巴里德河衝突影響了當地局勢,近年更因敘利亞內戰,大量難民逃亡到黎巴嫩,成為了該國的負擔,一個個難民營在貝魯特外組織起來。雖然在文化上,敘利亞人都嚮往到黎巴嫩,例如敘利亞著名詩人阿多尼斯(Adonis)就曾在黎巴嫩大學教授阿拉伯文學,很多為了生計的敘利亞人在戰亂前就已經走到貝魯特尋找工作,但兩國多年在政治上敵視對方,如今超過200萬難民湧入,令原本只有100萬人口的黎巴嫩一下無法應付。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都在等待離開到西方國家的機會,大人無法合法工作,小孩並非每一位都有讀書機會。不少敘利亞人所居住的市中心舊城區或貧民區,與早已商業化、帶有西方城市風貌的首都中心,形成極大差異。薩博對此的觀察在短片和同名攝影作品《One Dollar a Day》(暫譯《一天一美元》,2016)中。 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營」並非由當地政府資助,而是由聯合國或部分西方國家負責,薩博將著眼點落在難民營的帳篷上,而這些帳篷往往由巨大廣告篷布剪裁而成,篷布上都是迷人的香水,項鍊和奢侈品牌的廣告,薩博不只拍攝了難民營,還拍攝了大量難民肖像,象徵著資本主義的拼貼畫以及受戰亂傷害者同在一個畫面內。她又用吊車將他們送到貝魯特山上拍攝,在這片城市風景背後,她問了一個問題,「一個人每天可以只能靠一美元過活嗎?」薩博不單要為這群人發聲,更要讓電影向不公義的事和人開火,視所有人為一體,就像她在《貝魯特三部曲》時所做的事一樣,讓人類成為善良和理性的代名詞。她沒有停止過思考影像,她的電影雖然一直描寫現實狀態,但內裡帶有詩意,也一直在質問世界、暴力,邊緣者的生存狀態,晚年的薩博除了拍攝電影,也投入攝影和裝置藝術創作。 而她最後作品,是只有7分鐘的《My Name is MEI SHIGENOBU》(暫譯《我是重信五月》,2018),這部影像創作關於一位「恐怖份子的女兒」——逃到黎巴嫩的日本前赤軍份子,重房信子的女兒重信五月。可惜這部作品並沒有在這次影展中上映,關於重信五月母親,這一位曾堅信「武裝鬥爭是最大的宣傳」,「世界革命將會發生」,並策劃過恐怖行動的左翼份子,對於這位旁人眼中的恐佈份子,作為女兒會如何想,而以生活、身體、攝影機親歷戰爭與衝突多年的薩博,又會如何想?此亦令人好奇。
文/原文刊載於性別力 多莉安過著普通的生活,直到有天發現乳房腫瘤,開始變了調。為你精選女影影評《多莉安的幸福人生》。 聽我說話好嗎 圖片|女影提供 身為一位母親、一位妻子,跟一個女兒,多莉安成長為家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依靠,那之後,似乎就不得不扮演好堅毅存在。她不能讓眼淚恣意流淌,她必須讓疲倦藏匿在面容的縫隙裡。在家人面前,她能表達情緒的最大出口,只有裝瘋賣傻,與其讓全家和她一起哭,她寧可對著外人毫無包袱地崩潰解放。多莉安知道她的「能」與「不能」不由誰限定,不過卻要等到風波接連襲捲生活,她才真正明白只有她自己能夠主宰自己的生命來去。 另一種母親與妻子 <span style="letter-spacing: normal; caret-color: rgb(66, 66, 66); color: rgb(66, 66, 66); font-family: " pingfang="" tc",="" "heiti="" "noto="" sans",="" "source="" han="" verdana,="" helvetica,="" "microsoft="" yahei",="" jhenghei",="" sans-serif;="" font-size:="" 17px;=""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不失幽默的筆觸與細膩地情感描繪,把紛擾的家庭問題提升至更加沉著穩當的層次。多莉安所面臨的問題不只關乎生命,也關於生活的一切。就像是或大或小的水流都不免在經過之處留下紋痕,多莉安不得不因此重新雕琢人生的樣貌。人際關係的不可逆與身體的不全然修復,只得由自身心態轉變,才能再次尋得自我的平衡,找到自己在世界裡的位置。
文/吳淇瑋 原文刊載於LEZS 從低頭探看自己裸露的身體到女聲重疊詢問,提出問題的同時將自己的身體撕扯開,最終以成體走回陰道裡。這是紀錄片《尋找乳房》的開頭動畫,也是女性在思考、面對自己身體的過程。 乳房,性徵中最先「被看見」的部分,不論型態都帶來社會的凝視和自我質疑。開始被教導「把胸部包好」的羞恥感,遭受到「身材不完美」的批評,如果說乳房的發育是外部的攻擊,月經的到來就像內部的戰鬥。常見的經痛、下體的不適、月經突然造訪的恐慌和「只有我莫名其妙在流血」。女性被迫參與這場戰役,而戰爭留下的痕跡深深淺淺,只有重新定義、接納才能彌平。 除生理特徵的不同,女體也總被凝視、被當作物品,胖、瘦、年輕、年老,懂得反抗後面對自己身體的面貌卻分不清究竟真的想要,還是社會價值已侵蝕思考能力?想要男性的形象、想要強壯的形象,部分女性脫離傳統言情框架邁入BL(Boy's love)世界。 歌曲《七點二十分的反省》裡寫到「棒球國手對不起/妄想投手捕手打擊手的三角關係/忘了加油輸掉比賽真是對不起」,在BL世界裡我們妄想男性的身體、戀愛,把對女性的要求全數拋開。身體平等所創造的戀愛故事在近年得到相當大的關注,但另闢蹊徑拋棄原有的載體,想像的世界是否真能擺脫父權積習則成新課題。在新世界裡我們的抵抗吶喊終須回到現實努力,認同自己仍是每個人無法擺脫的課題。 「他們看到的不是我這個人,他們看到的是一個裝寶寶的……女人。」 「母親孕育生命」、「母愛自然流露」、「母性光輝」,社會對母親的形容預設女性成為母親的必然、必須,也對母親會付出所有給自己的孩子毫不懷疑。偏離、背離此道的女性遭受洶湧質疑,但在成為母親之前,她先是一個個體。 面對生理的連結、被忽略的自主,女性和自己身體的距離總是忽遠忽近,於是我們探尋生命的根源、聆聽生命的故事,從尋找乳房到尋找自己。
文/譚以諾 原文刊載於映畫手民 台灣女影今年邀請了客席策展人卓庭伍策劃亞洲「女性復仇」影片的單元,突破性地選入了男性導演孫仲和男性編劇司徒安的作品《沙膽英》(1976)。據說,女影甚為執着電影製作者的性別,這次選入男性電影製作者的作品,實有助擴闊觀眾對「女性」電影的理解。至於論到女性復仇片,選邵氏兄弟的出品着實是不二之選。以往提及邵氏的女性復仇片,較少會點到《沙膽英》,往往會談論的是更前的《愛奴》(楚原,1972)或同年的《毒后秘史》(孫仲,卓庭伍在她的策展人語有所提及)。 《沙膽英》向來被視為「女版大哥成」,一來是因為《成記茶樓》(桂治洪導演,司徒安編劇,1974)和續集《大哥成》(桂治洪導演,司徒安編劇,1975)中的主角大哥成(陳觀泰飾)在片中擔任角色吃重的男配角,甚至在最後的「復仇」中與女主角馮英(陳萍飾)並肩作戰;二來,更重要的是,《沙膽英》中的「沙膽英」馮英的角色設定與大哥成有所類同:同是武力非凡,同是赤誠而會照顧弱勢,同是仗義而願意與同道中人團結抗敵,亦同是在香港七十年代法治未彰、庶民要自求多福的類現代社會中爭扎求存的英雄人物。一如《鐵娃》(羅維,1973)中的鄭佩佩被視為「女版李小龍」,「沙膽英」亦因而被視為「女版大哥成」。然而,策略人卓庭伍把《沙膽英》放在女性復仇的單元中,則把這展濃厚的男性陰影抹去,讓我們得以從另一角度和另一條歷史脈絡去觀看《沙膽英》。 若論到邵氏兄弟的女性復仇影片,不得不提《毒女》(何夢華導演,邱剛健編劇,1973),而在討論《沙膽英》時更是必須提到這影片。這不單因為《毒女》算是香港電影中女性復仇片的元祖之一,亦是因為兩片的女主角同是台灣來港發展的陳萍。她因着在《毒女》和《風流韻事》(李翰祥,1973)的大膽演出,在其時香港的「肉彈」潮中突圍而出。《毒女》與《沙膽英》一樣,同是以女工當主角,但是《毒女》中陳萍飾的楚玲並未演化成「沙膽英」,她在一夜不幸被五人輪姦,並染上性病「越南玫瑰」(在求醫時固然要裸露一下,差點又遭醫師毒手)。影片及後帶點《愛奴》的影子,楚玲投身酒吧,當陪客,誓要找出施暴她的人復仇。後得酒吧老闆王達(羅烈飾)授她功夫,最後二人合力殺死施暴者,楚玲亦在血戰中身亡。 《毒女》的情節安排是典型的強姦復仇類型的套路:弱女受害,確定復仇意志,武裝自己,血戰殺敵。然而,情況在《沙膽英》一轉再轉。電影開局看似是《毒女》的套路:陳芳(莊莉飾)新入職即遭工廠女惡霸威迫,要與她「交朋友」(意指同性性愛),陳芳差點像《毒女》中的楚玲般,在工廠的廁所中被強姦。此時,陳萍飾演的「沙膽英」突然闖入,以拳頭屈服了惡霸,救了陳芳,使陳芳和細珠(邵音音飾)想要與她做朋友,學習她的「沙膽」。我們可以從「沙膽英」出現的一幕,看出陳萍這位演員作為互文的轉變:她在《毒女》中是長髮而顯柔弱(一如莊莉在《女膽英》的造型),但在《沙膽英》中則是短髮配以運動長衫長褲,一副陽剛的模樣。從互文上的陰柔到陽剛,我們已得知「沙膽英」已非楚玲;而從情節上的安排看,「沙膽英」救走陳芳後,影片就不走強姦復仇類型的套路了。 在此,《沙膽英》就遇上了《成記茶樓》。《成記茶樓》被論者喻為香港電影史上首批「黑社會/黑幫」電影之一,它不單講述大哥成的義氣,描繪着成記茶樓中兄弟相助的類社團組織,還真實地呈現社團的儀式, 這些元素成為日後香港黑社會電影的參照。《成記茶樓》和《大哥成》中的成記茶樓,是大哥成及其兄弟的據地,甚至可以看作是七十年代香港庶民社會的縮影:因制度腐敗,庶民難以依賴法度,則維有自強而共濟,以在弱肉強食的香港社會中生存。 《沙膽英》取了《成記茶樓》和《大哥成》的外殼,但其關心卻不在社會與法度,而是毫無疑問地指向女性(甚或是女工)在男性主導的香港中的生存狀況。眾所周知,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實有賴一眾女工及其撐起來的輕/重工業。然而,女工在七十年代的香港中,不論在社群上、經濟上、家庭上,還是性別上,都是處於裸命狀態。電影中有一幕是細珠和陳芳聚在馮英的住處中,各自細訴自己的辛酸史:陳芳和細珠一個是「油艇女」(母喪夫再家),一個是孤女,都不得家庭的照料,隨時可被家庭棄置;陳芳亦述及她在工作上各種不合理的待遇,如茶客和老闆的非禮,亦見其在經濟和性別上的裸命狀態;馮英現在如此強悍,原來曾待過黑社會,跟過「大哥」,在賭檔為「大哥」出千騙財,卻因不想作惡而被逐並被追殺(被驅趕於社群之外)。面對這個狀況,她們選擇結拜為姊妹(取代家庭),並積極地在工廠與其他女工互動,結成女性共同體(取代社會上的社群,經濟上互相援助,肯定性別上的位置)。這裡的共同體與圍繞着大哥成的社群有別:前者是針對經濟、家庭和性別的;後者是針對社會法度的。 因此,《沙膽英》與香港典型的女性復仇片有所不同。它不是單人匹馬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也不是武裝自己來自強和復仇(這實與香港武俠/武打片於六、七十年代興起有關,有機會另文再述),而是透過構作共同體而成的,而這共同體不只限於結拜的三姊妹,而是擴而至同一階級的「工廠妹」(女工)。而事實上,這共同體也不只限於女工,在結尾「沙膽英」身陷險境的一幕,女工聯同大哥成一同到場救人。這在在說明女性共同體的包容性質,而這點,則是透過兩位男導演和編劇之創作道出來的。 如此,《沙膽英》在女性復仇的脈絡中,不再是「女版大哥成」,反倒是,《沙膽英》透過「沙膽英」這人物及一聚團結的女工,把大哥成納入其中,一同在社群、經濟、家庭和性別上,改變可被廢棄的生命的裸命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