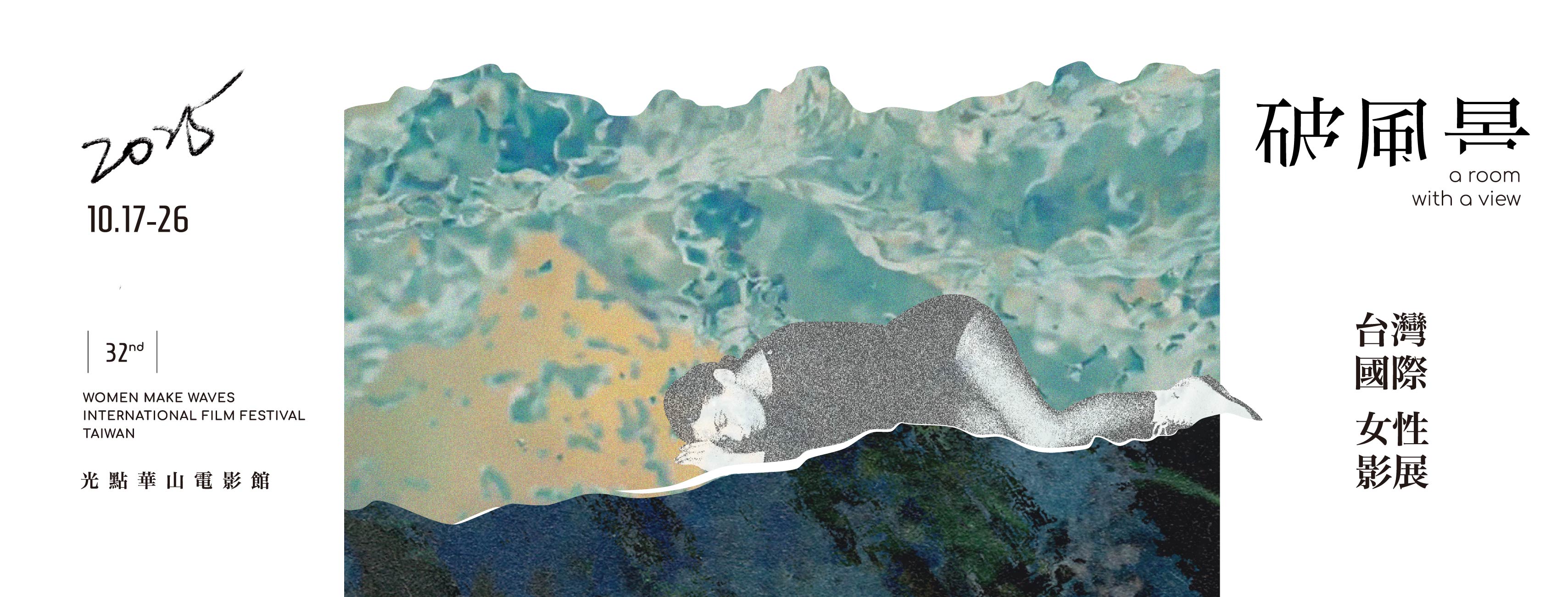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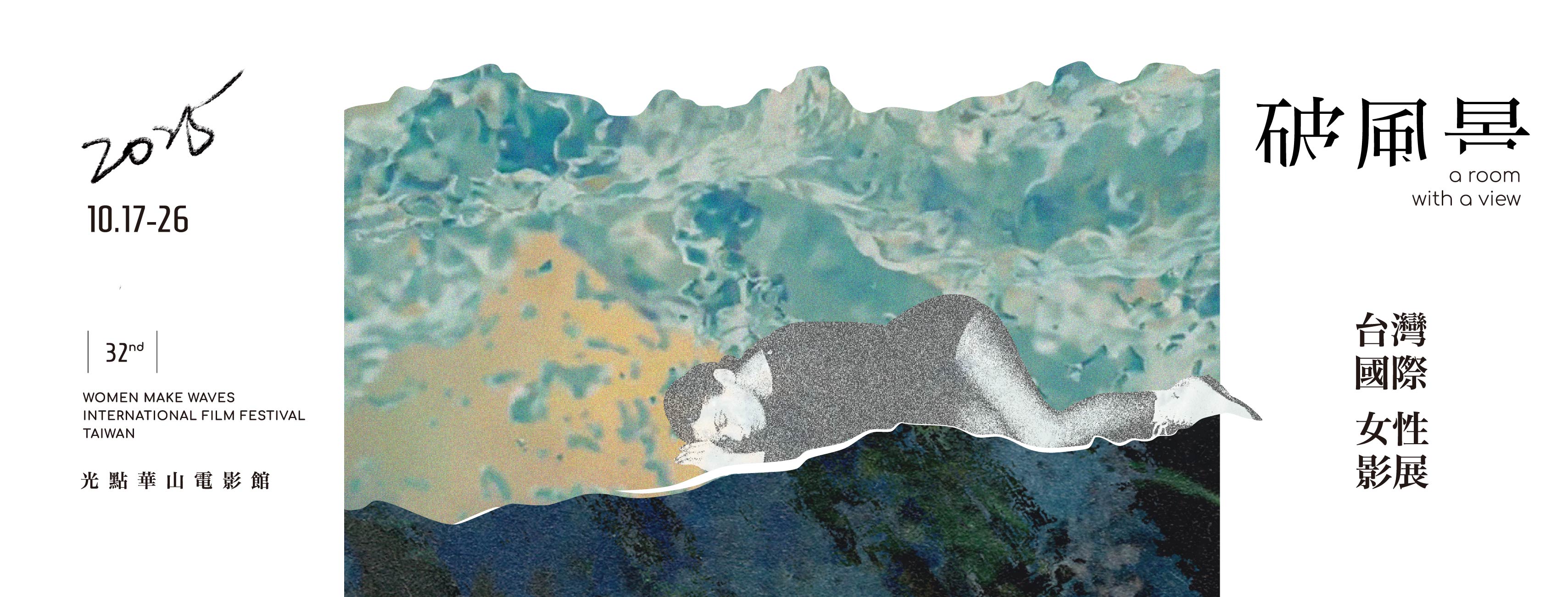
2020 女性影展看什麼?每一個她他,那些未命名的成長游移/BIOS monthly 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10561 釀特務|女影 2020|台灣競賽單元:新世代的「沒關係」青春/釀電影 https://vocus.cc/filmaholic/5f6189a7fd89780001e6ab78 《游移之身Moving In Between》觀影心得:游移流衍間,往復織就日常/濡沫 https://lezismore.org/wmwff_2020_moving_in_between/ 【2020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在冤魂與英靈以外──《宵禁》的同志敘事/映畫手民 https://www.cinezen.hk/?p=9330 越南看護在台逃跑4094天!資深導演跟拍她6年真實生活,驚見最強大人性:覺得我們都輸了/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3092350?mode=whole 這128個骨灰罈全是「拋棄式勞工」悲歌!她拍下越南移工最痛身影:想給家裡好的生活,怎麼會變這樣?/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3092356?mode=whole
文/CJ Sheu 原文刊載於The News Lens The four shorts selected as part of the “Queering Voices” section at the 2019 Women Make Waves Film Festival offer an eclectic array of sexual and gender experiences. From a classic character study to an off-the-rails allegorical comedy, this combination of short films is far from predictable. Photo Credit: Mathias / 2019 WMMFF Mathias (Austria, 2017, 30 mins.) Mathias follows the transgender title character (Gregor Kohlhofer) as he takes his first post-op job at a logistics warehouse with a group of bros. Co-written by director Clara Stern and cinematographer Johannes Höß, the plot contrasts the attitudes of the people in Mathias’s life: Marie (Magdalena Wabitsch), his girlfrien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nsition; friendly coworker Emir (Ahmet Simsek), and “I’m a tolerant guy, but” coworker Andi (Michael Edlinger). Without being didactic about it, the film explores how changing our entire identity can turn willing companionship into bonds of obligation, and how even supportive gestures come with unsaid pressures. The script emphasizes Mathias’s masculine work environment and how he struggles to pick up the bro code, so it’s ironic that he’s so good at manfully refusing to communicate with Marie. Kohlhofer’s shy, alienated performance grounds the film in Mathias’s subjective viewpoint, and we palpably feel his relief when someone finally treats him like just another person. By the end Mathias has less in his life, but what he keeps is more meaningful. Photo Credit: Switch / 2019 WMMFF Switch (Belgium, 2018, 18 mins.)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Marion Renard, Switch has so much going on that it could easily be expanded from an 18-minute allegory into a 90-minute fantasy, and could probably support a franchise, too. Riffing off of the book Esmera by Zep and Vince, the film is a sensual beast, voraciously consuming all our attention and awe with its audacious premise, explicit sex, frontal male nudity, and body horror. It even boasts a pop rock soundtrack. There’s a glaring continuity error near the beginning, but pales in comparison to what comes next. Concluding the first third of the film is a nightmare sequence shot in bold red and black by cinematographer Lisa Willame and edited like a Darren Aronofsky climax by Mailys Degraeve. I can’t say a thing more about its plot without giving it away. I can’t even tell you how many actors there are, aside from the protagonist (Nora Dolmans) and her love interest in the festival program photo (Manon Delauvaux). Rest assured, every performance passes muster. The moral, if you’re looking for one: Accept yourself as you are, and life will surprise you. Photo Credit: A Great Ride / 2019 WMMFF A Great Ride (USA, 2018, 33 mins.) A three-pronged documentary about two aging lesbian communities and another lesbian still seeking hers, all in California. Apparently in the heyday of the ‘70s, California boasted numerous lesbian communities, men-less places outside the patriarchy, one of which is “Woman’s Land,” Willits County, whose population is aging out. Sally Gearhart and Susan Leo, the oldest and the youngest respectively, guide the film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place, and its uncertain future. Sue Lebow and Patty Rhodes recount how they moved to the retirement community of Oakmond and started the Rainbow Women lesbian group, now with about a dozen women. And Brenda Crawford was priced out of Oakland to the small town of Vallejo, where she gradually accepts that this is where she’ll spend her last years and starts to engage with the community. Directors Deborah Craig and Véronica Duport Déliz know how to keep things lively. The technique for each prong of the film is the same: witty and thoughtful talking-head interviews intercut with archival and B-roll footage (energetic editing by Ondine Rarey). When the pace starts to slow, that’s when Bradley Dujmovic’s quirky soundtrack comes into play; there’s also frequent and always justified use of the Sue Fink song “Leaping Lesbians,” which just gets funnier each time you hear it. Even when the film’s subjects are contemplating death, the joy of their lives is still radiant. Photo Credit: Hotel Oswald / 2019 WMMFF Hotel Oswald (Netherlands, 2017, 22 mins.) Finally there’s writer-director Kim Hotterbeekx’s Hotel Oswald, a style-over-substance horror showcase with beautiful art direction (by Lukas Bruns) and a slightly problematic script. Helen (Sophie Höppener) arrives at the titular hotel to await her girlfriend, Naomi (Rozanne de Bont). The creepy concierge (Toon Konings) stares at her without blinking as she signs in. Naomi arrives, and the two women share a romantic evening. In a dream, Helen sees Naomi walking away from her, but she’s still there beside her in the morning. Helen goes to buy a smoke. Then weird things start to happen. Like Get Out (2017), the film plays on the ambiguity between garden-variety hatred and actual freaky shit. There’s a slate of standard horror tropes — like the transformed room, the empty town, and the unsettling score (by Rico Derks) — but there’s also more psychedelic-horror stuff, such as a perpetually burning tree (VFX also by Derks). All of this madness is kept in coherent shape thanks to the collaborative editing by Hotterbeekx, Derks, and cinematographer Jasper van Gheluwe. It’s ambitious, maybe too much so. In its allusion to a major 20th-century historical event, the ending offers a somewhat logical explanation that struck as a bit overwrought. This review is based on complimentary media screeners provided by the 2019 Women Make Waves Film Festival.
文/瓦西里莎 原文刊載於云閱讀 一個國家的狀態究竟會如何影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處於人生某刻的我們無法切實明白,總要到驀然回首才驚覺自己因深陷漩渦而觸發的太多思索與困頓;或者,我們藉由一位紀錄片導演的眼睛,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試著去理解一群同樣處於渾沌青春的人們。 《愛在德涅斯特河畔》是瑞典導演安娜・艾朋(Anna Eborn)獲得2019 鹿特丹影展大銀幕單元首獎的作品,她被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國的青少年吸引,用16釐米的膠捲為這部電影打造了濃厚的懷舊感,彷彿凝滯於上一個世紀,就像這裡的政治狀態一般。 講一個戰爭故事太過無聊了,談一個不被聯合國承認的國家又顯得沉重,她謹慎地紀錄片中五男一女的日常,在日復一日的玩耍、嬉鬧、交往、分手中度過,在這裡似乎不需要考慮明天,不是因為明天不需要擔心,而是在這個國家的人們已經習慣了未來的空白。導演依然稍稍揭示了這裡的「蘇維埃日常」,片中的女孩譚雅有個五年級的弟弟,他加入了軍校,典禮上歌頌著社會主義的美好,他們對於未來可能的戰事毫不畏懼,即使為國捐軀都是一種光榮。今日德涅斯特河岸的國旗仍有錘子與鐮刀,也能看見駐紮的俄軍,與其建交的國家也都是世界上的爭議地區,彷彿不被承認的集體哀愁。 譚雅必須離開,她明白自己在這裡沒有未來。 不同於許多紀錄片有訪談畫面或導演的提問,本片導演就是記錄著,她說她不是記者,青少年的瘋與真在導演的特寫鏡頭下格外衝擊。譚雅是這群青少年中唯一的女孩,她想與誰一塊就與誰一塊,男孩們追逐著她,想了解她的喜好,為什麼喜歡誰,又為什麼討厭誰,她跟他們學游泳、清理身上的疹子,他們粗魯、玩世不恭,與背後廢棄的住宅與老舊設備如此相斥卻又填塞了他們的日常。在這個三不管地帶,一切竟如此和諧,片中托亞的媽媽說摩爾多瓦語或羅馬尼亞語,譚雅的媽媽則說烏克蘭語,也有人說俄語,這幾種語言就如同這個地方面對的勢力衝突,但它狹長的國界彷彿隔絕了境外的紛擾。 譚雅必須離開,她明白自己在這裡沒有未來,即便所費不貲她仍然想飛,而留下的這群男孩將會失去他們日日追逐的人。最後托亞唱著,「我對你滿心憤懣,你是否真已將我忘卻?我擔心我不會回到你身邊。我恐怕不會回到你身邊了。」這群青少年在情竇初開的年紀嚐到了不被愛與分別的苦澀,他們在這個不被承認的地區並沒有明顯地表現出憤世忌俗的情緒,唯有的僅是一句關於普丁的玩笑,他們被時代浸染著,愛情伴隨的失落和成長的陣痛與這個環境帶來的無望緊密貼合。 一個國家的長成如一個人的人生一般,總是會經過些許衝撞,必須與其他的個體磨合,自身也有許多的問題必須解決,在尚未成熟之前,也許會經歷一段渾沌時刻,摸索適合自己的模樣,也許會愛誰而不得,也許會在與他人相處的過程中受傷,甚或有了自我傷害的行為,這些都將成為一個人成長的印記,也是一個國家從新生到成熟的必經之路。身在台灣的我們或許會覺得自己已看過了許多政治上的大風大浪,也習於強凌弱、弱弱再相殘的狀況,然每個國家與民族必然有屬於自己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在觸碰他們的前世今生時,或許該小心自己草率而高傲地評斷了他們。
文:(OR)伊森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網 「旅程,與電影製作,都應該將我們引領到從未到過的地方。」 –安哲羅普洛斯 經常深入烽火之地,書寫阿拉伯之春與中東戰地現場的香港女記者張翠容,2015年發表的著作《另一片海》,標題即來自已故希臘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生前未完成的同名作品,同時也是「希臘三部曲」的最後一部。 而由法國女導演艾洛蒂蕾露(Elodie LÉLU)執導拍攝的紀錄片《尋找安哲羅普洛斯》的動機也是出自《另一片海》。 艾洛蒂蕾露一方面透過這部紀錄片追憶安哲羅普洛斯,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安氏拍攝的《另一片海》,與其親身參與大師電影的吉光片羽。 張翠容因安哲羅普洛斯而踏上地中海、踏上巴爾幹的國際採訪之路;艾洛蒂蕾露則因安氏的一通電話留言,買了一張前往雅典的單程機票,展開了與《另一片海》和安哲羅普洛斯的親密對話。 導演消失,人去樓空,徒留下陰鬱灰濛的天際線,與鏡頭不及攝下的比雷埃夫斯港日常。 Photo Credit: IMDb 《尋找安哲羅普洛斯》的第一幕,來自安哲羅普洛斯1995年的《尤利西斯的凝視》,導演艾洛蒂蕾露特意引用劇中主人公的猝逝,來象徵2012年1月24日安哲羅普洛斯的親身經歷。那一場車禍猝不及防地奪走了安哲羅普洛斯的生命;更準確地說是歐債危機,是他一生關心與投注的國族歷史,帶走了他的生命。 透過《時光之塵》(The Dust of Time)女演員伊蓮雅各(Irène Jacob)的旁白,畫面從《尤利西斯的凝視》轉向人去樓空的拍攝現場;長鏡頭對準的灰色天際下,是城市的破敗景象。 安哲羅普洛斯在他「希臘三部曲」最後一部作品《另一片海》裡,原來即瞄準(與預示)了希臘的難民問題。在這部寫給比雷埃夫斯港難民日常的作品裡,艾洛蒂蕾露捕捉到猶如《霧中風景》(Landscape in the Mist)那對小姊弟抬頭望著飄雪的鏡頭,藉以緬懷安哲羅普洛斯。 Photo Credit: IMDb 安氏劇作成了今日希臘的日常。 如果《霧中風景》是越不過的滄海,那麼《另一片海》則是到不了的彼岸。「導演之死」貫穿了《尋找安哲羅普洛斯》整部紀錄片,艾洛蒂蕾露則寧願用「消失」(disappearance)來形容安哲羅普洛斯的缺席。從《尤利西斯的凝視》預視了自己的生命終結,到《另一片海》預示了今日希臘人的日常生活,這些都是艾洛蒂蕾露透過書信紀錄,想一一還原,並解析給觀眾知曉的訊息。 「狄奧,你的來訪總讓我們感到不安。每次來視察工作進度,你總想把貧民窟加大兩倍甚至三倍;最後你卻沒能在這裡拍片。你的劇本已經成為了希臘的日常。」 今天,就在電影拍攝場景的幾公尺外,難民被撤離到港口的另一邊;邊界關閉了。還有更多生存與現實問題天天在希臘、在比雷埃夫斯港上演。艾洛蒂蕾露只能想像,如果安哲羅普洛斯還在,那些移民們的掙扎,是否和當初拍攝的《另一片海》一樣,過了這條藍色的線就出了希臘。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鸛鳥踟躕》 劇中有一幕來自《鸛鳥踟躕》的劇情,男子站在邊界上,當他跨越了藍色的邊界線,或是身在「他方」、或被「射殺」。安氏過去的電影題材,如今不斷地在現實生活中搬演,「他方」是什麼模樣?或許正是安哲羅普洛斯始終透過電影在探問,並期望和觀眾一同抵達的彼岸。從「導演之死」到「另一片海」的揭露 艾洛蒂蕾露短暫地參與了安哲羅普洛斯的《另一片海》拍攝過程,卻從安氏的電影裡找到了這位電影大師面向歐洲,背負國族歷史,永恆地追尋他方等命題。 「我想,若我能認識自己,就會停止拍攝電影。」 「我拍電影是為了認識自己,認識這個世界,也為了尋找平衡。為了理解,這樣的信念得以支撐我,憑藉如此的好奇心,還有源源不絕地,旅行的慾望。」 《尋找安哲羅普洛斯》結尾,安哲羅普洛斯現身說出了上述這段獨白,一如艾洛蒂蕾露當初所踏上的旅程。如果沒有安哲羅普洛斯,她便不會隻身前往雅典;日後也不會佇立在希臘街頭,望著安氏始終在等待的陰天,和日光底下那些失魂的臉龐。 是《另一片海》,引領我們到往未曾去過的「他方」。
文/米恩 NPOst 特約記者 原文刊載於NPOst 現代社會,女性同時擁有美滿家庭、一番成功的事業,就稱得上達到男女平權了嗎? 事實上,很多女性常常在家庭和工作中分身乏術,職場挑戰重重,家中負擔往往沒有調整的餘裕。被期待成為一個好妻子、好媽媽、好員工或好主管的多重身分之下,家庭或工作成為職場女性面臨的第一重抉擇。 此外,在許多男性主導的工作環境中,職場性騷擾、性暴力揮之不去,即便被討論了無數次,相同的情境卻仍在日常生活中不斷上演。 她們或為了生活選擇隱忍,或因為缺乏性別平等意識,而未將自身幽微的困境和職場性暴力連結在一起。直至更嚴峻的事件發生後,說出來還是保持沉默,成為職場女性面臨的第二重抉擇。 正是職場性暴力界線的模糊、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性別意識的缺乏等等,在職場上受到侵害的女性,有許多仍像《歐娜的抉擇》當中的主角--歐娜,一步步落入主管設下的困局,甚至在被侵犯後,也仍然無法辨認:「我是否被性侵了?」 階級與權力 幽微的職場性暴力 歐娜丈夫新開的餐廳還未盈利、家裡有 3 個未成年的孩子要撫養,對於職場女性歐娜來說,她不僅需要賺錢養家,也需要一個更好的發展前景,主管班尼給了她這個機會。 大部分職場性騷擾來自主管,或是位階較高的同事、業界名流等,這種權力關係的不對等,讓歐娜陷入困境。歐娜的困境,也是各個遭遇職場性騷擾女性的困境,只是在程度和形態上有所差別而已--未經同意的撫摸、過分靠近、騷擾簡訊、糾纏不清、黃色笑話、具有性別意味或歧視的言詞,或是以升遷為由、以解僱要挾、以其他形式的交換,要求發生性行為。 似乎從一開始,歐娜就未被尊重。相較於出色的工作能力,主管班尼似乎更在意歐娜的外形 ——「妳把頭髮放下來會更好看。」、「妳有漂亮的裙子嗎?」 但僅憑這幾句話就斷言是職場性騷擾,又未免有些小題大做。於是歐娜聽從了主管的建議,她想著隔天要和客戶開會,她確實需要更有品味的衣服,她也放下了長髮。但,班尼卻在會後強吻了她。 臺灣《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 條將職場性騷擾定義為兩大類:敵意工作環境的性騷擾,與交換式性騷擾。同時,第 13 條規定,僱傭 30 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和懲戒辦法。 然而,當職場性騷擾真實發生時,很多女性還是會選擇隱忍。一方面,她們不願意失去工作,另一方面,職場性騷然的幽微模糊也讓很多女性難以舉證,發聲後,反而可能遭受更多的性別暴力。 「妳怎麼這麼開不起玩笑?」「是不是妳太敏感了?」「是妳別有用心勾引主管?」「誰叫妳平時喜歡搔首弄姿!」 正如影片中歐娜的遭遇,被強吻後,她在第二天綁起長髮,並在上班的路上,看著街上的玻璃櫥窗整理儀容,抹掉一點口紅、將領口拉緊。但歐娜並未採取強勢的態度,她只對班尼說:「或許你誤會我了。」而班尼回以道歉與承諾:「不會有下次了。」這件事就宣告落幕。 接下來一段時間的平靜,讓歐娜以為一切沒事了,但她心中仍有顧忌,直到班尼讓她升遷的那一日。歐娜很高興自己的能力被認可,她卸下心防,接過班尼看似善意遞來的,剝好的橘子,她在一開始是拒絕的,她想著也許這個「霸道總裁」真的只是把自己當做一個工作上的「完美搭檔」。 歐娜在升遷后更努力工作,班尼卻沒有罷休。雖沒有類似強吻或撫摸的實際行動,但他會在晚上突然關掉辦公室的燈,在歐娜慌張不已後卻指責她開不起玩笑;他故意去歐娜丈夫開的餐廳,展示作為主管和男性的階級與權力;最後,他要求歐娜和自己單獨去巴黎出差。 性暴力過後--我被性侵了嗎? 即便為難,歐娜還是和班尼去了巴黎。巴黎很美,業務也談得順利,兩人都很開心,於是一起喝了點酒慶祝。 之後,場景來到飯店的走廊,他們原本是要各自回房休息的,但班尼藉口拿錯房卡,打不開房門,歐娜幫他開了門,道了晚安,轉身欲離開。這時,班尼突然把她推進了自己的房間。 「歐娜,你讓我慾火焚身。」 「不要!班尼。」欧娜雖然反覆拒絕,但她沒有激烈反抗,因害怕而全身無法動彈。班尼侵犯了歐娜,射精在她的裙子上。女性被性侵時的反應,有時不是強烈抵抗或逃跑,而是因害怕而出現短暫性麻痺交。 什麼叫「妳讓我慾火焚身」?歐娜允許了嗎?歐娜需要為主管的慾望負責嗎?她是一個員工,她為她的業務負責,而不是為著主管的慾望。 回到以色列後,歐娜心神不寧,噩夢連連。母親看出她的不安,歐娜告訴母親,自己在巴黎出了點事,她犯了一個錯誤。歐娜還來不及說明情況,母親就匆匆安慰她,人都會犯錯,她在巴黎沒守住界限,但一切過去了。 歐娜覺得事情並非如此,但又對沒有堅決反抗的自己感到困惑。直到後來她向丈夫坦誠,歐娜仍然沒說是班尼性侵了她。 「他掏出他的傢伙,結果沒成。」這是歐娜對丈夫的解釋。她說自己喝酒了,即便她說自己沒醉……丈夫指責,「為什麼沒揍他?為什麼留下來?」 「我不知道。」歐娜如此回應。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但歐娜是自願的嗎?歐娜喜歡班尼嗎?這是歐娜希望發生的嗎?歐娜有勾引主管嗎?她想要從班尼那得到什麼嗎? 對歐娜來說,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為何沒有激烈反抗?為何在班尼強吻她以後,仍繼續上班?為何在班尼的幾次調戲後,仍跟他去出差? 歐娜被丈夫指責時,也在自我譴責。從一開始,丈夫就希望歐娜做一份普通的工作,可以兼顧孩子和家庭。而歐娜想要在職場上證明自己,也想賺錢撐起這個家。這也是歐娜在最開始面臨的抉擇之一,家庭還是工作?女性投入職場的起點,與男性相比,從不平等。 歐娜沒有辦法像旁觀者一樣清楚地認識到,班尼的行為或許沒有構成法律上的性侵,但這無疑是一場職場性暴力。她感到失落茫然,這樣任人擺佈;她不僅身體受到侵害,對自我的認同也變得支離破碎。 熟人性暴力 深陷自責羞恥之中 人們往往以為性侵來自於暴力的陌生人。根據聯合國統計, 80% 的性侵來自於熟悉人,加害人可能是親屬、朋友、同事、前任等等。因為是熟人,所以沒有防備,而加害人也正是利用了這種關係上的信任和親近。也因為是熟人,在遭到性騷擾或性侵後,受害人更加難以言說。 怕其他處在這個社會網絡中的人議論紛紛,怕關係弄僵一發不可收拾,怕得不到周圍人的理解和信任。於是受害者在被侵犯後,會表現得猶豫不決,或是陷入自責羞恥的情緒之中。 而熟人性暴力發生後,即便是立刻報案,也很容易因為證據不足而無法立案。受害人還會因此遭到譴責--妳是不是做了什麼讓人誤會的行為?妳為什麼不保持距離?妳其實是自願的吧? 班尼對於歐娜來說,既是主管,也是熟人。歐娜和班尼在工作時很愉快,即便在班尼強吻歐娜之後,班尼還是取得了歐娜的信任。 歐娜最終退無可退,只好選擇辭職。她堅持向班尼拿到了推薦信,要往下一個職場邁進,這是她在這場性暴力中一點小小的勝利,但也僅此而已。與此同時,她仍未獲得丈夫的諒解。 不論職場或是家庭,性別暴力有聲或無聲地壓迫著女性。在這個父權社會,女性身在其中,不論優異與否,都仍可能被迫背負罪責與罵名。歐娜最終對班尼說,「跟你工作,讓我好好上了一課。」儘管路遙,但仍要整個社會一起,提高性別意識。 No means no ,沒有欲擒故縱,沒有欲迎還拒。有朝一日,讓性別暴力能夠終止。
文/溫若涵 原文刊載於BIOS monthly 看陸小芬如何殺絕五個強暴她的男人 看陸小芬的野 看陸小芬的艷 看陸小芬的辣 看陸小芬的狠 1982 年《瘋狂女煞星》上映,海報上陸小芬手持刀刃、眼神銳利但披掛類似白色床單包裹而成的裙裝,開高岔幾乎到私處。報紙上的電影時刻表,她則身著深色低胸禮服,胸前一片雪白,小手槍看起來只是裝飾,並搭配上述宣傳詞——要說是情色片的宣傳,也並無不可。 陸小芬在片中飾演女記者徐婉清。在一起廣告女星被富家公子強暴的大案裡,眾人皆責備女明星平素行為「不檢點」只是來刷知名度,只有她持續調查。不料女星一日身亡,她也再次因關切路上女性被嚴重性騷擾情事反被五名男子輪暴,因而展開殺光他們的復仇之路。 出自 1982 年《中華日報》電影版。 2019 年,女影策劃〈狂女起駕・復仇來襲:亞洲篇〉,橫跨日韓港台、六〇到八〇年代選片,讓我們重新得以審視亞洲文化裡誕生的女性復仇電影。歐美七〇年代後的 B 級片浪潮裡即可見以女性主角的強暴復仇片,後續女性主義論者對此有不同觀點,難有定論。今年女影引言提及,歐美在女權運動、反主流文化盛行時誕生這樣的剝削電影分支,「極盡剝削女體裸露與血腥暴力元素,低俗的高潮背後是女權抬頭與社會階級衝撞下的集體焦慮」,或許可以作為我們思考的開端。 以當時最引起爭議的《我唾棄你的墳墓》(I Spit on Your Grave,1978)為例,此片以長達三十分鐘的輪暴鏡頭為人所惡,影評人 Roger Ebert 便曾稱其為「一袋垃圾」。不過故事女主角 Jennifer Hills 倒和徐婉清有共同點:她們都是「新時代的獨立女性」,Hills 是從曼哈頓遷居小鎮的作家,希望幽靜偏遠可以幫助她完成首部小說。徐婉清則是報社裡的「一顆煞星」,仗義執言個性不時讓主管頭痛。兩人都時常單獨行動、性格堅韌,而強暴她們的男人幫眾則多為社會中下階層工作者。《我》片中一重要橋段,是施暴者們試圖逼女主角為其中一男子破處,也顯露強勢性別反為社經地位弱勢者的性焦慮。 因《我唾棄你的墳墓》被罵翻的導演 Meir Zarchi 後來說明,Jennifer Hills 的遭遇其實來自他的親身經歷。有天晚上他在公園邊目睹一名年輕女子帶血、赤裸從樹叢中爬出,得知她在行經陰暗捷徑前往男友家過程中被強暴。帶她前往警局時,Zarchi 感受到警察對此案的漠不關心,引發他寫下 Jennifer Hills 與她的受害、復仇故事。為 Zarchi 說話的還有以《男人,女人與電鋸》(Men, Women and Chain Saws,1992)提出「終極女孩」(final girl)理論,改寫恐怖片裡女性形象的克洛佛(Carol Clover)。她在書中提及,電影裡的殘暴使觀眾視角全然同理女主角,即便是男性觀眾,也會站在女主角這邊,贊成復仇。 先完全摧毀再賦權,到底是不是賦權的必經之路?摧毀過程中引來的享受目光,道德上是否合情合理?《我唾棄你的墳墓》與《瘋狂女煞星》勢必還是會回到這樣的疑慮。如今重看,強暴段落依然帶有窺視的刺激興奮感,也有許多人會因此感到不適。為什麼主打陸小芬,當然是為了她的胸與她的臉,被追殺時扯爛衣服、無助的性感身軀服務了多少慾望的眼睛。即便是復仇段落,每殺一個人就換一套裝,踩馬靴、化全妝美麗,說是 M 性格異男的性愛幻想,也十分合理。 此次客座選片人卓庭伍於講座中分享,同單元播放的香港電影《沙膽英》,其實也被要求放很多不必要的裸露。陸小芬當年因《上海社會檔案》大紅,趕拍《瘋》片於大概二十天內完成劇本,邊寫邊拍,還需要顧及票房等等。在一個難以要求完全政治正確的年代,我們還能如何看待這樣一部電影?特別是,導演楊家雲是男性主宰影視業時期少見的女性導演。 「我想,今天晚上你一定睡得很好,強暴一個人的肉體和心靈,都需要用很大的力氣。」——《瘋狂女煞星》 電影雖然聚焦在徐婉清的經歷,卻是由朱姓廣告明星的性侵案為起點。故事一開始,我們看到她拍攝一個情境奇妙的廣告,草原上被開槍後,倒在地上爬行直到拿起化妝品才復生微笑。男性導演要求「笑得性感一點」時她不滿離去,搭上公子哥李世傑的便車,因此被性侵。從不滿男導演的指揮、要求,朱展現了某種自主意識與反抗能量,但這樣的能量,卻在後面的審判場景被李世傑、及他身後整個社會給扼殺。 開庭時,她先是被要求「把扣子扣好」,而後李講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故事:朱既然是豔星,拍廣告時「勾引了全香港的男人」,怎麼可能被性侵?是她主動勾引的,她換衣、她一舉一動都是在表述主動。李的律師十分有把握,說只要照他的說法一定會贏,側面表示了:這個社會根本不可能相信一個性感的女人可以被性侵。甚至徐婉清的未婚夫也持相同論調——「這也不是我一個人說的,姓朱那個模特兒,根本不是什麼正經的女人。」 如今看來,朱姓女演員的遭遇隱隱對應現實生活中的陸小芬。明明《上海社會檔案》內涵近似於傷痕文學,看點卻一直在她的胸部;而不只一部《瘋狂女煞星》,彼時幾乎所有人都想拍一部陸小芬的女性復仇片,看她被近似奇觀式地輪暴,再華麗地、美豔地、火辣地展現強勢。朱姓女演員的慘劇,像是為所有被社會慾望的客體留下一絲哀悼與同情。 而劇中徐婉清被強暴後,楊家雲也細膩拍攝了她的不知所措與痛苦。雖知劇情走向勢必如此,但當未婚夫得知她的遭遇說出「我的未婚妻被五個男人強暴,叫我怎麼面對我的朋友」時,依然讓人覺得恐怖。 從剝削電影與社會寫實中走出一條折衷道路,《瘋狂女煞星》難以定義,但這也是它值得被重新關注的原因。《瘋》片上映的 1982 年,同時也是台灣女權運動值得標記的一年。婦女新知雜誌社不畏提倡「新女性主義」的呂秀蓮入獄在前,依然成立,每月發行《婦女新知通訊》,成為台灣解嚴前重要的性別運動基地。在慾望的眼睛與產業壓力下,身處觀眾的刺激需求激增、性別權力關係變化劇烈的時期,八〇年代的女性們是否曾找到一點點反抗的敘事能力,即便不那麼純粹?這是屬於我們歷史的一部分,正因為混沌,更需要重新思考。 【後記】楊家雲導演後以紀錄片《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的故事》獲第 35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也喚起大眾對慰安婦議題的認識。從《瘋狂女煞星》到《阿媽的秘密》,楊家雲走過三十年的導演路思考,歡迎親至女影導演場感受。 時間|2019.10.11(五)19:30 地點|思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