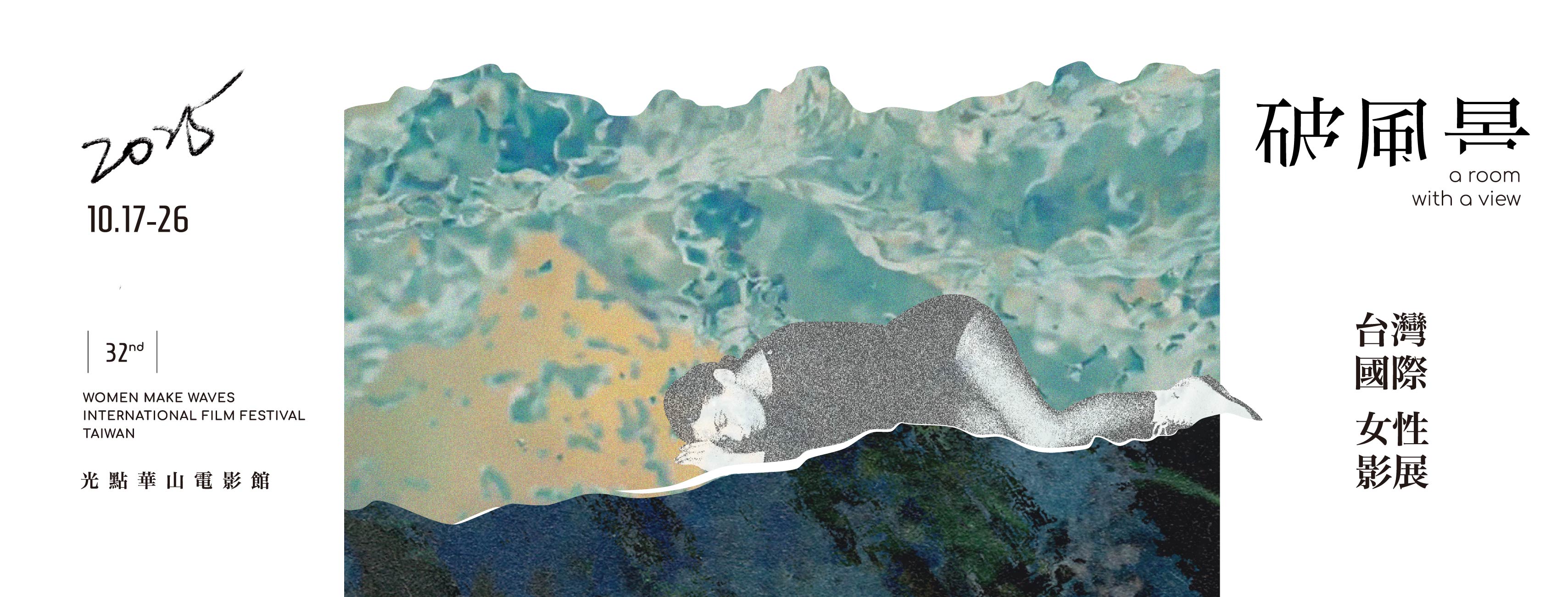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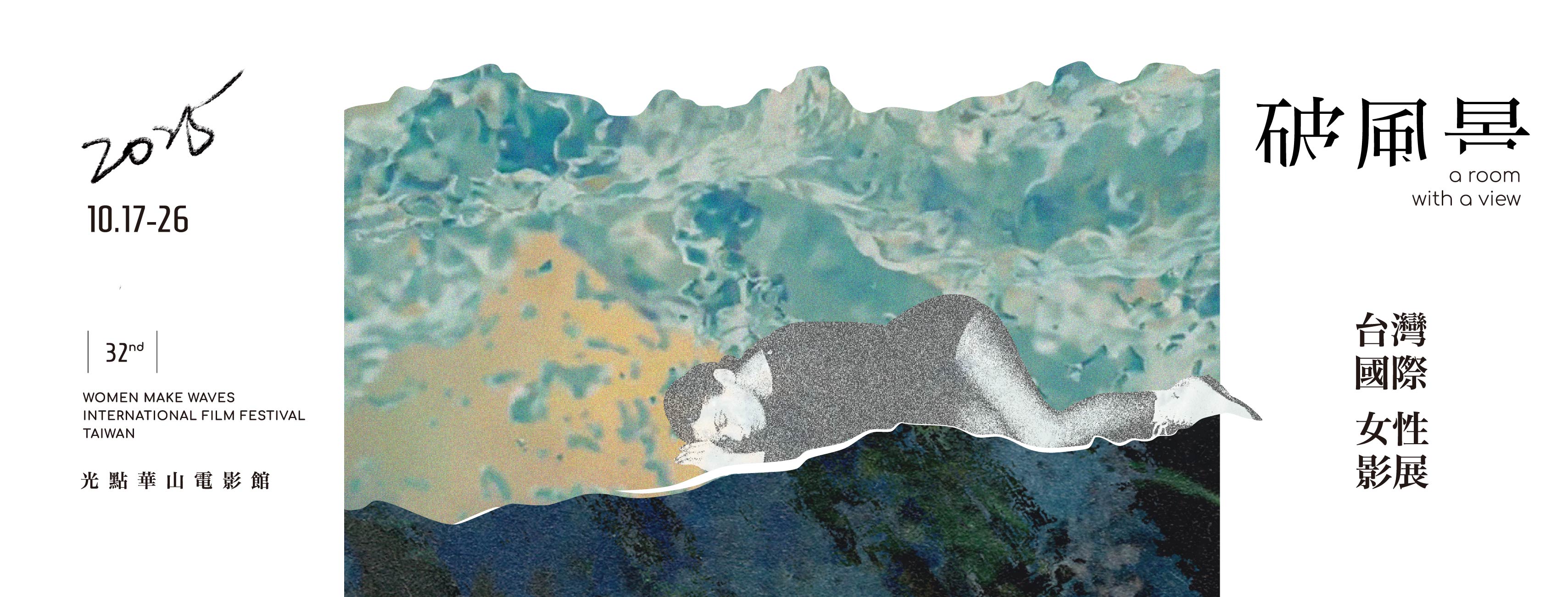
作者:鍾昀珊 發布時間:2018/09/18 女人被發派的劇本裡沒有政治,當她們脫稿演出,只被當成玩笑,但光是這樣,已經夠讓男人害怕了。歇斯底里、情緒化、不講道理,所有他們用在女人身上的詞彙,又爬回他們身上。 一反往常女性主義電影公式,女性角色各個智勇雙全,總是能堅決地起身對抗父權社會的不平壓迫,展現姊妹情深,並化危機為轉機。要是帶著這樣的期望,《女伶們》可能會讓你看得一肚子火,大罵真是一群扶不起的布爾喬亞蠢婦!她們不僅沒有高尚節操,還貪戀物質享受、意志不堅,當人家小三,腦袋空空,連句話都說不清楚。但這正是這部片不斷要叩問的,「是什麼讓女人失去話語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被劃限在日常的庸俗之中,使女人明明在社會系統裡很重要,卻不被允許成為言說的主體。 《女伶們》是由 Mai Zetterling 所導,以及名字也總是和柏格曼「御用女星」分不開的 Bibi Andersson《野草莓》、Harriet Andersson《芬妮與亞歷山大》、Gunnel Lindblom《處女之泉》共同主演的荒謬喜劇,讓這齣戲中戲又延伸出了更多劇目,在真實人生不斷上演。 但讓我們先回到電影本身,它精巧地貼合了形式與內容,主要敘事架構清楚,為三位女伶在巡迴演出希臘 Aristophanes 喜劇 Lysistrata 的線性過程,期間不斷穿插戲外婚姻生活的紛擾和內心獨白,明確的架構下,讓這部片的一大亮點——超現實的場景安排,更有發揮的空間,而不至於鬆散凌亂。 戲劇給了女伶們脫離日常的想像,然而現實總又像遊魂不停威逼,無法靜止不動,卻又難以真正離開。於是排練時浮現日常印象,生活中又念起劇中台詞,在不斷輪轉中,超現實場景也隨之切換,可以看到 Mai Zetterling 對鏡頭的野心,和玩心大開、極富實驗精神的一面。這也造成了許多奇異的笑點,雖說這是部女性意識強烈的荒謬喜劇,但不是那種會讓你在戲院捧腹大笑,而是默默莞爾,想想其實還蠻悲哀的那種黑色幽默。像是女伶 Liz 被要求放下演藝事業,回家服侍丈夫,讓他能專心發展他的「事業」,而這幕跳接到丈夫邊正經地說服 Liz,邊打開巨型公事包,幫裡頭裝著的洋娃娃般的情婦們一件件脫下衣物,再新娘抱上床,堪稱睜眼說瞎話的最高境界,諷刺地直指許多女性在婚姻生活裡所受的不平待遇。 《女伶們》搬演的劇目 Lysistrata 是首部以女性為主角並以反戰為題材的荒誕喜劇,由女人們發動「性罷工」,向男人施壓爭取和平。挑選這部西元前411年的希臘喜劇絕不是空穴來風,它巧妙地呼應了這部電影上演的時代氛圍,1960年代正值反戰高峰,也逢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的崛起,十分重視女性生育的自主權。在避孕與節育受到限制的年代,女性不僅要多次承受生產對身體和精神上的耗損,還要應付隨之而來龐大的母職壓力。Mai Zetterling 在處理這些議題時,也保持幽默而不失批判性的筆調,一幕女伶 Gunilla 在演出空檔去超市購物,卻被一大群孩子追逐的狼狽戲碼,在詼諧童趣的配樂下,卻暗藏了母職無所不在的焦慮,一旦身為母親,就得時時刻刻掛念著孩子。丈夫、孩子、金錢,當女人擁有這些後,整個社會就逼迫妳必須感到快樂,不然就是自私又貪得無厭,Gunilla 遲疑了,隨即又自我催眠,是的,我很快樂。 台上演得賣力,台下卻早已睡成一片,關鍵衝突起於 Liz 有感於此而在散戲時召回大家、封起大門,發表了一段演說,希望喚起大眾對事物的重視,不再如此漠然,這個舉動引起了軒然大波,也開啟了兩性大戰。她確確實實覺得哪裡不對勁,卻無法順暢且有邏輯的訴說,像演員不習慣發表台詞之外的言論,而在父權社會下,這就是女人所面臨的困境。在《女伶們》裡女人試圖言說、拒絕父權的姿態或許有些生硬,甚至愚蠢,最激烈的抵抗表現竟是齜牙咧嘴地往男性權威圖像砸雞蛋?但或許忽略了,但在很長的一段歷史上,甚至直至今日,女人是沒有話語權的。 「為什麼選擇今天發作?是不是有什麼個人因素?」女性的憤怒與想法從來不被正視,在政治上也不容許有介入的餘地,只要女人一開口就被打成「抱怨」,男人提出的才是高明的「見解」。經濟、語言、教育共謀,將女人排除在政治之外,再羞辱她不懂政治,先使其失能再加以定位,層層剝削,社會不斷惡性循環這樣的困境。這樣的劣勢下該如何發掘女人的能動性? 沒有人一出生就會跑,但如果從不開始,那將永遠沒有前進的可能,我們習慣將學爬階段視之為「黑歷史」,《女伶們》卻不將之視為恥辱,用充滿詩意的鏡頭,溫暖地捕捉當時當刻的稚嫩與笨拙。「女人從 Aristophanes 時期就沒在長大的,為何現在會呢?」面對男人的質疑,像尾聲 Gunilla 登高呼喊「我們有太多事情要做、太多尿布要換,但未來的女人們會做到的,她還沒出生呢。等著吧,這只是個開始!」好戲還在後頭呢。 1968年 Mai Zetterling 銘記了所有生澀的刻痕,溫柔地期待她們的成長,50年後的我們,做到了嗎? 場次資訊 華山1廳 10/06(六)SAT 17:10 華山1廳 10/11(四)THU 19:40
作者:徐翌全 發布時間:2018/09/18 一部電影,跨越數十年,來回應這個時代 本次修復單元鎖定1960到1980年代的女性主義大師作品,收錄了來自五個國家、八位導演的九部經典之作。脈絡扣合1960年代從美國逐漸擴張至歐洲及世界各地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並與當地原有的影像論述及女性主義思想合流的歷史背景,一窺當時女性先鋒們如何以原創性十足的影像語言和社經政治意義帶來劃時代影像革命,並為女性電影於電影發展進程上開闢出不可抹滅的重要途徑。 法國新浪潮教母-安妮.華達 許多人對安妮・華達(Agnès Varda)都不陌生,她不僅是一位富有女性主義色彩的電影創作者,在生活中,也用自身的力量對抗社會對女性的打壓與不平等對待。1971年,在法國墮胎仍屬非法行為,她聯署「343蕩婦宣言」,是聯署的343位女性其中一人。宣言由西蒙·波娃撰寫,聯署人承認她們曾經接受墮胎,她們要求法國政府將墮胎合法化。 然而,在台灣看過她作品的人卻不多,撇除影展的放映,最近期在台上映的是2010年的紀錄片《沙灘上的安妮》,以這部敘述自己一生的片子窺看她,我們或許就可以理解,那些在她的其他作品中帶有批判性卻又溫暖的影像,是如何產生的。 今年 90 歲的華達,以《最酷的伴侶》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並獲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典禮上,致辭的安潔莉納・裘莉說道:「謝謝妳安妮,謝謝妳身上的一切,唯獨沒有所謂的正常」。 女影今年選了《無法無家》做為開幕片,對25週年來說別具意義。影展每年都帶來許多女性議題與觀點的影片,試圖透過放映,引起關注與探討。 然而現今影展很多,需要被關注的議題事件也是,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女影不只是曇花一現,而是選擇保有自己的風格,持續在女性議題上深耕。或許過程中總是艱辛,就跟華達拍片時一樣,總是不知道下一部片資金的著落,但為守護心中強大的理念,硬著頭皮讓很多事情得以實現。現今的第三波女性運動#metoo正引起全球關注,遍地開花,對華達或對女影來說,#metoo一直存在心中,不僅僅是哪次的運動或者哪部電影的呈現而已。 回到開幕片《無法無家》,講述一名女子被發現陳屍在小村莊的壕溝裡,關於她生前的任何事,沒有人知道,進而開始了一段以仿紀錄片的方式訪問曾與她接觸過的人,並以她所到之處發生的各種事件,建構出這名女子人生最後的流浪時光。 這名流浪的女子是Mona(Sandrine Bonnaire飾),在旅途上她所接觸的人中,好像是一面面鏡子,照著正在看電影的你我。而片中訪談不時越過第四道牆與正在看電影的我們對話,讓觀影者意識到自己不只是一個旁觀者,那突如其來的對話,似乎在提醒著,嘿,你怎麼看? 有人羨慕Mona的自由自在,開始從新審視自己所處的生活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認為她雖然貧窮,卻真真實實地活著。但一對牧羊人夫婦卻不這麼認為,他們積極想要幫助莫娜,提供一個穩定的工作與住宿給她,但莫娜並不遵循這個遊戲模式,不僅沒有在白天從事勞動,也沒有做出任何貢獻,牧羊人深感煩惱和失望。 他告訴莫娜,對於所有浪漫的觀念,道路上的生活,以及她所招惹來的貧窮,都是一種活著的死亡。 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 確實,對那在路上飽受飢餓,寒冷與強暴威脅的她,也曾想過怎樣才是合適的生活。而在做與不做之間,最珍貴的固然是選擇權,我有權選擇並執行我心之所向,我不需要對誰交代,亦不需要承受誰的眼光。無論觀眾如何評價Mona的放逐,是好是壞,都只是個人解讀,與她無關。 「為什麼我不能選擇自己的生命?」 電影人盛讚的安妮華達顛峰之作 這部片或可以說是安妮・華達從事影像工作中探討女性與生命的經典之作,在當年推出後造成轟動,先後得了1985 威尼斯國際影展金獅獎以及1985 法國凱撒獎最佳女主角。而當中最多人探討的除了自由之外,還有女性該不該,能不能做拋下一切,追尋自己。 在一段訪談中,華達提到關於片中流浪女子的角色說道:「在電影裡,Mona持續在移動,總共有13段一分鐘的鏡頭;當她走路時,沒有言語,我們靜靜的看著她走路,整部電影你有時間親自去感受一下她。 也許你不喜歡她, 你沒有同情她,因為她沒有同情心。 也許你為她感到難過,也許你對她感到生氣, 而我喜歡觀眾保持自己的想法,意識到自己是誰。」 活著這件事該如何定義? 《無法無家》提供了一個破口,提醒你是時候懷疑自己,懷疑任何事,尤其是當一切都進展得順利時,便是僵化的開始。也許我們都需要一個像是Mona的人來提醒我們,生命的狀態不只一種,活著定義也不是單一的,價值這種東西並不是誰說的算。 女影今年特地選這部數位修復片,乃是一記打在現代人的耳光,在2018年,許多人還是對女性存在著特定的幻想甚至歧視,或許不會像電影中那些男性這樣公開地談論,但有時候不說,不代表不存在,除了那些性幻想,還有潛在心理那對女性行為上的約束,其實都沒有結束過。 女影25重磅修復單元 關於看修復電影,其實就是重新想像過去。本次女影的修復單元,除了帶來安妮・華達的片⼦外,也有柏格曼御用演員梅・柴特琳(Mai Zetterling)投入導演工作的三部經典片。此外,去年以《夢鹿情迷》獲得第67屆柏林影展金熊獎的伊爾蒂蔻・恩伊達(Ildikó Enyedi),她的早期作品《我的二十世紀My Twentieth Century》,同樣是帶有奇幻⼿法的作品,闡述⼀段女性⾃我追尋的故事。而 茱莉亞·雷徹特與吉姆・克萊(Julia Reichert &Jim Klein)的紀錄片《成長中的女性Growing Up Female,》透過多段訪談,描繪出70年代男性與女性對於自⾝與他者的印象與潛意識的控制。 有幸親自在大螢幕感受這些女性先鋒用攝影機拍出她們內心的躁動與對世界的想像,實屬難得。 老片,它有很多不同的意義,透過看修復片,我們才可以重新定位出⼀個更理想的世界,透過挖掘老電影,或許可以找到合適得答案。 場次資訊 台北新光2廳 10/04(四)THU 19:20 華山1+2廳 10/14(日)SUN 13:00 台中新光8廳 10/31(三)WED 19:30
作者:李語晨 發布時間:2018/09/15 「攝影和愛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都只有當下,都沒有未來。」 我們看著幸福的畫面,被拆解、重組、調色,層層疊疊的藩籬,阻擋通往歡笑的道路,於是幸福變得遙遠。關於影像和愛都是,在經歷快樂的至高點之後,留在黑暗的每一日,都煎熬難耐,都撕心裂肺。這是鄉愁。 《鄉愁/餘像》 Spectrum of Nostalgia Spectrum,導演以羅蘭‧巴特的說法詮釋,是鬼魂。幸福的記憶魂牽夢縈,環繞在生命各處,然而,就是因為愛變質了,多年前歡樂的笑聲,而今看來都是愁緒,成為痛苦的催化劑。 導演將兒時母親拍攝的影片和照片,解構成為新的影像,用反覆出現、加強雜音與雜訊、聲音設計等形式,把原先快樂的畫面變得不自然,甚至有點駭人。「我好害怕,」導演的對白說道,此時搭配的影像,卻是兒時和爸爸玩耍的幸福時分,於是沉痛就這麼蔓出來了,如幽靈般縈繞在腦海。 全片以導演的旁白作為解說,捨棄前幾個對話式問答的版本,導演決定拉近自身、作品與觀眾的距離,親自解析影像。因而,極具張力的畫面、美得徹骨的文字與細膩的旁白構築了這部深刻的實驗電影。 關於預先 「從一個人叫你的聲音,就可以知道他愛不愛你。」 在誰都未明說以前,早一步感知情意流轉,是為預先。就這樣,我知道你愛我,你也知道我愛你,我們都不說,相視而笑。預先這份愛的產生,令人心悅。相對的,當愛不小心掉入雜質,又會是怎麼樣的情緒? 黑色的幸福 「所謂的愛,就像點火柴,你一根一根的劃,然後一根一根的看他熄滅,你捨不得,所以又再劃,不管未來,只管劃到沒有為止。」 當我們知道幸福的高度,體會過溫暖且無憂慮的快樂,一旦失去,痛苦往往是加倍的。回憶過去,只剩黑色的幸福,掉進深深的泥沼,不斷下墜,等待被淹沒。於是,影像裡的笑聲好像不屬於自己,而是某個陌生人的,看著應該要是自己的小女孩,卻覺得好像看著別人。原先該是避風港的永恆歸屬,卻颳起狂風,下著大雨。 這是導演的鄉愁,回不去的,最遙遠的幸福。 場次資訊 華山2 廳 10/07 ( 日) SUN 10:50 華山2 廳 10/13 ( 六) SUN 10:20
作者:酸鼻子 發布時間:2018/09/05 《被監禁的女人》的伊蒂說:「有些愛是假的,人們假裝愛你。」 深刻、乾裂甚至發紅的紋路就這麼癱在那兒,在發冷的早晨支撐起全身重量,餵養著主人的所有;除了她以外的資產。在這兒,遵從與服侍是唯一應允,挨餓與挨打則是必要對待。一個菸不離手的女人,連活著都嫌多的存在,猶如空殼般的了無貪戀;強壓在她幾近佝僂的背,依附在生命裡的細微,倚靠在稍縱即逝的逃脫意念之上。 53歲的她,十一年來作為一個管家、幫傭、女工、母親,甚至是奴隸的瑪莉許,日復一日工作二十個小時,毫無報酬、床以及該有的食物,什麼自由意志在她身上都是不被允許的罪行。你說這哪算是人的生活,但今日歐洲卻仍有為數約四百五十萬的現代奴;而她只是其一。 「幸福啊,一直都離我好遠。」翻開相本,回首在此之前的自己,一旁擺著的《如何找到幸福》就這麼尖銳的割開記憶破口。無奈至極就這麼爬滿全身,好提醒自己早已是個失去身份、失去價值資產以及喪失母親角色的女人。對照同樣身為女人與母親的主人艾塔,只能說上天從不慷慨,就連家中狗兒都能得到的關愛,在她身上卻反倒成了奢侈。 「妳在怕什麼?為什麼不跑走?妳跑走他們會怎樣?」 「因為沒有人會幫我。」 孤立無援的過一天算一天,難以掙脫那拴鍊於心的奴役枷鎖,主人的成天辱罵好讓「限制自己,成就更多」的想法一再凌駕於前,以至裹足不前,勇氣不再。《被監禁的女人》導演貝纳黛特·里特透過貼近的紀錄與對話,小心建立起那被強加剝奪的信任感,喚醒那氣若游絲的自我;介入也直搗人心的本質,摻入倫理道德的是與非。「該不該成為整個事件的協助角色呢?」對於一個記錄者、旁觀者抑或參與一場逃亡的目擊者而言都是種抉擇;一場預想之外的拍攝計畫,竟推了她一把。 「我在發抖,我怕到發抖,我好怕妳背叛我。」 「我不會的。」 然而,人是否真有高低貴賤之分?那些厭棄、執拗的欲加之罪究竟從何而來?「不可以這樣對待別人,就算對方一無所有。」扯了個謊,逃脫的大清早跟著狂跳的心臟節奏,狂奔在相隔許久的自由路上,就好比她小心黏著的耶穌之手;正一步步修復當中。「你找到了,就屬於你的。」帶著僅存的150歐元,吃上一頓早餐並將買來的禮物害羞的交到導演手上。那是,即便貧困卻不吝於給予的溫暖,你知道她還是愛著這世界的。 車子駛過以前長住的地方,滿腹感慨化作淚水傾瀉而下,灌注在失而復得的親情之中。於是,那曾說過「男人會利用你的一切,然後離開。」的瑪莉許又再次成了母親、奶奶以及一個會為男子雀躍的人;是個化好妝,穿上大衣,走進公司面試的女人。「瑪莉許是他們幫我取的,我原本的名字其實是叫伊蒂。」 於是,那個監禁許久的靈魂開始有了夢想藍圖。「其實啊,我未來的夢想是開一間清潔公司呢。」她是伊蒂,一個再次享受自由的女人。 導演/纳黛特·里特 Bernadett Tuza-RITTER 匈牙利獨立紀錄片導演及剪接師。《被監禁的女人》是她第一部紀錄長片,亦是匈牙利第一步進入日舞影展該單元競賽的紀錄片。該片入圍「2017 IDFA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2018 日舞影展」。 場次資訊 華山1 廳 10/07 ( 日) SUN 15:20 華山1 廳 10/14 ( 日) SUN 15:30 詳細資訊/活動 第 25 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跟著電影語言的敘事重生 https://solomo.xinmedia.com/photo/153897-wmwff TEXT/酸鼻子 文字的影響力還是有的,尤其在這時常避而不見的時代,總有些需要寫下才得以喘息的情事。作品散見於網路、雜誌刊物,如欣攝影、《SENSE好感》、《欣旅遊》等。網路搜尋:酸鼻子專欄
文/陳慧穎 在《銀翼殺手》的尾聲,瑞克·戴克(Rick Deckard)跟隨瑞秋(Rachael)進電梯前,撿起了掉落在地上的錫箔獨角獸摺紙。當電梯門再度打開,摺紙被再次撿起,走進電梯裡的卻是玲子(Reiko)與迪西(Dizzy),電梯廣播正經八百地放送著各種性愛用語,與一般電梯廣播用語交互使用,同時間在這黑暗密閉空間裡淫聲四起,各種聲音交雜相融,場景早已置換成鄭淑麗的異色幻境 ──《I.K.U.》(2000),即所謂《銀翼殺手》A片版,接續著《銀翼殺手》的結尾玩起故事接龍。即便如此,光是看著開頭的動畫仿若電玩場景開展出詭譎色彩,又幻化延伸成整片的數位地景,其中陰莖形狀的粉色高樓射出透明汁液又跟隨著高樓電梯急速下樓,到地面上時絢麗詭譎的色彩化為簡約,只見隨著電梯門開合不斷變換性愛姿勢的肉體,這些讓人目不轉睛的畫面早就讓觀眾把《銀翼殺手》的想像拋的老遠。好不容易以為正片將要開始,隨著電梯門開合,畫面又瞬間切換,端坐在學校課桌椅的高校女學生腿也開合著,進而堆疊出多排高校女學生的畫面,高度混雜無序卻又充斥著重製與無限疊合的調性,彷彿無止盡的昏眩狀態。擋不住的淫聲浪語,高速穿梭異質空間,與電子音樂共感碰撞出虛幻感,把觀眾一同拋進不斷旋轉的高潮數位幻象。 《I.K.U.》的背景設定在西元2030年的東京,如同《銀翼殺手》裡面的泰瑞公司;影片《I.K.U.》裡的跨國企業「基因集團」,推展出生化特工「I.K.U.Coder」,XXX型是最高機型。「I.K.U.」乃日文「行く」的英文拼音讀法,即要高潮之意。XXX型可以變換成七種不同面貌,任務是蒐集性高潮的各式情境與感受,存放於體內的生物圓盤。公司派出他們旗下I.K.U.Coder最高等級的生化特工玲子(Reiko),以各種相異面貌,接觸各類性愛對象與情境,身體在虛擬網絡及實體空間之間游移,以收集屬性各異的數據來迎合不同性取向的消費者。這些數據一一被存放到「I.K.U.芯片」,使用者能在路邊的販售機購買取得,透過I.K.U.芯片就能直接體驗高潮,而無需身體接觸。仿若《銀翼殺手》中生化人的記憶皆可被追溯回某記憶原型,私密感知僅是可被演算、被複製儲存、被收集的數據,性已脫離愛,脫離情緒,身體接觸不再是必要。數據即是高潮,即是歡愉。 歡愉當前,高潮萬歲 《I.K.U.》與《銀翼殺手》之間的文本互涉,有時更趨近於惡趣味玩笑,折射出光怪陸離的詭譎色相。《銀翼殺手》開頭由泰瑞公司所奉行的世界法則「這不叫做處決,而是退役」起頭,生命泉源與死亡陰谷並行,全片緊緊追問著「究竟何而為『人』?『生命』到底又是什麼?」的生命根本命題。影片結束在瑞克.戴克與瑞秋試圖衝破當下世界所設置的生存疆界,同時拋擲出為愛遠走高飛的浪漫想像,但當這一切置換到鄭的異色世界裡,調性全變,開頭的字句亦早被改寫成「這不叫做愛情,而是性交」,替換掉退役男警探瑞克.戴克的卻是跨國企業基因集團的跨性員工迪西,男女二元想像成為一種玩笑,浪漫逃脫則被置換成企業的管控程序,兩體交纏,索取愛液,口口聲聲是愛,卻毫不掩飾地打著反浪漫化(Anti-romance)的旗幟。 似男非男,似人非人,似愛非愛,四不像的世界裡,不正經地大玩邪擬。更有趣的是,《I.K.U.》開頭接了《銀翼殺手》的結尾,自己的結尾又把《銀翼殺手》棄之不用的原版結尾找回來:一片風光明媚,這回玲子坐上了迪西的車,模仿公路電影為愛走天涯的畫面,自嘲了「這不叫愛情」的開頭宣言,卻在最後又加了四個結尾選項,並播放了第二個選項,表面上的男女轉變為男男戀情,對象的切換僅是選項的操作。把結尾裝在開頭,又把對方已拋棄之結尾回收再利用,顛倒裝卸後再製出廠,原有的愛情寓言已鬆綁,能夠比照的只剩表像,底下已被大肆翻攪。 撰寫《新酷兒電影》的魯迪.瑞奇(B. Ruby Rich)曾提及「鄭淑麗現象」(the Shu Lea Cheang phenomenon),進而闡釋鄭的影像世界本身就是一種現象,跨性別又跨電影類型,卻能夠在跨各類影像類型的同時,拒絕任何類型所附加上的定義。《I.K.U.》便是電玩、劇場、網路世界、電影(其中又結合科幻片、粉紅電影、A片、低成本實驗片)所合成的異質有機體,矛盾的是,異質間充滿斷層卻又絕對平面化,身體場域與空間向度彼此呼應貼合,以另一種狂暴奔馳的高速狀態吞噬觀影者。 身體作為戰場 本片導演一方面藉由玲子的七種變身,穿梭各式情境,串連深夜電視台、劇場化展演、網路等異質媒介,捕捉到日本特有的色情文化以及地下實驗性表演團體的前衛展演,乃九零年代末日本色情/情色展演的集大成,但另一方面,既是致敬亦是竄改,以再創敘述的方式介入日本的色情電影脈絡,直接去改寫當地的色情政治。實際拍攝時,導演去拜會了操持色情行業的黑道頭們,女主角鈴子即為日本衛星電視台深夜時段女優,迪西則由Zachery Nataf知名跨性別學者,亦為倫敦跨性別影展創辦人所飾。藉由直接參與演出,展演跨性身體,以嘲諷了「黑人男性與亞洲女性組合」所延伸出來的生理性徵/種族崇拜,而玲子做愛過程中所變身出來的魔幻手臂,類似電鑽形象不禁讓人聯想起日本賽博龐克(cyberpunk)的先聲之作塚本晋也的《鐵男—金屬獸》中陽具化身成的高速電鑽,既是類陽具與SM中的拳交形象結合,亦是另類戀物的一種極致表現。在多重意象堆疊下,加以玲子做愛的對象與情境如收集不盡的數據幻化無窮,性別疆界早已模糊到不可被辨認之境地。利用動畫呈現出的陰道內景則強化了過去總是缺席的陰道視角,反轉A片中強調男性視角的傳統,而此視角又與轎車、跑車、機車各類交通工具反覆進出隧道或迴旋梯的意象疊合,深淺來回穿梭,在視覺意象的建構過程中擊垮色情產業中的「陽具崇拜」,乃至於在試圖重現日本多元興盛的色情產業切片的同時,已與優越於多重選項卻又恪守傳統原則的日本色情文化全然背道而馳,大行解放掉原有的性迷思。 在這些層面的翻攪之下,影片《I.K.U.》中極為耐人尋味的矛盾點在於,身體上性別政治∕色情政治的解放乃根基於大企業的控制、規訓以及干預。同時被企業化、網絡化、媒介化(藉以收集數據)的「非自由身」也同時在演繹與之無法切割的性別政治∕色情政治解放的可能性。一方面來看,在科技與身體逐漸結合之際,性別政治∕色情政治的延展性與科技賜予者之間的關係也變得緊密,意即誰掌握了科技權力,誰就也能夠去更動身體∕性別∕色情政治裡面的意涵。但另一方面來說,身體本身亦幻化為多方爭奪、角力、抗衡、甚至反動的場域,監控與解放同時存在。 鄭淑麗曾在訪問中多次強調:「身體即是最後的資產,未來一切都將會在你的身體裡進行,你的身體即是最後的戰場。我把身體視為網絡。」《I.K.U.》所揭示的即是「身體即為生物網絡」的基本概念,身體透過連線啟動,性交的過程、身體的運動幻化為數據的收集及傳遞,皮膚即介面,平面化的網絡與身體的物質性合而為一,但企業所掌控的身體並不代表完美,網路也會中毒,玲子即受到名為「東京玫瑰」的病毒所入侵。「生物網絡」概念後續也直接體現在《I.K.U.》所延伸出來的電玩互動裝置作品《UKI-Enter the BioNet》,「UKI 」為一種由大企業散播的病毒,不僅會感染人體內紅血球,還會改變人的感知系統,導致失去所有感知能力,玩家所要做的就是試圖對抗病毒的散播。隨著《I.K.U.》後續系列作品延伸,「生物網絡」的概念讓「身體」更具有可塑性,同時也承載了更大的能動性,這點也可以在2017年的《體液Ø》中看見。 經過十多年,《I.K.U.》的續集《體液Ø》最終於2017年完成,與《銀翼殺手》的續集《銀翼殺手2049》同年。時間來到2060年代的柏林,進入所謂後愛滋時代,超級政府宣告無愛滋時代的來臨,但實際上,愛滋病毒並非憑空消失,反而變種的愛滋病毒促使人類基因產生變異,出現「零世代」(ZERO Generation),零世代身上帶有編碼為DELTA的白色體液,乃最新潮的超級藥品暨性愛商品,僅透過肌膚接觸就使人歡愉上癮,其珍貴程度可比擬為二十世紀的白粉,於是「零世代」的存在便夾在腐敗政府、地下藥頭及只想從中圖利的財團三方勢力的斡旋與勾結。政府出動帶有抗體的複製人「獵零特工」(agent ZERO)緝捕零世代,表面是要進行所謂的「性治療」(sexual reassignment),但其實是將零世代送至製藥所進行身體改造,好以大量生產體液,接著再送到地下工場,終日被強迫自慰、高潮,成為不斷生產白色體液的「工人」,形同人質,地下工廠再將珍貴的液體輸送回最大的性∕藥工廠「DELTA」,以提供製藥的重要原料。 時空向度來到《體液Ø》之際,「生物網絡」的概念持續生長,身體與科技的結合度更為緊密,體液仿若「I.K.U.芯片」的終極進化版,變成人人爭奪的藥品∕毒品、性產品,液態狀態可塑性更高,甚至可被製成為保青春永駐的「養眼爽霜」,打入保養品市場,再度回到皮膚(身體)上。同時它又是政府加強監控身體的終極戰利品。獵零特工的身體亦然,手掌可掃描人體眼部,手臂擁有向上級匯報的通訊功能,肚臍眼上方的特工型號也顯得比《I.K.U.》中肚臍鈕更加進化。 全面監控與反抗的能動性 很顯然,當身體與科技緊密貼合,企業的控制便更加往下扎根,且更加張狂、複雜,除了企業的掌控外,身體亦是被集中管理、全面監控,且被政權強加意義,被書寫污名,全方位性的干預可說是無處不在。整部影片逮捕畫面不斷出現,充斥著強烈閃光及高分貝的廣播,直接藉由感知系統的干預來控制身體,在強光環伺下,身體的警覺度不斷被刺激,如被抓到地下工廠的零世代們鎮日眼神空洞地面對小便斗自慰高潮,閃爍刺眼的強光也讓觀眾觀影過程感到不適。片中所出現的手術改造過程—把眼睛撐大,注射不明液體,重新改寫數據,改造生物體質的畫面讓人想起《發條橘子》把眼睛用機械撐大加以洗腦的畫面。 與《I.K.U.》相比,《體液Ø》的時空整整往後推了三十年,卻不斷召喚過去,其中隱含的歷史與政治性寓意顯得更加鮮明。片頭以1980至1990年代於美國紐約街頭抗議的新聞片段開場,那是愛滋病最肆虐的時候,眾人上街遊行抗議美國政府跟醫藥廠商政商勾結,不願釋放愛滋病的解藥,最後導致愛滋嚴重擴散。而《體液Ø》中,從零時代存在的事實、獵零特工的暴力逮捕、「性治療」(身體改造),到政府、藥頭、財團三方勾結,其中所反射出來的無一不是過去的鏡相,甚至當年據稱要在愛滋患者身上紋身,玆以辨認的歧視性宣言,在片中以一個烙印在身體上的「Ø」字直接被體現出來,一種既視感(deja vu)不斷騷動著。愛滋病及其憂患從未結束,反而在宣告後愛滋時代的來臨同時,再度重演二十世紀的戲碼。過去的街頭抗議映像不斷穿插未來景象,如歷史的幽靈重現,鬼影幢幢如魅,時而與當下不願被逮捕的抗議聲浪呼應疊合,迴盪於時空長廊,重新印證二十世紀末政府與藥廠合作終止,愛滋計畫的徹底失敗,並且對於政府及上下游產業暗地裡勾結的虛偽態度與其全面監控的體系再次發出指控,沈痛地控訴未來。 在這樣的架構下,以身體為場域所開闢出來的戰場,是否還能留有反動的可能性?生物數據能被藥廠改造,改寫的權力是否也有下放的機會?這是抗議的聲浪所不斷回溯的核心問題,也是片中「舌與鞭俱樂部」(LICK)裡的表演者口中所發出的宣示性吶喊。「舌與鞭俱樂部」,相對來說場域型態較為模糊的陰性空間,與地下工廠的高控管性與「汁男」成列的型態形成強烈對比。俱樂部的中心座落著圓形舞台,劇場式的空間開展開來,台上女性姿態各異,潮吹本身的展演即是一種宣言。藝名為「腥羶恐怖份子」的表演者(由知名酷兒色情片演員暨藝術表演者Sadie Lune 所飾)一手自慰,一手在空中揮舞著,義正嚴詞地宣示: 我的身體是人間凶器 我不會再讓我的身體淪為戰場 不要再有死傷,或任何毀壞 不要再有傷口,或任何苦痛 我將帶著我的武器深入敵營 侵奪他們的身體,他們的生命 用我的高潮震垮他們的宮殿 用我的潮吹淹沒他們的廟宇 用我的香汗溶解他們的牢獄 用我的字字句句毒殺他們的信仰 這些字句從Sadie Lune 口中說出,與其各種大膽前衛的酷兒表演形象疊合,句句有力。Sadie Lune 咬牙切齒地說完後,潮吹液體四處噴灑,同是液體,亦能預示解放。事實上,當漢斯被抓去改造的時候,娜塔莎欲前去救援,卻被層層線路機關所困,「舌與鞭俱樂部」的人趕來,拿著皮鞭一甩,成功破解層層機關,把漢斯解救出來,字句不再只是宣示性的吶喊,而是可被實踐出來的時代預言。 與「舌與鞭俱樂部」場域類似的是地下派對,類嬉皮打扮的眾人集聚於廢墟,對著牆壁上撒尿。他們是所謂的「數據駭客」(data hacker),另一型態的液體噴灑所標誌的是破壞、挪用、竄改、亦是解放,眼前出現各種數位程式碼,彼此堆疊後崩塌剝落,既能寫碼、解碼,也能加密,一切就像遊戲。 在後愛滋時代,尿液能幻化為科技病毒,與已變種愛滋病毒(生物性病毒)加入同一個戰場,重申病毒本身的無盡變化與可能性:病毒既然能變形、傳遞,本身也就具有可被挪用為反抗的能動性。在這樣的基礎點上,體液的概念亦同,可塑性高的白色液體,即便在各個產業鏈環節承載著不同的意義,看似可能性無窮,實際卻是控管無所不在,但另一方面,同為體液—尿液與潮吹液體的存在,則揭櫫了挪用意義的可能性,證明反動的可能性能與之並存。這麼一來,再回過頭來看片名「體液Ø」,把體液放進圓圈裡,所召喚出打倒愛滋的歷史重相,與2060年後愛滋時代的體液戰場疊合,但同時也疊合了白色液體、潮吹液體、尿液噴射的多重映像。在全面加強身體上的控管之際,解放的圖像也被偷渡進去,暗示反動路徑。 從《I.K.U.》走到《體液Ø》,時空推移,科技更加先進,身體被外界入侵的可能性與受控制的層度不斷飆升,所召喚出的樣態卻與實際的人類歷史走的更近,欲控訴與反動的聲音亦更加張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