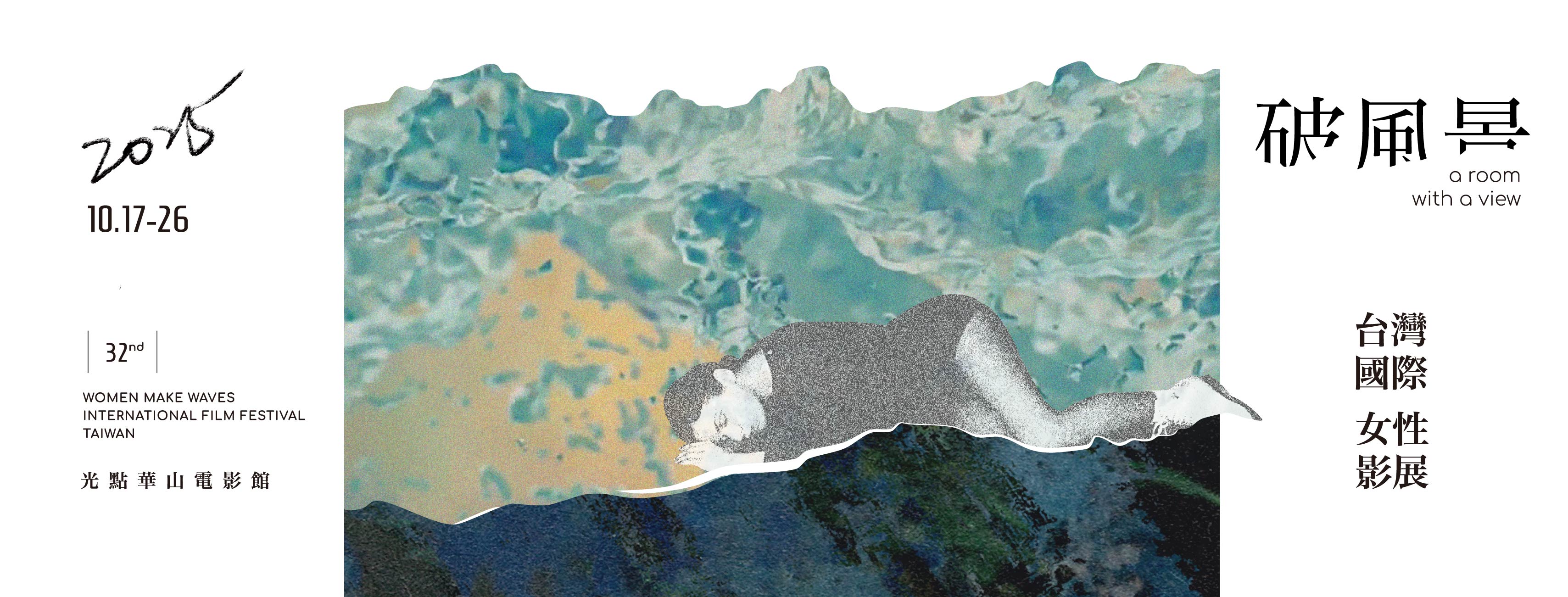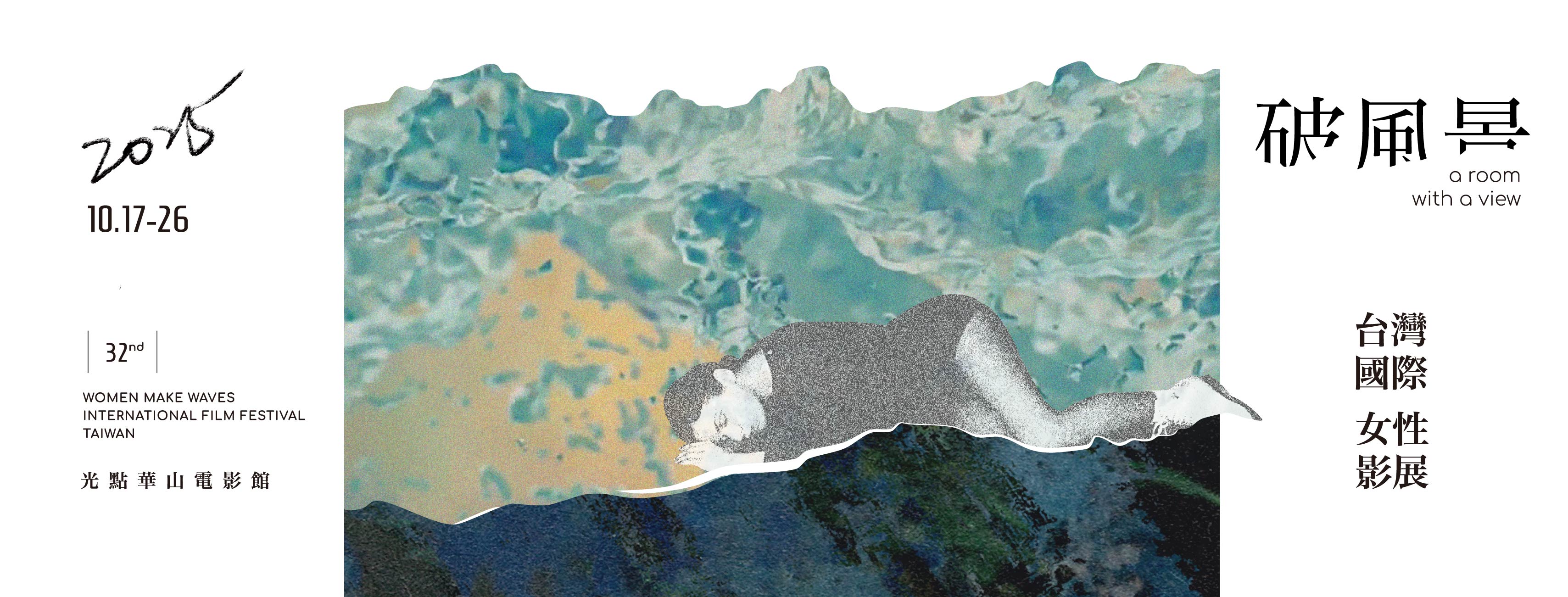既然不可迴避,何不把鏡頭再拉近一些?
文/V太太
女影三十年了,而自第二波女性主義追求女性身體與情慾自主至今,也已超過半個世紀。在此刻重訪「身體」這個主題,乍看之下似乎顯得老掉牙甚至陳腐。
然而當我們環顧世界,綜觀各地女性眼下的經歷,我們看見伊朗女性為了爭取衣著的自由在極權國家的街頭上抗議;美國女性在羅訴韋德案判決被駁回的一年後,生育自主權不斷地被限縮,甚至因此而面臨監禁的命運;跨性別女性因為不符合人們對「女人身體」的想像,使其性別認同不斷地被質疑、拒絕,甚至遭到驅逐。而在台灣,自6月起掀起的MeToo運動裡,女性們透過訴說自己的受傷經歷,企圖重新奪回對身體、情慾和自我的話語權。
於是我們發現,在此時此刻,探究女性與身體的關係、女體與社會—一個以資本主義、父權體制、種族主義和身體健全主義為背景之社會—的關係,竟是如此至關重要,甚至帶有不可迴避的急迫性。
女人的身體素來意義豐滿,它是個人的,亦為政治的;它經常被作為譬喻的素材,同時又成為現實的展演舞台;它往往受到箝制、貶抑、汙名,但卻也是女性最值得信賴、甚至是唯一的工具,以此來挑戰、逃離、反叛父權體制的壓迫。
今年的「移動身景:凝視、抵抗、創作與歌唱」單元挑選了九部影片,主角、題材各有不同,表現方式也大相逕庭。其中有直白對女體的展現,從近乎純粹「生理性」的角度出發,看見女性身體所經歷之美好與創傷;亦有以身體為「載體」,展現性別、種族、國籍、階級如何彼此交織,形塑特定身分之女性在社會中的處境;更有看似不直視身體,卻反而更鮮明地昭示了,女性對於身體的擁有與掌握,如何定義女性之存在。
《診間的身景》在巴黎的醫院裡,以毫不遮掩的鏡頭記錄下女性的身體經歷,這些經歷名為「醫療事件」,卻總回歸到女性和自身身體之間的距離與感受,有時那是緊密的連結,有時卻是疏離和恐懼。而同樣的緊密和疏離,我們也在愛沙尼亞的森林小屋桑拿中目睹。《桑拿私語》以大量的近鏡頭觀察女性身體最細微的特徵與反應—如體毛與汗液,而在桑拿這樣一個帶來極致身體感受的空間中,全然的身體裸露和彼此肌膚的緊緊相貼也讓女性得以訴說那些和身體相關的痛苦。
裸露的女體經常被視為脆弱甚或風險,彷彿女人的阿基里斯腱,一旦女人裸露了身體,便該無所適從。然而,裸露也可以是女人的力量來源,是讓女人得以擺脫那種和自身身體之間長期以來,因為社會賦予的羞辱,而培養、累積的羞恥感受。《她與她的自畫像》裡,面對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領域、有時希望自己可以沒有身體的阿波羅妮亞卻在感到最脆弱的時候以裸身給予自身力量,更在描繪其他女性身體的過程中回頭建立個人的身分認同。
女人的身體也從不獨立存在,而是被放置於由種族、性別、國籍和階級,在各種社會眼光凝視、甚至監督下的細密網絡之中。
《大地母親》與《夏日片羽》兩部作品,便清晰而深刻地記錄了,在美國社會中,系統性的種族歧視、邊界的管控、世襲的階級弱勢如何和性別交織,針對黑色與褐色的女性身體打造出獨特而嚴苛的監管與壓制,甚至是暴力對待與放逐。在這些女性的身體上,我們也看到不同的政治力量如何交錯,女體成為被爭奪與侵略的戰場,而女性又是如何以這樣被高度性別化、種族化、標籤化的身體,尋求生存、進行反抗,建立自身主體。
說起父權體制與種族主義結合後對特定女性身體的監管,《誰來做主:運動殘酷記事》這部紀錄片所訴說的事件,是再為明白不過的例子。看似以追求體育競賽的「公平」為目的,這些針對非白人女性田徑運動員所進行之性別檢查,其實是在種族偏見與二元性別刻板印象下,針對「誰才是真女人」的粗暴定義。
另一方面,對於女性的身體監管也經常以傳統、文化之名,全面地被實行於女性從衣著到言行的日常生活之中。印度導演以伊朗為主題的紀錄片《通往美好小徑》透過它的鏡頭與對談對象,以極為溫柔的口吻拆解著這些監管,以及被監管的當事人如何在長久的不自由之下,將監管的精神內化,又如何在生活的縫隙中予以脫逃、抵抗。這部電影乃是受到了早逝的伊朗女詩人、導演芙茹弗・法洛克扎德的啟發,而法洛克扎德拍攝於1962年、以伊朗北部一處漢生病人收容所為主題的紀錄短片《房屋是黑的》亦收錄於本單元中。漢生病人因為疾病而改變的面容,及因此被定義、限制的身分,結合他們如何透過音樂與詩歌和身體的苦痛抽離(抑或是合而為一?),何嘗不是女性生命經驗的隱喻?
最後,法國劇情片《光》看似並未以「身體」為主題,卻在作為主角的四位女演員追求職場成就、愛情、家庭與慾望的過程中,重新探訪了身體的脆弱與堅實、飽滿與消逝。如果沒有身體,我們又當如何寄託與直視靈魂?
這九部電影的觀影過程其實必然帶來某種疼痛。但與其說那是一種感同身受或物傷其類,倒不如說是一種親密卻又疏離的體會。女體經常活在他人的凝視和檢查下,被細細打量、被評論、定價,但女性自己卻總被迫與自身身體切割,進而感到遙遠和陌生。於是,這些觀影經驗彷彿矯正某種長久的僵直,血液重新流通的甦醒過程難免伴隨肢體末段的痠麻感,但疼痛又是令人期待的,因為那代表著回到自己之後,每一根神經都再次活絡的新生。
V太太
女性主義者,七年級生、台北出生長大,如今旅居德國。以前學社工與社會政策,現在常用的職業標籤包括譯者、性別議題評論者、家庭主婦。譯有《不只是厭女》與《厭女的資格》,性別評論可見於鳴人堂、端傳媒等網路媒體,及性別部落格Queerology和個人臉書頁。也與Queerology團隊共同經營Podcast節目,討論大小性別議題。 混跡社群網站十數年,深信語言與溝通的重要性和力量,因此覺得回覆網路留言是很難的事情。不相信身分政治是唯一,但最大的願望之一是看到越來越多的女性創作者說女性的故事、寫女性的經驗、拍女性的人生。不認為台灣是一個女權過高的國家。
Feminist, translator, writer, housewife, and movie-lover. Born and raised in Taipei but currently living in Germany. Loving movies for their ability to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we live in and to transport us anywhere and anytime beyond us. Deeply believing in the power of stories, and therefore always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more female creators tell women's stories and exper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