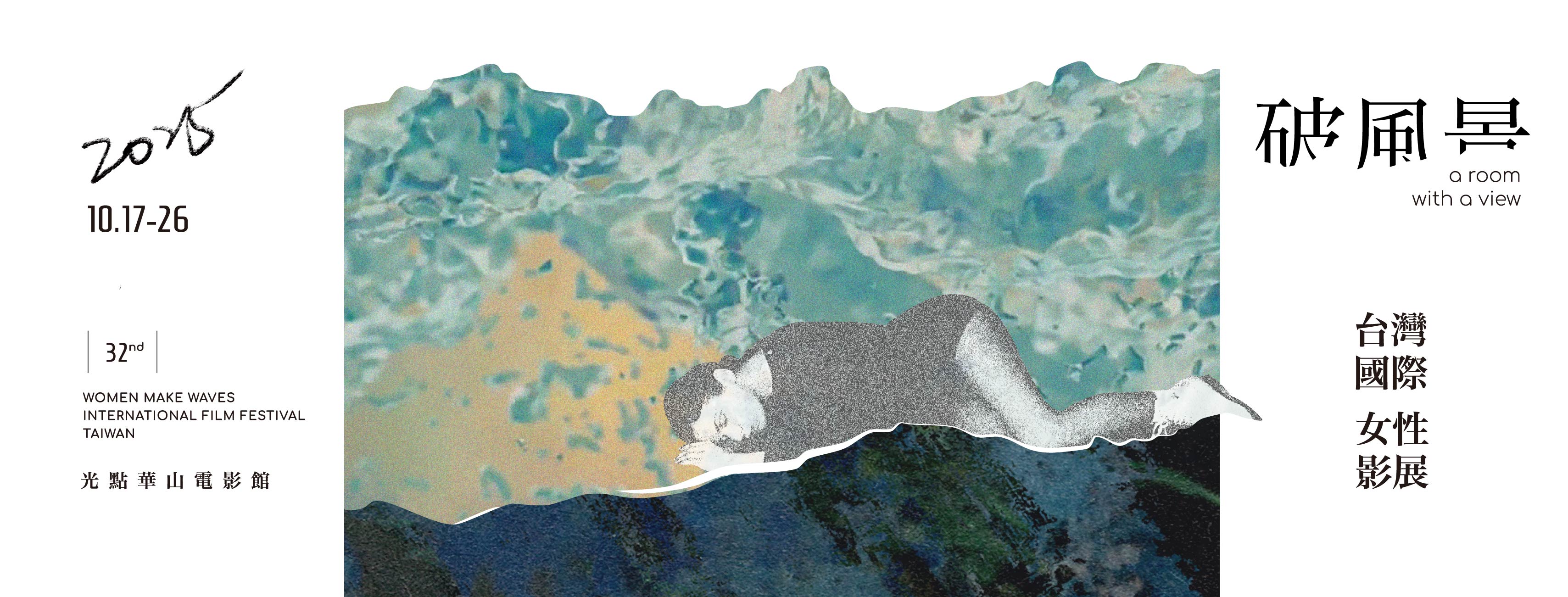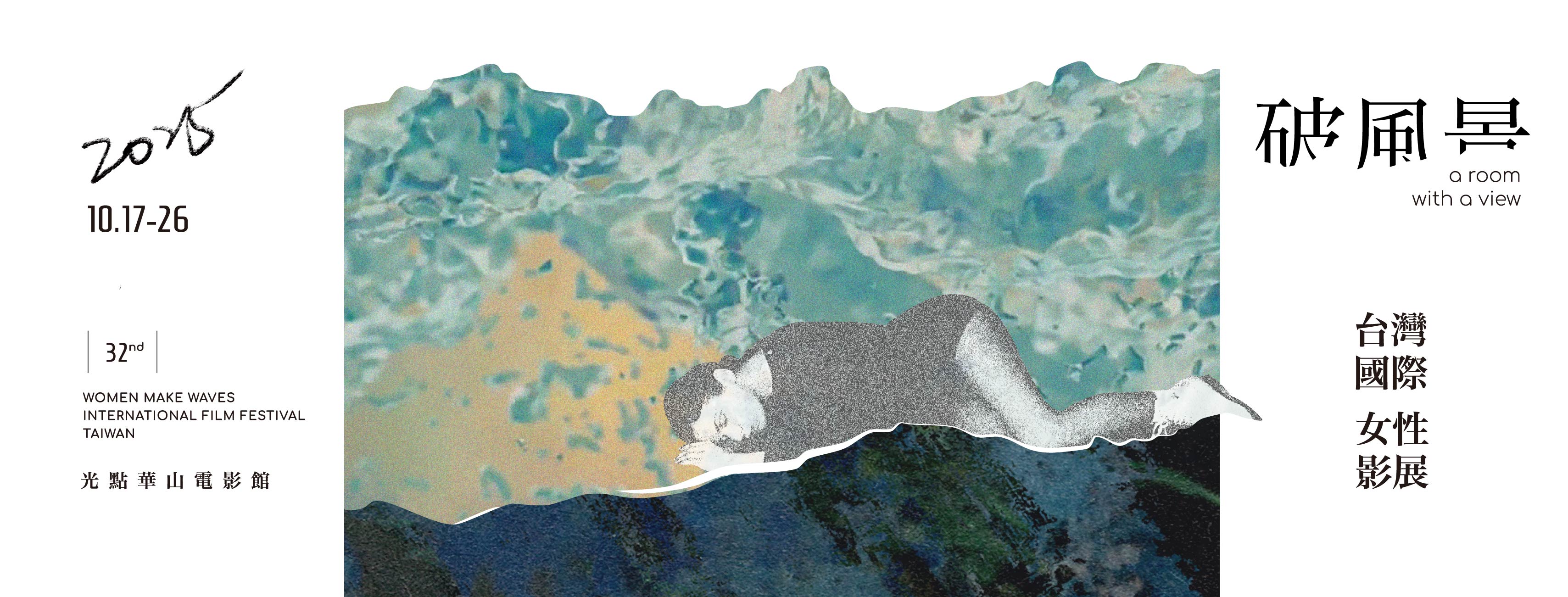在給我的記憶裡記得我 Remembering myself in history
文/郭敏容
在定義本單元的幾個關鍵字——家庭、國家、記憶與私影像以外,無所不在又游移不定的另一個關鍵字,是個體的我。即使是私影像的「我」,一旦開始解釋我所理解的世界、希望你談你的感受、試著了解她的過去,描述被他們拿去的國家敘事,那個「我」就進入協商、找尋、被否認、學習對話,這是稱作為社會化的過程,找到能被理解、習得生存法則的歷程。同時,又再試著重建被稀釋的我,和理解我的社群,至少我得記得我自己,至少我得找到理解我的人。
《愛的缺口》的主角黛兒娃所面對的殘酷即在此,五歲被父親綁架的黛兒娃,直到國家介入與社福保護下才以另一種暴力方式理解到父親所稱的愛,其實是長期性侵,她一直活在與父親兩人世界的謊言。但進入正常社會,她得先否定自己的認知與記憶,仍應屬童年的她長期被過度性化,以致於就連她對情感的需求也構成威脅。當黛兒娃靠近照顧者,表現好感,照顧者對她肢體接觸的謹慎所代表的既是社福系統的規訓,也是機構的自我保護;影片並不解釋黛兒娃的想法,那是國家進不去的空間,也是這部影片的善意:黛兒娃的情況是如此,國家將她自受虐的狀態拉出,影片劃出社會的界線,但盡量不以拯救者的姿態告訴黛兒娃該怎麼否定自己以讓社會接受她。
《芒果成熟時》帶著另一種殘酷,那份殘酷沒有國家的介入,而是跨世代、跨文化的質疑與尋求理解。導演拿著攝影機希望能理解她母親遠離斯里蘭卡家庭的痛苦,和她的祖母,她母親的母親讓自己女兒長期承受家庭傷害,卻選擇不改變狀態的藉口。或許更難受的是這三代女性的故事並不陌生,家庭中同為女性的長輩出於社群壓力,對家中加害者的繼續容忍,對在西方出生成長的導演來說不可思議。傳統社群的約束力是共同加害者的藉口,或是需要外來者擾動——在本片,作為孫女的導演因為文化距離,轉換成能質疑傳統社群的外來者,而不完全被家庭關係所綑綁。在片外的文字訪談資料,當導演被問到要揭開母親過往傷痛是否充滿困難,導演回答母親是希望說出口的,希望能找到機緣說自己的故事。作為觀眾,我曾玩味導演是否透過拍攝,將自己轉換成三代女性解放者角色,這樣輕微的質疑,在結尾的另一個翻轉再次被複雜化——私影像的拍攝總是逃脫不了對自我難關的處理。
《我未曾到過的故鄉》同樣是三代女性的遷徙,也同樣是孫女輩、出生成長在西方的導演希望了解母親那邊的故事,母親在1979年伊朗革命期間來到美國,自此未能返國,與家人離散多年。導演對伊朗的想望或許是受到伊朗女性上街抗議鼓舞,或許是對前往伊朗的念頭被母輩再三勸阻而更執著,影片拼湊母親與祖母的個人記憶,交錯剪接導演學習波斯語的挫折,伊朗對導演來說是什麼意義的母國——除了作為母親的母國——是我在看片時找尋的答案,溫柔的母親是理解的。
《蜜莉蘇坦多:想像的旅程》對國家與個人記憶的對比有著強韌的力道,既對大寫歷史提出質疑,也對個人成長及認同展開尖銳但必要的對話。成長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內部被完美設計與白人隔離、由黑人自治的川斯凱共和國,導演所以為的未曾經歷歧視記憶,其實是被更大的種族主義所欺瞞,而結束這場謊言的曼德拉,讓導演這一代人首次與白人同齡學童一起上學、相信南非彩虹之國的夢想。但就像自小被父親綁架,活在平行世界的黛兒娃,社會和國家所稱的正常,對個體是痛苦的記憶否認,對自我認同的重建。以自己名字作為片名的蜜莉蘇坦多導演不僅透過檔案畫面、照片和家庭訪問詰問過往,她將製片,自己的白人好友拉進對話裡,只聞其聲不見影像的聽同世代兩個種族的對話——體驗種族不只是黑人認知到自己的被排除,白人不能在種族主義的討論與反思裡缺席。她與好友的對話是私密又政治的,那既不是兩個個人,也不是家庭,也不是個體對社會或國家的反抗,那像是更劇烈的越界,但又必要。
《小嫉妒》來自維德角的保母與法國白人女孩的連結自然是種族的,也是跨國勞動的女性經濟產出,影片沒有迴避這些可以分析的角度,但選擇著墨在情感連結,影片像是選擇保留一個在談跨國勞務付出的私密空間,不否認這樣的情感也是對記憶的處理。《若愛有形》有著本單元最溫柔的親密,首任文化部長寶玲娜及在獨裁者皮諾契特主政時任記者的奧古斯托這對伴侶形塑智利近代史及國家文化,拍攝失智的奧古斯托像是以另一種方式讓人思考記憶是如何被塑造、又多麼脆弱。《都是你們害的》由畫作及案例討論在經濟高度開發的西方社會,面對家暴威脅下反擊的女性,影片挑明的讓這些女性冷靜述說選擇暴力作為最後手段的理由。《交易》是一部聰明的黑色幽默電影,將社會的道德真空推至荒謬的極限,以解決一個家庭的長照問題諷刺當代全球民粹當道、另類事實成為常態的社會現實,作為巴西電影,劍指前總統波索納若的意味明確。
回到亞洲,《密語者》在形式與影像上並不張揚或創新,就連被傷害當下也是安安靜靜、難以被描述指名的,但那傷害卻本質的否認一個集體,那集體不是家庭、也不是國家,而是女書所留下來百多年來在女性間所流傳的書寫與私密記憶。女書於上世紀即將凋零前夕被外界發掘,直至今日,除了被收編在國家體系,由官方認可正統的傳承方式,也在父權及資本兩股力量下只遺留符號性的商業利益。影片中讓人安心的片段,是女書傳承人與女書耆老在無國家介入的空間內繼續聊著,彷彿再度回到隱晦私密的空間是唯一可能。
在台灣社會終於試著提出不需要為大我犧牲的當下,本單元影片再次提醒在大歷史、社會規範底下,個人記憶始終具備擾動可能性。不否認這些個人的記憶是從這些影片裡冒出重要的決定,即使那可能像《密語者》無意識下暗示的嚮往——從國家體制收編中缺席,在私密的空間裡再度找到自我。
郭敏容 KUO Ming-Jung
獨立策展人及製片。曾任台北電影節策展人,新加坡國際電影節節目總監、藝術總監,瑞士盧卡諾影展Open Doors工作坊評選委員及顧問,台灣國際人權影展選片召集人。她於台北電影節策劃主題城市、焦點影人,與法國南特三洲影展合辦,引進國際合製一對一工作坊、策劃電影正發生及VR放映、展覽、論壇及駭客松、新導演論壇。為《葡萄牙電影》、《一瞬二十》等書總編輯。於新加坡時主持東南亞電影學院,包括資金補助、導演培訓、青年評審團及製片論壇,於2022年擔任坎城導演雙週顧問,並擔任國內外影展如鹿特丹、釜山、香港、TIDF、金馬等競賽及國際基金評審。
Programmer and producer. She was Program Director for Taipei Film Festival. She joined Singapore Intl. Film Festival in 2019 as Artistic Director. From 2019 to 2021 she was on the selection panel for Locarno Festival’s Open Doors. She set up Island X Pictures in 2022 to develop feature films. In 2022 she joined Directors’ Fortnight as a consultant covering Southeast Asia and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