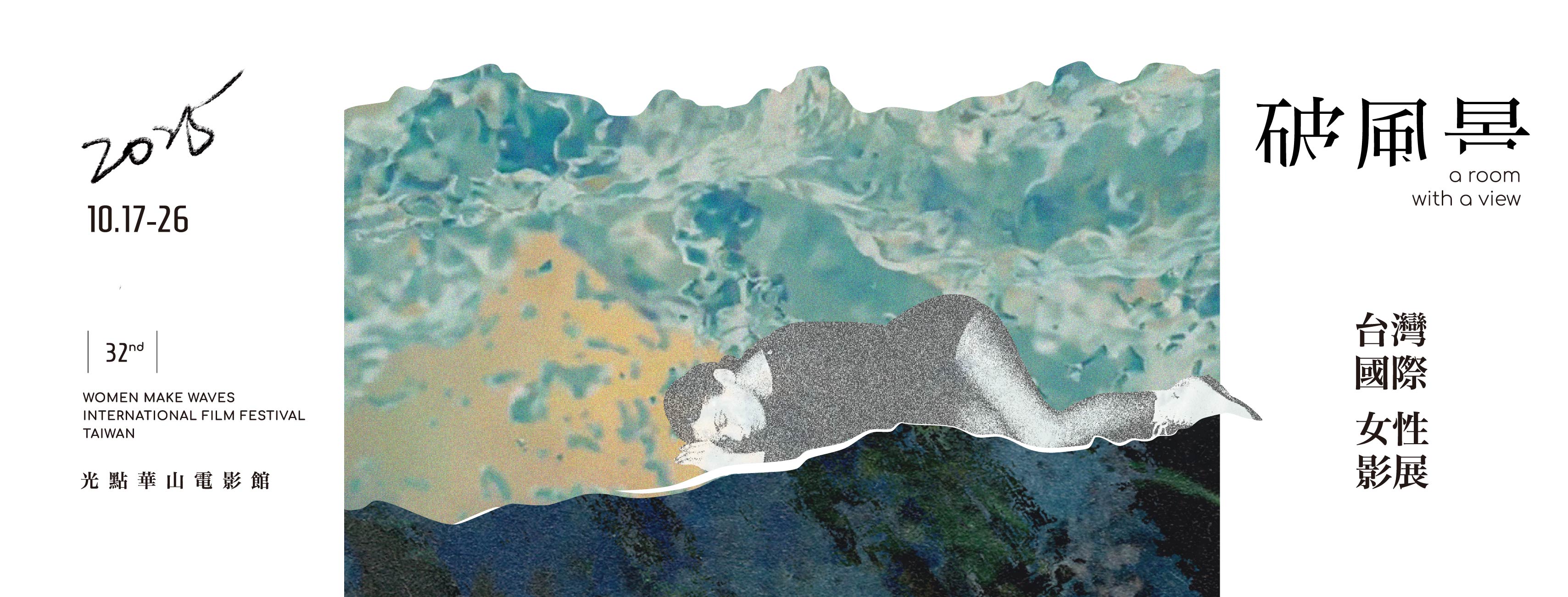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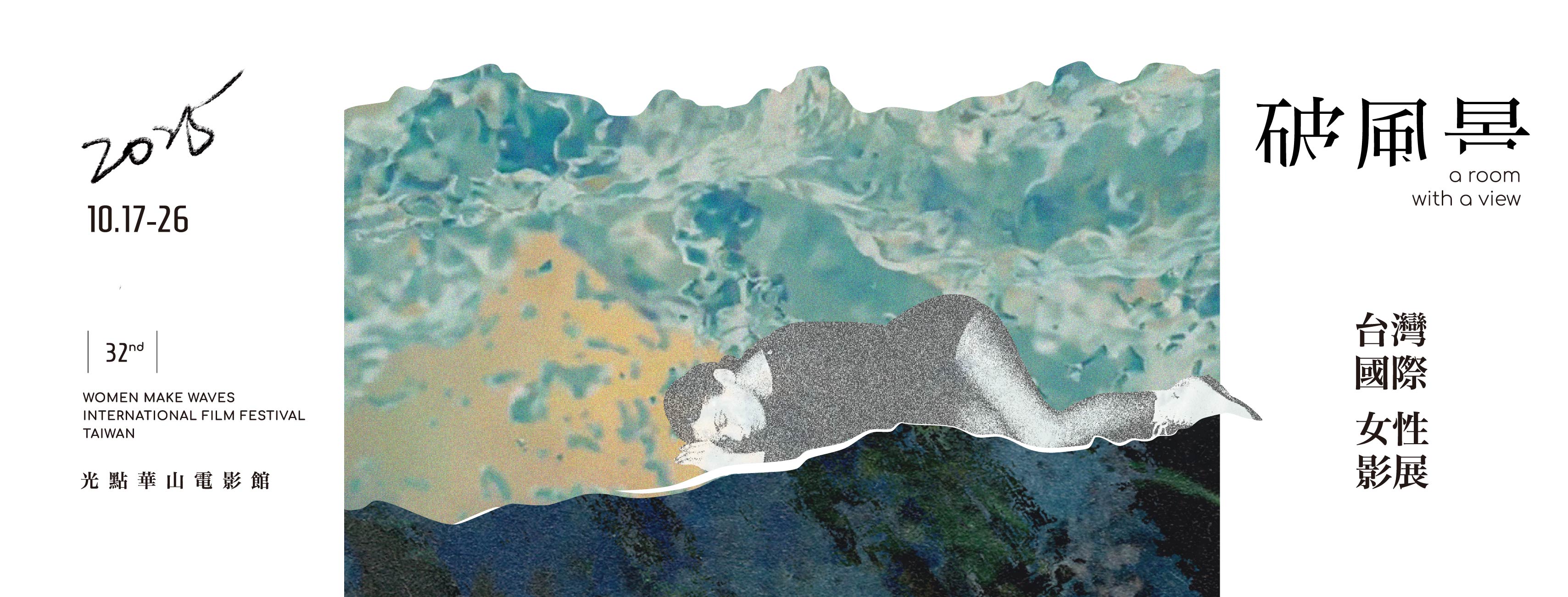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時間:10/18 (三) 19:30
地點:有河書店
與談者:
陳慧穎(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策展人、《她的電影意識史》主編)
謝以萱(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選片人、《她的電影意識史》主編)
朱孟瑾(電影文字工作者、《她的電影意識史》大事件編輯)
慧穎:這次很開心能夠在有河舉辦新書分享會,今天會簡單分享為什麼會有這本書,今年是女性影展的30週年,為此團隊策劃了一個特別單元,叫做重返新時區,這個單元爬梳了過去這30年的作品,原則上以台灣的電影為主,一部分是過去在女性影展放映過的片子,雖然是以女導演為主,但是也不全然只有女導演,後面可以再多聊其中的選擇。我們想說這個單元,只有影片的放映其實有點可惜,想說也許可以搭配一個出版品,一方面也是透過書寫電影,讓這些影像的討論可以用另外一種型態再延續。其實出版品跟電影的單元規劃是一起產生的,它們是兩種不同的媒介、不同的呈現方式,但是彼此可以互相對話。待會也可以再聊關於重返新時區單元的選片過程,因為這也會牽動到我們如何去思考這個出版品的內容。
以萱:我們就先從這個問題意識開始好了,書名叫做「她的電影意識史」,各位可能會好奇這個「她的」到底是誰的?女性到底是指什麼,是指女性導演,還是談論女性題材的電影,好像可以有不只一種答案,這對我們來說其實很重要。
慧穎:回扣到女性影展選片的體質,到現在還是會有很多疑問,像是女性影展是否就只有女性觀眾,身為男性是否可以去看?或者說我們是否只有放女導演的作品?光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其實都是不是,我們希望它是越來越開放的一個狀態,雖然說書名用了「她的」,但其實光是女性怎麼定義本身就非常的複雜,它絕對不是單就順性別來歸類,而且我們還滿希望這個定義是遠超過認同政治的,我們這邊只是稍微舉一些例子,所謂的「她」可能會牽扯到的東西,包含女導演的、女性主義的、女性電影的、女性議題的,或者比較是機構面,像是台灣女性像學會、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那從機構面來講,我們就已經不是只有在放女導演的作品,我們有點像是透過這些關鍵字,希望可以網出一個彼此交織、也許彼此不見得是完全整合的,但希望它是一個不斷擴充的狀態。至於電影意識史,其實我們一開始討論的時候,的確是想要碰觸到歷史的,但是這個部分我們很快就觸礁,因為要談歷史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我們也希望這本書比較像是,它可以不斷地拋出一些問題,去思考女性影像到底可以怎麼樣想像,台灣到底有沒有女性影像史,還有女性影像史又跟女性影展是什麼關係。我們還是有稍微地拉回到女性影展的部分。這本書等於說是從很多的問題意識開始,光是這些問題我們就討論了非常久,這過程我們也不想把它定成一個很絕對的答案,但透過這本書,再加上重返新時區這個單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自己也有很多收穫。
在進入下一章之前,我想要再稍微講一下為什麼會取作電影意識史,其實也跟另外一本書有關,就是張亦絢的《性意思史》,這本書其實對我本身也非常重要,因為它裡面很誠懇地去碰觸到很多關於性、還有性別等等很麻煩的一些事情,以及為什麼大家談到性總是會卡住,我覺得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境,回到女性影像或者是任何以性別稱之的電影,大家好像也常常會卡住,好像一牽扯到性別大家就會有很多的疑問,比方說書中游靜的一篇文章就有提到,他們之前有辦過女性影展,馬上就會受到很多的質疑,可是這樣的質疑在辦其他也是特定特質的影展,比方說以美國某一段時期為主的電影,他們也不見得會引戰,但是只要牽扯到性別的時候,就會有很多的質疑出現,所以也有一點想要回扣到亦絢他在書裡面的那種感覺,這本書也像是透過書名來回應這件事情。
以萱:這本書比較像是提出一個階段性的提問,當然一方面我們回顧過去女性影展或是台灣的女性電影,我們有一個階段性的,也不能說是定論,而是有點像呈現一個階段性的成果。剛剛慧穎有提到我們在討論女性影像史的時候,發現會不斷地觸礁,而這個觸礁,其實會有滿多面向的,我覺得滿關鍵的是,我們在思考重返新時區單元的時候,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很海量的片單,光是整理出那個片單,將橫跨三十年以上、不同媒材的電影,整理成現在可以跟團隊一起看、一起討論的檔案模式,這件事其實就花了團隊非常多的時間。也補充一下我們在規劃重返新時區的單元,除了我和慧穎以外,還有另外三位成員,分別是羅珮嘉,王君琦,還有卓庭伍,五個人一起討論重返新時區的片單,最後是從四、五百部片中,選出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單元裡面的27部片,過程中也有滿多掙扎的,因為就會回扣到開頭的提問,也就是到底什麼是女性影像,我覺得我們現在也沒有一個全面的答案,因為老實說它就是一個不斷在變化的過程,它也會牽涉到女性影展在台灣的社會位置上,也經歷了不同階段的轉換。
拉回這個出版品,我們在編排這個出版品的架構上,它主要分成兩大塊,一部分是another herstory,這比較是從一個影像史的角度來看,另外一塊是another festival,就比較回到女性影展作為一個主體,它可以捲動的各種事情,可以分享一下我們為這件事情的前置作業,其實兩個是一起的,因為包括片單跟another festival,都有重新梳理女性影像學會的歷史,因為作為機構的出版品,它承載的任務,一方面也是要去梳理女性影展的歷史。

慧穎:這兩個面向它雖然我們這樣分,但它其實是有時候交織,有時候甚至是互斥的,會說互斥是因為我覺得影展無論如何,它一定會有很現實的影展機制,可能因為不同的考量等等的,也許有些片就沒辦法放映。在做重返新時區單元的時候,我們先從女性影展本身的archive先找起,再從中去思考這些年代當中是否有一些,傳說中或者是我們曾聽聞過,一些也非常好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我們沒有辦法看到、過去沒有辦法在女性影展放映,或是因為各種原因錯身而過,所以another herstory某種程度上也在回應影展本身,它可能是無法觸及的部分,很多部分是分別來自不同的人群,有學者、曾經辦過女性影展的人,也有國外像是香港的女性影展的人,以及一些比較是社運或是檔案影像的面向,都非常不一樣,還有一部分是作者,像是書中曾文珍導演的一篇文章,希望從他們的角度去碰觸一些面向,可能有時候我們單純在講女性影像歷史的時候,不見得會往這些面向走,這次有點像是這兩個大單元互相交織的感覺。
和這本書配合的除了重返新時區的單元之外,我們也做了一個還滿瘋狂的事情,就是我們一邊在撈過去的影像,同時我們希望能夠找尋過去參與過女性影展的歷屆的理事長、策展人,大家一起來談,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是因為我們發現大家的記憶有些不太一樣,有很多記憶是互相錯置的狀態,我們辦了兩次茶會,希望大家直接地來談女性影展的歷史,過程非常的精彩,我們把這個過程所談到的一些歷史整理出來,做成類似編年表的形式收錄在這本書中,我們也有邀請他們進行比較是個人回顧的部分,也有收錄在書中。
以萱:當我們回頭爬梳女性影展的歷史,我們看到的現成的東西,可能是影展手冊、傳單,但你要想它已經從90年代橫跨到現在,可能網站也已經不復存在了,比如說第一屆的節目手冊,應該就只有那一份正本吧,我們現場只能展出影本,因為真的太稀有了。回頭爬梳影展歷史的時候,會發現我們有的東西其實並不多,關於女性影展的其他記憶,其實是分散在不同的人的腦中,或是他的身體經驗裡面,所以其實辦茶會的時候,那個場合我覺得就非常有趣,你會看到很多不同時代參與女性影展的前輩們齊聚一堂,有的人是線上參與有的人是實體參與,我們事先有列一些問題作為當天討論的題綱,就請他們來聊他們經歷的那一屆影展,在他們印象中的一些事情。我覺得滿有趣的是,就像剛剛慧穎提到,每個人的記憶會有一些對不起來的地方,那些對不起來的就會是很有趣的部分。
慧穎:比對記憶的部分我覺得就非常有趣,包含大家對於地點,比方說辦公室,我們其實很後來才有辦公室,然後光是辦公室的地點,大家的記憶都不太一樣,還有關於第一屆是怎麼樣辦成、有多少人的參與?我覺得這個過程非常有趣。
以萱:像這一部分的討論,我們邀請了曾經參與過的重要前輩們,可能是歷屆理事、策展人,請他們講述,就我們討論過的內容,再由幾位作者書寫出來。而我們討論的內容都有留下紀錄,可能也是作為未來的機構檔案的留存,過往這些東西可能相對地沒有很有系統地在保存,其實這次三十週年,無論是節目單元的規劃也好,或者是透過出版品的過程,也都是在重新梳理、歸檔跟累積材料。
慧穎:必須很誠實地說,女影經歷多次搬遷,內部的資料非常的亂,我們也透過這次梳理過去的歷史,以及不斷地修正大家的記憶,我覺得光是內部的人在仔細確認每件事的真確時,都是很浩大的過程。
以萱:或者說找到某種…不能說共識,但是其實有點趨近那種感覺,就是寫上彼此記憶中可能沒有對起來的地方,經由一起重新回憶的過程,找到一個比較趨近的共識。這個主要是我們這本書的兩大結構,還有另外一塊大結構就是年表的部分,這邊交給孟瑾來談。
孟瑾:其實我是第一次寫年表,我在寫的時候發現,年表是一個比想像中還要主觀跟專斷的東西,它不像寫文章,你可以在寫的過程中鋪陳,透露你可能是怎麼思考這些事情的,但是大事記它就這樣羅列出來,你好像沒有辦法那麼明確地知道寫作者本身到底在想什麼,所以我來講一下,當初寫這個大事記的過程。大概今年1月左右,慧穎來聯絡我,那時候就知道前面兩個部分已經確定,會有一個電影文化場景和另外一個性別與運動場景,然後我接到的時候,其實年表的部分也已經開始在收集基礎的條目了,所以我的部分比較像是,比如像電影的部分可能還有一些缺塊,或是有可以增加的內容,除了把已有的基礎條目再編修以外,也增添一些跟電影有關的條目。我們每個月都會線上討論,需要討論或增刪的資訊,決定內容的去留。可是因為我自己的背景跟女影的關係沒有那麼接近,也不是專門在研究女性影像、女性運動發展史等等的,我比較熟悉的是電影史,所以那時候我覺得在性別跟女性運動場景的部分,主要是依據慧穎提供給我的資料,吸收跟認識女性運動在不同的時間點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當時慧穎提到,希望除了一些常見的比如修法、法律上的、遊行上的活動以外,還能夠納入一些社會上組織的形成,一些雜誌、出版品,或是其他的一些活動,所以這部分比較像是,透過慧穎給我的東西去理解台灣社會不同時期發生什麼事。
再回到電影的部分,因為女影早期跟當代藝術的關係其實滿密切的,所以會希望其實可以擴及到其他的藝術領域,另外是其實台灣一直以來的電影,跟文學改編也是有很大的關係,大部分女性或許沒辦法在早期成為導演,可是她有可能以女性作家的作品或是編劇改編成電影,跟文學的關係也是很密切,所以那時就希望可以以電影為主,其他藝術領域為輔,去增加它們彼此的關聯性。我接到的時候,第一個疑問其實也就是,到底女性影像的範圍是什麼?我那時候還問了很多問題,比如說我們是不是要列生理女性,那如果是男導演可是有女性意識的呢?像台灣新電影就常常被這樣說,或是如果有些女導演,像瓊瑤的作品,可能現在我們看起來會覺得,這個意識是不是落伍了,當時碰到很多問題是,我們到底要列什麼東西進去,我覺得有個比較明確的範圍是,生理女性導演的作品一定是裡面最核心的,因為她們可能在過去的影像史上是不太被提及的,這一定要最主要地放在這本書的重點,男導演的作品因為相對討論度比較高,可能在這就先不去提及他們,或是像比如說張毅跟楊惠姍合作的作品,可能就反過來以楊蕙珊的視角,如何呈現了不一樣的女性形象,凸顯出當時社會對於女性形象一些矛盾的想法等等的。
台灣寫電影史的書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多,撇開是不是女性,光是電影史本身就不是很多,我主要參考的書,是《跨世紀台灣電影實錄1989-2000》,就是電影資料館,黃建業老師當時主導編輯的書,我覺得它滿好的地方是每個月有像大事記一樣條列出來,但是每個月後面又會有一個附錄,附錄是選擇當月一些比較具代表性的事情,會提供像報紙的報導,可以從附錄看到有哪些人名看起來就是女性,再透過這些名字去聯合知識庫或是搜尋這些名字、關鍵字,反覆比對她可能其實是位女製片、女導演或是從事相關工作的人,我的資料來源其實最主要參考的是這個。慧穎提供給我關於性別的部分,我那時候看了一個網站叫台灣女人,我覺得還不錯,是台史館那時候委託中研院,合作建置的一個研究計畫,後來文化部就把它弄成網站。
慧穎:我先稍微講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大事記,其實跟女性影展本身的歷史是有關的,因為1993年女性影展叫做女性影像藝術展,這個展其實是在霍克藝術中心舉行,所以它一開始是在類似藝廊空間的狀態下舉行,第二屆1994年的時候是在皇冠藝文中心,後來又到了帝門文教基金會,在帝門文教基金會辦了兩次,然後再移到當時算是文化場景之一的誠品,後來才慢慢地進入戲院,等於說我們是在2000年的時候才進入戲院,那時候已經到了第七屆了,所以我覺得女性影展的發展,其實不是一開始就以現在大家所認知的影展的方式呈現,我覺得光是這點就還滿有趣的。前幾屆在帝門文教基金會的時候,現場也有一些展覽,可能是攝影、裝飾藝術,甚至也有一些行為藝術的表演,所以它其實是非常複合的展演形式。女性影展在一開始的時候,是由黃玉珊導演的黑白屋電影工作室,還有婦女新知基金會一起合辦的,婦女新知想透過影像做運動,跟當時黃玉珊導演的想法是有一致的,因此合作進行了第一屆,但從第二屆之後婦女新知就沒有繼續參與,等於是回到真的以影像為主的發展方式。但我覺得婦運的這一塊,其實在女性影展早期發展的時候一直都在,所以我覺得看女性影展的歷史,不能把它完全從性別運動或婦運那邊分隔開來,所以在大事記設計的思考上,才會特別把電影文化場景跟性別運動場景都拉進來,為什麼我們會很複雜地包含了這麼多東西,也是因為覺得尤其是在談女性影展,電影跟性別都會碰觸到的時候,好像很難真的進行切割,所以我們就是盡量包含有相關的,尤其是我們還滿希望可以帶到場景的部分,它可能不見得真的是作為一個運動,還沒有到遊行的程度等等的,可是它可能在當時有非常特別的性別氣氛,那我們會想盡辦法把它也寫進去,這是我們在思考大事記的時候會做的一些事情。
我也想要稍微講一下為什麼會用大事記,這個我們也有稍微討論過,因為像剛剛說的,它是開啟問題意識的一本書,但是在我們討論的過程中,真的要談女性電影的時候就會發現,它非常的斷裂,或者是身世不明,光是要定義都很難,也非常的邊緣。這個邊緣是,我們在實際查找資料的時候就會感受到,很多資料都是東撿西撿地試圖拼湊,我們最後把它弄成一個大事記,希望它還是一個時間的堆疊,那這個時間的堆疊,我們在做的時候其實也非常的剉,因為它畢竟牽扯到很多,什麼是重要什麼不重要,什麼該碰觸什麼可以先放在一旁?光是這個過程,尤其是很多歷史都還沒有真的離開,或者是我們一直會覺得,我們好像還沒有到可以去定義或是書寫的時候,問題是那什麼時候才可以?這個過程我們就是戰戰兢兢地在進行,所以我們也開了一個網頁版,大家在書的最後一頁有一個QR code可以掃,就會連接到這個網頁版,這個網頁版基本上就是希望大家編輯,因為我們能夠做的其實也還滿有限的,畢竟它是一本書有篇幅的限制等等,我們又碰觸到非常廣的事情,所以我們把編輯權限完全打開,希望大家可以藉此質疑也好、回應也好或者是編修都可以,希望儘量完整那些斷裂的部分。
以萱:我覺得就如慧穎說的,其實寫年表是一件滿危險的事情,待會可以聊到這個書的設計,因為在年表的部分我們把它切分成上下兩塊,那電影文化場景跟性別運動場景,你會看到它在翻頁上是分開的,是可以對照著看的,在設計上我們也跟設計團隊和圃設計滿密切地討論,到底要怎麼呈現這個看似平行,但事實上有很多交織的兩條時間軸,要怎麼在出版品的框架下呈現這件事情,出版品的框架會有各種限制,比如說年表在排版上會有一些字數上的侷限,這也會是一個限制,經過這個過程也引導我們思考,如何讓這個年表可以是一個開放的狀態,因為當它變成出版品的時候,還是會有一定程度是被定型的,那未來的人要怎麼樣透過這個定型的材料再重新地運用或是延展,那其實就是我們在思考的事,所以才會有這個網頁版的出現。可以舉一個例子,比如說裡面的一位作者陳韋臻,她爬梳了1990年代的拉子電影,那我覺得她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完全體現了我們剛剛提到的很多困境,包括這部分的電影史是斷裂的,我們看不到那些片子,很根本的是,當我們沒有辦法看到這些電影的時候,我們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對這些電影做太多討論的,能夠依據的可能也只有現成的文字資料,但是女性電影在歷史上偏偏就是很少被書寫,所以有著各種困難。像作者陳韋臻她回頭去訪問這些影人,其實找人的過程也是滿艱辛的,回頭去訪問就是在提供更多在電影之外的記憶,讓這些故事或是場景可以更完整,更讓我們認識當年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創作狀態。
慧穎:我想要稍微補充一下,剛剛孟瑾提到性別與運動場景,我們後來去請教了滿多有實際參與過,無論是婦運也好,或是性別運動的一些前輩,我覺得這個討論的過程非常有趣,等於是我們呈交了一份性別運動場景的年表,大家來回地不斷修改,我覺得幾乎像是打仗的那種感覺,大家會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光是這個編輯過程,當它是有限的條目,想要特別地強調哪一些,或是說重要性在哪,不斷在不同的版本之間來回地協商,最後大家OK了、累了,其實這都有一點,可以說一定是有個彼此妥協、權衡到了某個境界的時候,像性別尤其是如此,我覺得在性別那幾乎是吵架的一個狀態是非常明顯的,但我覺得這個過程非常有趣,我自己也學習到很多。電影文化場景的話,對我來說那個過程反而比較像是撿拾,因為真的太少部分有被好好書寫,當然有很多是遺漏的,剛剛孟瑾有提到滿多關於我們想要從哪方面著墨,我們的確後來比較著墨在生理女性導演的作品,但其實有向外擴充,因為在過程中發現滿多,尤其是早期的前輩,她可能是從製片或者是演員再轉導演的。
孟瑾:我在寫年表的時候覺得,除了女性創作者和作品很少被提到,其實它還是跟整個台灣電影環境很有關係,比如像早期台灣製片業沒有很發達的時候,主要可能就是像中影這樣的官方機構,比較有資源去做這些事,所以像彭月娟或是陳文敏,有這樣的背景或資源能夠去當導演或製片的人,其實是少的。在找尋這些人的名字的時候,比較常看到的反而是女演員們開始累積了一些資源之後,她們也不會去當導演,可能因為當導演背後還是有一些技術、器材,其他方面的門檻限制,她們可能會轉而做製片、開公司之類的,但是到後面一點的時候,就會開始看到像李美彌在出來拍自己的片之前,也擔任了很久的場記、副導演,漸漸開始在拍攝幕後的培養裡面出現女性,可是女性要能夠獨當一面地拍片,又是另外一個門檻。我們可能就會看到她們擔任了很久的副導,最後終於拍成一部片,但是可能在80年代初、70年代末的時候就開始轉進了電視圈,電視圈提供了另外一個管道讓她們去發展,這也跟整個台灣電影發展的大環境有關,像後來1978年的時候金穗出來了,然後1988年中時晚報電影獎等等,也都提供了另外一些管道,讓短片創作者或是獨立的拍攝者,可以有其他曝光的地方,所以整個環境的變化也會讓女性在這個時候,有些人可以先出來。我在查的時候發現,金穗好像從前幾屆開始,就已經每一屆都有女性被提及,但這些女性好像都沒有順利地進入主流的商業體制去拍片,她們可能一直都潛藏在一些比較獨立的領域。在寫這個年表的過程中,除了一開始聊到的,到底哪些作品或哪些人要被放進來以外,它其實也跟整個台灣大環境的種種限制,如何影響這些女性往哪些部分發展都很有關係,這也是寫這份年表的同時覺得很有趣的。
慧穎:很有趣的一件事是,會發現某一個時期特別多副導是女性,但是去追蹤後續,她們有點像是消失了。我們會把金穗放進去,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包含金穗、純十六影展,還有中時晚報電影獎,都是幾個需要被特別提及的獎項,因為它畢竟是有別於更主流的,甚至是商業院線等等作品的一個平台,金穗之後接軌的各種影展,你會發現開始有一些重疊,當然又跟所有的設置條件,尤其是媒材的變換都非常有關係。
以萱:比如說重返新時區中的短片輯,你會發現裡面幾位導演,當年入圍的影展大概就是剛剛提到的金穗獎,那個時候還有16mm跟DV的競賽項目,這些影展在主流電影沒辦法有位子給女性導演的情況下,提供她們另外一個空間去進行這個活動。

慧穎:稍微帶大家看一下照片好了,這個是1993年在霍克藝術會館的照片,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空間,鄭明河當時被翻成曲明菡,她的《姓越名南》是1993年的開幕片,當年也特別來台參加影展,這是陳若菲導演,這年她代表的作品是《強迫曝光》,1995年的作品,還有曾文珍導演,那時候放映的是她的第一部學生作品《心窗》,另外這是我們這次也有放映的《波城性話》,下一張是1996年在帝門藝術基金會,那時的總策劃是陳儒修老師跟蔡秀女老師,後來1998年來到誠品,2002年到戲院的時候,開始慢慢趨近於大家比較認識的女性影展,更後面這是2008年在星光影城,還有2014年的胡台麗。我們的第一個章節another herstory裡面,剛剛有提到其中超過30年的時間軸,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黃色故事》,這是女影沒有放映過的一部作品,希望藉這次的放映讓大家看到,也算是片單裡不太一樣的作品,它透過三段式的敘事講述一個女性的成長故事,某種程度上也回應到《十一個女人》,張艾嘉和陳君天製作的電視劇,是非常有趣的呈現方式。
以萱:這部電影是1987年的,有點說是可以對照於,那時候新電影的幾位男性導演的作品我們都很熟悉,但是像張艾嘉、王小棣、金國釗合導的這一部,可能就沒有太多人看過或聽過。
慧穎:這次還滿開心的是,我們有收錄一篇游靜的文章,游靜寫的角度比較是在講她跟女性影展的淵源,可是我覺得不只如此,她也碰觸到了一個提問,就是到底辦女性影展這件事情有什麼意義?像她舉的一個例子是他在1990年的時候,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了女性電影節,當時聯合策展的還有黃愛玲女士,裡面有談到黃愛玲女士覺得很荒謬,為什麼辦女性相關的影展,就會不斷被質疑的這件軼事,她們的片單非常的有趣,這其實可以在游靜的個人網站上找到,她有留存當時的PDF檔,片單內容非常有趣,包含它的本月焦點是唐書璇的《董夫人》;除了有在香港辦女性電影節的相關經驗之外,她其實跟台灣的影展,不只是女性影展也有一些其他的淵源,2005年的時候,在台灣有辦一個亞洲拉子影展,這個影展其實在很多的史料中不斷地出現,也特別提到2015年的這一屆辦得非常盛大,游靜在文中提到她其實也有參與整個過程。
來去T吧看電影則是跟陳韋臻的那篇文章有關,其中碰觸到了滿多作品,像是我們這次也有收錄的陳若菲的《強迫曝光》,還有談到她學生時代的作品《我的男朋友和女朋友》,這部作品我其實還沒有看過,非常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看;除了陳若菲以外,還有另外一個靈魂人物,就是李以霏,李以霏其實之前叫做李湘茹,她非常重要,因為她的獨攬大權工作室跟台灣的性別影像、許多小型的放映等等都非常有關,包含她也曾經以工作室的名義跟熱線一起合辦獨立的同志影展,這些脈絡都有收錄在這本書裡。但是李湘茹她的這個脈絡,好像不斷地出現,但在歷史上卻是有點斷掉的,等於是她有一陣子非常的活絡,跟很多的性別團體都非常的緊密,但是我們去查近幾年來其實沒有什麼放映,後來是循線慢慢去找到她本人,才得以放映這次也有收錄的《2,1》,而這部作品當時在1999年,跟陳俊志導演的《美麗少年》部分的場次一起放映,在學者影城以及戲院上映,那也是第一次女同志影像在戲院上映,那個經驗其實也很特別,韋臻也有把它寫進文章當中,
以萱:可以預告一下韋臻訪問了三位導演,分別是陳若菲、李以霏,還有吳靜怡,她會將三個專訪分別寫成三篇文章,可以期待一下,因為她真的還滿用心的。
慧穎:我覺得這三個導演的經歷,也不能說完全補足,但是至少補充了滿多遺失的部分,像是大家談論拉子電影的時候常常都會提到《私角落》,和周美玲導演後續延伸出來的許多脈絡,但是相對的,有很多影片反而很少會提到,還有一部是邱妙津導演在1990年的時候,曾經參與了一個類似培訓班這樣的一個時機,拍成了《鬼的狂歡》,1991年的時候完成,這部片也是被對遺忘已久的一部片。另外這些是方念萱老師所提及的片子,因為這次重返心時區單元很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們希望能透過這個片單,稍微地碰觸到台灣性別影像史很少被觸及的一些部分,其實很大程度就是紀錄片,所以我們這個單元真的大概八成是紀錄片,其中很多的無論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歷史事件紀錄,或是某些很少被觸及的議題,我們有特別地收錄在其中,像《阿媽的秘密》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應該是楊家雲導演唯一的紀錄片作品,也是第一部關於慰安婦的作品;《老查某》跟《一代名妓——官秀琴》則是都碰觸到1997年台北市廢公娼的事件,這兩部我覺得都是非常難得的存在,這次放映的《老查某》是今年才剪出來的版本,但它之前2006年的版本跟《一代名妓》,其實都有在台灣的春光疊影影展進行放映,是日日春特別舉辦的一個電影節,它等於又向外擴充到性別相關團體所舉辦的影展的脈絡當中。
以萱:我覺得《老查某》2023年的新版本,跟它2006年的版本非常不一樣,我覺得這個滿有趣的是會回應到這部電影本身,當年拍的時候其實是運動取向很明確的作品,而《一代名妓——官秀琴》跟2006年版本的《老查某》它們是同年份推出來的,你可以看到兩部影片都有很明確的政治訴求,包括影片的敘事手法和呈現方式,比如說長度也好,或是它想讓裡面的人物展現什麼樣的立場的方式,其實都跟我們現在看到2023年的《老查某》版本非常不同,所以還滿推薦大家可以趁這個機會去看新版《老查某》,因為我覺得新版本更將焦點放在人物上,為什麼她會是現在這樣子的情況,更從情感面去談,而不是那麼地想要在那個時間點,去做社會上的抗爭,或是抗議。
慧穎:我也想要補充一下,日日春那時候其實是有公娼運動紀錄小組的,這個也是很少被提及的,大家可能都知道綠色小組等等的團體,可是那時候在做公娼運動的脈絡下,其實他們是有組織一個小組,很有趣的是,你會發現他們有些畫面是一樣的,就是大家互相共享這些畫面,因為這個運動真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下,為了要去紀錄這個運動進行的互相合作,尤其是在他們的credit都可以看到,哪一些導演也曾經有投入其中,我覺得是這兩部片滿特別的地方。這些是我們這次也有碰觸到的一些東西,這些比較是從社會運動的脈絡去談,主要收錄在方念萱老師的一篇文章中,包含這些影片為什麼跟現在有關,她在寫這些文章的時候,也剛好是#MeToo運動正在發生的時候,所以她寫的時候其實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個經驗。最後是《逃跑的人》,會收錄在曾文珍導演的文章,她從一個人為什麼要拍片開始記錄,做了滿回顧性的梳理,我覺得是滿特別的。
以萱:我們接下來跟在場的各位,可以有一些提問或是討論,從剛剛聽到現在,看有沒有對比如我們剛剛講的內容,或者是這個出版品本身有什麼樣的好奇,或者是今年女影的節目也可以。
Q:我的問題可大可小,我想要問說因為像是女性影展,它出現在一個很特定的時間點,就是90年代初,其實你們談了很多要怎麼把它放回社會文化運動的脈絡當中,去思考在90年代的時候台灣社會有這樣的變遷,影像當然是這樣子的變遷的一部分,我其實有一個比較好奇的部分,是我們怎麼樣又把這個女性影展的傳統,或是這些女導演她們的某種能動性,再扣回台灣電影史,它可以怎麼樣去回應某一些台灣電影史的缺漏?我們一直都會罵說台灣新電影有女人又沒有女人,雖然說有女人,很多女性作為主角的片子,但你會覺得女性好像又沒有什麼主體性,有那個衝突跟矛盾在,所以我想說那你們可不可以談一下,因為你說這本書是提出問題,但似乎提出問題的前面也有一個暫時的答案,所以我想要請你們聊聊,這個暫時的答案對你們來說是什麼。對不起好像問了一個大的問題。
以萱:我覺得好像沒有辦法將它指向一個方向,但以我們現在年表的內容來說好了,因為年表在書寫女性影人不是只有導演,它其實有製片、攝影、編劇等等各種不同職位,你會發現在台灣電影史是有這些女性參與在其中的,我覺得就會變成他們好像某種程度上,進行以前台灣電影史書寫上補位的工作,那些東西本來是漏失的,我們在討論台灣電影史的時候,我們討論的可能是演員或者是導演,是某一些比較特定的電影,我覺得目前比較像是這樣,從各種不同的面向一起去補位,但是你說怎麼樣回扣,只能說可能現在我們提供多一些基礎材料,期待未來會有更多的研究者也好,或是評論者,可以來使用這些材料。
孟瑾:這幾天在翻年表的時候,我心裡覺得它真的應該要比較像,陳韋臻在文章裡寫到關於,她在尋那些線頭,因為我覺得寫這份年表,當時有個滿困惑我的地方是,如果我們要用作品來討論,可是我們看不到作品,那到底要怎麼樣去討論這些影像?實際上,所以我覺得自己多少覺得像是,我把他們都寫下來,希望可以看到片,或是後續挖掘的人可以從中得到一些什麼,像一個線頭一樣去挖掘後面的想法,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慧穎:我覺得那個缺漏是很明顯一直在那邊的,我們會不斷地碰到,也許它真的是實質上的缺漏,很現實的一點是可能在某些時候就是沒有女性導演,也可能很少或者是很邊緣。或是我們書寫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我們轉換視角,從某一部片的製片等等不同角色,重新再講一些作品,可是那個缺漏是非常明顯的,就像孟瑾講的,我們在列條目的很多時候,很明顯的一個問題的確是很多片我們都看不到。我們最後有整理一個影片索引,光是看那個影片索引也非常有趣,你會發現也有很多男導演的片子,我覺得這個會牽扯到你怎麼樣去思考女性影像史,它可能因為裡面的某一個角色,或是幕後工作人員的突出,而被寫進去,但它可能不一定是女導演的作品,或者不見得是因為它的影像非常具有性別意識,我覺得是一個滿複雜的狀態。也很現實的是我們的時間很有限,所以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先拋出問題,先把它列出來,也許這樣的方式是錯的,或者不是那麼好的方式,可是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到,能嘗試看看的一個路徑,希望這樣有回答到。
Q:你們剛剛說有很多媒材看不到,那在這次挑選的過程中,因為有很多是獨立的…不一定是膠卷,不一定已經數位化,可能是DV等等的,那你們是怎麼找到可以放映的素材去做放映?
慧穎:的確有一些不同的現實考量,必須說重返新時區的這個單元,能夠成是因為有很多的幸運,像陳若菲導演的作品《強迫曝光》,是因為剛好她自己有做數位掃描,我們接洽的時候她有一個這麼好的版本,很多短片其實狀態都非常不好,有一些是導演再去舊家找出來的,很多不見得是女影本身有保存,而是剛好導演真的有相對應的一些拷貝可以提供。我們有部分的素材也是請南藝大進行數位掃描,才得以有今天的一些放映。比較坎坷的應該是《鬼的狂歡》,它其實是因為國影中心有這樣的一個掃描調光版,我們今天才能夠放映。
以萱:我覺得這就會回到影展這件事情,因為各位看到的影展節目,其實是已經經過了各種協商、妥協挑選出來的成果,這個協商、妥協不只是節目內容或策展概念的部分而已,還包括我們有沒有辦法取得素材,所以其實有非常多現實的條件,構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
慧穎:還有《2,1》也是因為我們透過PTT慢慢找人,真的找到導演後才確定有可以放映的版本,所以都是滿坎坷的。
以萱: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是可大可小,因為你大可以討論到,比如說國家影視廳中心典藏的政策,其實就會牽涉到非常多的問題,歷史性的發展等等。
慧穎: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就是目前女導演實際有被修復的只有李美彌導演的作品,像楊家雲導演也都沒有任何一部被修復,所以我覺得這個的確會牽扯到非常多現實的狀態
Q:很好奇的是整個出版品,還有今年的影展,在規劃的期間的上半年,在台灣雖然來得很遲,但是是#MeToo運動的能見度終於比較提高的一段時間,我滿好奇這個對於今年的影展也好,這次出版的規劃也好,你們覺得有受到什麼影響、啟發,或是做為一種回應。
慧穎:影響其實蠻大的,包含我們在做編輯的某一段時間剛好重疊到那個時候,在方念萱老師那一篇應該是滿能夠直接回應,她光是寫作的那個過程就非常痛苦,我覺得她也有把那種感覺放入其中。在年表上面,其實我們有因為這起事件,因為年表原本是到2022,我們原本想說今年正在發生的事太近了,但就是因為在編輯的過程中,也不斷地感覺歷史很好玩的一件事是,我們可能在碰觸到以前的歷史,就發現2023年好像又重新洗刷一遍的感覺,我們後來就把年表又稍微拉長一點,到現在也就是2023年,所以這一點其實有點像是,除了內部以外,還有跟性別運動的一些前輩,算是一個滿大的共識,我覺得今年好像非常的激烈,希望把這些重要的事件,雖然還是進行式,但還是放入其中。至於節目上,也有滿大的影響,重返新時區單元裡,這次有收錄一部陳俊志導演的《玫瑰的戰爭》,所謂的台灣第一部控訴性侵、性騷擾議題的紀錄片,我們把這部片放入其中,去回應它有一種很大程度的回溯感,除了這個單元以外,它也影響整個影展滿多的,我們有一個單元叫做「移動身景:凝視、抵抗、創作與歌唱」,那個單元完全就是一邊在感受,一邊在選片,所以它其實很實質地反映在我們選片的內容。
以萱:我覺得慧穎回答到很實質的面向,就是具體是呈現在什麼面向,那我覺得我可以補充可能是情感的面向,是比較內化在這些內容裡面,以及像剛剛提到,本來的年表只想要收在2022年,其實#MeToo這件事情,好像某種程度也給我們一些精神上的支持,知道說OK,我們現在其實是可以寫一些什麼,可能在那之前老實說也許會有點逃避,你會覺得我好像還不知道要怎麼去談它,我覺得情感面向它帶來的影響是這樣。
慧穎:年表設計成兩排,我們把它切一半,你可以互相對照,上排是電影與文化場景,下排是性別與運動場景,可以翻著對照。
慧穎:對,這個在設計的時候,確實讓設計師跟印刷廠很傷頭腦,因為可能在印刷跟製作的難度比較高,那時候我們對於年表要怎麼呈現,也有滿多討論的,因為它是一個文字量很大的東西,也希望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是比較舒服的狀態,包括說我們要怎麼樣列它,或者是橫式直式等等的,有很多討論。
Q:對不起我可以請問一個問題,我可能不是這一行的人,我完全是一個消費者,那你們剛才提到讀者,你們出版這個書,有一個很大的目的也是希望,就像書店老闆講的要推廣這個書,那你們有想過目標客群是誰這個問題嗎?
慧穎:先講一下我們設計這本書的概念,希望它越輕越好,有點像是工具書,它可能不見得那麼容易一下子消化,因為很現實的就是裡面有一個非常厚的大事記,所以我個人比較希望它可以變成一個某種程度的工具書,能夠有一點參考價值,尤其是我覺得女性影像史對很多人來講,都是一個虛無飄渺的東西,然後這本書其實有一個英文書名,just another cinema,為什麼會有just another cinema是因為它有點像just another feminist,就是那個概念是一樣的,覺得好像碰觸到性別很容易會被另眼看待或者是小眾化,所以用這樣的名稱,也是希望它能夠提供另外一種觀看方式。
以萱:我覺得工具書這一塊是我們滿重視的,比如說我們花那麼大的力氣在年表,還有後面的索引都是,因為在查找資料的過程就會發現,那些資訊是很零落的,那我們就會很希望,如果今天要以一個出版品的形式存在,那它可能就要兼具甚至有點像是字典的感覺,假設你想要找2003年,台灣關於這個題目有什麼樣的內容的時候,它就可以這樣來查找,但是也必須說因為整個開本的關係,確實對一些讀者來說可能會不太容易閱讀,因為像是字體還是滿小的,這個可能是我們未來可以想想看要怎麼去調整的,因為你剛剛問到目標的讀者群,我覺得這個確實對不太習慣看這麼小字的讀者來說,可能就會相對沒有那麼友善一點,所以就會有各種需要拿捏的地方。
文字記錄:楊詠琦
攝影: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