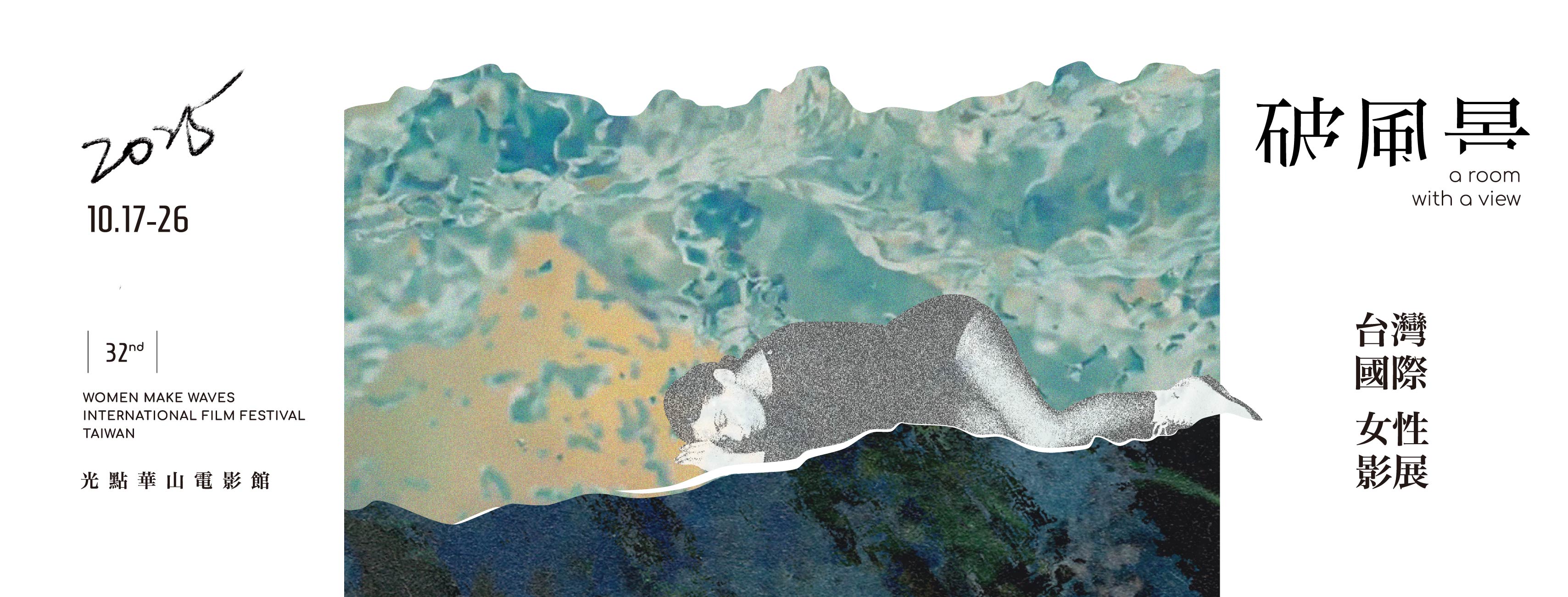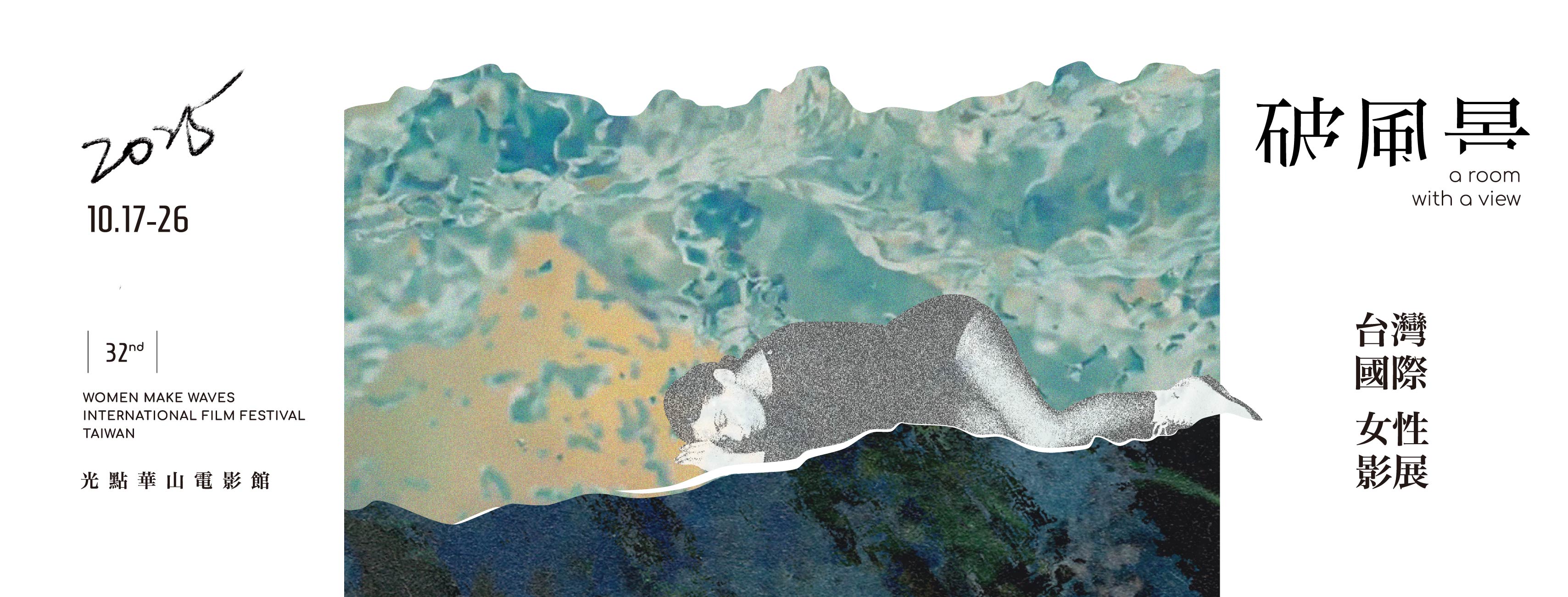漩渦響起—貝蒂・戈登講堂
時間:10/16 (六) 13:00-14:00
地點:光點華山二樓(線上同步進行)
主持人:
陳慧穎|策展人
與談人:
貝蒂・戈登(Bette Gordon)|《情色戲院》、《人盡可夫》、《I-94》導演
現場口譯:林若瑄
文字整理&編輯:玟伶、慧穎
陳:首先來介紹一下貝蒂・戈登(Bette Gordon),她是紐約1980年代獨立電影、地下文化圈中重要的一位導演,也經常和龐克、無浪潮(No Wave)連結在一起。當時紐約的音樂、電影、戲劇圈之間其實沒有那麼明確的分野,大家jam在一起,處於創作力非常旺盛的狀態。很多人會認識貝蒂・戈登主要是因為《情色戲院》(Variety),但她早期的創作主要是以實驗片為主,這部分可能較少人關注。這次女性影展在【漩渦迷情】單元收錄了她最知名的《情色戲院》,搭配早期實驗短片《人盡可夫》(Anybody’s Woman)與《I-94》(I-94),今天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貝蒂・戈登與女性影展線上連線來進行今天的大師講堂。
《I94》劇照
我們就先從《I-94》開始,這是貝蒂・戈登與另一位知名實驗片導演詹姆斯・班寧(James Benning)合作的作品,這部片呈現裸體男女分別走向、走離鏡頭,交疊呈現出銀幕上「從未同時同框」的銀幕性愛,想先請貝蒂跟我們分享一下當初的創作契機。
貝蒂・戈登:我在1974年拍《I-94》時,當時還是美國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大學的學生,當時詹姆斯・班寧也是學生。我們相遇時,實驗電影主要被一種詩化視覺的傾向所主導,比方說像Stan Brakhage的作品,但同時我們更想積極探問「電影是什麼」、「影像是什麼」,就如同1970年代當時許多畫家會特別關注媒材的運用,會思考顏料和畫布之間的關係,顏料的厚度等等,比較偏向極簡、甚至是概念藝術的手法。
那時候跟詹姆斯・班寧想要探索的,電影何以是個特別的媒材,電影是時間跟空間的藝術,一秒24格,當我們看見一秒過去,其實已經跑了24格。一格在畫面上停留的時間這麼短,但電影之所以如此迷人就是因為它能改變時間與空間之間的關係,例如我們可以透過用光學印片的手法改變這層關係。當時學校有一台光學印片機(optical printer),光學印片機基本上一端是放映機,另外一端是攝影機,當我們把拍好的素材放進放映機端,在攝影機那端放進新的膠卷,你就很像透過攝影機在拍放映機端呈現的影像,透過攝影機的鏡頭看那小小的膠卷。
基本上就是在重製拍攝的素材。我們先拍了兩捲,一捲是我拍詹姆斯從遠端走向鏡頭,另一捲是詹姆斯拍我走離鏡頭,我們就拿這兩捲膠卷去光學印片機,我們重新拍攝了這兩捲各60次,也就是說每一格都拍了60次,然後又拍了60次黑畫面。方法是,我們先把其中一捲放進打印機拍攝,第一格有拍攝的畫面,我們再用手遮著攝影機讓第二格畫面是黑的,同理第三格就是有畫面,第四格是黑的⋯⋯,另一捲剛好相反,第一個先用手遮住變成黑畫面,第二格有畫面⋯⋯。兩捲底片交會起來,那速度是非常快的,很像是子彈一樣,速度造成了影像交錯交疊的效果,因此最終《I-94》呈現了兩人的身體在銀幕中交疊,兩人各自的走路在中間的點交會的狀態,但事實上從未同時同框,只是透過光學印片達到重印、重新調整畫面的效果。過程中,我們花了非常長的時間在暗房,因為我們真的是每個畫面都拍了60次,我認為這個過程很美,有個韻律在其中。我認為膠卷媒材的可觸可碰,它的物質性、實體性是非常具有誘惑力的。這樣的誘惑力是延伸到影像本身,讓時間延長、空間感置換,讓走路也可以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當然,裸體已經暗示這跟性有關,但是類比影像的呈現方式、機器、快門的運作、媒材等等都是非常性感的,數位影像相較就背離我所說的性感,它與以往我們看見底片上的顆粒以及底片在播映時的跳動等心跳感與呼吸感是非常不同的,對我來說數位影像是純粹資訊的閱讀。
陳:如同剛剛貝蒂所強調的,她是如何利用非常手工的方式,來呈現持續不斷交疊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時間不斷被延長,延長的閃爍狀態。
想接續詢問,您在這部片不只呈現了身體交疊,聲音的處理也很有趣。一開始貝蒂的聲音是很清楚的,但越來越小聲,內容提到了自己似乎不夠受到重視,而詹姆斯則訴說著自己好像卡住了,以及一些關於自己的問題,他的聲音則由小漸大,到最後幾乎只剩詹姆斯的聲音。當初為何會如此設計?
貝蒂・戈登:當時拍這部片時,我們錄製旁白的方式是我們各自進到一個小房間,彼此都不知道對方要說什麼,旁白就是我的聲音跟詹姆斯的聲音。唯一只有說要講一下非常個人的事情,因此我進到小房間時就開始說一些個人的掙扎跟困擾。當時我21歲,困擾著為何周遭好像都不能認真看待我?不把我當一回事,是因為我的長相、穿著、還是年紀?當時整個社會體制當然是非常父權的,在這樣的體制結構下我好像不太能擁有一席之地。這點是非常有趣的,因為的確在1970年代早期,女性還在找自己定位的方式,當時有一些英國的女性主義者,著手重新發掘早期好萊塢女導演的作品,其中很重要的一位是朵洛西・阿茲納(Dorothy Arzner),她曾執導過那麼多部片,但為何當時在教科書上從來沒有看到這些女性導演?
個人掙扎也是政治的,我不是說詹姆斯沒有他的掙扎,而是我認為他們的掙扎比較是在一個結構中的掙扎,他們已經進入到這個世界,再去想他們要怎麼辦,但當時身為女性的我根本就還沒能踏入這個世界。這部片也記錄下我們兩人的關係,當時我們是伴侶,經常共同創作,我和他的關係持續了七年,詹姆斯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人,至今仍舊是如此,分開後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夠離開這段感情的影響,真正走出自己的道路。但當我逐漸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時,我們的關係也就結束了。我認為當時的女性,甚至至今依然如此,很多時候都得跨越某些阻礙或屏障才得以獲得認可,當年拍這部片時,其實只是單純在片中娓娓道來我當時的困擾,現在回看才會意識到那些話非常切合那個時代。
你可能會問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有何不同?
的確是有些不同了,但其實這個時代還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像我就希望有更多女性能出現在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崗位,特別想看見更多女性導演。與其爭取銀幕上的能見度,我更在乎女性是否能握有更大的職權,特別是導演的角色。因為只有當你是導演時,你的聲音才會被重視,才擁有一些能改變現實條件的權力。我對台灣電影的認識,還是停留在有許多知名導演都是男性的印象,我還不太認識台灣的女導演,因此希望在座的一些人也可以考慮當導演,藉此做出改變。
陳:剛剛貝蒂・戈登提到Dorothy Arzner,這跟《人盡可夫》也有關聯。這部片是她後來搬到紐約後,開始跟很多藝術家合作的作品,雖然說貝蒂・戈登作品中劇情、紀錄或實驗片的界線經常是模糊的,但這部片也算是她從實驗片逐漸過渡到劇情片走向的開端,也可視為《情色戲院》的故事雛形。《人盡可夫》這部片的英文名字「Anybody’s Woman」,與朵洛西・阿茲納在1930年代的劇情長片同名,其中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當劇中角色在翻閱情色照片,其中也參雜早期好萊塢女明星的照片,同時你聽到了旁白透過口述的方式,描繪1930版的《Anybody’s Woman》劇情片段,這段有各種元素拼貼,是否能談談這一個片段,以及為何會引用朵洛西・阿茲納的作品?
《人盡可夫》劇照
貝蒂・戈登:我想先提一下,我在拍《人盡可夫》之前,拍了一部《Empty Suitcases》,那部就可以看得出來一種轉向,做了比較強調敘事的嘗試,其實我一直對於敘事感興趣,甚至我早期的實驗片也都是有敘事的,《I-94》是關於一對情侶的故事,關於「再現」,電影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再現女性,而我們要如何讓「再現」這件事有不同的轉變與呈現。我在拍攝《Empty Suitcases》的時候,我想拋出一個很直接的問題:「什麼時候暴力才是適當的?」。當時我住在曼哈頓下城,我拿攝影機從我家窗外拍紐約世貿中心,我當時只是在想「暴力作為一種政治武器」這件事,比方說以暴力作為一種政治行動、社會運動,比方說黑豹黨。當時來自愛爾蘭的朋友也剛好寄給我一份製造炸彈的說明步驟,我不知道為何要跟你們說這些(笑)。總之,我覺得紀錄和虛構之間的關係是很有趣的,當時世貿大樓還沒有被摧毀,但好像未來在某個時空上跟上了過去,過去也會在某個時間點追上未來。
我對過去的東西很感興趣,但早期我們竟然都不知道Dorothy Arzner這位導演。後來我逐漸認識這位導演,愛上她的《Dance,Girl,Dance》(1940)。片中兩位女主角,其中一位是脫衣女郎,Lucille Ball飾演,她同時也有演《I Love Lucy》,另一位女主角是芭雷舞者。芭雷舞者找不到工作,因此也到脫衣舞酒吧工作。其中有一場戲非常著名,芭雷舞者在舞廳表演的時候被男性瞧不起,說她不夠性感,她突然停下表演把桌子轉過來,接著說「你難道認為只有你在看我們嗎?讓我告訴你我們從上面是怎麼看你的!」一個大翻轉,鏡頭的呈現方式非常驚人,在1940年代就有導演做到如此顛覆性的敘事,怎麼沒有被大家認識?Dorothy Arzner的作品就在探討「看」與「被看」之間的關係。我的好友,Laura Mulvey當時寫了蠻重要的文章《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其中就定義了「男性凝視」,傳統的好萊塢敘事架構是如何將女性放置於男性凝視的對象,並緊扣觀影的視覺享受。
那時候有個朋友Karyn Kay,她是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在Dorothy Arzner過世前訪問到她的人,《人盡可夫》中那段引用Dorothy Arzner作品的片段便是由她來擔任旁白。Dorothy Arzner作品那一段非常有意思,兩位男性剛好看到有兩個兩人坐在窗戶旁邊,天氣很熱,女人們把衣服脫掉⋯⋯。這段精彩呈現了「觀看」的權力關係,於是我就想挪用她的片名,在自己的作品中繼續去探討「看」與「被看」之間的關係。當然那時候Laura Mulvey的文章也影響我許多,當時在歐洲也有舉行大型研討會,許多女性齊聚一堂討論電影中的再現,回想起來當時是非常自由、豐富的年代,有種興奮的感覺。
事實上我所有的短片都在處理「身體」,特別是女性的身體。在一個開放的結構下去思考再現,核心的問題是,敘事如何闡述慾望?是誰的慾望?誰來定義快感/歡愉?
陳:接著想來談談《情色戲院》這部片,這部片更深刻地探討了情色影像的觀看狀態,尤其這部片很常被稱為「女性主義版迷魂記」(Feminist Vertigo),這當然是影評或片商經常引用的稱呼,但某種程度上也呼應這部片是如何透過一個異性戀男性主導的情色空間進行敘事,甚至將整個場域挪為女主角的情慾地景,想先詢問貝蒂・戈登對於「女性主義版迷魂記」稱呼的看法,並談談片中的權力關係的翻轉。
《情色戲院》劇照
貝蒂・戈登:我還蠻喜歡「女性主義版的迷魂記」這個稱號,但當然「女性主義」這個詞在現在有點過於濫用了,所以現在也不會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但在那個時代女性主義基本上是很顛覆性的,我認為自己比較像是找麻煩的人,喜歡把事情顛倒過來。小時候我是看黑色電影(film noir)長大的,當中最吸引我的是,女性角色具有一種不羈且危險的情/性慾,是壞女人,突破一般傳統女性被賦予的角色。至於希區考克的電影,我很喜歡當中的一種執迷、或迷戀的狀態。所以我試圖結合這兩種概念,一個是黑色電影當中用非傳統的方式去探索性的女性角色(並且讓她成為一位偷窺者);另一個則是希區考克電影中的「迷戀」。在希區考克的《迷魂記》當中, James Stewart深深著迷上Kim Novak,Kim Novak把頭髮盤在腦後,因此我也讓本片女主角是一位金髮女郎,並把頭髮綁起來。此外,我也想要繼續探究一些問題,這也關係到Laura Mulvey文章中所討論的,觀看電影所帶來的歡愉經時常來自於以男性視角的觀看,女性作為被觀看的對象,我想要翻轉這件事情,不想成為被看的人,而是當觀看的主體。那時候我在紐約深夜都會跑出去玩、不害怕夜歸。尤其如果有些只有男性去的地方,我也想去那裡,比方說情趣用品店,那時候的時代廣場有非常多這樣的商店,我就走進去,我想要成為偷窺者,我想要成為觀看者,就像這些男性一樣。
其實我是到1980年代才剛搬來紐約,所以我對紐約的印象都停留在小時候從電影當中看到的紐約:黑白色調、危險、黑暗、犯罪,這黑暗且充滿犯罪的城市對我來說很新鮮。有天我跟朋友晚上吃去喝酒玩耍,準備要回家時,突然撞見「Variety」戲院,戲院的招牌絢麗奪目,我被吸引到目不轉睛,走進之後看到牆上的海報才發現是情色戲院,我也想進去看,結果我剛好遇到放映師,我問他是否能進去看片,於是他就邀請我去放映室。進去之後,我往下看,發現觀眾席中沒有任何女性,只有男性,但其中我也發現有男男在做愛,但銀幕上卻是異性戀的性愛,但觀眾席卻有部分是非異性戀男性,那我就覺得戲院空間是一個很微妙的狀態。我後來就因此在這個戲院拍了兩部片,一個是《人盡可夫》,另一個則是《情色戲院》。
《人盡可夫》對我來說比較像是素描,初步探索一些我想要談論的概念。我邀請伍斯特劇團的Nancy Reilly進到戲院,我也邀請另一位男性朋友Spalding Gray,他是非常知名的表演者、獨白藝術家、演員(可惜他已經離世了)。我跟戲院的經理洽借週日來拍攝,然後在戲院裡,我開始去思考如何從「色情」的角度去思考歡愉、幻想、慾望?這兩部片基本上就是在探討這個問題。我認為情色/色情片運作的機制是去營造慾望,答應我們的慾望會被滿足,但這個慾望是一個幻像,我們實際上無法真正得到它,不過運作機制會告訴我們可以,因此我們會在一個永遠不會被滿足,但卻想要被滿足的情況下繼續看下去。這機制跟任何電影或敘事運作的方式都是類似的,甚至廣告也是,情色/色情片運作的機制是充斥於整個文化當中的。
但我想做的事是奪回我的權利,我不想要當受害者。我想要當觀看的人,而不是被看的人。觀看象徵了權力的掌有,我想要進一步在電影當中探索這議題。我的女主角Christine,重點不在於是否真的握有了慾望,而是她探索的那個過程。對我來說,角色很重要的事情便是要拿回主控權,她是否能控制敘事,控制故事,如果她能夠擁有主控權,那我就能擁有主控權。我能掌控整個敘事。這當中是否有任何是具有顛覆性的?比方說片中有一個場景是,你也坐在觀眾席中看著銀幕上的畫面,但誰能掌控這敘事權?我能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