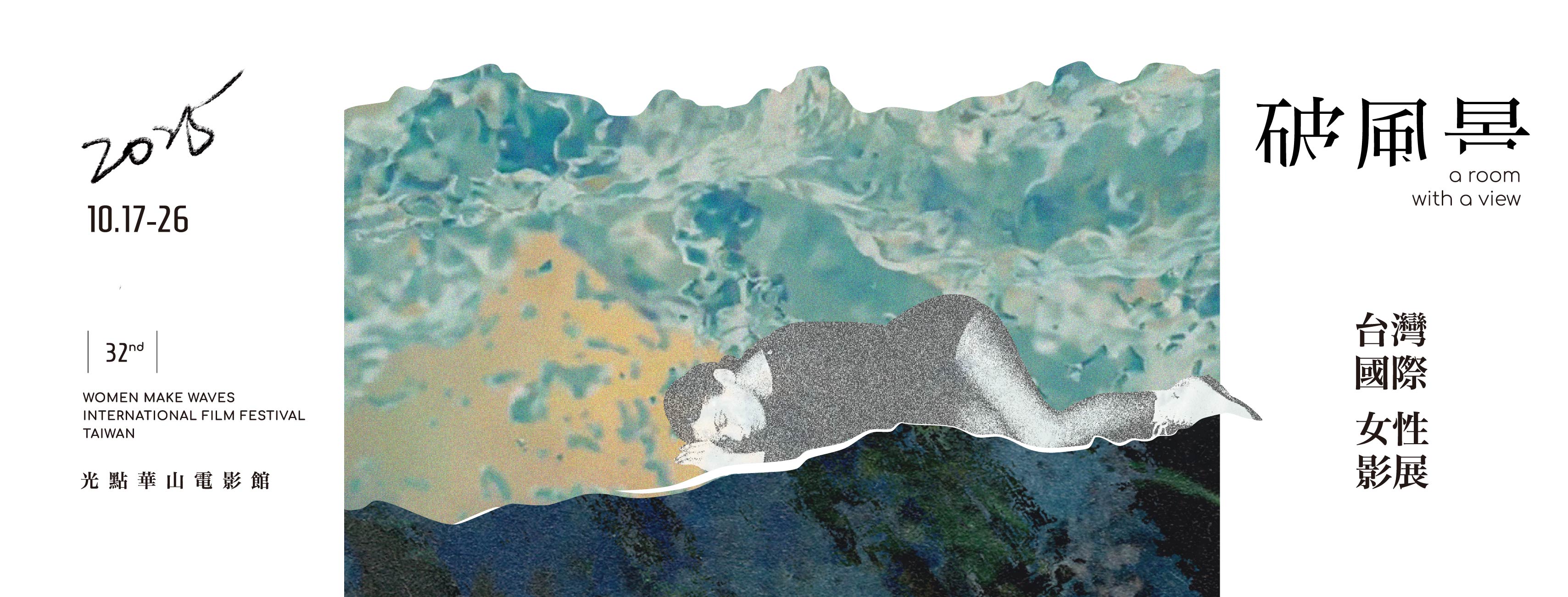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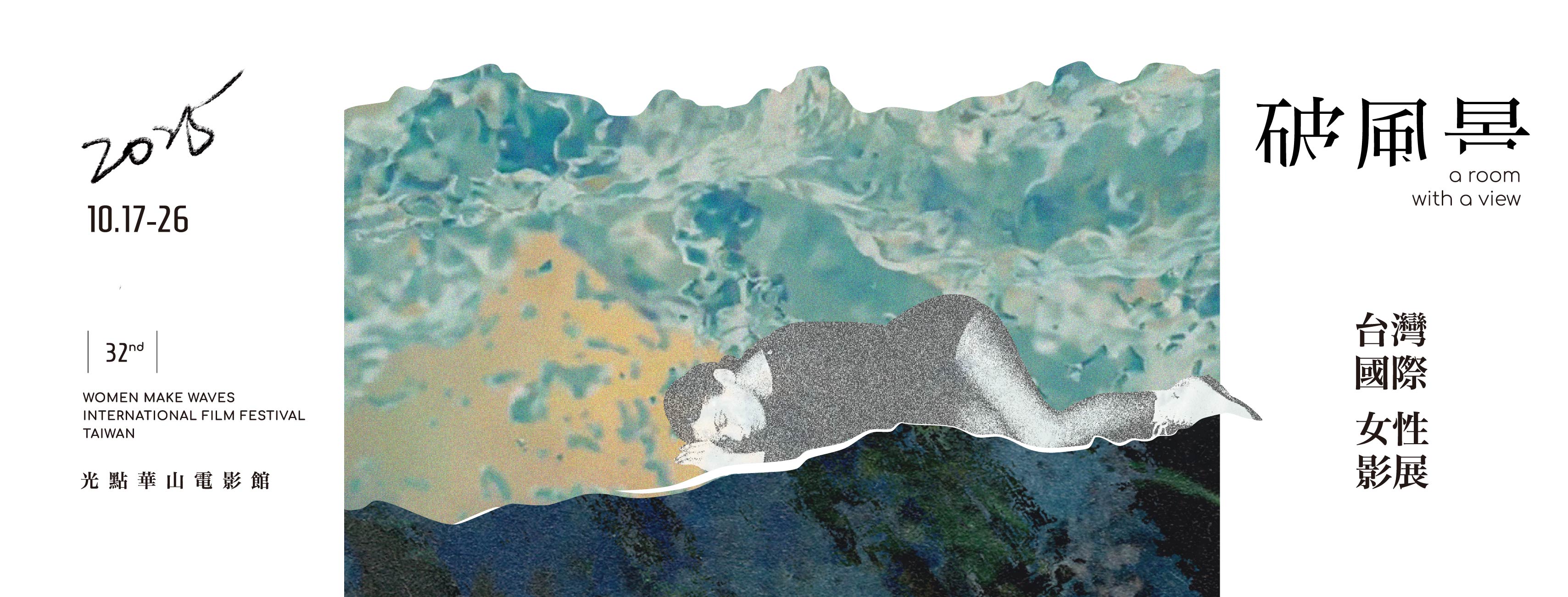
片名: 《漂流廚房》
場次:台北華山2廳 10/05(六)12:00 ★
主持人:陳俊蓉
與談人:陳慧萍 導演
開場
主持人陳俊蓉:知道導演在剪接的部分花了很多時間整理,大概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是怎麼樣變成我們現在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構跟樣子?

陳慧萍導演:它的後製過程比剪接過程長,從2012年一直拍到2015年,
當時後一直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遣返這件事,心裡有個直覺是這件事跟莎麗與柯雅是有關係的,思索著要怎麼結合。自從2015年被遣返之後我面臨到情緒的問題,回到台灣後我很激動,我的身份無處證明,因為我們跟泰國沒有邦交,台灣辦事處勸我去改名,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也不知所措,所以後來我就去走路了。
走路的時候身體上的痛苦能中和心裡的痛苦,回來後遇到2016年TIDF所辦的的身體工作坊,透過工作坊,我能了解自己的恐懼是甚麼形狀,如何被轉化,在工作坊產出的戲劇也放在這部影片中,但是戲劇是立體的呈現,不見得可以被放在影片裡,在2017年,也是在TIDF的活動,認識了一位法國剪接師,他提出意見,覺得劇中光影很像警察掃射的燈光,於是重新處理這個戲劇靈感,變成現在大家看到的。
實際投入剪接,這是第五個本,前四個版本我讓自己比較像受害者,想透過片中沙麗與柯雅去控訴,我遭遇的事情,卻讓自己格格不入,我還特別請不同人來試片,從這個過程中,也漸漸願意放下這個心態。思考要如何去和莎莉與柯雅在一起。

主持人陳俊蓉:那還有沒有觀眾要詢問導演問題?
在講講認同這件事的時候,我自己好奇是如何建立在食物或是味覺,這個身體經驗上面,透過身體經驗去擴散這個記憶,變成更大的東西,導演可以跟我們聊一聊這個部份嗎?
陳慧萍導演:
我很有口福,第一次去台灣南洋姐妹會的時候,被拉去廚房,當時有種很親密的感覺,雖然聽不懂語言,但對我來說不重要,我感受到那種真切的感覺,廚房裡的他們叫做科雅,叫做阿珍…,他們是獨立的個體。我想說菜是他們很直接表現,從菜出發,從味覺出發。最一開始影片其實不是長成這個樣子,味道可不可以被做成抽象的樣子,在東南亞的時候,我很震驚,味道的幻覺在我走在街道上的時候出現了,嘴巴裡好像出現了黑松沙士的味道、排骨飯的味道…這些再現實都不存在的,對比在台灣的柯雅與沙麗感覺更深刻了,我不知道在台灣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連我自己都覺得模糊,可是到那趟旅行的時候,一切都變得好清楚。

主持人陳俊蓉:
我喜歡片名「漂流廚房」,鄉愁的滋味,因為沒有所以特別想念,從鄉愁再扣到「我是誰」,從食物連結到認同,我可能是泰國人,同時也是台灣人…...一層層堆疊上去,很喜歡這個觀察角度。
陳慧萍導演:
我覺得關於「我是誰」,好像不是大家在台灣島內,用腦袋思考就可以釐清的事,這通常發生在國外,經歷了某件事情,才會意識到這個。
主持人陳俊蓉:
有沒有觀眾想問導演問題或是有想法想要分享的?
觀眾:
片頭有一段文字,是泰戈爾的《漂鳥集》,覺得那段文字可以看到整部片的感覺,想問導演怎麼想用這段作為開頭?
陳慧萍導演:
這個詩其實就是一個偶然、一個意外,看到的時候就覺得,『這根本就是我影片要說的事』,於是就被我拿來用了。雖然片中莎麗、科雅、我,看起來是不同國籍的人,來自不同的地方,有各自的生命記憶,但就如詩裡面說的:『夢醒後我們是一起的』,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部份。我本來就是想排除這些標籤,去議題的,比較是從人出發。
主持人陳俊蓉:
有沒有人還想分享呢?
那我自己純粹好奇,導演在拍攝的時候有沒有困難的部分,我很驚訝片中竟然能捕捉到柯雅與母親的片段,感覺是無法彩排的,是如何精準重現日常對話?
陳慧萍導演:
有事先跟科雅說,想訪問他母親,關於一次在菜市場的經驗,科雅媽媽被問小孩是不是外傭所生的,當時她內心很受傷,我想請他們重現這個訪談內容。拍攝那天,家裡就我們三個,很輕鬆自然的情況下,他們母女兩個躺在床上,我坐在床邊,攝影機就在我腿上,我是一直回到台灣,才知道她媽媽說的內容是什麼。
主持人陳俊蓉:
想問導演是事前就和他們認識很久了嗎?
陳慧萍導演:
在這個之前,我有跟著她一起回去參加婚禮,我們很投緣,當時科雅說了一句很讓我感動的話: 我有可能是她妹妹。那種親密感是無法說清楚的。
主持人陳俊蓉:
這真的是拍紀錄片的魔力,永遠不知道這種連結會在哪裡出現。
好,還有沒有其他觀眾想要分享呢?
觀眾:
我很喜歡片中的一些夜市、和街道的景,街景很像台灣。我覺得核心是去國族,去種族,雖然片中談的是食物的記憶,去建立自我認同,但影像呈現的是這樣。另外,我覺得有個遺憾,似乎沙麗回不去是因為她先生的控制,我看過之前的一個版本,同樣是在餐桌的場景,沙麗似乎有個慾望想追求某個東西,但是她先生的控制好像是從一開始的買菜,就隱隱約約地感受到,這好像是現實,她先生決定了很多事。當柯雅在車上談論到有人建議到她做心理諮商,兩個角色之間,導演好像觸碰到內心最深層的部分,只是沙麗那一塊,比較沒有那麼深,好奇導演是否有處理到這一塊,或是想更深入處理這種關係?

陳慧萍導演:
沙麗跟先生其實每天都在吵架,有種權力的抗衡,關於Sam的部分力道減弱了,我自己覺得,那是Sam愛沙麗的方式,不能說沙麗是完全被壓迫的,她是家裡最小的一個孩子,他們家有十三個兄弟姊妹。我認為,沙麗對於消逝的感傷,是一直都有的,是她沒有辦法追回的,其實她想回去的老家是她爸爸媽媽的家,而不是兄弟妹的。而她在台灣已經成家了,她也意識到已經回不去了。不免,我們有時都會回頭看,雖然心裡知道回不去,但是嘴巴還是想說一下,就像她說的,那裏的人都已經不認得她了,對我來說是很衝擊的,思考著當你不被記得之後,你還不存在。對我來說,關於Sam跟沙麗的部分我只想處理到這。我相信對於嫁來台灣的或是嫁到外地的媳婦們,都會有一些這樣的感情吧。

觀眾:
看到導演與母親回去掃墓的那一段,我想是與沙麗、科雅的內在狀態是一樣的,不僅僅是新移民,或許是亞洲文化底下,被嫁出去之後,要回到原生家庭,心裏就會卡一個坎。
陳慧萍導演:
沙麗的狀況,是變得有一點無法分身兩地,只能做出一種選擇,我覺得她做出了選擇,就會有另一種遺憾的。
主持人陳俊蓉:
雖然沒有看過上個版本,但是能感受到這位朋友所說的,內心的拔河,Sam所說的,兩個人在的地方就是家,而沙麗說為什麼不能回泰國,但這似乎就是他們兩人的相處模式,從那段看的出來有種力量在拉扯,是蠻有趣的觀察。
還有沒有人想問問題?
我自己想問導演,之前看到,除了泰戈爾之外,另一個作家影響你很深,能否分享一下,她對你的影響?那段話是怎麼打到你的?
陳慧萍導演:
那段話是說:每一個人的身後都會拖帶一個世界,那個世界,是由你所愛的,你所好奇,你喜歡的事物所組成的。為什麼會打到我,因為在現場,就是完全看見他們身後的東西,就是看不見的那些,菜啊、味道,記憶啊、社會習慣,為什麼我的片名會叫Homesick tongue,片中的人物在講中文的時候都會有腔調,那就是他們。
主持人陳俊蓉:
這其實很動人,就是他們的血緣,或是血統、國家,成長出生的點點滴滴,其實是所有的生命經驗。這些組成,而成為你這個人。
陳慧萍導演:
其實很多東西是藏在生活裡,很多keyword,很多關鍵時刻,那些關鍵時刻會組成一個公共的東西。
主持人陳俊蓉:
那還有誰想要發問嗎?
觀眾:
我一開始以為導演是男生,後來有陳慧萍這個名字的出現,才知道喔,導演是一個女生,關於女生男生,好像我們都會有種性別刻版印象,不論是性別,國族,血緣認同,好像就是導演講的,是很多東西組成的。
主持人陳俊蓉:
我其實在泰國機場也被懷疑,到底是男是女,在機場,個人的身分是不重要的,他們只在意拿出的護照,它代表了你是誰,你變成一張文件、一張照片、一個證件,一個扁平的東西,關於我到底是不是陳慧萍一點都不重要,因為他們說你是誰就是誰了。

主持人陳俊蓉:
等會導演還會在場外,如果有人還有疑問也可以找他,那謝謝大家今天蒞臨,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