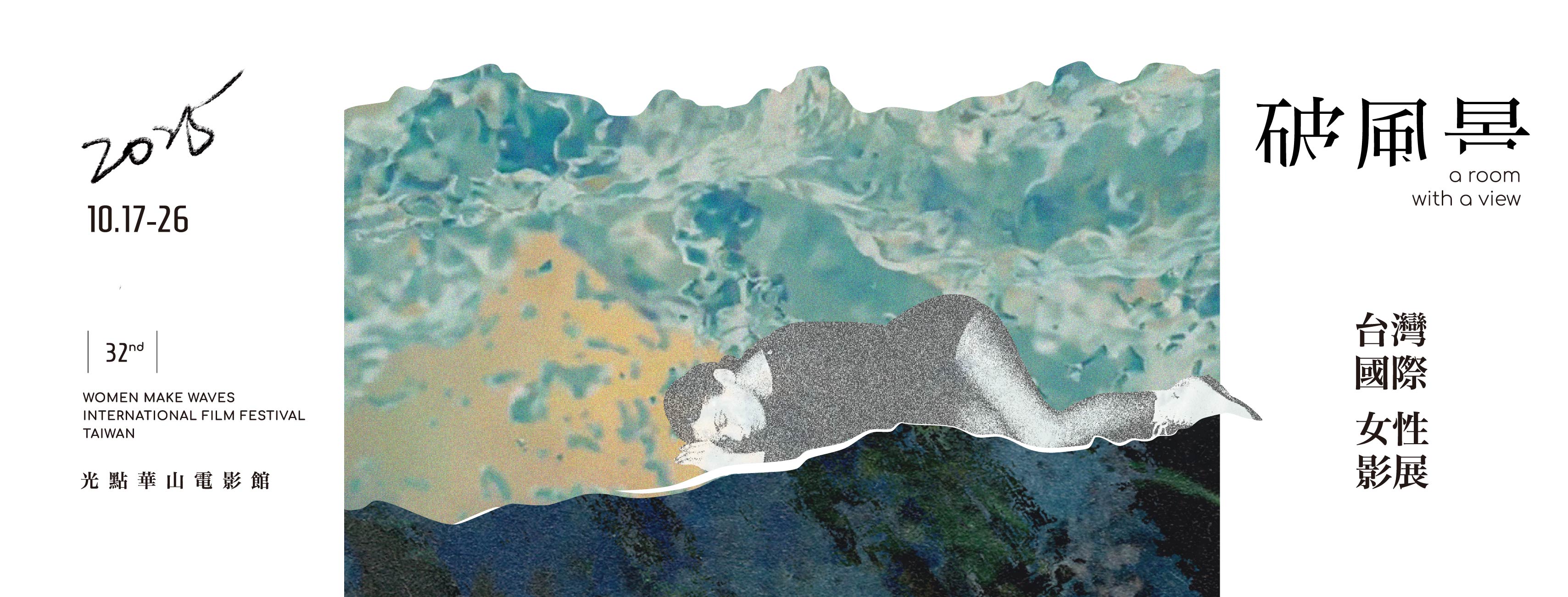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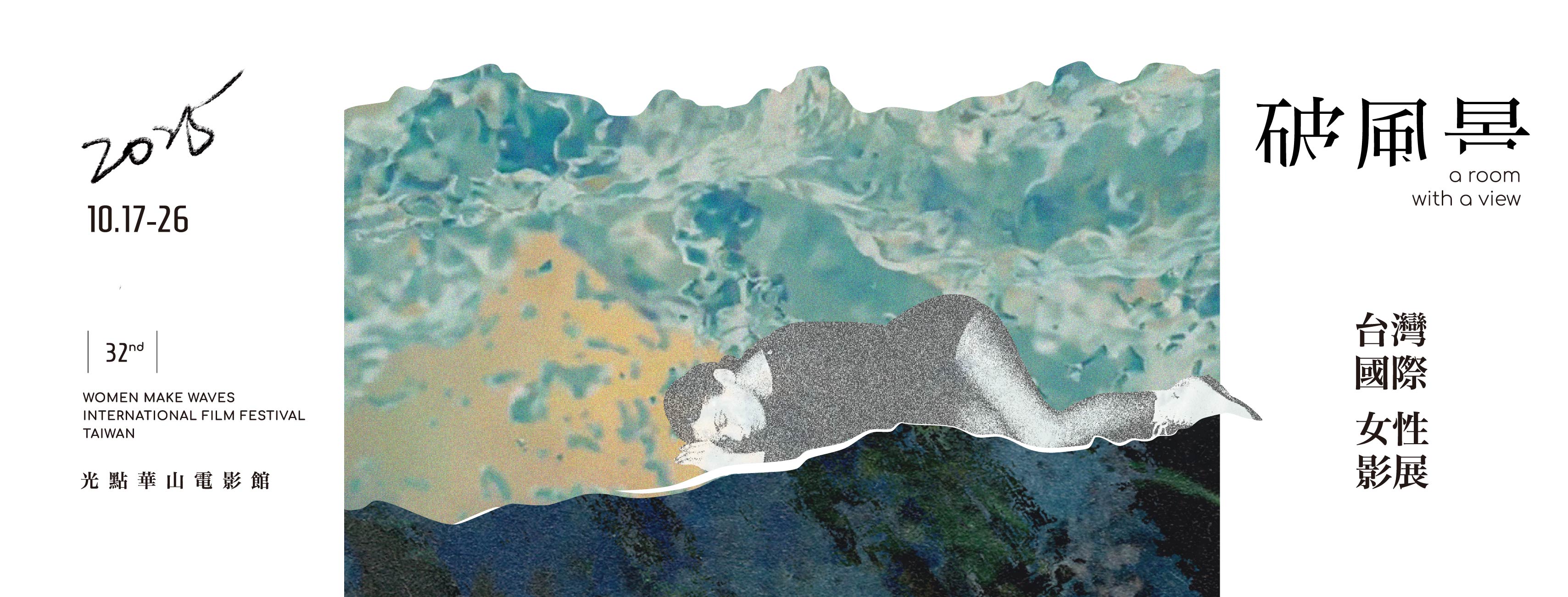
時間 09.16(日)18:30
地點 浮光書店(台北市大同區赤峰街 47 巷 16 號)
主持人 陳慧穎|女性影展選片人
與談人 鴻鴻|詩人、劇場及電影編導
蔡華臻|交通大學社會及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文字紀錄 吳心荷、賴禹安
編輯校稿 黃靖茜
平面攝影 張維珊
(開 場)
陳慧穎(以下簡稱慧穎):謝謝大家來,這場講座針對經典修復單元,總共有九部片,非常難得的機會,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鴻鴻和華臻老師對這單元作更深入的講解。
鴻鴻:我們的片單是女影分配的,我接到這片單其實蠻開心的,因為有些是年輕時看過的,像是《無法無家》,當時看過的感覺其實跟現在不太一樣,還有一些是如雷貫耳的,以前根本沒機會看到,淹沒在茫茫片海當中,像是《女酒鬼的肖像》我看到就非常的驚豔。
鴻鴻:先來介紹三部片子,我想可以先談談數位修復片中的一位導演-梅・柴特琳,《夜之遊戲》待會蔡老師會談到,非常大膽喔,其中我介紹的是《俏冤家》、《女伶們》。我先介紹一下梅・柴特琳,她是位瑞典導演,講到瑞典,大家印象中對瑞典片的印象是什麼?對,柏格曼,而且剛舉辦完影展,但如果你看對比年輕的瑞典導演,你會發現他們跟柏格曼非常不一樣,我以前看完柏格曼電影,第一個,我絕對不會想去那個地方,又冷又暗,每個人很憂鬱,還會喃喃自語之類的,但這是一個藝術家風格的意象,但另一方面由於柏格曼,另一印象就是可能非常風格化,然後視覺上會非常精緻,主題可能都是跟生命、存在、人跟神的關係,他非常擅長把私人的情感關係、家庭瑣事變成電影的主要元素。
那回頭過來看梅・柴特琳,老實說我以前沒看過她的電影,現在看就非常驚訝,因為就是六〇年代拍的,其實就是柏格曼拍出最好作品的年代。看這部電影我就透過柏格曼看到很多演員,包括攝影師就是這幾部片的攝影師,等於是我透過柏格曼的眼光看她的電影,所以可以說我們是政治正確,你可以在這裡看到,原來這位偉大的攝影師還拍過很多別人的電影,不只是柏格曼的電影,還有很多別的電影。我要講的這兩部片《俏冤家》跟《女伶們》,在劇情設計上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關於三個女人的故事,或者在一個女人群像當中,她都挑複數當主角,而非單一人物,那就意味著她更關心的是一個共相,這群女人們在六〇年代的瑞典社會,她們遭遇的是什麼。《女伶們》在創作企圖上面更大膽,《俏冤家》就是一個蠻典型的台灣新電影的時代,台灣導演有可拍出來的電影,因為它就是一個以一個產房為核心跟出發點,圍繞跟生命有關的三個女性在交錯,這三個女性之間各有各的困難和歡樂,因為每個人面對她即將懷孕這件事情,有的開心,有的煩惱,各種各樣的狀況,所以她透過生育這件事,做為一個女性,你也可以說這是女性獨有的天賦或包袱,這些事情在這些女性身上,包括她的伴侶、工作等等產生相關的效益,你也可以說它是一個跟懷孕有關的百科全書,或懷孕這件事對女性產生的影響的電影。

那《俏冤家》的拍攝方式是比較傳統,是用一種比較能夠跟大家溝通的方式來講故事,我們可以以此認識這些女人,發現她們在不同狀態裡面的對照關係,這個導演非常用心經營,到最後會慢慢產生一種情感的效益。但相對來說《女伶們》的創作意圖比較大膽,比方說手法比較前衛,她採用戲中戲的方式,講的是一個劇團的三個女演員正在參與
《利西翠妲》的演出,是一齣在文學上蠻重要的古希臘喜劇,雖然它是男性作家所寫,但完全伸張女性的力量。我們知道古希臘的喜劇悲劇有兩個是戲劇經典,一個是《美狄亞》是最早的女性復仇,一直到今天不斷被重新詮釋,那另一個就是《利西翠妲》,台灣也演過,它是一個非常大膽跟有趣的設想,因為那個時候希臘跟斯巴達長年戰爭,在這部戲裡這戰爭如何終止的呢?就是因為兩個城的女性連結起來,利用性罷工的方式阻止男人的戰爭,就是我不會跟你發生關係呦!除非你們這些男人發動的戰爭你們可以停止,這個前提跟故事想法放到今天來看都是非常大膽有趣的,因為發動戰爭的都是男性,但是受苦受難大都是女性,不過這部做為一個喜劇,本身就有很多女性群體裡面的內鬨,跟一些像有人會想烙跑去安慰她的老公之類的,那這些在《女伶們》裡面就是非常關鍵性的位置,因為這三個女演員在排演跟演出是出去巡迴,那瑞典說起來就是個小國,不像百老匯或倫敦,一齣戲可以排完就一直演,可以靠那齣戲吃飯,在這邊沒有,他們非常像台灣,就是一種小劇場的方式,你必須多演幾場,但你如果在一個城市多演幾場就沒有人要看了,因為觀眾數量就是很有限,所以她們必須去巡迴。
巡迴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女性其實都有家庭,有男朋友、有老公、有小孩,那巡迴的時候就會直接面臨生活的改變。因為去巡迴就意味著這個女性有她自己的事業,不再是作為一個男性的附庸或支助所在,所以直接挑戰了女性的家庭關係這件事情,那開始出去巡迴以後,她們的伴侶關係跟家庭關係就發生了危機,比如說有的伴侶很希望她趕快走,因為他有外遇,但有的是非常不希望她走,因為有小孩老公顧不來,會有這樣的狀況,那這三位女性遇到的狀況跟她們在戲裡的角色和台詞,都產生了奇妙的呼應關係,那這位導演採用的剪接方式。如果你們看過楊德昌的《恐怖分子》,蠻像的,就是音畫經常是分離和對立的,就是你看在她生活中的畫面,但你聽到的是她跟其他演員正在對台詞,那戲的台詞很像正在解釋或者說諷刺這段生活。那我只舉一個例子,不爆雷爆太多,就爆一個小雷,就是這場戲是男性導演,是個非常倨傲的大男人主義者,那他要做一個這麼女性的戲,所以他關心的是在藝術上的主題,他並不關心同樣的問題發生在生活中間的時候,他怎麼去面對這些演員?
我想這兩部片是可以等量齊觀的,因為《俏冤家》是關於一個女性在進入家庭,或是說一個兩人關係要開始變成更穩固的家庭關係,就是要有小孩的時候產生的變化,可以說是比較寫實,但也比較多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每天會遇到的狀況,這部片裡算是蠻多面向和整體的呈現。《女伶們》就是比較跳脫跟理性分析的眼光,包括它的藝術企圖,它用了一個戲中戲的方式對照現實和理想,另外它的敘事手法是比較跳躍和前衛的。
鴻鴻:另外我要講兩部片,先講《我的二十世紀》,匈牙利電影,它本身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寓言。我記得台灣小說家蔡秀女也寫過《我的二十世紀》,其實很多人都會寫過我的二十世紀呀,那這部片就是講一對雙胞胎女嬰長大後不同的遭遇。我又想到義大利導演的《1900》一個是地主一個是農奴的小孩,兩個人一輩子從小打架麻吉麻吉的到長大之後完全隸屬於不同立場的階級,那這位匈牙利導演用
兩個女性來講她的二十世紀,用黑白片來表現,其實不是因為1989年那種大家都用黑白片,她是故意用黑白片拍攝,而且一開始拍的像默片,就是因為她想要把二十世紀初才誕生跟萌芽的影像。
從《我的二十世紀》開始講起,用早期電影的手法去拍黑白片的模式,一開始就引用了安徒生的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這對雙胞胎從小家境貧苦,所以兩個女孩就在街頭賣火柴,火柴賣一賣就在街頭睡著了,結果就出現兩個男人出來丟錢幣,決定你抱走這個我抱走那個,接下來就是講長大之後兩個女人如何相遇和愛上同一個男人,這個男人還根本搞不清楚遇到雙胞胎,還以為是同一個人。整個故事設計蠻妙的,還放進很多二十世紀的發明,變成一些重要的象徵,比方一開始愛迪生發明燈泡,所以電影開始沒多久,我們就看到燈泡博覽會在森林裡把所有的樹都放上燈泡,當突然一起點亮的時候,大家就「哇!」好像電影剛發明時的火車進站一樣,那種驚奇和眩惑的狀態,愛迪生也變成劇中非常重要的象徵,有了人造光明的光明之後,這個世界會如何改變。這兩個女性其實就是大家對於女性很刻板的印象,一個是妓女一個是母親,所以可以看到一個妓女非常會挑逗各種各樣的男人,她可以同時跟這個男人勾搭中,同時眼神上試圖跟另一個男人放電,可以說在情感上非常自主的女人,也非常的艷麗,非常風騷,也了解自己的魅力何在;另外一個就是很靦腆,很害羞,很純潔,但她卻是一個革命份子,會去放炸彈的無政府主義者。

導演用女性來講述兩種可能,就是善用她的天賦,「性」這件事情,在男人世界裡如何存活,另外一個就是性別完全無關緊要,跟任何男人一樣她可以去改變這個世界,所以她可以背炸彈在街頭到處走,例如她遇到一個男人,可能有點好感,但她要執行這個任務,這個任務可能有去無回,那她可能想如果我這條命還在再去找那個男人,她把愛情放再第二位。這兩個女性的代表,就像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女性在今日的位置,那讓他們遇到同一男人這件事情,應該也可以視為整個故事寓言體,代表一個男人在追求同一女性的不同面貌,或者是對一個男人來說就是個外貌協會的人,你只要長這樣,不管你是個妓女還是革命家都沒差,這點來說導演保留了一個曖昧的空間讓觀眾自己解釋。但這個劇情設定本身就蠻有趣的,然後我還要再講就是其實男主角是我最喜歡的一部片塔可夫斯基《鄉愁》的男主角,他演完《鄉愁》之後過了5年他演了這部電影,看起來稍微有一點發福,因為我非常喜歡《鄉愁》,以粉絲心情,所以如果你喜歡《鄉愁》的話可以看這部電影。
鴻鴻:接下來我要談的是《女酒鬼的肖像》,是部德國電影,是這次幾部片當中我最喜歡的一部。導演本身就是個怪胎,這部片超級怪的,很像看到法斯賓達的女性版,因為法斯賓達合作的主要演員都在裡面,法斯賓達的配樂Raben不但有主演電影其中一個角色,同時,他也負責這部片的配樂。她拍的這部影片是完全無目的酗酒的女人,為了取得她的自由就跑到柏林去過浪蕩生活,她在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看到酒就喝,喝到掛掉就被人趕出去,有點像喜劇版本的《無法無家》。她在酒鬼的浪遊日記裡遭遇了無數匪夷所思的事情,有趣的是,這導演在跟觀眾玩一些視覺和符號的遊戲,比如說在機
場遇到一位侏儒老男人,這個男人後來不斷的出現,在他出現的場景中,我就會想「喔!原來大衛·林區是看了這部才有了《雙峰》」裡面的情境很多非常詭異,很像大衛·林區。
那裡面也有三個女人跟她對比,因為這個女人顯然是個瘋子,但有三個穿著很規矩、非常正式、保守的無聊女人,會在這位酒鬼小姐參加一些聚會時出現,自己在旁邊講閒話,內容都跟這個女人做的事情有所呼應,代表一種正常社會保守的正常關係。這個導演很有趣,因為這部電影不是由男人講,而是讓三個無腦的女人來講,在這點你就要看到完全是用概念在經營影片。這個女人還做了很多事,其中很多部分你會不知道是她幻想的還是真的,譬如她可以隨時變身,突然變女秘書一面上班一面酗酒,老闆就受不了,結果她就在很開心地把那些文件在那邊一直撒一直撒,然後就被fire掉,但她根本就不該被錄取嘛。
女人還變成走鋼索的雜技藝人,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跑去;另外還有一個女人不斷在她出現的地方洗玻璃,所以導演的意思是在說她不斷喝酒就越清醒的意思嗎?之類的,很多弔詭的概念,這部由於劇情架構和構圖都非常瘋狂,所以從頭看到尾,第一個你會覺得毫無邏輯可言,是所謂的公路電影。但這種公路電影通常每個環節都有象徵意義,比方說《野草莓》都前呼後應,但這部片這條公路走到最後,其實很多環節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組合,雖然沒有一個起承轉合,但反而讓我們看到一種結構上面的自由!喝酒讓她自由,對導演來說也是拍電影的自由,她把人生很多可能不可能的身分轉換,以及在任何現實空間裡你可以胡作非為,以酒為名你可以做這些事,其實也是在展現一個人,不管男性女性,你在真正的自由狀態底下你可以是什麼,我覺得自由最重要的是一種可能性。就像我們講的,不行動就無以言自由,不行動就等於不存在,在這裡可以看到所有行動的可能,雖然片名叫《女酒鬼的肖像》,但並不是在歌頌喝酒這件事,而是讓自由可以正當化,也讓電影裡這些瘋狂被接受。
這部片有兩位重要演員,一個是高達電影裡的男主角,另一位在唱歌的是尼娜・哈根。劇情是在說,女酒鬼遇到的一個在酒吧的歌手,是八〇年代德國非常轟動的龐克歌手,她的資歷顯赫,因為媽媽也是非常厲害的東德歌手,她就是以歌劇式的演唱,在電影裡的這段等於是清唱,你去聽她的歌通常是轟炸式的配樂,裡頭有她的表演非常誇張好笑。女酒鬼還在街頭撿了一位流浪婦人,把她打扮漂漂亮亮的一起出入很多場合,你會發現這個歌手跟流浪婦人原來是舊識,好啦我只是要說尼娜·哈根有出現就開心,因為我大學時一直聽到像嗑藥,非常好聽,這是她兩張專輯剛出,正當紅的時候跑來演這部電影,後來去美國巡迴在那個年代大家都非常喜歡她,不過後來就沒有那麼賣座,就有點退出潮流,但我就非常高興原來這部還紀錄下她最光彩的年代裡的表演。
鴻鴻:最後介紹的是《無法無家》,是我們最愛的新浪潮祖母安妮・華達,她每部片都讓我覺得她比我還年輕,非常活跳有趣!這部是她得到威尼斯獎的影片,算是她得過最高的榮譽,而且這部的
女主角還演過皮雅拉的《To Our Loves》得到最佳新人女演員獎,之後演這部又立刻得到最佳女演員,我看是同年拍的。這部是講一個街友女士在街頭浪蕩的故事,以有點推理電影的形式出現。一開始就看到她的屍體,以半紀錄的形式去訪問她遇到的人,你會發現跟她相遇的這些人反應出生活很多面向跟價值觀,裡面有些人會說既然你在街頭,這麼可憐,那我就給你麵包你去工作,讓你可以賺一點錢維生,但她都愛做不做,她內心想:「我如果要賺錢我就不會來街頭了,我是離開我原本的工作才來街頭的!」
當然有很多不同人問她說為什麼要來街頭,比如有一位貴婦,跟《女酒鬼的肖像》有點像,就收容她到車子裡給她食物,最後她就到一個宴會拿了香檳還給她喝,她說我可以把你帶進去暢飲,但主角說不要,她想要留在外面,因為街頭的香檳比較香。所以在這裡可以看出原來她是有意要選擇背離規矩的社會的這種人生,當然最後她自己選擇被凍死,但你可在裡看到她的情感關係跟性關係,像是利用性去交易住一個晚上,但有時候她又有明確的選擇,你可以看到所有事幾乎她都是自主的,就這點來講,應該是華達拍這部電影的精神所在。
另外我想提供小小的觀察,後來許鞍華拍的《黃金時代》,最讓人側目的表現就是偽紀錄片的方式,劇中人會突然轉過來對鏡頭說話,但老實說《無法無天》用的更天衣無縫,也有可能許鞍華就是對華達致敬,一方面會突然在劇情中跳出來對採訪者講話,中間常常虛實莫辨。在形式上來說你如果瞭解華達,你會發現這種手法上的自由的確就是華達的特色,她完全沒有包袱或對電影敘事的邏輯牽制,對她來說她可能才是《無法無天》的創作者,在創作一種非常自由的方式講述女性生活自由的可能。

蔡華臻(以下簡稱華臻):在鴻鴻老師後面講比較不安,你竟然可以在《我的二十世紀》看出裡面的男人是塔可夫斯基,也就是《鄉愁》的導演,我最喜歡的導演之一,實在是太厲害了,其實我今天也有學到東西。
鴻鴻:我其實是臉盲,每次都是老婆點出,我大概僅能夠認出演員而已。
華臻:我其實現在是剛開學,所以我現在情形大概比較像女酒鬼!我稍微說一下我要講的五部片,第一部是梅.柴特琳的《夜之遊戲》,梅・柴特琳是柏格曼電影裡非常重要的女演員,所以我預設是這部應該很嚴肅、很沈重,但我看完發現他是一個半瘋狂的電影,看的時候心裡在想這一定是六〇年代的電影,因為裡面有很多蠻禁忌的東西,每次只要看到六〇年代的電影都會覺得「我怎麼不早點生一點」,因為所有有趣的事都發生在那個年代。
基本上這部電影是在講一個男人帶著他的未婚妻,回到他非常富有的老家,但是他顯然有些情感的障礙,這個電影就展開他的回顧,他要解決童年的發生的問題,這樣他才能繼續跟他的未婚妻走下去,裡面發生非常多奇怪的事,比方說瓦特媽媽盛裝在一個派對裡面,走下華麗的樓梯,突然我們就看到她躺在一個華麗的大床,很多人圍著她,結果她是在生小孩。裡面充滿奇怪的情節,但拍攝方式其實蠻柏格曼的,用一種比較冷的方式去拍瘋狂的故事,蠻刺激且對比也蠻大的。有些有點碰觸到亂倫的禁忌,電影還有非常多瘋狂的情節,所以這電影在參加威尼斯影展的時候是私下放映,什麼是私下放映呢?台灣曾也有經歷過這樣的事,在九〇年代之前,有個電影叫《感官世界》,裡面有非常多的真人性行為的鏡頭,當時台灣民風比較保守,那部電影就決定不公開放映,但如果你是專家、電影行業的人、學電影的學生就可以去看。這部《夜之遊戲》就是類似的情況,當時只有評審可以看,那去看這部電影之前不要吃太飽,因為他有影史上第一部真實描繪嘔吐的電影之一,不要吃太飽,去享受他的瘋狂!那對於這部電影,我就不講太多了,不然看的時候就不好玩!
華臻:第二部,我要介紹的是《女性成長史》,在我看來是比較中規中矩的紀錄片,是1971年的黑白電影,它其實是以紀錄片形式去對社會做些批評,訪問蠻多人,比方小朋友或年長者及成年的女性,訪問她們一些身為女性在當時的美國社會成長的感覺,其實電影裡面有很多東西,一直到現在的台灣,大家去看可能都還會很有感覺!比方有個女孩說很羨慕男生,她發現作為一個小女孩就要被期待只能玩女生才能玩的遊戲,但她覺得小男生反而可以自由自在。剛鴻鴻老師也有提到「自由」這個概念,基本上貫穿所有我要介紹的電影,但當然我們的社會對男生還是有限制,比方說會期待你成為異性戀。而女性則被期待結婚後要做為妻子,是要為丈夫有所付出的,這些都呈現在電影裡面的訪問中。電影是紀錄片的形式去拍攝,我個人也比較喜歡紀錄式!
華臻:第三部電影要講《硝烟中的玫瑰》,跟之前的《女性成長史》比起來風格差非常多。首先它是以劇情片的方式在做社會評論,也有年代差別,比如說在第一部片,1970年,像剛才那部《女性成長史》表現方式比較中規中矩,訪問小女孩、已婚的女人、在工作的女性,但現在這一部是八〇年代了,我以前在美國讀書,就有朋友說八〇年代很保守,是雷根主政的年代,整個政治大倒退,八〇年代對美國是比較嚴肅的!但在電影裡面可以看到的是自由的氛圍,其實是非常開放的,裡面出現的女性非常多樣化,有白人、有色人種等等,人類的性取向也非常多樣化,還有很多在街頭的女士,這個電影不再是以中產階級的白人女主角為主。它有個很有趣的部分,在這個電影開始的前十年,美國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它的預設,十年之後,這些電影裡的女人覺得在理論上,社會主義不是應該改變嗎?不是大家都解放了嗎?
但發現並沒有,完全沒變,除了階級解放,但所有女人還是受到各個歧視,在工作上還是沒有跟男人得到平等的待遇。剛提到有個女子軍團會出現,她們開始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所以這部電影是個幻想式的劇情片,穿插一些紀錄影像。
華臻:再來第四部電影《迷失之地》,這部電影是最早被認爲的非裔美國女性導演凱斯琳・科林斯,通常我們談論非裔美國電影是比較被忽略的類型。在歷史上,非裔美國人不是自願去美國的,是被歐洲人綁去的,因為這樣子,非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裡面一直被編排在下階的位置,這個情形仍維持到現在,芝加哥有百分之四十的非裔美國人。如果你是美國黑人,只要走在路上,警察可能會射死你,整個國家機器對他們是非常不友善的。那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非裔女性,你要能拍電影更難,這部電影最特別的是從一個非裔女性的角度去拍一個給非裔群眾看的電影,這是什麼意思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姐妹》(The Help),這是部明顯以白人眼光拍的種族電影,講說有個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大學生,她很有愛心,她想要寫書,內容是關於美國社會裡的幫傭非裔女人,她想要寫幫傭們的故事,這個電影出來後在美國票房蠻好的,但很多非裔美國學者、導演、社會學家都批評蠻多的,都覺得太一廂情願了。
那這部電影比較特別的是說,針對的觀眾不會是白人,他不考慮說裡面的主要主角沒有白人,它也不需要去取悅主流觀眾,講得是非常簡單的故事,一個非裔女哲學教授面對的一些難題,譬如她明明研究做的很好,但每次學生去找她談話,學生覺得受益良多後,就會講:「你丈夫真幸運。」身為一個非裔女性,你不被期待是中產階級,通常是女傭角色。第二項被期待的是說,你要是個好妻子,當你在職場上表現優秀,但卻是被稱讚「你丈夫真幸運!」其實蠻奇怪的。她的丈夫是個有點性感的畫家,這樣的描繪事實上,在美國社會是比較難的,因為美國種族歷史的關係,通常男性容易被描繪成過度動物化、與性連結,有點汙名化的想像都是跟非裔男人連在一起,通常沒有辦法這樣拍攝非裔男性,但這導演可以這樣拍,而終於女主角不是奶媽。
因為非裔女人在美國電影史上通常都是奶媽,各位去看的時候可以發現,他是一個小成本電影,大部分時間都是事後配音的,後來這個大學教授去拍電影的時候遇到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男人,有一些故事,叫Losing Ground,她的立足點慢慢流失。
華臻:最後一部是《無法無家》,這個電影我覺得最特別的是,你看到的是完全徹底自由的女人,她什麼都不在乎,她其實曾經工作過,她不想工作的理由可以呼應到《女性成長史》,女人在社會分配、期待的角色其中一個就是秘書,她就幹過祕書,但她不想過這樣的生活。但這部電影有趣的是,它又沒有把流浪放在粉紅泡泡裡,讓你看到的是一個女性流浪者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在電影都會發生。另外一個有趣的是,這邊電影很有時間感,時間感可以跟香妲・艾克曼相提並論,或是和台灣電影導演蔡明亮,有種「緩慢電影」的感覺。
香妲・艾克曼在他自己的電影裡有幾句話我蠻喜歡的,在這部電影也適用,他說:「有一種電影,比如說像好萊塢電影,是從你的人生中偷2小時或90分鐘,出了電影院後,你的時間就過了;那我的電影是,你做為觀眾跟我的電影角色一起經驗這兩小時。」所以在這電影裡面有很多跟拍鏡頭,做很多是在回溯畫面,去反映她生前遭遇的時光,去訪問她們,可以看見很多日常生活的細節,但是你完全不會覺得不好看,跟他一起經驗片段的時刻,還可以看底片時代的細節之美,包括去看那些樹、牆上的石頭、皮膚上的皺褶,這些是數位時代比較難看到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在《無法無家》你都看的到。看完之後你會對甚麼是自由會有不同想法,像在追尋自由會伴隨而來的危險,這個電影都有,我覺得是這部電影讓我最喜歡的地方。
慧穎:稍微補充一下,《迷失之地》所呈現出來的真的是不同於大家正在大銀幕上所看到的非裔形象,當時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在媒體圈上才不得廣泛上映,沒有讓這麼重要的影片繼續流傳。這次非常難得可以再放映這部片,我們這次修復單元有很多驚喜埋藏在裡面,像是《危機倒數》的女導演凱薩琳·畢格羅本人在裡面有演某個重要的角色,譬如說《假面》Persona裡面經典的男孩,也就是《夜之遊戲》的男主角,所以非常鼓勵大家進大螢幕觀賞。
Q&A
Q1:我想鴻鴻老師也說很喜歡《夜之遊戲》,想聽你分享這部片.
鴻鴻:老實說我沒看完,看前面半小時,我對於前面她講故事的方式,第一場戲是一個男生把一個女生眼睛蒙起來,帶到一個地方,眼鏡不打開時就說說我帶你進入我的童年」,我沒想到開頭這麼吸引我,既真又幻,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兩人關係是什麼。我看完這三部片覺得,導演想傳達的東西非常不一樣,我覺得《夜之遊戲》充滿了未知、魔幻感,即便他是在拍很現實的東西;《女伶們》充滿了辯證,像《恐佈分子》;《俏冤家》很像台灣以前張毅會拍的,他要談很多問題,但採取的方式是比較通俗、戲劇性且觀眾比較喜歡的方式;那我會進戲院去看完《夜之遊戲》,我覺得觀影感受是很被他包覆的。
鴻鴻:不如我再推薦幾部片,台灣競賽的某些片我之前有看過,譬如說《二十分》,是講勞工非常非常厲害的電影,拍一個做保麗龍回收的工作,為了處理機器,他睡覺都不能超過二十分,對於身心來講都是非常的煎熬,裡面就拍說他為什麼會來做這個工作、這工作目前所遇到的狀況是什麼,這部片讓我想到在紐約的藝術家做個這樣的藝術行為,他每一小時都要打一次卡,那這個《二十分》比打卡還殘忍無數倍,是部片是讓我看完後非常無法忘懷的電影。還有《大帳篷-想像力的避難所》陳芯宜導演的,我覺得很值得看,十年來的帳篷劇的經歷,是一群很瘋狂、很傻的人在做一些他們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情,很多藝術跟生活的議題被提出來,還有台灣作為一個東南亞的小國,在整個亞洲的歧視底下,屬於台灣的藝術及發聲的方式為何,他中間也有觸及到,我覺得是一部很難得的紀錄片。
Q2 :在講《迷失之地》提到非裔女性導演,那有沒有什麼經典作品可以推薦?
華臻:最著名的是茱莉·達什1991年《塵埃的女兒》,那在《迷失之地》被發現之前,這部電影在導演生前是比較被忽略的,是後來才被發現,在被發現之前,一般在在影史上都被認為《塵埃的女兒》是第一部由美國非裔女性導演所拍攝的劇情片。這部電影出現之後就往前推,當然美國的非裔美國電影史可以推到在20世紀上半葉,非裔美國人有自己放映的電影院,這方面晚近幾年有很豐富的研究。如果在20世紀上半葉,大部分非裔美國人可以看到
的電影都是在詆毀非裔美國人,那他們到底在幹什麼?這牽涉到reception的問題,與其說我們作為受眾,真的會無限地接收電影影像的訊息嗎?如果你是女性,或者是一個你覺得跟其他男性不一樣的女性,大家每天都在看一樣的主流片,不見得都會全然接受,非裔美國電影研究有很大一塊都是在做這個。
再來是說,很多早期的非裔美國人電影都是在拍喜劇,在喜劇裡面,黑人甚至會去嘲笑自己,有自嘲傳統,他們會扮演自己在美國主流文化中被詆毀的那些形象。我突然想到鴻鴻老師剛講到《女酒鬼的肖像》,提到的法斯賓達,身為電影學者也跟大家推薦一下他的影片很棒,雖然沒有在女性影展出現。所謂先鋒就是後來的人把他定位進去,很多人躲在失敗的前面,像《迷失之地》也是一樣,導演在生前或者是拍攝時,並沒有去強調自己是非裔女性的視角,但以電影史學者角度來看是這樣。
Q3:男性導演跟女性導演在拍關於的女性的內容時,在更早期可能男性導演會站在比較話語權之位置,他們看女性可能會有男性視角的問題。我想問兩位老師說,在男性和女性導演拍攝下的女性,有沒有無法跨越之處、或是電影的特質、細膩的地方?
鴻鴻:身為男性導演,我先回答一下,我看到的很多很棒的女性電影,他們是男性導演拍的,但是他們多半是Gay,像法斯賓達,但他是雙性戀。不是Gay的男性導演,譬如說我會想到費穆拍的《小城之春》,有中國人的溫柔和寬厚,所以他看的到的東西比較細膩。我覺得無法跨越的東西,像我在看這次修復的影片,如《女酒鬼的肖像》、《女伶們》,我覺得女性導演更不在乎女性的形象,可以更突破社會上的女性被認為應有的樣子,不顧形象但更能傳出真實感,這是在那些電影時,我會有比較強烈的感受。
華臻: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會有兩個層次。第一個是說,我們很難預測什麼是男性、什麼是女性,生理男性還生理女性?像鴻鴻可能是比我還細膩的女性,而我裡面可能是個老男人,這牽涉到說,我們如何去思考何謂女性與男性,女性氣質跟男性氣質又是什麼?這牽涉到社會化的問題。
那從另外一個層次來說,其實我是拍電影出身的,很久以前我還在女性影展放過電影,從創作者角度說,我覺得要想的不是如何超越,而是認清自己的限制。尤其當我們開始老,會發現每個人的視野與經驗不同,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豐富性和像度,同時,每個人也都有不一樣的限制。作為創作者,應該要思考如何把你的限制轉換成可以加的東西,變成你的特色,尤其是拍電影這件事,所有的電影要面對的限制首先都是預算,有多少預算可以拍多少電影,這講的是限制,包括說去創作的時候也是。
那為什麼我會很喜歡法斯賓達、《女酒鬼的肖像》、《無法無天》?因為完全沒有限制,可是這個限制並不是說讓你看電影時覺得導演在所有人之上,他其實是在認識自己的局限,但在那個侷限內,你會得到自由。
結尾
慧穎:這也是女性影展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像我們今年也要開放一個單元,放映這次唯一一個生理男性導演所拍的電影,林摶秋導演的系列作品,共三部,裡面主要也都是在描繪女性形象,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一下,究竟在男導演下所拍攝的女性會是怎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