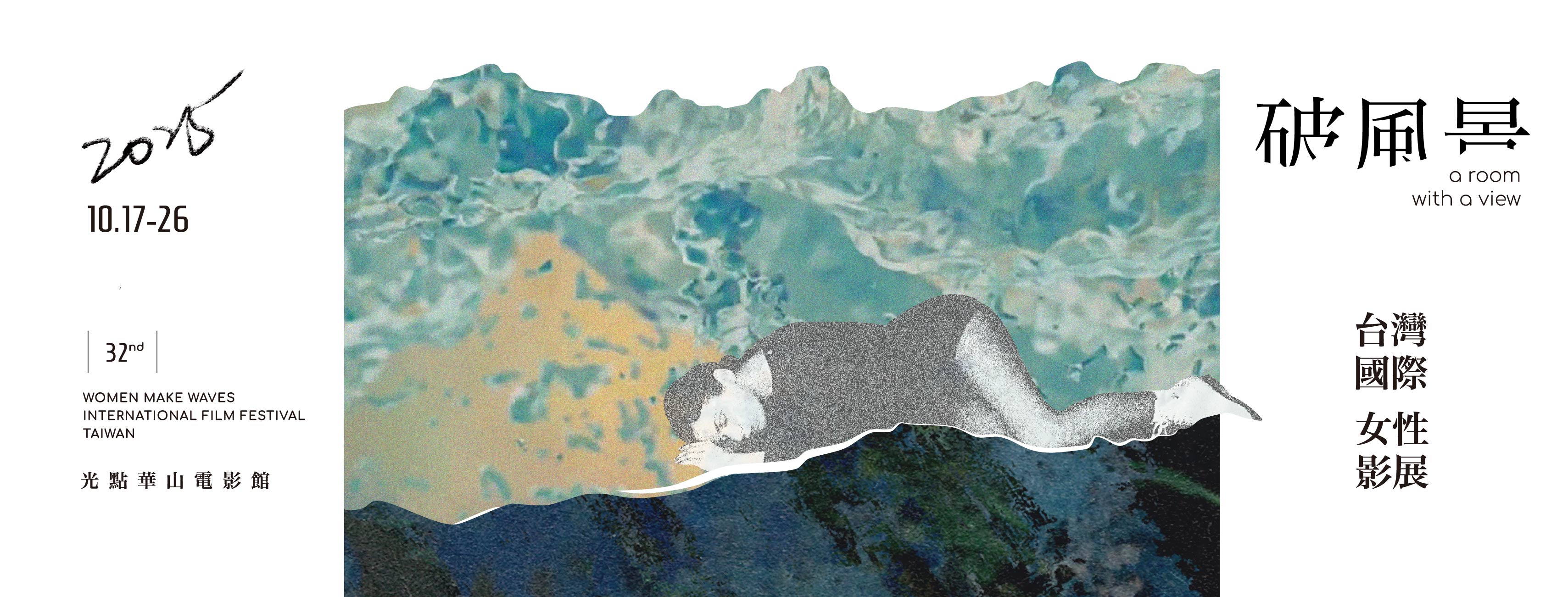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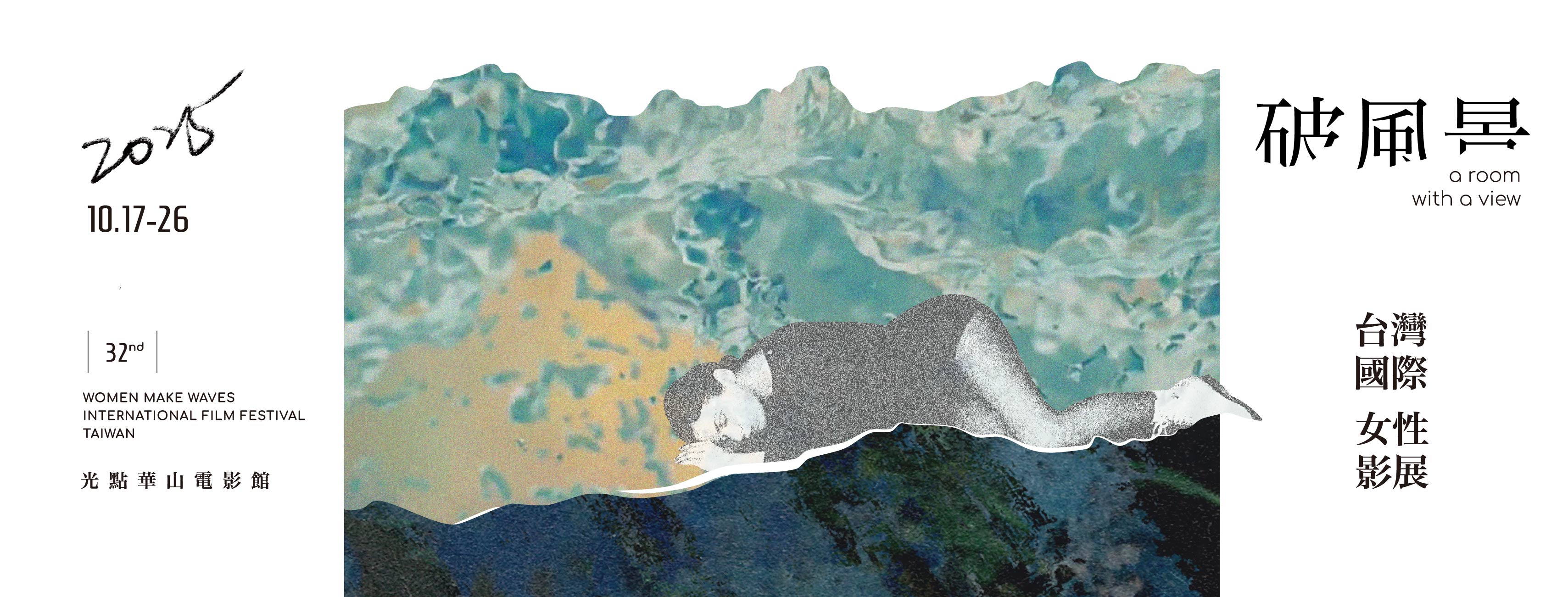
撰文/章郡榕
劇照提供/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十足的瘋狂是最最靈光的 ——艾蜜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87年,夏洛特.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在長期飽受精神崩潰與憂鬱症的折磨後,求助於專業治療,一名「有智慧的男醫生」為她開出「休息療法」三項治療建議:一、盡可能過著安逸馴順的生活,直至終老;二、每天若需動腦,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三、此生絕對不得再重拾紙筆、畫筆或鉛筆。(註1)
然而,在治療的三個月期間,吉爾曼卻發現自己離「完全精神崩潰的臨界點」愈來愈近。最終,她在「千鈞一髮之際」決定違背醫囑重新拾起紙筆,寫下女性歌德文學經典之作〈黃壁紙〉(The Yellow Wallpaper)。〈黃壁紙〉中並沒有大張旗鼓的女權宣言,而是巧妙地以一牆壁紙後的隱喻與驚悚懸疑的敘事,揭示當時女性被壓抑與孤立的現實,描述女主人公在過度理智的丈夫與森嚴的生活規範下,如何在家庭與社會壓力中逐步崩潰,最終陷入瘋狂。
吉爾曼曾自述,寫下〈黃壁紙〉的目的是「希望把大家從被逼往瘋狂的途中給拯救出來。」當我們回顧歷史,從「屋裡的天使」到「閣樓上的瘋女人」之間(註2),無不經歷著一個「被逼往瘋狂」的過程,尤其當女性試圖在創造中尋找逃脫的路徑時,社會便會與之將精神上的瘋狂劃上等號。
而這樣的拯救,作為一種自19世紀以降越發清晰自覺且具普遍意義的女性力量的展示,同樣發生於20世紀中期以來由女性導演所執導的實驗電影之中。穿過歷史的驚悚與恐怖,瑪雅.黛倫(Maya Deren)、珍.雅頓(Jane Arden)與佩姬.阿維許(Peggy Ahwesh)這三位身處不同時空的女性導演,分別在創造中為我們找到了一絲打破束縛、鑽出那牆「黃壁紙」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