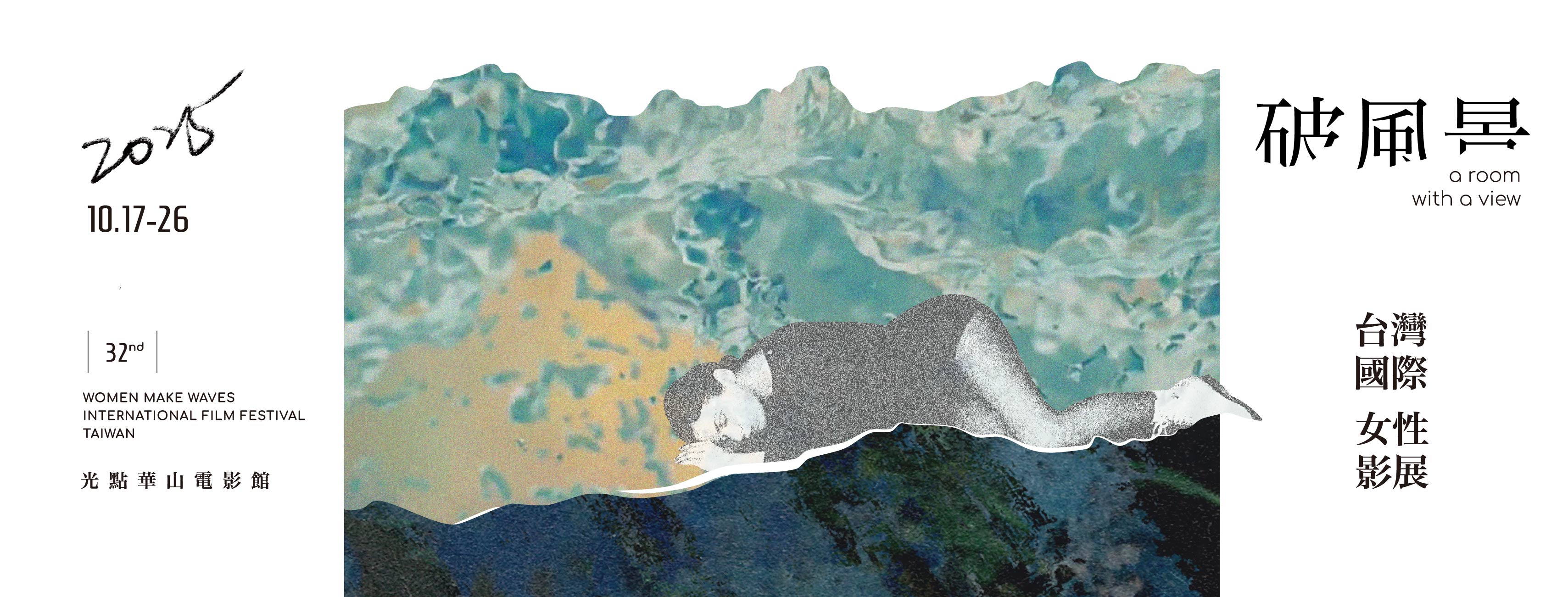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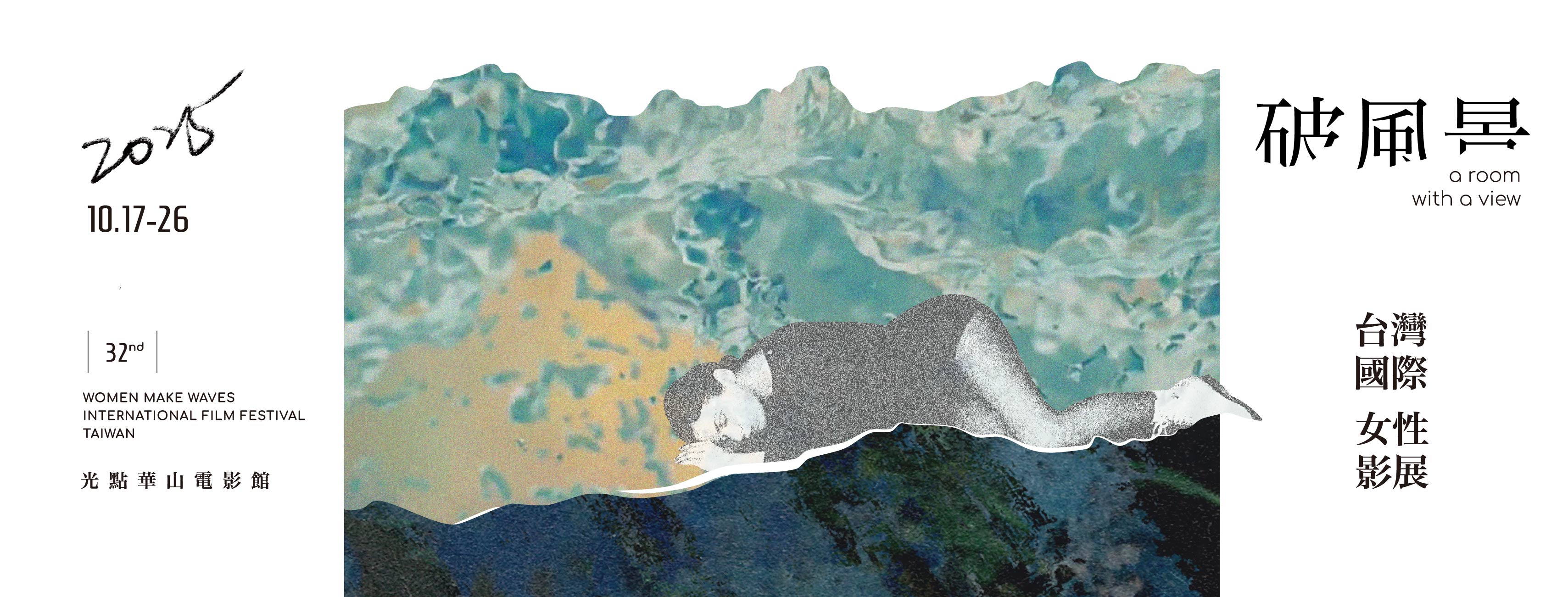
文/鍾適芳
「在邊緣聽見世界」透過3部劇情短片、6部紀錄長片,探訪音樂旅路上獨行的女性樂人──她們以各異的節奏聲響,解放身體與性別的束綁。
單元從《噤地搖滾夜》、《不存在的歌聲》和《我想聽你歌唱》3部關於伊朗女性樂人的日常展開,她們隨時隨處遭遇警戒、威脅與暴力的每日。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後,立法規定女性需於公共場合配戴頭巾(hijab) ,違者處以囚刑或罰款。法令亦嚴禁女性樂人公開獨唱、獨奏,只允准團體形式演出,且觀眾需為全體女性。
就在為此單元撰文時,伊朗社群媒體正興起一波「女權革命」,抗議伊朗政府頒定「頭巾與貞潔紀念日」(Hijab and Chastity Day)。在多個拒戴頭巾的口號下,伊朗女性不畏刑罰,上傳各自在公共場所卸下頭巾的短片。一個女孩露出一頭秀髮,放聲抗議:「繼續抓吧!把每一個為和平、自由與人性尊嚴抗爭的人都抓起來!」
以真實故事為本的《噤地搖滾夜》,講述伊朗重金屬搖滾樂團女主唱希瑪,面對雙重的道德審查──唱奏西方搖滾,以及女性擔任主唱的違禁。在宗教保守主義日益加溫的控制下,裝束與表演的限令,不斷限縮伊朗女性的自主空間。女主唱為追求發聲的自由,意圖逃離伊朗,一段她與失聰的妹妹的對話,在無聲的真空中,手語及唇語一字一字放大:「因為在這裡我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不只將伊朗女性樂人排除在歷史的聲軌外,西方樂史也實錄了一部女性被靜默的歷史。樂史透露了技藝的單脈相承,女性作曲家鮮被記載的系譜。西方自19世紀以來,歷經數次女權運動的波潮,婦女權利逐步獲得立法保障,然而,一旦涉及職業與家庭分工,女性屬於家庭、天賦母性的神話,瞬間又將她們推回至傳統角色。
美國作曲家、實驗及電子音樂先驅寶琳.奧利維洛(Pauline OLIVEROS),曾在1970年代的紐約時報著文疾呼:〈還有,別叫她們「淑女」作曲家〉。文章開宗明義提問: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性作曲家?才華與創造力,系統性的培育,在那時代,仍被視為與從屬「家務」的女性無關。被歷史埋葬數十年的英國電子音樂先鋒迪莉亞・德比夏(Delia DERBYSHIRE),也曾定位自己為「獨立思考者」(independent thinker),以逃離性別對其創造力的框限。然而,一戰背景下成長的德比夏,在科技與聲音藝術的演進道路上,得推翻多少社會頒訂、歷史篩定的女性形象,才能到達獨立的自我。
《調頻姐姐們》與《德比夏的異響世界》兩部影片,填補了歐洲一戰後音樂科技史遺漏的名字,以女性創作者共振出的時代前沿、所探險的聲響景觀,開啟歷史扉頁,寫就一部嶄新的電子音樂史。透過兩部呈現大量稀珍歷史檔案的影片,我們得以重訪這些「玩電女生」的叛逆人生。她們體內躁動著無法被阻壓的發明欲念,在電路、磁帶、噪訊之間,探險無人之境。在「噪音美學」還未被正名,女權運動方興未艾的時代,女性與「電」的關係,還只被安置在她們與家電間,這群女性實驗先鋒,以電力解放自己,追尋無以名狀的聲響與美感。
這群透過非定律的音樂編排、抽象思想的表述、音訊的斷裂、重組與擴張,追尋自由的女性音樂人,獨自對抗家庭與社會分工、職技訓練的偏見。世代承襲的「母性神話」,又足以消沈意志、黯淡才華,女性樂人得窮盡一生力氣,讓身體裡的另一個聲音,持續擴增放大(amplified)。
母性的神話,對於民謠唱作人凱倫.道頓(Karen DALTON)來說是困擾一生的課題。巴布・狄倫(Bob DYLAN)在他2004年的回憶錄〈Chronicles〉中,坦言最愛的歌者是凱倫.道頓。然而在美國民謠樂史的光譜上,道頓那發自喉嚨深底,捲動老樹年輪的吟唱,卻未見亮澤。紀錄片《以她之名:凱倫.道頓》首次揭露她騷動、不安定的一生,憑藉道頓僅有的兩張錄音、稀罕的影音紀錄及手稿,重訪其民謠思路,拼寫並論證她並非1960美國民謠時代的過客,而是啟動同時代民謠樂人靈感的引航者。
民謠是凱倫.道頓與大自然共享的生態,她希冀終日與吉他和弦、斑鳩琴彈撥、詩謠即興為伍。環繞她的男性民謠樂人,自她身上汲取才賦精髓,名字在音樂工業的排行上擦亮,留她在母性的罪惡感中掙扎,在成名與抗拒成名中流浪。凱倫.道頓那唱作以活著、一個毫不華麗極為謙遜的夢想,身為女性,終究難以抵達。
母親的扮演與龐克的實踐,傳統社會分工與反社會的兩極角色,該如何共置於同一人身上?《我的龐克老媽》講述1980年代英國龐克音樂圖騰人物──波利・斯蒂林(Poly STYRENE)自15歲逃家到54歲罹癌病逝,浪跡英國龐克音樂文化的一生。影片透過波利・斯蒂林女兒賽萊斯特・貝爾(Celeste BELL)的視角,敘述其家庭關係中的「母親」,相映他人眼中英國龐克之母的形象。女兒透過閱讀母親遺下的文字、圖像、設計、音樂創作,重訪其成長與唱作的生命旅徑。我們也得以隨之重返1980年代英國次文化場景,見證那口袋裡只有3英鎊的逃家少女,如何叛逃女性被約定俗成的生命軌路。
「自由在我身體裡,就是我不用顧忌別人怎麼看待我……」,美國搖滾樂史上的圖騰偶像 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到了晚年仍堅挺其追求自由的意志。音樂做為叛離性別的武器,抗爭為獲得表述思想的權利,帕蒂・史密斯首先得掙脫搖滾樂生態中男性壟斷聲量的約制。她以中性衣裝「模糊性別」,音樂上讓自己「無法被定類」,讓自己看起來「壞」,以換取做自己的自由。紀錄片《龐克之詩:帕蒂・史密斯》記敘了從青春到灰髮,永遠獨樹一幟的帕蒂・史密斯。
一度隱退,49歲重回舞台時,帕蒂・史密斯宣告自己仍有「怒」(rage)。憤怒不分年歲與地域,憤怒也是點燃黎巴嫩第一個全女性金屬搖滾樂團「Slaves to Sirens」爆裂聲響的因子。金屬樂被禁錮地下,樂隊5位女性成員以絕不甜膩、加速度旋升的電吉他音量,伴奏黎巴嫩女性沒有出口的日常。只有音樂能帶她們逃離,樂團靈魂人物雪莉如是說:「所有的痛、所有的憤怒,那些我們試圖逃離的……」。做為黎巴嫩政治動盪、人民抗爭、2020年8月爆炸事件的前景,《愛,死金與海妖》紀錄了「Slaves to Sirens」樂團的分合,隱沒暗處的女同志情愫。金屬噪音與嘶吼,為爆塵霧霾與政治黑幕下的貝魯特市民,譜寫悲憤的樂章。
《愛,死金與海妖》是關於歌唱與愛的權利。片尾,吉他手雪莉與莉拉,曾是不能公開的戀人,一前一後探入前方暗黑的隧道。這一幕也似為「聲音的孤島上獨舞」註釋:未知、恐懼、憤怒、孤獨,化作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女性樂人穿越黑暗的力量。
本文為客座選片人鍾適芳所撰寫之《在邊緣聽見世界》單元論述,刊載於天下獨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