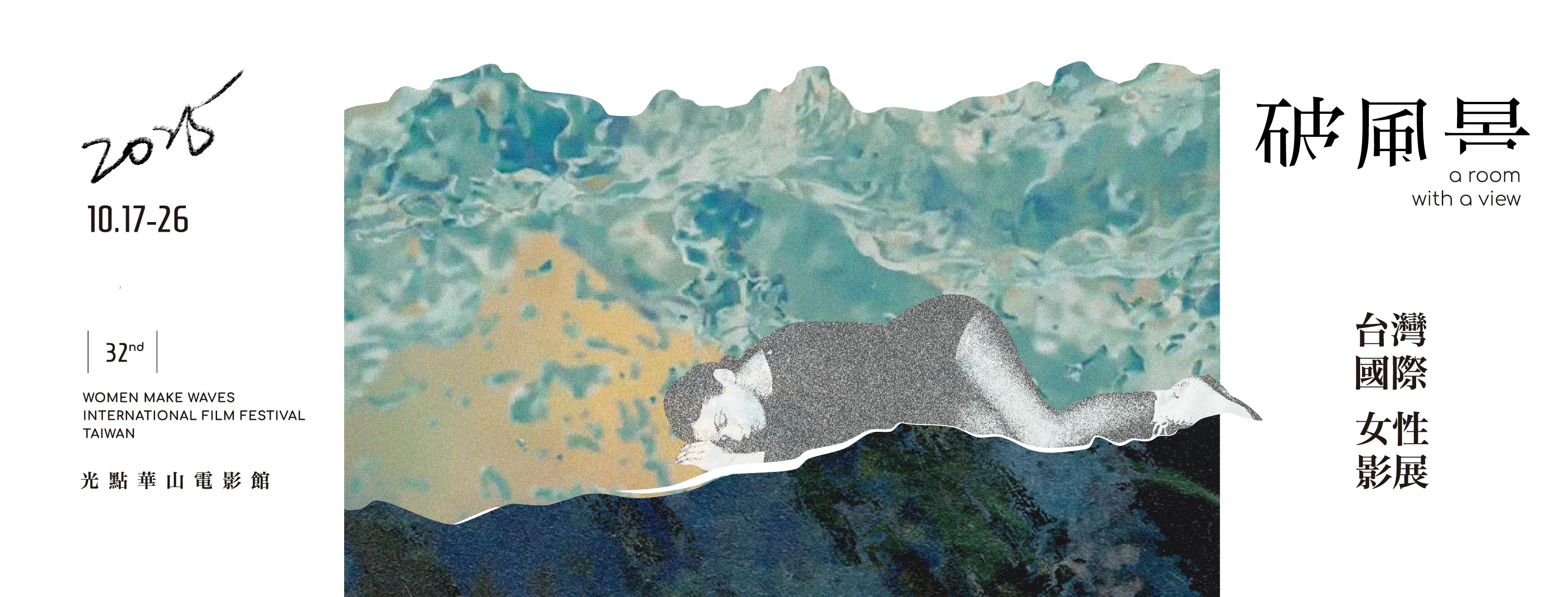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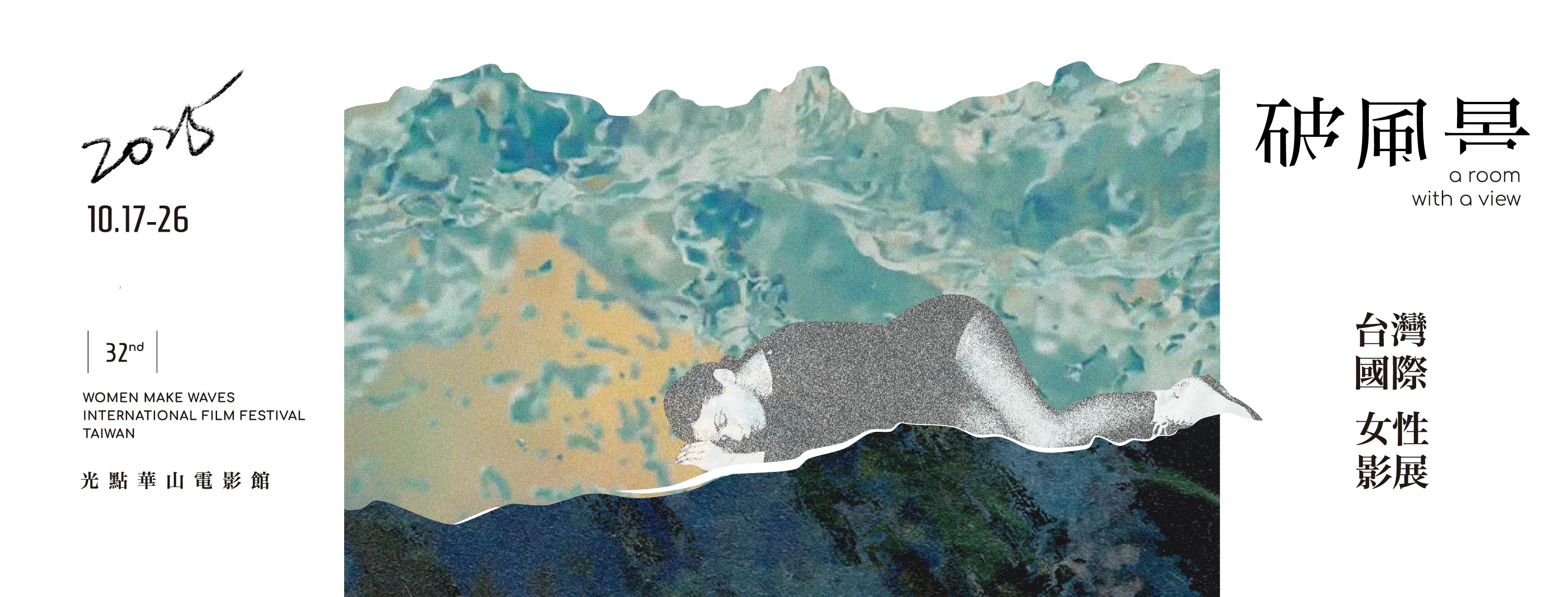
採訪:洪偉珊、陳品瑄
攝影:黃鈺涵
在台灣,有七十一萬人口為跨國移工,這七十一萬人為何選擇來到台灣工作?他們在台灣是否過著與我們相同的生活?面臨到任何困境?
曾文珍導演於2002年以《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贏得三十九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此次入圍本屆女性影展台灣競賽的紀錄片《逃跑的人》中,細膩的呈現出兩位主要人物—草雲與維興—為了家庭來到台灣工作的點滴,以及回到家鄉的後續發展。
此篇專訪就讓曾文珍導演帶我們更深入了解拍攝八年來的過程,以及她想透過《逃跑的人》和觀眾傳達的訊息!

圖/《逃跑的人》導演曾文珍
導演已經拍過很多題材,今年《逃跑的人》是選擇拍移工,為什麼會想選這個主題?
當我對什麼題目有感受,就會開始投入拍攝。因為草雲與我年紀相近,讓我開始思考,同樣身為女性,做為一個女兒或母親的角色,怎麼樣看待自己的身分和工作,這過程我們有很多的對話跟呼應。我自己在創作這方面也有很多很多挫折,可是這個挫折跟他比起來好像不算什麼,我看到他很堅強,這就讓我有蠻大的勇氣,是這個片子會持續做下來到那麼久的原因 。
所以原本的計畫不是想拍這個主題嗎?
我原本就想拍這個,只是因為拍了很久,從2012一直拍到2018,也很擔心被攝者會被抓到,變數很大,所以大概前半段時間就比較積極在拍,我心裡其實是非常焦慮的。
也常常會有人問我說:「拍片什麼時候你覺得可以殺青了?」我幾乎每天都在想這件事,想這片子該怎麼辦。我也在想,到底拍片是為了參加影展,還是為了什麼,這個問題每天都在反覆問自己。
後來我覺得拍紀錄片其實讓我的靈魂是比較安定的,我也覺得拍紀錄片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比如說白色恐怖的那個紀錄片,公共電視還有抽版權給我,那可見得說這片子還有人在看。我覺得這就是意義,勉勵自己如果你還有力氣、還有想法、還有餘力,那應該就可以繼續拍下去。
那一開始怎麼會找到兩位主要人物草雲和維興?是人家介紹認識的嗎?
張正(現中央廣播電台的台長)跟廖雲章(現天下獨立評論的總監),他們最早是在四方報。當時草雲會投稿到四方報去,維興會畫插畫,他們是這樣認識的。後來我是透過四方報介紹而認識草雲和維興,那也是他們介紹我說他們兩個很適合拍紀錄片。我大致花了半年的時間在跟草雲建立信賴的關係。
移工的工作畫面其實是最難拍到的,怎麼去讓對方同意拍攝?這其實是很耗心力的。這個過程,我反倒發現我接觸到的台灣人,其實大部分都很良善,包括租房子給維興的那位大哥,其實這些在台灣角落的人對他們的接受度其實是很高的。我覺得,傲慢跟高傲是因為這個社經地位所產生的歧視問題。
這移工的問題,他們沒有選票,政治人物不會去關心他。台灣一個號稱所謂人權的國家,我真的覺得那個人權是有選擇的。台灣現在有七十一萬名移工,這七十一萬的人跟我們享有同樣的人權嗎?

圖/《逃跑的人》劇照
所以你一開始就確定草雲會是你的主角嗎?跟草雲相比,維興就比較沒有跟拍這麼長的時間了?
因為維興是男性又住得比較遠,在苗栗的竹南,我比較不好去找他拍攝,甚至有時候我要拍維興,我必須透過草雲聯絡。反倒跟草雲是比較是姐妹的那種關係。
阮廷山則是草雲一開始在幫助越南人的個案。我有一陣子在草雲的臉書上一直看到這些工傷的東西。他們習慣就是非常赤裸、不遮掩地放在臉書上面。草雲就幫他們發起募款,幫他們可以讓骨灰回越南。
後來最後我想說:到底觀眾們要看什麼?我希望讓觀眾看到一個移工背後其實是有一個家庭的。我在剪接上面其實也做了一點調整,拉到一個人之常情的角度,那為什麼會去逃跑?這個視角其實蠻難做的,所以我做了一個這樣的挑戰。
您提到您期望透過這部片可以讓觀眾看到移工與家庭的聯繫,除此之外,您還希望觀眾可以從這部片得到什麼?您希望告訴他們什麼或是可以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他們到台灣來工作所企盼的就是更好的生活,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希望在看這些移工朋友的時候,可以多一點疼惜,我最感動的是我覺得他們願意這樣為家庭付出是超乎我想像的。如果可以從片中感受到這個的話,那我想我們比較可以將在我們身邊的移工看成我們的鄰居或是朋友,我覺得這樣的思考能幫助改善這些移工的工作環境、居住環境,當然這事很複雜的,有雇主面、仲介面,甚至政府面,都是很結構性的問題,
英文片名取了The Lucky Woman有什麼涵意呢?
其實我是希望可以給草雲祝福,希望他回越南之後生活會比較好,比起在台灣,我覺得他的生活是相對比較安穩一點的。她的能力現在也變得很好,有台灣這些經驗,回去之後在旅行社裡面當類似總機這樣的角色,他也把事業做得有聲有色。

圖/《逃跑的人》劇照
您是一開始田調的時候,就決定要跟著去草雲越南的家嗎?還是是拍到中間的時候才覺得要去?
去他家是需要的。到底為什麼他要來台灣工作?他們的貧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覺得這是台灣人比較無法想像的。我在2017年,我到印尼的時候就發現大家都坐地上,他們家裡的地上都是非常的乾淨,那他們就席地而坐。某種程度我們也應該很自豪,說我們北車是這麼亮潔的空間所以大家就席地而坐很舒服。那如果我不是透過這樣親自去看或是感受一遍的話,對我來說,我就不能理解。我覺得我需要去感受,需要花很多時間去理解、去找尋。
那這麼多的素材裡面你那時候是怎麼去分配各角色比重或者敘事方向?
其實後來那敘事的部分很難進行,因為太久了,後來變找主題去做。你要怎麼樣讓逃跑這件事情是被理解的?也有人問我:「那為什麼要逃跑?」,不是工作勞動環境或居住環境太差,就是他想賺更多錢,假設他五年的時間可以賺到九年的錢,那他為什麼不逃跑?
媒體因為逃跑外勞做了一些什麼事而取了「治安死角」,我其實看到蠻多低調認真的工作,就為了不要被檢舉,所以根本不會刻意去做些什麼事,通常很容易被抓的就是剛逃跑出來的,一看到警察就跑。
好像一開始仲介費的龐大的剝削也是造成逃跑很根本的問題?
仲介費是 6000-8000美金,對我們來說是24萬,在他們那邊工作的薪資大約是我們的四分之一,所以那24萬再乘以4會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賺到的錢,回越南也會是4倍的價值,所以在一個全球經濟化這種脈絡底下,這些經濟弱勢的國家的勞動力怎麼樣流動到這些經濟力比較好的國家,為什麼他們都會這樣流動,就是要賺取這個經濟上獲得的價值會比較高。

圖/《逃跑的人》劇照
您是不是也不確定什麼時候才能讓草雲看到全片?
因為這片子也有入圍南方影展,未來是會在線上進行的,那我想透過線上的方式將片子給他們看,這樣至少是透過點閱的方式而不是丟個連結,如果丟連結怕會到處流通。草雲非常喜歡跟大家分享和被大家看見的感覺,如果有機會還是希望可以透過某些方式和觀眾見面。
經過8年後,這部片終於可以上映了,導演現在心情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是很幸運進女性影展,從第一部片到現在,我拍片27年了,算算其實也蠻可怕的,就是用1/6的生命專注在這件事情上面,讓我確定我很喜歡拍紀錄片,透過這過程認識自己,我是希望這片子能讓更多人看到、能有些論述出來,讓我們好好看看在台灣這71萬人他們可能有些什麼樣的問題,那我希望這部分是可以被看到然後被討論。

剛剛導演有說現在正在拍印尼移工,拍攝過程還順利嗎?
最大的問題也是他們工作情況無法拍攝,能拍到的就是他們禮拜天出門,那禮拜天拍到的會和工作時的狀態不一樣,那我在想這片子剪出來,觀眾看到的就是印尼移工們開心出遊的樣子,我擔心會有負面的印象,所以我還再整理想這些人物到底要拍些什麼。
那您還有在做別的計畫或者未來還有想要拍什麼?
有耶,我有在思考說是不是把像逃跑移工這樣的題目寫成劇情片的內容,因為在紀錄片上還是有很多侷限,覺得有些部分必須透過戲劇手法去處理。這8年的每個素材拍攝的過程,背後都還有東西是可以繼續說的,也是希望找到對這方面有想法或有興趣的後輩可以一起著手,想把這方面的經驗給年輕人,怎麼樣可以讓你在這領域中生存下去?除了熱情之外,現實面要如何維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