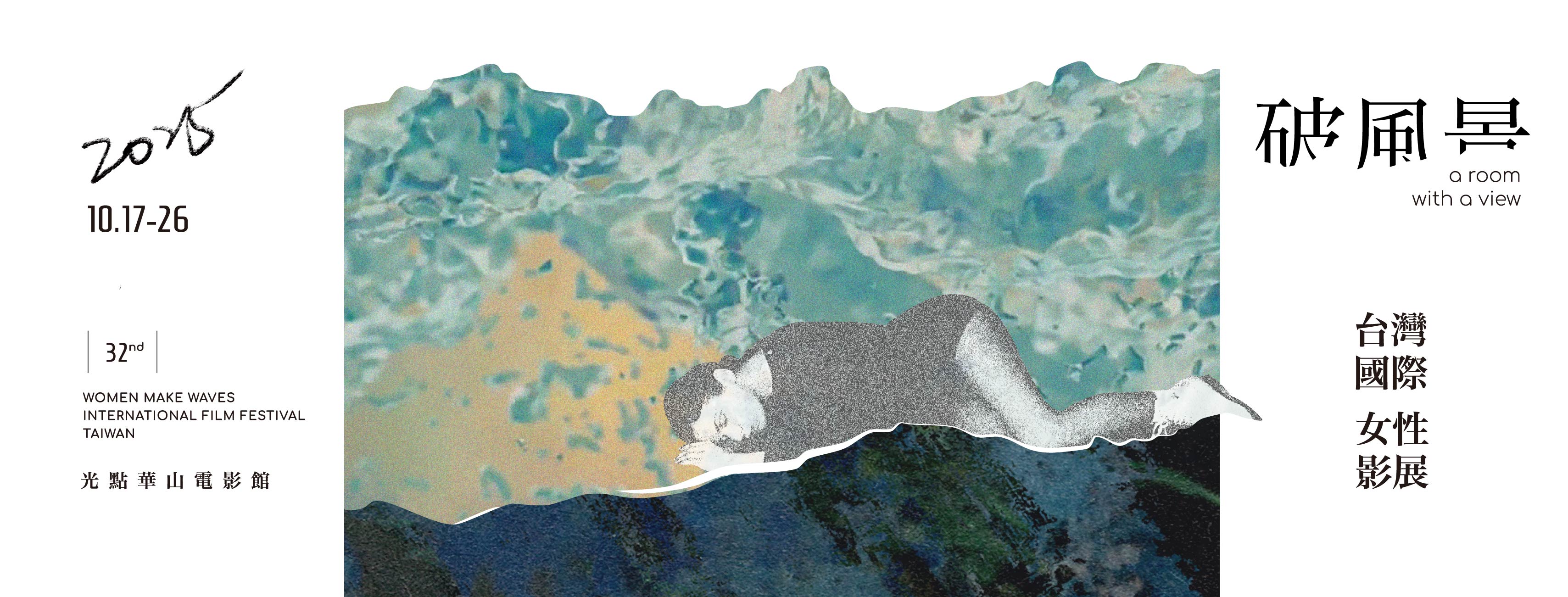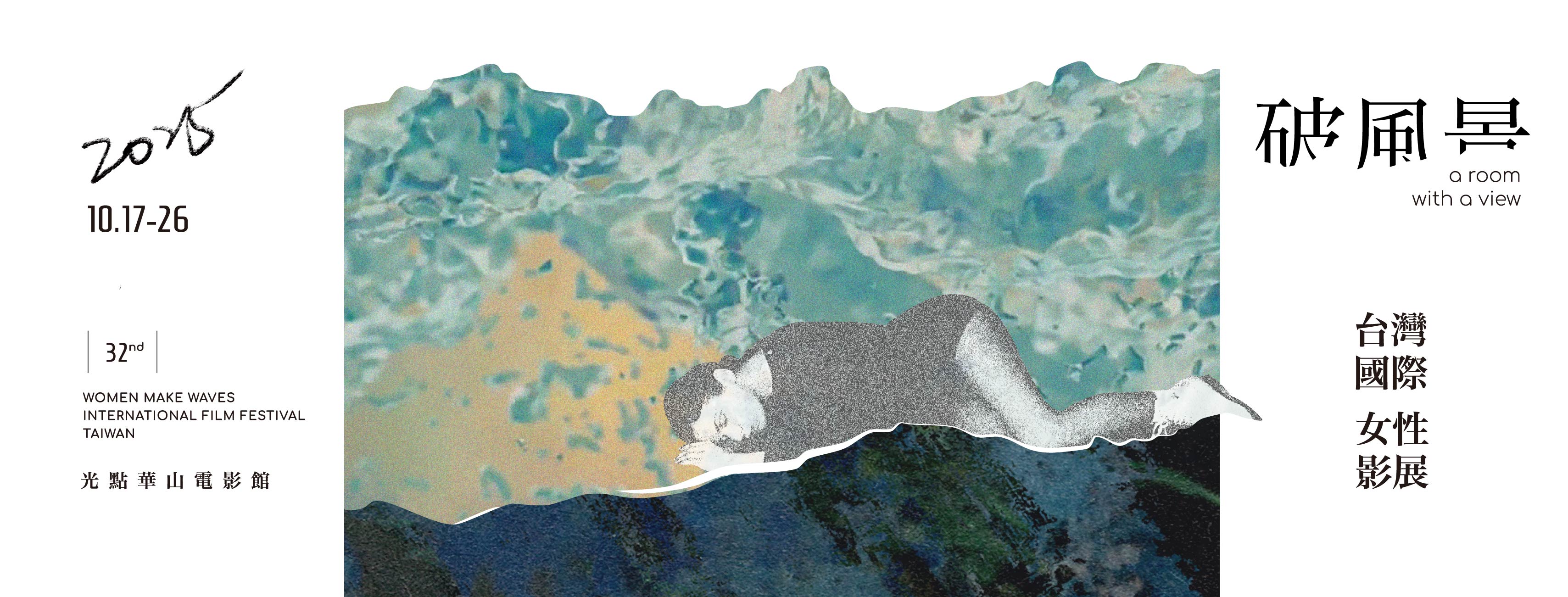故事就是力量:書本和想像的空隙,我們還有酷兒電影
文/陳劭任(藝文媒體編輯)
這幾年常看到一句流行話:「有讀書,勿說教」。大多放在社群軟體的簡介欄,像是一張護身符,用以防堵飄散社群無處不在熱愛鍵盤指點江山的路人說教,提醒對方知識就是力量,力量用在擊退自以為是的說教人士。
在酷兒議題的戰場尤其如此。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解放了女人,男同志女同志,無性戀和跨性別,泛性戀和非二元性別,被解放的人們走出書本,披上酷兒理論走上戰場,捍衛自己也保護盟友,創造自己的理想國。
只是用來保護的盾牌有時也能傷人,甚至分化彼此。實際逛一圈社群,「有讀書,勿說教」的美麗新世界尚未到來,多的是滿口理論,遂行「我讀書,我說教」的場景——把他人的真實困境視作虛妄臆想,為那些不夠「酷兒」的貼上標籤,直到最後發現看誰都是敵人,想要破除刻板與壓迫,踩碎的卻是每一個真實的生命,於是沒有人再值得驕傲。
請別認為我在鼓吹大家拋掉書本或不再吵架。適量吵架是正常能量釋放,有益身心健康,而書當然更是不能不讀的,許多問題的答案,其實早就存在在書本裡,在文獻和數據裡。因此最讓人厭煩的,還是一知半解,只學了個名詞就化身為標籤檢查員,裝著半本書就沒有空間再塞下同理的腦容量——在開罵之前,我們能不能先暫停打字三秒鐘,好好思考他人那些或許刻板、或許開倒車、或許強化污名的行為背後,可能存在什麼樣的經歷?畢竟理論並不總能沒有縫隙地鑲嵌進每個人的生命經驗,空隙撐開的地方,才是酷兒理想國應該直視的現實。
因此我們需要書本也需要故事,需要各種各樣不同的生命在陽光下顯身,否則我們如何指認黑影處是父權敵人,或又只是一個難以揭露的苦難傷痕?
這幾年的工作裡累積了不少採訪經驗,許多故事來來去去,在受訪者的口中重回事件的第一現場,這些聆聽與對話的過程告訴我,許多時候甚至不必大張旗鼓地將個人經驗連結至口號或理論——單純地說出故事,本身就足夠力量。
而故事哪裡找:(帶著書本)上街去,走進田野,故事在遊行裡,在同志三溫暖和夜店,在網路聊天室和路邊小吃攤。當然還有電影。
「幻化為真的酷異旅程」單元中,五部電影裡的故事有虛構也有紀實,不論情節是否為真,故事反射的性別處境,絕非光靠腦袋隔空想像就能輕易觸及的。
由單口喜劇演員薇拉.朱自導自演的《小丑萬萬歲》有著古典的酷兒電影敘事,一位覺醒的跨性別女性離開鄉下的原生家庭,在大城市裡找回身分和同伴。電影毫不客氣地直接借用蝙蝠俠與小丑的故事背景,女孩變身成在舞台上講笑話的小丑女,與一眾酷兒版本的小丑、企鵝人和毒藤女,表演「非法」的單口喜劇。
影片既然有著超級英雄電影(未經授權的)外皮,最好看的當然是對英雄角色的反轉:瓦昆.菲尼克斯的小丑從小會不由自主大笑,需要仰賴藥物控制;然而在《小丑萬萬歲》中,跨性別小丑裂開嘴笑,那是一種賦權,又或者是不得以的偽裝副作用?
許多時候,電影裡的笑容擔當角色和解的起點與終點,但真實世界裡每一個嘗試越界的酷兒,未必都能迎來和解。《藍色旅程》以一劑睪固酮注射劑為起點,注射的對象是正在經歷性別重置的盧茲卡・埃科茲拉——變性之前,他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尼爾・埃科茲拉,而當時他的身分還是土耳其有名的女演員。
新的身分有新的挑戰,挑戰不只在身體的變化,更在於要如何與恐同更恐跨性別的社會和平共處。我們往往期待性少數的戰鬥終將被人與人的交流同理取代,但許多時候和解之難,在於壓迫的對象如此巨大,尤其當埃科茲拉身在土耳其——一個跨性別遭謀殺比例高居歐洲第一的國家。
有些人在日常生活裡進行性別的戰鬥,有些人則把抗爭搬上舞台,讓槍砲火花炸出一片燦爛。《暴力蜜桃調教中》跟著搖滾暴女前輩暴力蜜桃的腳步,回顧他橫衝直撞的音樂生涯:從唱著民謠的女孩,到大聲唱著「來吸我的奶」「把避孕器都留在學校吧」(這首鼎鼎大名的〈Fuck the Pain Away〉,應該有不少人是從影集《性愛自修室》裡認識的。)即使如今年逾五十,舞台上的肉身衝撞依舊力道不減。
影片裡,暴力蜜桃長年合作的音樂夥伴是這麼說的:「僅僅是活著,就關乎政治——我們的任何選擇,即使在微小的地方,都有政治的痕跡。」簡直像極了辛波絲卡那句傳頌在許多抗爭場合的〈時代的孩子〉:「不管你想不想要/你的基因有政治的過去/你的皮膚有政治的色彩/你的眼裡有政治的神情」。
名人的故事往往自帶閃亮濾鏡,然而酷兒創作最難能可貴之處,是能夠在平凡樸素的生命經歷中提煉出光芒萬丈。紀錄片《唱爆女子監獄》把歌舞片的形式搬進阿根廷的女子監獄,在這裡異性戀、女同志和跨性別女性混處一室,專擅 Voguing 的跨性別女性在監獄開課教學,練舞的第一步得先想像把不存在的陰莖夾起來——那是閃亮又充滿魔法的一幕。《致我們的夜晚》則跟隨四位跨性別好友的腳步,度過他們漫長又剔透,有愛意與擁抱,也有歧視與對抗的一日。乍看鬆散,但那樣日常的面貌,難道不是我們對於非我族類最缺乏的想像嗎?
性別運動年復一年地嘗試讓不同性別樣貌的人們在大眾面前現身,意義不只在於看見,更是在生命的空隙中連結彼此。締結盟友不能只仰賴對苦難經驗的憑空想像,在故事面前,我們更永遠保持最開放的想像力。林奕含婚禮上的誓詞說,「我想要成為一個對他人痛苦有更多想像力的人。」這幾年來四處流傳,許多人都會背了。而每一次面對新的故事,我總要再一次提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