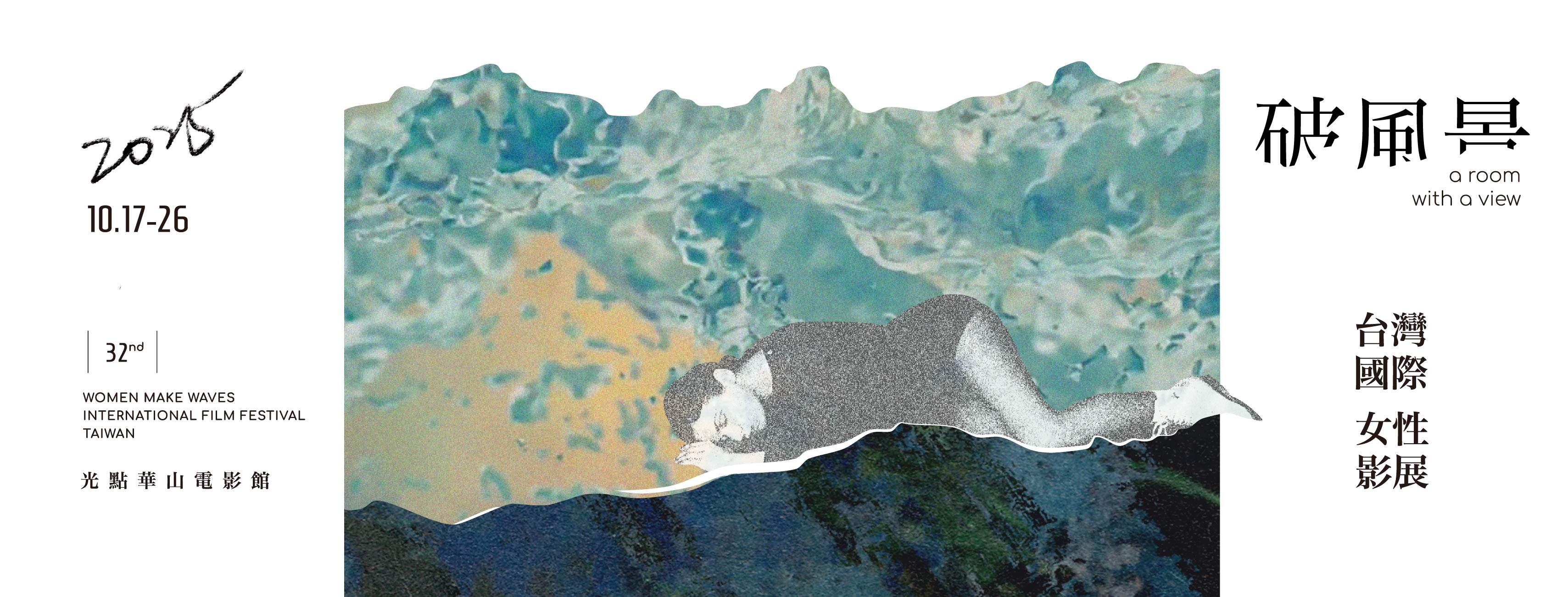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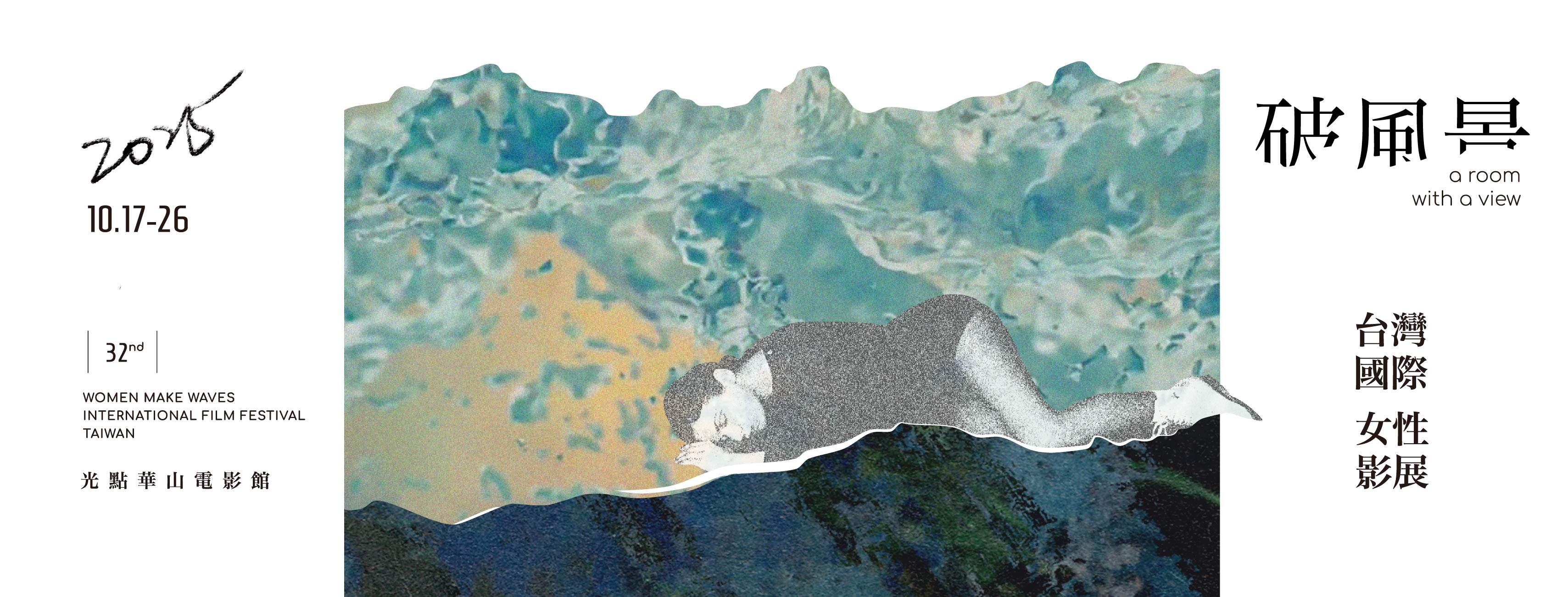
朝向「不進步」的未來:酷兒的時空不服從 文:林新惠 在台灣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同志(包括性少數主體和生活等等)似乎不再是難以再現、不可再現之事。然而,在這個同志越來越不「稀奇」的時候,或許另一個問題也逐漸浮現:同志運動還能如何進展?同志的未來是什麼? 在本屆女性影展「酷異幻化・非關定義」所收錄的五部長片中,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些許答案,以及更多的提問。 從反思「進步」開始。在《引領風騷:回顧 Curve 雜誌三十年》中,美國重量級女同志雜誌《CURVE》創辦人法蘭可.史蒂芬斯問道:「如今還有人需要『女同志』這個詞嗎?需要女同志雜誌嗎?」生於1967年,並於1990年創辦《CURVE》的法蘭可在2019年遭遇的,不僅是雜誌的倒閉危機,也是性少數族群中的世代差異,以及媒介轉型的動盪。片中,年輕酷兒表示,「女同志」一詞帶有排他性,他們更樂於使用「酷兒」來標示自己。對於法蘭可世代的美國白人女同志而言,為了爭取平權和能見度,「女同志」這個「擁有較為明確定義」的主體定位不可或缺。然而,對於生長於較為平權時代的年輕酷兒,「定義」反而需要挑戰。甚至,連「具體的」刊物也搖搖欲墜:法蘭可感慨,網路上有這麼多影片,這麼多社群軟體和網紅,使得實體雜誌似乎不再擁有當年的前瞻意義。如此我們可以看出片名的雙關:英文「ahead of the curve」有「改革前鋒」之意,這是1990年代法蘭可和《CURVE》雜誌的成就;然而,到了現代,同樣一句話也可以詮釋成ahead of the CURVE(超越《CURVE》雜誌)——在當代,《CURVE》雜誌幾乎快被新興的酷兒文化、數位媒介給超越。 不過,這不意味著往日的、實體的、女同志的時代已然陳舊而不值得一提,反而意味著此刻正是重建「過去的政治」的好時機。許多學者都已提醒,酷兒性(queerness)如果一味強調「進步」、「解放」、「邁向光明未來」等等現代社會發明的正向價值,恐怕會有和資本主義現代性共謀的風險。因此,酷兒政治在當代的挑戰,也許不再只是「性別不服從」,也需要納入「時空不服從」。 《忽男忽女》和《忽男忽女.後篇》對應到「時空不服從」中的「時間」。1999年,德國導演莫妮卡.楚特拍攝《忽男忽女》紀錄片,記錄多位在舊金山具代表性的跨性別藝術家,以及支持跨性別者的社群和醫療系統等。時隔20多年後,莫妮卡推出續作《忽男忽女.後篇》,再度拜訪當年她在《忽男忽女》採訪的人。莫妮卡的系列作品避免讓酷兒成為「一次性」的、解放的、歡騰的煙火。意即,觀眾對於跨性別者的理解,將不止停留在《忽男忽女》中各個跨性別者展現的「身體可塑性」,而會延續到《忽男忽女.後篇》中已經成為58歲到84歲的中老年酷兒,如何面對年老、退化、死亡等等「身體有限性」。因而,從《忽男忽女》到《忽男忽女.後篇》,「跨」的身體所呈現的時間,不全然是向前進步,也呈現許多退步——不如年輕時的活力、張揚、狂歡等等。正因如此,我們可以看出酷兒時間的難以界定:既是進步(例如挑戰性別的疆界),也是退步(例如因年老而鈍化的身體)。同時,我們也看見這些跨性別者如何在酷兒時間的模糊地帶中,和自己的身體、和時間共存。不服從時間並非抵抗時間,而是承認時間的所有方向性同時存在於己身。 除了反思「進步」隱含的「直線向前的時間性」,我們也要反思「進步」和西方、都市、資本主義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姥姥惹人愛》和《關於愛的生存法則》當中,我們得以看見生活於非西方、非都市的酷兒主體們,如何掙扎於身份和抉擇之間。《姥姥惹人愛》講述一位失去丈夫且和女兒疏離的年長女性克勞蒂娜,如何在傳統社會角色(如異性戀女人、母親、年長者、寡婦)和非典型身份認同(如女同志)之間的掙扎。傳統和非典型之間,不只是時代上的差異,也是空間的落差:克勞蒂娜生活在智利南部鄉村,既缺乏接觸高科技產品的管道,也和全球化的世界疏離。《關於愛的生存法則》則呈現了雙重「夾縫」的重疊:女跨男亞歷山大居住於不承認、甚至迫害跨性別者的喬治亞。亞歷山大的身份在夾縫中:他的身份認同和身體改造都傾向男性,但他的官方性別(由各種身分證件載明的性別)只被允許為女性。喬治亞也是夾縫中的國家:地理上處於歐亞交界,文化上介於全球西方的現代性和全球南方的另類現代性之間。這兩部片呈現的「空間不服從」,並非主動的抗拒和逃逸(這兩個行為都需要資本),而是在被給定的處境中,游移在不同身份之間,也猶疑在每一次人生交口之間。 從上述五部長片,我們可以發現,同志和酷兒的未來將不再只侷限於性政治的思索,而是將不同光譜交疊起來考量。這些光譜橫跨世代、性別、種族、時空、階級、身心障礙等等。酷兒模糊一切界線,也重新定義界線。美國科幻作家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作品中充滿性別曖昧不明的酷兒角色,她曾言:「小說家用文字呈現無法以文字敘述之物」。我們或許也能說:酷兒以曖昧性呈現曖昧難言之物。每一個個體都是複雜的,每一種物事都是費解的,或許除了給予框架和定義之外,我們也能以「酷兒」去定義那些難以定義之事。
(一級玩家X異境幻遊)=監控遊戲+海陸拼盤+嬰兒 文:陳慧穎 「歡迎來到2020/2021年」這句話與它的變奏時不時在不同語境中迴盪,一句歡迎,背後究竟能藏多少諷刺和苦難?全球疫情的持續擴散、人與人接觸的詭譎感、全身式防護衣的白色意象、空蕩蕩的超市層架、疏離成為國家級指令的當刻,這一切都彷彿是從科幻片擷取出來的影像片段,在日常生活中隨機播放。抑或,我們的目光所及,已處處暗藏著科幻影像的編碼錯誤或畸變,呈現出影像與現實彼此干擾而成的故障變體?有時,電影與現實的距離又像是一種回放機制,過去這段時間《全境擴散》(Contagion)、《末日之戰》(World War Z)、《阿基拉》(Akira)等片不斷被人提起,以「預言成真」的陳述句在網路上大量流竄。過去的預言尚未完全失去作用,借用未來的寓言體卻已焦急來到跟前,這兩年來釋出的科幻片數量尤其眾多,無論是數位發行,或在實體電影院或開或關、命運未明之際,排起長長的隊伍等待上映,其中也包括了令全球影迷癡心妄想的《沙丘》與《駭客任務4》。身處科幻不過的時刻,看科幻片,或許正是最與現實相符的超現實情境。 不過,在女性影展放映科幻片又自帶另一層意義。首先這本身即是一個難題,科幻片長久以來作為一個高度性別化的類型,尤其在好萊塢無限上綱的權力體制下,幾乎成了女導演的禁地,長期性別比失衡的現象使得「女性執導的科幻片」變相成為影視圈衡量性別平權的指標。在這樣的脈絡下,凱薩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在26年前執導的《21世紀的前一天》(Strange Days,1995)絕對值得一提。畢格羅因本片成為第一位獲得土星獎(Saturn Awards)的女導演,然而科幻類型的初啼之聲並沒有想像的風光,不僅票房慘淡、評價兩極,甚至有不少影評將電影的突破歸功於負責編劇的詹姆斯.卡麥隆,票房的失利也嚴重威脅到畢格羅的導演生涯,使她沉寂了好一段時間。事實上,這部片後續引起爭辯與討論不斷,多年後好萊塢高層才開始意識到「是否可以讓其他女導演嘗試一下科幻類型?」這件事情不免令人思考起另一個問題:假使1999年執導《駭客任務》的華卓斯基「兄弟」,在當時已改名為莉莉和拉娜,在性別議題上永遠後知後覺(或未曾真正開竅)的好萊塢仍會願意提供比《21世紀的前一天》高出許多的製作預算給《駭客任務》?我們今天還有《駭客任務4》可期待嗎? 話說至此,類型片本非好萊塢所獨佔,也不一定要有磅礴場景才能稱作科幻片,即便科幻類型至今仍舊是男性主導的場域,有時把目光從好萊塢身上移開,便能看到更加廣闊的天空。科幻敘事所鋪展開來的光譜自始以來便具有極大可塑性,其類型元素及意象可明確純淨的容不下一粒雜質,卻也同時具有吸引其他類型元素的磁性體質。本單元所收錄的「科幻片」便以雜異的類型拼貼為主軸,貪婪擁抱所有影像元素混雜一氣的異質觸感。當科幻成為連接基點,我們所熟知的大師級導演作為星象定位,在類型元素成層形變擴張與收縮之間,聯覺串連出有別於典型的科幻想像,又不設限於科幻框架的「一級玩家X異境幻遊」單元。 這場異境幻遊將帶領觀眾一躍回到半世紀前,轉身進入60年代的安妮.華達(Agnes VARDA)的《創造物》世界,透過絕妙視角觀看小島上村民的生活。跳脫出純粹的類型實驗,「科幻」化為一種後設媒介,層層藏匿創作過程的各式隱喻,從語言的鬆動變形到情節角色的編排,皆有趣味盎然的深刻探討。擅長處理史詩格局的莉莉安娜.卡凡尼(Liliana CAVANI)則以《食人族》呈現「科幻版希臘悲劇」,並藉由濃烈的時代圖像打造出嬉皮感十足的末日異托邦景致。同樣改編自文學作品的《美少年格雷與八卦新聞》更是將類型拼貼實驗玩到癲狂之境。順著下水道進入「暗黑媒體帝國」,烏爾麗克.奧汀格 (Ulrike OTTINGER)式的奇幻旅遊誌以不正經敘事帶出可怖的權力網絡,敢曝展演與科幻元素的無縫結合更是展現出奧汀格獨到的美學手法。雜揉砍殺電影/ 驚悚科幻/ 恐怖喜劇元素的《狼穴》,在薇拉.齊蒂洛瓦 (Vera CHYTILOVA)巧妙安排下,孩子們的滑雪訓練營轉瞬變調為充斥精神折磨與人性實驗的政治寓言場景。來到90年代,鄭淑麗的《鮮殺》在充斥著電子垃圾的末日荒景中,透過跨種族女同志情侶的意外際遇,揭示跨國媒體、網路駭客及全球環境危機等議題,也可從中洞見穿梭於日後創作中的科幻軌跡。時序瞬間拉回眼前,由克萊兒.丹妮絲(Claire Denis)執導的《黑洞迷情》於2018年上映,當時已有不少女導演踏入科幻大片的領地,此片亦是本單元唯一將場景設置在外太空的作品。然而就算具有最靠近「典型」科幻意象的場景設定,克萊兒.丹妮絲也堅持稱之為「監獄電影」,其溢出典型科幻類型的顛覆性本質亦為納入本單元的最大原因。在無限偏離「返回地球」的二元式正向論述之餘,開展出圍繞在禁忌、生育、性、慾望、控制之間的不可逆航程。 大師級導演一次羅列,其中最常與科幻併作聯想的是鄭淑麗,其他導演的科幻之作反倒甚少在科幻片的討論中被提及。而這樣的聯想之難或這之間產生的斷裂,正與以科幻作為基盤所孕育出的混雜體同調,從科幻元素的變形到典型科幻元素的大膽屏棄,在在勾勒出類型公式無法精算出的非一般想像空間。除了混雜的類型元素外,這些電影在題材上皆涉及到由上而下的控制手段──「femme fatale」主宰之下的全面監控,或權力無限放大的政府、企業、媒體,體現權力結構的監控遊戲儼然成為這些電影的骨幹。另外,在異質科幻的想像空間下,食材、動物或非人意象的移植與轉化也成為不斷出現的母題,小小嬰兒更是肩負重任,且待觀眾自行發覺。在此先行植入監控遊戲、海陸拼盤、嬰兒的雜異想像,好讓這趟旅程儘速啟程。只能說這批科幻不太純,但是絕對適合骨灰級影迷一次將心愛的導演作品一網打盡,也適合已看膩太過潔白乾淨的典型科幻片,需要一點骯髒感的你,也可把自己打包成太空垃圾,在暗黑的戲院中拋向宇宙,只能說這批科幻不太純,但是絕對適合骨灰級影迷一次將心愛的導演作品一網打盡,也適合已看膩太過潔白乾淨的典型科幻片,需要一點骯髒感的你,也可把自己打包成太空垃圾,在暗黑的戲院中拋向宇宙,歡迎大家一同來參與最符合時下情境的超現實觀影儀式。
喪屍電影陰性化:拉子、生態女性主義與酷兒童話 文:陳穎(瑄) 說到喪屍電影的起源,通常會從以1968年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以下簡稱《活》片)開創此類型的喬治.A.羅梅羅(George A. ROMERO)談起,但也可追索至1932年的《白殭屍》(White Zombie)。相對於我們熟悉的前者,《白殭屍》中的所謂喪屍趨近於海地民間傳說中被巫毒教巫師下毒並召喚為奴者。這種喪屍與羅梅羅喪屍的共通點不多,但若把焦點放在喪屍被去除的性別上,兩片實可相提並論。《白殭屍》的劇情大致如下:已訂婚的男女寄住在種植園主人的家,女主角被園主盯上,園主求助於巫師把她變成喪屍以便操控。該片的結局是「好」的,男主角撃倒巫師,成功拯救女主角。但從女性角度看,這結局真的好嗎?直到結局,女方都是被盯上、被操控、被拯救的被動角色。她不是沒有戲份,但能動性極有限;《活》片雖未複製這英雄救美的劇情,其女主角芭芭拉同樣是個等待救援的弱女子。 時至1990年,《活》片的同名翻拍把芭芭拉從金髮蠢妞改為束短髮的T,把槍械這男性象徵交到她手裡,又讓她成為唯一的倖存者。正如以生替換死,以陽剛替換陰柔是最直截了當的翻轉,但同時也使兩者對立,形成非此則彼的二分。以女性主義剖析砍殺電影的學者卡洛.J.克洛弗(Carol J. CLOVER)指出,在這類凸顯女性受害之過程的電影中,女性經常被簡化為「奶子與尖叫」。原版芭芭拉較符合尖叫的部分,但「奶子」不一定是指實際上在銀幕上露奶,也指向一個刻板化和被貶抑的女性形象。 T版芭芭拉直截了當地以對立翻轉此女性形象,但T畢竟只是眾多女性形象之一,或T其實也不只一種。不只一種的女性形象正是本單元的發想所在。恐怖電影的傳統固然不乏女性作為受害者的性別刻板,但喪屍電影作為恐怖電影中較另類的次類型,於近年在女導演排除萬難的投入下,也充當另類的女性形象及情慾關係的載體。此單元中的兩部長片《末世之后》和《七十分鐘末日直播》皆把女女情慾拍進了喪屍電影,前者更被視首部女同志喪屍電影。此兩片互為對照,前者是女同性戀與生態敘事結合,後者則是女同性戀與末日敘事的結合。這種混搭風在短片中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先有戲仿(parody)之作《喪屍魅影》,不但開創了喪屍音樂劇這個「怪胎」,更以此反諷我們耳熟能詳的主流音樂劇,再來則是把喪屍電影拍成了奇幻電影的《稻草人之戀》。四片中有兩則截然不同的女同志故事,有人屍相戀並共舞,也有稻草人與喪屍的童話式戀愛──全部皆不符合類型傳統,卻正好從性別乃至於超越性別的角度,想像更另類的喪屍電影。
焦點影人塞西莉亞.曼基尼:詩、電影、戰鬥 文:陳慧穎 「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四海皆可為家。我奉自由為至高圭臬,將反抗思想永存於心。」 ──塞西莉亞.曼基尼(Cecilia Mangi) 她是義大利戰後第一位紀錄片女導演,也是編劇、攝影師、評論家、知識份子、無政府主義者,永遠選擇站在前線的戰鬥者,一個自由的靈魂。去年曼基尼甫以92歲高齡參加《遺忘之間:越南記事》在鹿特丹影展的世界首映,一年後與世長辭,享年93歲。在創作的路途上,曼基尼始終關注當前最迫切的議題,以堅韌毅力和過人智慧回應著這世界所給予的一切。 1927年誕生於法西斯義大利時期,童年在南方阿普利亞(Apulia)度過,六歲時隨家人搬遷到北方。早年的遷徙路徑勾勒出抽象途徑的原型,預示日後的不斷往返,透過身體的移動實際感受著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理論與土地接軌的模樣──南方與北方的差異性化為丈量歷史發展、經濟動向、權力結構的空間化隱喻,繼而在曼基尼的電影中落地長出更鮮明具象的樣子。除了葛蘭西之外,曼基尼也深受德馬蒂諾(Ernesto de MARTINO)啟發。當前者提醒她權力的無所不在及公民抗爭的重要性,後者則明示人們對於民族學、人類學和宗教學的關注,皆源自於「為了挑戰自己身處的社會體系所做出的激進選擇」。借助這些理論架構,曼基尼在重疊向度中找到一個最適切的戰鬥位置,讓影像成為反抗基點,任何意識形態(無論是法西斯主義、消費主義)延燒過的餘火痕跡皆漸次清晰。曼基尼踏入電影界的方式是從影評書寫開始,再從攝影進入紀錄片製作。這樣的軌跡或多或少也體現在曼基尼的作品中,再微小不過的事物或現象,都能精巧摺入宏觀視野,以犀利又不失細膩的觀察,將人民日常的勞動、嬉鬧、歌唱、祈禱、嚮往,乃至細微的動作和手勢重新賦予意義。她至始至終關注著那些被社會主流拋棄在後的面孔──所有的格格不入,抑或背道而馳,並為社會帶來不安擾動的一切,同時有意識地拒絕奇觀化的消費性視角。 《女人的哀悼之歌》是創作早期十分重要的作品,原片名「Stendalì: Suonano ancora」含有「再唱一次」(sound again)之意。面對近乎消逝的儀式傳統,既然捕捉真實勢必徒然,曼基尼與德馬蒂諾反覆討論,如何以最精準貼近的方式重現哀悼儀式的歌調及動作。她讓巴索里尼根據當地婦女的僅存記憶書寫歌詞,請演員布里尼奧內(Lilla BRIGNONE)用義大利文朗誦歌詞,並讓當地婦女以方言唱出這段「不存在的哀悼之歌」,代代相傳的儀式記憶透過女人的手勢、動作轉譯,透過「建構出來的現實」來極大化趨近介於消逝與保存之間的儀式本質,以積極的介入方式將這場哀悼儀式轉化成召喚傳統、阻擋文化消逝的抵抗場域。曼基尼將文化記憶回溯的過程加以激進化,藉由影像語言挪移出政治性意涵得以運作的空間,也確切體現了曼基尼對於紀錄片的「真實」及「媒介」頗值得玩味的獨到理解。此外,透過重構現實、儀式重演,曼基尼與巴索里尼得以嘗試精煉出一種「詩性的影像語言」,也可從中洞見巴索里尼日後提出的「詩的電影」(Cinema of Poetry)理論雛型。更重要的是,這部片向後開展出各種創作母題,對於日後創作影響深遠:在影像編排上,同樣由巴索里尼編劇的《夏日河畔》與《女人的哀悼之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藉由現實重演,將一場河邊的嬉鬧日常轉化成貧窮年輕世代的未來寓言;《親愛的瑪莉亞》透過農村的勞動生活彰顯女性角色的核心位置,日常便是抵擋現代文明衝擊的無聲宣言;描繪宗教儀式的《神聖之愛》則承襲了曼基尼對於民間儀式一貫的關注,風格強烈的影像手法及帶有前衛實驗感的配樂,諷刺地被當局解讀為「褻瀆宗教」而遭到禁演。 若說《女人的哀悼之歌》收束了日後作品的影像雛型,《成為女人》則可視為集大成之作,無論是電影際遇或影像內容都階段性的總結了曼基尼的創作軌跡。首先,這部片由左派電影公司委託製作,希望透過當前社會問題的描繪,闡述義大利共產黨(PCI)對於女性議題的重視,並預示日後的政黨改革之路,以作為政黨競選宣傳所用。作品完成後,卻因內容過於顛覆性遭到該公司上級封殺,並慘遭當局禁演。根據戰後義大利的法律規定,任何戲院放映場次皆得在長片作品前放映一部紀錄短片。也就是說,紀錄片在當時其實是相對被保護的媒介,然而一旦遭到當局禁演,在戲院端全面封殺的情況下,作品也失去院線放映的機會。曼基尼的作品時常因政治意涵濃厚與當局有所牴觸,遭到程度不一的封殺和禁演。即便本片主題不像《戰鬥吧!我們是法西斯!》直戳當局敏感神經,其議題的深度及激進性仍遠超出左派政治框架的想像。延續曼基尼以往對於女性議題的關注,《成為女人》從家務分工、勞權、生育權到公共參與,砲火猛烈地將女性在社會扮所扮演的角色、被賦予的意義、長久以來面臨的困境、掙扎與反抗一字排開。《女人的哀悼之歌》中不斷重複的性別化儀式在《成為女人》中轉化成更加無處不在、永劫重複的勞動日常,簡單的手勢動作皆能連動宏觀意義,曼基尼俐落的剪接手法不僅激化了影像中潛藏的連續性和對比性,在影片開頭便倏然構築出層次分明的控訴格局。題材上即便與描繪工廠夢的《少年托瑪索》、觸及家務分工不均的《頑童法比歐》有所呼應,《成為女人》更聚焦地探討女性於家庭、工廠、農地的勞動困境,將消費主義的遺毒、南北資源分配不均等相關脈絡梳理清楚,更不忘回歸受壓迫者的反抗圖像,以女性上街的抗爭意象重申本片的政治意涵。「成為女人」背後因此包藏了雙面途徑,一方面揭露「成為女人」的過程勢必挾帶的多重壓迫與被動性抉擇,另一方面也強調了「成為女人」本身的能動性,得以將壓迫反轉為女性特有的反抗力量 。 十分有意思的是,片尾的反抗圖像可進而連結到曼基尼的政治電影創作軌跡,通常與丈夫利諾.弗拉合作創作,指標性作品除了《戰鬥吧!我們是法西斯!》、《安東尼奧.葛蘭西的監獄歲月》,還有一部未完成的越戰紀錄片:1965年,與《成為女人》差不多時間,曼基尼與丈夫前往越戰前線紀錄人民的抗爭,計畫已久的紀錄片終究沒能拍成,以未完成的狀態跨越半個多世紀後收錄在《遺忘之間:越南記事》,當年紀錄下的越南女性身影仍舊和《成為女人》閃動著親密連結,抵抗場域更由實際的戰爭前線回歸導演的生活日常,抵抗著年老記憶的消逝、時間的消逝,巧妙地總結了曼基尼衝鋒陷陣的創作人生,並且在時間的淬煉下,所有的反抗亦有了更溫柔細膩的陳述。
生與不生的自由,都該由子宮提供者決定 文:周芷萱 生與不生的自由,一直是跨文化、跨時代的難題,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國家,支持與反對者不斷進行辯論與各式角力。反對人工受孕的其中一個論點是人工受孕「非自然」,然而這種對人工受孕的反對,往往只會針對單身女性與非異性戀族群,這種「非自然」的論點極少被用來針對不孕的異性戀已婚伴侶。單身女性和 LGBT 族群沒有生的自由,問題真的是出在非自然嗎? 與此同時,反墮胎論者總以「保護生命」為名,強調胚胎的生命權應該凌駕於其他之上,顯然在這些人眼中,子宮提供者的生命,打從受孕的那刻起就被迫退居第二。直到 2021 年的今天,全球仍僅有 67 個國家可應孕婦要求進行合法墮胎,許多國家完全禁止墮胎,包括強暴懷孕。高唱著保護生命的反墮胎人士,眼裡顯然只有未經人事的胚胎,卻假裝沒看見他們的反墮胎倡議讓更多的底層女性遭遇困難,無論是因為性別暴力而被迫生育、接著落入更不利的社會處境,或是被迫使用維持基本生命需求的金錢來支付墮胎費用。 不生:賦予選擇的可能,可能不只是選擇 以阿根廷青少女為主角的《少女孕事》採訪了幾名青少女,他們大多在毫無預期的狀況下迎來孩子,對避孕措施的不了解、長期處於性別暴力等不利的社會處境,讓他們對無論是正在經歷的事情或是自己與孩子的未來,所知的選擇都很有限。以天主教徒為主的阿根廷經過五年的倡議長路,在 2020 年終於通過合法墮胎,成為拉丁美洲中第三個允許自主選擇墮胎的國家。回顧這條維權之路,源頭也來自一個 14 歲懷孕、最後被男友毆打致死的青少女。 在有些國家,墮胎雖然沒有違法,但國家社會卻利用其他方式從中作梗,變相強迫經濟條件不利的女性必須生下孩子。《您好,這裡是墮胎專線》以協助經濟弱勢女性籌措墮胎費用的專線作為切入點。在美國,墮胎雖然合法,但是政府長期利用〈海德修正案〉來限制社會福利支援墮胎費用。因為 1976 年通過的〈海德修正案〉,聯邦醫療補助基金被規定不能支付墮胎費用,弱勢婦女被迫以僅有的積蓄支付墮胎費用,包括用來繳房租、買食物的錢。讓女人可以為自己的生命做決定,是一條不斷折返跑的漫漫長路。可笑的是無論生與不生、〈海德修正案〉納入或不納入,都是事不關己的異性戀男人們在國會高堂上說幾句話,就決定了弱勢婦女們的選擇權利。 但若要說墮胎就全然是女性自主權的展現,這麼非黑即白的觀點大概會在《如果我不是女生》的觀影過程中被打破。在南韓,因為社會長期重男輕女,許多懷孕的女性持續墮掉女性胚胎、直到產下男嬰,非法墮胎讓他們處於險境。然而當倡議終於成功,墮胎合法之後,失衡的性別比會平衡回來嗎?大概不會;因為要生兒子而持續墮掉女性胚胎的情況會減少嗎?大概也不會。 如果將墮胎單純當成女性自主的展現,也就是美國墮胎倡議時常說的擁護選擇權(Pro-Choice),恐怕在重男輕女、盛行墮掉女嬰的亞洲國家,很難直接畫上這樣一道擁護選擇權和擁護生命權(Pro-Life)的分隔線。選擇往往不只是選擇,還必須考慮社會結構對個人選擇的影響。在台灣,即使法律規定不得進行胎兒性別篩選,性別比依然持續失衡,每年出生的男嬰遠多於女嬰。雖然人工流產合法,但若是已婚就需要配偶同意,我們能說墮胎全然是女性「個人」的選擇嗎?在不生與生之間,生下來跟沒生下來之間,還存在一些模糊的可能。《噬》這部短片則講述了一個關於執著的故事。 生:跳脫異性戀家庭常軌 我們通常會用女性、女性身體之類的詞彙描述生育,但在本次的《生而育矩》單元中,用子宮提供者來描述這個群體,可能會比「女性」來的精確。因為男人生孩子的可能是存在的。懷孕經驗不一定是專屬於女性的經驗,擁有子宮的人不見得是女人,《海馬爸爸要生娃》帶我們擴展性別與生育的視野。一般人聽到懷孕生子,腦中浮現的是女性的形象,跨男用他們的身體突破人們想像的邊界。一個男人決定要自己生下孩子,為了懷孕必須停用正在施打的男性賀爾蒙藥物,讓整個孕程同時面對生理與心理上的挑戰。以男性認同、男性外表來懷孕,更可能遭受社會異樣眼光甚至死亡威脅,跨越邊界雖然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當嬰兒在溫柔生產中誕生,真實的喜悅無可取代。 這世界因為人們努力追求想要的東西而不停跨越邊界,讓我們的未來擁有更多可能。有一群人為了擁有生孩子的更多選擇而努力。《同路人》中的三個故事、三位單身女性,一個為了進行中國不允許的單身女性人工生殖遠赴紐約、一個為了單身女性要凍卵卻先被醫院勸婚而一狀告上法院、另一個則為了讓女同志也有生育孩子的權利而努力。他們的處境不同、身份不同、經濟條件不同,甚至對生孩子的意願也不同,唯一相同的是,他們想要有更多選擇的未來。在中國,生與不生幾乎不是可以自己決定的事情。從一胎化政策,到如今因人口老化而開始推行的二胎,生育權利掌握在國家手上。中國不是沒有人工生殖技術,只是不為單身女性而存在。台灣亦是如此,人工生殖只為異性戀已婚夫妻而存在。我們有同婚,只是用的是專法;有人工生殖,只是單身不行;有墮胎,只是要綁配偶同意權。看似自由民主、擁有各種可能的台灣,其實無論是生與不生,國家與社會對個人的掌控依然如影隨形,單身女性、單身男性想生小孩,那生下來之後呢? 《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演繹了單身女性養孩子的過程,養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的努力,這句老俗諺在當代被重新詮釋。當一個人想要孩子但不想要伴侶,透過人工生殖或是捐精生下孩子,再由家庭成員共同養育,異性戀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想像被突破、養育孩子有更多可能。本單元七部片從不生到生,在生與不生之間,每部片帶我們從不同的故事切入真正的生命。「生命權」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你眼前活生生的人。
在電影裡,我們都是殘破的美景。 文:羅珮嘉 生命的長相難以捉摸,卻又是呼吸般的存在,而這些樣貌總能在電影形式的糅雜下形成抽象或寫實的姿態再現。這些姿態在無盡的螢幕和真實迴圈裡共享記憶,然後相互推擠或共存。這次探討電影科學與美學的「碎光重影」單元,即以二次凝視影像的意識重新覺察電影的量能。攤開單元裡的8部影片,有景框內外的生命交織,有形式風格的異質再製,有被攝者與攝者之間的親疏關係,甚至來到了創作者及其職涯人生的糾葛。 義大利知名導演維斯康提(Luchino VISCONTI)因為看中伯恩安德森(Bjorn ANDRESON)身上的脆弱與陰柔,於是從數百人中選擇他飾演《魂斷威尼斯》的美少年。在電影裡,中年男子難以拒絕凝視美少年的身影,因而放棄自己的性命,這情節很簡單,但它描繪的「癡迷」狀態卻很強烈,於是安德森就此被世界「盯」上,他那帶有陰柔氣質的外貌甚至影響整個日本動漫業。但一夜成名也讓他夢斷威尼斯,他認為自己被性剝削,被物化,於是年老後的安德森在《魂斷美少年》這部紀錄片中,決定赤裸面對鏡頭並層層剝開內心的糾結。究竟人該如何逃脱自己的影子,逃離戲如人生的囚禁,逃離世界的虛妄?本片雙導演試圖將他的精神過程搬上銀幕,再加上如意識流般的攝影和光影進入意識的深處,於是老年安德森與他記憶和電影裡的少年安德森猶如幻形共生,那種試圖擺脫的共存虛無,時而晦暗、混亂,且不可預測。 人的存在越是荒謬,電影的世界越是浩瀚,安德森所經歷的那種影像內外混亂迷失的感受,在梅賽黛絲.加維里亞導演的《片場與家的距離》中藏著另一種形狀。一位女性導演拿起攝影機紀錄她的知名導演父親,並用父親最擅長的東西——電影,一一刺破他投下的父權陰影。「男性凝視」 VS 「女性意識」在這個家庭裡掀起波瀾,父親創造的主觀鏡頭在轉為女兒的主觀鏡頭之後,新視角/對立因而產生。在這樣的異質空間裡,女兒試圖解構並重組大量影像,家庭關係以及作為男女導演本質上的差異也被層層檢視。這部片令人驚嘆的是許多珍貴家庭錄像和電影文本在個人記憶裡佔據巧妙的位子,而《來自他方的影像信》的取材方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它以詩意建構意識的延續並參雜現實片段的「混濁」。有如薩特對於存在主義的辯證,從西班牙到智利,兩位知名女性電影人藉由影像書信的交流,分享電影如何交織回憶與未來,以及彼此對生命本質及世界的看法。電影打破了時間與空間以及日常與螢幕之間的距離,兩位電影人的對話不再線性而是同時生長。 創作者從電影中思索本質,也從職涯中看見人性。2017年的#Metoo運動席捲歐美,無論是商業或藝術片,越來越多跳脫性別框架的影片相繼而生;銀幕裡的女英雄出現了,女明星的酬勞問題也開始被重視了,但真實存在的創作者「潛規則」呢?大富泉美導演的《東京澀谷16:30》細膩呈現一位日本女性編導在一次遞案機會中,面對男性製片性勒索時所承受的煎熬。權力不對等的職場性騷擾一直是難解的課題,這部片的誕生彷彿也為一直在性平運動上相對落後的日本,看到#Metoo效應的一線曙光。除了性騷擾,習俗或許是個更難的課題。在泰國,女孩收集香茅擋雨,前提是她必須是處女。彭.邦塞姆維查導演的《香茅女孩》即以此為題,呈現女性影像工作者因迷信被迫承受的職場困境。本片突出的新寫實風格帶出幽微平靜的意象,象徵性地闡述習俗是如此無形滲透。相對香茅女孩的寫實風格,馬天雨執導的《夏日美滋滋》的視覺色盤則呈現多彩層次,藉此打造都市邊陲人們無助空虛的疏離。兩部片的創作策略和手法不同,卻都呈現個別的魔幻寫實風貌。《夏》片略有當代躺平青年縮影,環繞編劇學子在創作靈感的乾枯時期,其孤立於周圍世界的內心和人際關係。 人生的寫實被電影環繞,那麼電影中的寫實又能呈現什麼樣的幻形?夏哈芭努.薩黛特的《孤兒前進寶萊塢》講述80年代賣黃牛票的阿富汗街童,在俄羅斯佔領年代,將自己置身於寶萊塢世界的故事。本片營造出舊時代的質地,卻又融合復古未來主義感,金黃質感的攝影效果凸顯寫實與魔幻之間的交錯本質,讓電影空間顯得既熟悉又新穎。導演選擇讓演員即興表演,以純真對照現實的殘酷,然後變調,然後再製,然後幻化成為戲裡戲外的影像烏托邦。同樣帶有魔幻寫實風格的還有安.歐倫執導的《迷幻擬音師》,猶如一趟將「聲音」、「畫面」、「肢體」三者融合的實驗旅程,讓擬音代表每個人身為獨特個體的專有樣貌,這種撿拾拼貼重組再製的實驗性格,也給予觀眾解構身體與影像的全新體驗。 電影類型的變形錯置也在提名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的《阿公偵探大鬧養老院》中展露無遺。本片以賈克大地式的懸疑喜感,將人際和日常建構成精采的冒險偵探電影。83歲的塞爾吉奧進入養老院當臥底,不只要學偷拍,還要學習智慧型手機。這部類情境喜劇消弭了生活無趣的痕跡,呈現老年生活的另類況味,並直指普世又純粹的情感。瑪蒂.艾柏地導演向來擅長挑戰劇情與紀錄片的界線,減少了紀實電影中常被強調的客觀價值,本片取而代之的是充滿決定性的過程,也驗證了觀察型紀錄片(Oberservational Documentary )與表述型紀錄片 (Performatives Documentary) 之間並非完全壁壘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