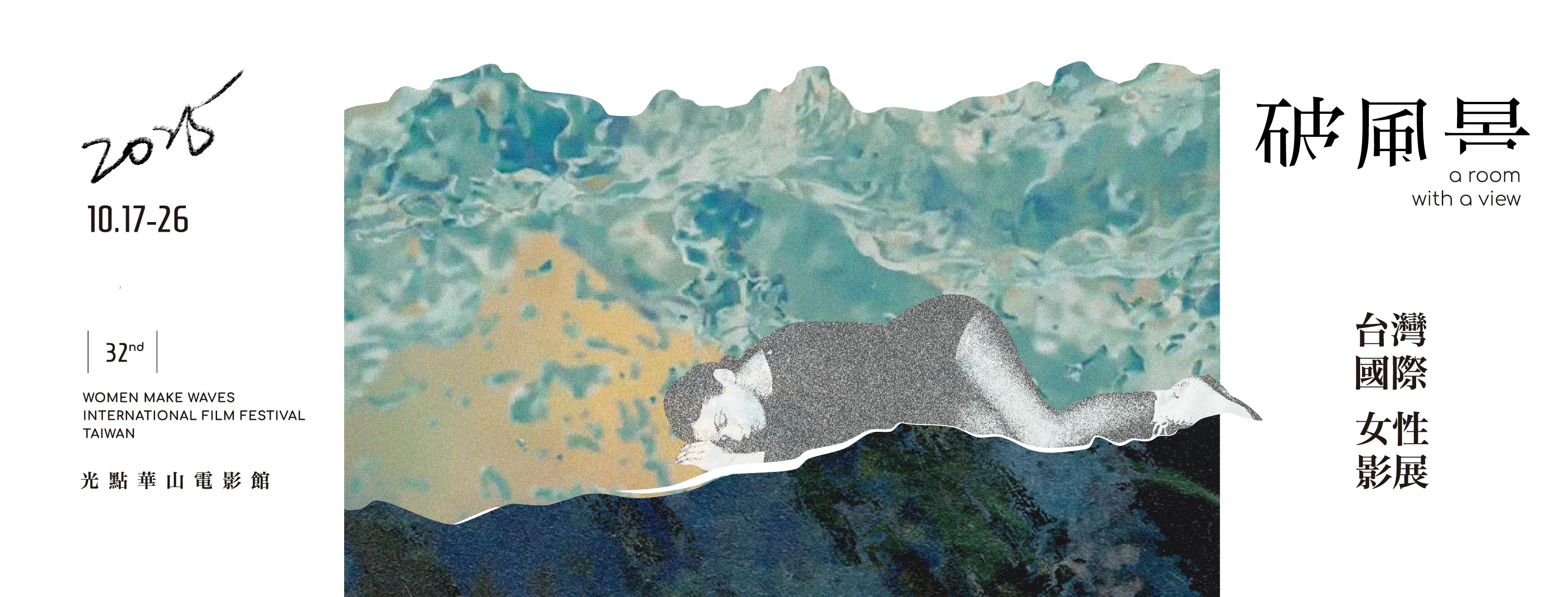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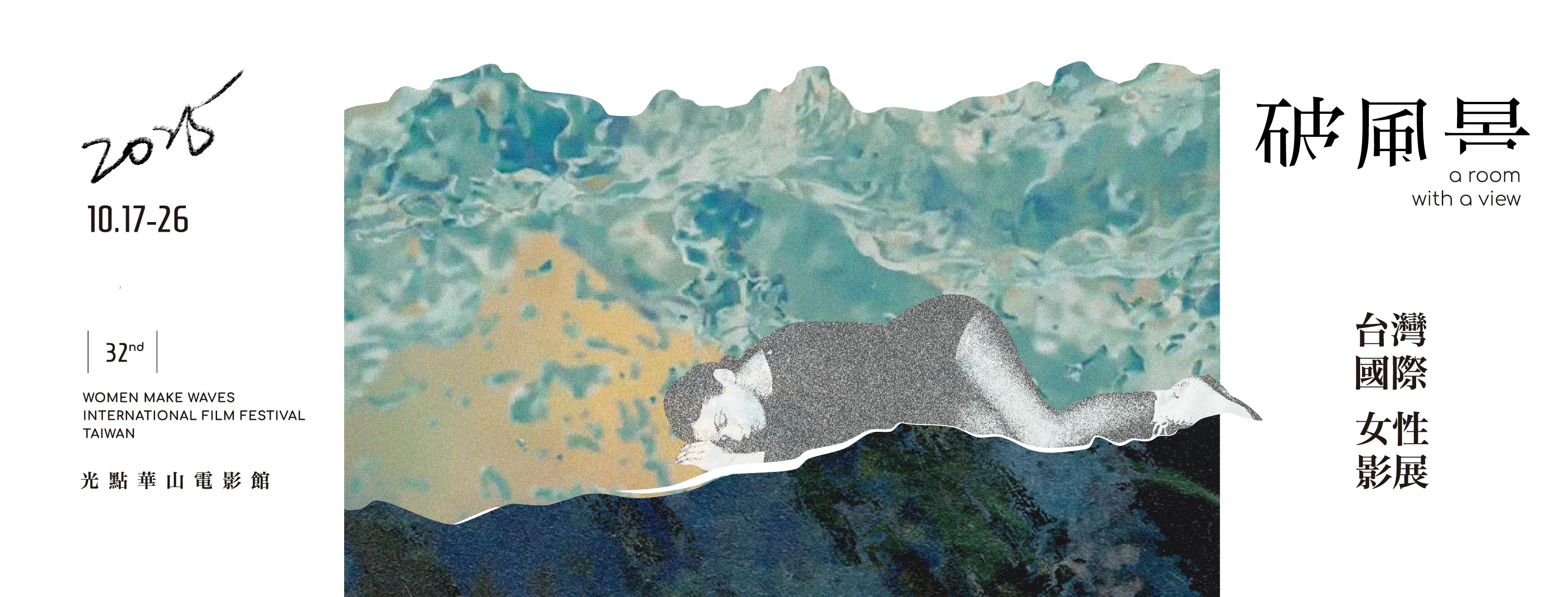
文字:林孍
側拍:黃雷敢
對於「林森北」也許我們有許多標籤化的想像,但在撕下標籤打開包裹的同時,映在我眼簾僅是那段純粹的情感。
那天我們與《我在林森北的那段日子》的 導演連晨輧Kawah與製片Nakaw相約在台北市一家極為復古的咖啡廳,一開始還深怕周遭環境的吵鬧影響到訪談,但就在導演和製片兩人掛著親切微笑一同出現在我們面前時,一來一往的問答,就這樣靜悄悄的將尷尬輕鬆瓦解。

圖/ 導演連晨輧Kawah(右)與製片Nakaw(左)
拍紀錄片挖掘自身生命故事,才終於真正認識母親
導演坦言,會踏進紀錄片創作領域的初心是因為亟欲拍攝自身的生命故事,而一次一次的嘗試讓她練習如何抽離,並冷靜地剖析那些略為沈重的生命故事,勇敢的一步步逼近內心深處。
在訪談一開始,她便提到了這支短片其實醞釀了一些時日,而起點則是從上一支片,拍攝Cilo'ohay部落開始。那支片所講述的是關於部落以及內部儀式的變遷探討,當時,不熟諳於母語的導演邀請了母親協助母語的翻譯工作,也是因為如此拉近了兩人的距離,後來才會有《我在林森北的那段日子》這部片的誕生。
《我在林森北的那段日子》是導演貼身拍攝自己媽媽的一部紀錄片,她說:「母親在我心中原本是一團謎樣,但就在我花了近二十年重新認識她和再度檢視自己的過程中,我發現我的媽媽愛唱歌,她跟我一樣有夢想,心裡也著實是個小女孩。」

圖/ 《我在林森北的那段日子》劇照,圖中為導演母親
導演的雙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已離異,而母親後來就輾轉到了臺北工作,所以跟母親的關係一直都不是特別親近。但就在十八歲之後發覺雖然和母親每個月都會見幾次面,卻對於眼前這個人相當陌生,尤其是在相處過程中相當明顯,例如不太知道這個人平常的喜好習慣,或是她所經歷的事情等等。所以一開始決定要處理這段關係時,也是花了許多時間,歷經了2012一直到2016的磨合,才漸漸終於能和母親坦承相見。
關於媽媽,關於「林森北」,也關乎對「家」的想像
導演提到,其實對於母親在林森北工作這件事情,在高中以前不曾跟任何人說過,對外都介紹媽媽是服務生,是在上大學之後才開始去思考說原來媽媽有這一段過去。從決定拍攝紀錄片後,一開始是帶著忐忑詢問母親作為被拍攝者的意願,但後來才發現原來自己的媽媽相當開明並且知無不言,一問之下媽媽半開玩笑的說著希望在自己死後,至少還有些事情能讓女兒回味。
問及片中導演和母親輕鬆自然的對話方式,導演說她在拍攝過程中其實常常思考,自己跟媽媽到底是母女還是朋友,她覺得「一下要當母女一下要當朋友,對小孩來說是困難的」。最後也跟我們分享了關於母親觀賞整部片之後的反應,她笑著說,整個過程母親在她身旁頻頻掉淚,如此珍貴的創作與交流,讓她重新省思了對於「家」的想像。

以母語旁白傾訴,慢慢了解媽媽、解開過去包袱
至於影片後段安插在黑幕上的問題,導演表示那其實是平常對母親較難以啟齒的疑問,也許是害怕聽到答案,卻又想讓母親知道自己的想法。但後來也許是因為隨著歲數漸長,思考的中心點慢慢從自身跨越到媽媽的部分,待慢慢暸解到對方立場後,發現彼此雖是親情羈絆卻是獨立的個體,也慢慢發現自己愈來愈能接受這段關係。
「比較像是我跟我媽的臍帶關係是切斷的,我可以成為獨立個體,不用包在一起,我們想要的家庭不一樣,而我也認清自己是可以不用被母親心中所想像的那個家有所牽制。」
導演說她雖然對於母語非常不熟練,但卻決定以母語講述旁白,是想以此轉換成另一個訴說對象,假裝女兒這個角色不在現場,像是轉述給第三者聽,抑或是一種傾訴。

有些包袱在生命過程的運行中,也許你會越來越感覺到它的重量,也許是因為如此,導演選擇追溯並去處理源頭。